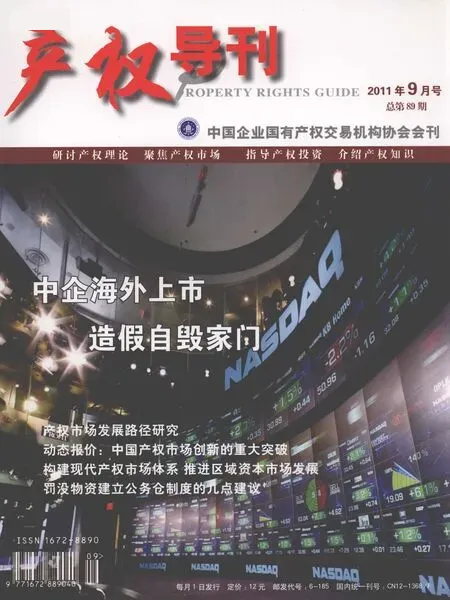知識產權保護研究現狀述評
■ 游芳芳
(安徽財經大學,安徽蚌埠233030)
知識產權保護研究現狀述評
■ 游芳芳
(安徽財經大學,安徽蚌埠233030)
本文對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已有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從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視角、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關系視角、經濟學視角、策略及建議視角對已有文獻進行逐一述評。
知識產權保護 視角

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大背景下,知識產權已成為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焦點,世界未來的競爭就是知識產權競爭。國內外有關知識產權方面的文獻很多,諸如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策略、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其中,關于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許多學者基于不同視角進行了研究。
1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視角
隨著對知識產權保護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逐漸開始從量化角度來研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最早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進行量化分析的是Rapp和Rozek(1990)[1],他們將一個國家是否制定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作為判斷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唯一標準,并將其劃分為1、2、3、4、5五個等級。Ginarte和Park(1997)[2]在Rapp和Rozek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更深入的度量方法,他們用五個指標來衡量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即知識產權保護的覆蓋范圍、是否成為國際條約的成員、權利喪失的保護、執法措施、保護期限。而我國學者韓玉雄、李懷祖(2005)[3]用執法力度來修正Ginarte-Park方法,并提出衡量執法強度的四個指標,即社會法制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國際社會的監督、制衡機制。許春明、陳敏(2008)[4]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提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應該由立法強度指標和執法強度指標構成,其中立法強度指標的度量包括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和其他法,執法強度指標從司法保護、行政保護、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公眾意識、國際環境五個方面進行度量。
2 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關系視角
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關系,一些學者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利于技術創新率的提高。Helpman(1993)[5]、Glass和Saggi(2002)[6]運用南北貿易分析框架進行研究時提出,加強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會增加技術模仿成本,從而降低北方國家的技術創新率,使得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的技術轉移率也就降低了,進而導致南方國家的技術創新率降低。有些學者則持相反觀點,他們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促進技術創新。魏龍、李華威(2004)[7]通過構建科技產出收益模型分析出,只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能激勵創造者,使其具有持續創新的動力和積極性,從而提高技術創新率,促進科技進步。張瑞麗、孫長峰(2011)[8]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完善會大大激勵和推動技術創新。這兩種觀點完全相反,那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到底是有利于技術創新還是不利于技術創新呢?基于這個疑惑,有學者提出,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既有促進作用,也有平衡和規制作用(李培林,2010)[9]。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取決于被保護客體。Tamirisa和Konan(1997)認為弱的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最初知識產權薄弱的地區迅速縫合知識缺口并轉為技術創新。Mansfield(1996)調查發現,加強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他們吸引外國投資和技術轉移。
3 經濟學視角
隨著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知識產權保護的經濟學研究引起國內外學者們的極大興趣。知識產權保護的經濟學研究是對知識產權與技術創新關系研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研究的延伸,其主要的兩個熱門話題是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關于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國際上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有些學者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會壟斷科學研究的自由(Harper and Row,1950),進而阻礙技術的合理擴散和應用,造成社會福利的減小(Caves Crookel Kilings,1993)。Helpman(1993)、Glass和Saggi(2002)也認為加強跟隨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會導致創新率降低,進而使領先國和跟隨國的社會福利水平都受到損失。另一些學者則持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 Markusen(2001)、Yang和Maskus(2001)[10]都認為,加強跟隨過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有利于跟隨國與領先國的雙邊貿易,進而提高兩國社會福利水平。第三種觀點則堅持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水平的影響應根據保護客體的具體情況來加以確定。韓玉雄、李懷祖(2003)[11]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水平的影響與跟隨國初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相關,即若跟隨國初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大,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會導致兩國福利水平都下降;若跟隨國初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小,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會使兩國福利水平共同提高;若跟隨國初始保護力度處在上面兩種情形之間,加強保護力度會使領先國福利水平提高而跟隨國福利水平下降。此外,韓伯棠、李燕(2008)[12]基于累計創新框架也分析出,當后發國的創新水平較弱時,較弱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能使社會福利更大,而當創新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時,較強的知識產權保護會使社會福利更大。
關于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國際上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Helpman(1993)、Glass和Saggi(2002)則通過運用南北貿易分析框架進行研究,得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不利于經濟增長的結論。第二種觀點則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他們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經濟的增長(Yang和Maskus,2001;Markusen,2001;Javorcik,2004)。現在學者們更傾向于第三種觀點,即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Thompson(2005)[13]通過實證證明,只有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知識產權保護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6)通過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對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是顯著正相關,而對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則不顯著。劉勇、周宏(2008)[14]利用我國省際面板數據對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在一定程度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但這種關系是和經濟發展程度正相關。于長林(2009)[15]也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依賴于經濟發展水平,且呈現出非線性特征和門限效應特征,當經濟水平位于知識產權保護門限水平之上,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而當經濟水平位于門限水平以下,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
4 策略及建議視角
由于知識產權保護策略是企業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方針,決定著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投入所能產生的效能(樓斌,2008)[16],且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又對經濟增長、社會福利水平、技術創新率有重要影響,因而較多學者從知識產權保護策略這個視角進行研究。何佩玲、呂本富、王丹(2003)[17]將知識產權策略分為四種:一是完全控制商品所有權,不允許盜版行為存在策略;二是允許消費者適度盜版;三是允許消費者廣發盜版;四是允許第三方生產者盜版,并分析不同的策略對單個產品收入的影響。萬迪、王光全(1997)[18]在分析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對策的基礎下,提出了加強產權保護的三點政策建議,一是處理好專利與版權的關系,二是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把握,三是知識產權保護時間的權衡。王中(2005)[19]在分析高新技術產業知識產權保護現狀和問題之后,提出強化自主知識產權戰略要加強知識產權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認識、要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要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管理體系三點建議。
5 結語
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率、社會福利、經濟增長的利弊應視被保護客體的具體情況而定。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模仿效應大于創新效應,寬松的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經濟增長;當技術模仿實現了技術進步或接近技術前沿時,創新效應就大于模仿效應,此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經濟增長(于長林,2009)。我國初始的知識產權保護較弱,隨著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逐步縮小,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升,我國應當要適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促進自主創新和經濟的增長,提升社會福利水平。吳凱,蔡虹,蔣仁愛(2010) 也通過實證證明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能夠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推動作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擁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工作相輔相承,共同成為區域經濟重點發展方向,因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變得尤為重要。
[1]Rapp R T, Rozek R P. Benefits and cos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0, 24: 75-102.
[2]Ginarte J C, Park W G. 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 A cross-national study[J].Research policy, 1997, 26: 283-301.
[3]韓玉雄,李懷祖.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5,(3):377-382.
[4]許春明,陳敏.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定及驗證[J].知識產權,2008,(1):27-36.
[5]Helpman E. Innovation, 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 Econometrica, 1993, 61(6): 1247-1280.
[6]Glass A J, Saggi K.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56: 387-410.
[7]魏龍,李華威.知識產權保護對科技進步推動作用的實證分析[J].中國科技論壇,2004,(2):97-101.
[8]張瑞麗,孫長峰.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相互作用機制研究[J].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11,(1):34-36.
[9]李培林.論企業技術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6):188-189.
[10]Yang Guifang, Maskus K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icensing and innovation in an endogenous product cycle model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nomics, 2001, 53: 169-187.
[11]韓玉雄,李懷祖.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水平的影響[J].世界經濟,2003,(9):69-77.
[12]韓伯棠,李燕.技術溢出——知識產權保護與社會福利研究——基于累計創新框架分析[J].經濟與管理,2008,(10):11-18.
[13]Thompson, Schncider, Patricia Higino.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panel data study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8: 529-547.
[14]劉勇,周宏.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8,(6):17-21.
[15]于長林.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基于技術供給的視角[D].廈門:廈門大學,2009.
[16]樓斌.跨國企業在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8.
[17]何佩玲,呂本富,王丹.知識產權保護策略分析[J].科學技術與工程,2003,(5):486-489.
[18]萬迪,王光全.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策略分析[J].科研管理,1997,(4):41-46.
[19]王中.強化知識產權戰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J].中國科技論壇,2005,6):75-78.
[20]吳凱,蔡虹,蔣仁愛.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0,(12):1832-1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