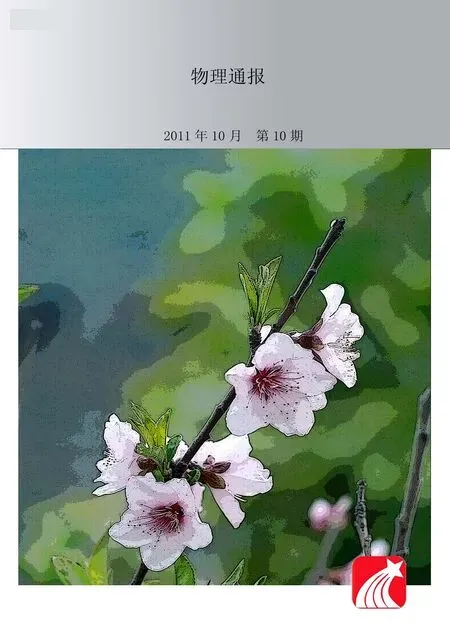發現星空秩序的路線簡圖
朱崇軍
(灌云縣教育局教研室 江蘇 灌云 222200)
康德有一句影響極廣的名言:有兩樣東西,我們越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著,就越有新奇和強烈的贊嘆與敬畏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我們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那里,星空與道德有了聯系,那是因為秩序.人類為了尋找星空的秩序,走過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展望這條歷史道路上熠熠生輝的里程碑,不禁讓筆者想到了皮埃爾·迪昂的一段深刻論述:任何物理學理論都是通過一系列潤色進行的,它使體系從無定型的第一批草圖逐漸達至比較精致完美的狀態[1].了解發現星空秩序的歷史即使是一條路線簡圖,對于我們也是有益的,因為弗蘭西斯·培根說過,對于那些想發現人類理性本質和真正用途的人來說,學習歷史是有實用意義的[2].
1 “兩球宇宙”模型
所謂“兩球宇宙”模型包括一個為人而設置的內球(地球)和一個為恒星設置的外球(天球).到“兩球宇宙”模型的形成,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已走過漫長的道路,因此“兩球宇宙”模型雖也源自人類的直覺和想象,但它更經得起推敲,也能解釋許多天文現象,所以它能容納自公元前4世紀到哥白尼時代 1 900年間大量不同且有爭議的天文學和宇宙論方案[3].
2 托勒密體系
在托勒密體系中,地球靜止且是宇宙的中心,太陽與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地位一樣,也是行星之一.太陽除做向西的周日運動,還沿著黃道向東做緩慢的周年運動.五大行星各自都在一個較小的“本輪”上做勻速圓周運動,但本輪的中心又在一個龐大的“均輪”上繞地球做勻速圓周運動.太陽和月亮沒有本輪,直接在均輪上運動,地球又稍稍偏離所有均輪中心.起初是單本輪、單均輪體系,但它所預言的運動和觀察到的行星的運動相比較時,行星并不總是出現在預測的位置,所以它并不是行星問題的最終答案,而只是一個有希望的開始.在從希伯克斯到哥白尼(1473~1543年)的17個世紀中,所有最富有創造性的技術天文學的研究者都致力于發明一些新的細微的幾何修正,以使基本的單本輪、單均輪技術更精確的符合觀測到的行星運動.在這些努力中最偉大的要算是托勒密(約90~168年)在公元150年前后所做的工作,他取代了前人,結出了《至大論》這一豐碩成果.《至大論》濃縮了古代天文學最偉大的成就,是第一部為所有天體運動提供完整、詳細和定量解釋的系統的數理論著,以至他的所有繼承者包括哥白尼在內都要模仿他來開展工作[3].這里要注意的是“托勒密體系”是指解決行星問題的一種傳統方法,而不是指任何個人的一種特殊的解答.
托勒密體系的所有版本,都只有5個大本輪,而用以解釋量上的細微偏差的小本輪,只取決于在預測精度方面對體系的要求.因此,托勒密天文學的不同版本之間小本輪的數目相差很大.使用6~12個小本輪的體系在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并不少見,因為通過對小本輪尺寸、速度和傾斜角度的適當選擇,幾乎所有微小的不規則性都可以得到解釋.在托勒密體系中還用偏心勻速點這個裝置,以幫助調和本輪理論與實際觀察結果.均輪的轉速保持恒定,但不是相對于它的幾何中心,而是相對于偏離中心的某點保持恒定,該點即是偏心勻速點.從均輪的幾何中心觀察,行星似乎是以不規則的速率運動或搖擺不定[3].
均輪、偏心圓、偏心勻速點和本輪,這些數理裝置并非一下子發展起來的,但是托勒密的貢獻是杰出的.解決行星問題的這全套技巧以他的名字而流傳,是因為托勒密首先將一組特別的組合圓放在一起,解釋在行星的視運動中觀測到的定量的規則性與不規則性.其效果如此之好、方法如此之有力,以致為了提高行星理論的準確性,托勒密的后繼者們在本輪上添加本輪,在偏心圓上添加偏心圓,以充分開發托勒密的基本技術中多種多樣的功能,并最終導致整個定量體系在數學上過于復雜和深奧.引發哥白尼去探索行星問題新的解決途徑的那些問題,正是在這種深奧的量化理論內部.
3 哥白尼革命
托勒密之后的眾多天文學家在不斷批評和修正托勒密體系,導致托勒密體系已不再是一個,而變成了一大堆.天文學傳統已經變得散亂,再也不能完全規定一個天文學家在計算行星位置時應該用什么方法,從而也無法確定從他的計算中得出什么樣的結果.像這樣的模棱兩可,是使得天文學傳統喪失其內在力量的主要源泉.一個理論的變形驟增,正是危機的通常跡象.危機的意義在于,它指出更換工具的時機已經到來了[4].散亂并且錯誤不斷,這是被哥白尼喻為“怪物”的迅速增長的傳統天文學的兩大特征[3].對于哥白尼革命所依賴的天文學傳統自身的明顯變化來講,這是兩個主要根源,但不是唯一的,哥白尼已經發現,古代人在這件事上已有分歧[5],另外“革命”還跟時代潮流有關.時代潮流表現在多個方面:航海業的發展拓寬了人們的視界,卻降低了托勒密的權威;歷法改革要求有新的天文理論的指導;人文主義帶來了新的信念(自然中存在簡單的算術和幾何規則)和新的觀點(太陽是宇宙中一切活力原則和力量的來源,它的輻射給予宇宙以光芒、溫暖和豐饒);柏拉圖主義的復活:數學在地上世界的不完善和變動不居的現象之中示范了永恒與真實.哥白尼生活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核心時期,由于老套的東西很容易在普遍騷亂的時期被拋棄,所以動蕩本身就有利于哥白尼的天文學革新.哥白尼革命是一場觀念上的革命,是人的宇宙概念以及人與宇宙之關系的一次轉型.在文藝復興思想史上的這一幕,被一再地宣稱為西方人思想發展的劃時代轉向.
1543年哥白尼《天球運行論》的出版[3],揭開了天文學和宇宙論思想上一場巨變的序幕.《天球運行論》是一個有多方面問題的文本,但它又是轉變科學思想的發展方向的文本,具有雙重特性;它既是古代的又是現代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激進的.
哥白尼是為數不多的一群最早復興整個希臘化技術性的數理天文學傳統的歐洲人之一.這一傳統在古代由托勒密的著作推至頂峰.《天球運行論》也正是為解決在哥白尼看來托勒密及其繼承者尚未解決的那些行星問題而著.在哥白尼的著作中,地球運動的革命性觀念最初只不過是這位熟練而又忠實的天文學家試圖改良計算行星位置的技巧時一個反常的副產品.哥白尼說,對當時天文學的坦率評價表明,靠地心說解決行星問題希望渺茫.舊有傳統的方法沒有也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相反還產生了一個怪物.他斷定,在傳統行星天文學的基本思想中,一定存在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這是首次有一位在技術上勝任的天文學家處于其研究的內在理由而拒絕歷史悠久的科學傳統,而且促使哥白尼推動地球的只是對數理天文學的改革.哥白尼革命本質上不是在計算行星位置的數學技巧方面的一場革命,但它的起點卻是如此.在認識到需要新技巧和發展新技巧方面,哥白尼為這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革命做出了唯一的原創性貢獻[3].
哥白尼并不是第一個提出地動說的人;前無古人的只是哥白尼在地球運動基礎上建立了數學體系.如果地球能夠像繞自身的軸旋轉一樣也圍繞中心做軌道轉動,那么逆行運動以及行星在黃道上相繼的兩次運行所需時間的不同,就不需要使用本輪也能解釋,至少可以得到定性的解釋.在哥白尼體系中,行星運動主要的不規則性都只是表面上的.從運動的地球上看,實際上規則的行星運動就顯得不規則了.
逆行運動和繞黃道運行所需時間不固定這兩大不規則性,在古代導致天文學家使用本輪和均輪來解決行星問題.哥白尼的體系解釋了這兩大不規則性,而且沒有使用大本輪.而為了對行星運動做出哪怕只是近似的和定性的解釋,托勒密用了12個輪.哥白尼對行星的視運動完成了同樣定性的解釋,卻只用了7個輪[3].他只需給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各一個以太陽為中心的輪,再給月球一個以地球為中心的輪.對于只考慮行星運動的定性解釋的天文學家而言,哥白尼體系肯定經濟得多.但哥白尼又并沒有解決行星問題.從純粹的實踐的角度來看,哥白尼的新行星體系是一個失敗,它并不比其托勒密派的前輩更精確,也沒有顯著的簡化.正如哥白尼認識到的,日心天文學真正的吸引力是審美方面的而不是實用方面的.只有那些把定性的簡潔性看得比定量的精確性重要得多的天文學家才會把這當作令人信服的論證,而不顧《天球運行論》中精致的本輪和偏心圓的復雜體系.
所以,被哥白尼說服而接受地動觀念的人們又從哥白尼止步的地方開始了他們的探索.他們的出發點就是地球的運動,而他們所致力的問題已不再是哥白尼所從事的舊的天文學中的問題,而是他們在《天球運行論》中發現的新的日心天文學中的問題.哥白尼給他們帶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前輩都無需面對.在對這些問題的追究過程中,哥白尼革命得以完成.
任何個人能夠做出的革新范圍必定有限,因為每個個人在研究中都必定要使用在傳統的教育中學來的工具,而他窮其一生也不可能把這些工具全部換掉.后來的相關著作越來越多地從《天球運行論》中借用數據、計算和圖表,至少是從它的某些與地球運動無關的部分借用.在16世紀后半葉,這本書成了所有天文研究中對高深問題感興趣者的標準參考書[3].天文學家已經離不開《天球運行論》,也離不開基于它的星表.哥白尼的方案緩慢但顯然不可動搖地贏得了地位.
4 第谷的調和
如果說哥白尼是16世紀上半葉歐洲最偉大的天文學家,那么第谷(1546~1601年)就是后半葉杰出的天文學權威.他設計和制造了許多比過去更大、更穩定、校正得更準的新儀器.憑借無比的天才,他檢查并糾正了在這些儀器的使用中發生的許多錯誤,建立起一整套關于搜集行星和恒星位置的精確信息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他開始對行星實行定期觀測;只要行星穿過天際,而不只是在某些特別有利的位置才觀測.現代的望遠鏡觀測表明,當第谷極為仔細地測定恒星的位置時,他的數據精度可以達1′,對行星位置的觀測精度通常可靠至4′,甚至更好;這是肉眼觀測的非凡成就[3].不過比第谷的個人觀測的精度更重要的,是他所積累的數據整體的可信度和廣度.在他的一生中,他和他訓練的觀測者,把歐洲天文學從對古代數據的依賴中解放了出來,并且消除了一系列由于錯誤數據產生的表面的天文學問題.可信的、廣泛的、最新的數據是第谷對解決行星問題做出的主要貢獻.除此之外,他還發明了既不同于托勒密又不同于哥白尼的第三種體系,即第谷體系——月亮和太陽的圓圈以地球為中心,而其余5顆行星的軌道的中心又是太陽.在第谷體系中,小本輪、偏心圓和偏心勻速圓也是必需的.
第谷體系最顯著、最有歷史意義的特征就是,它適合于作為對《天球運行論》導致的問題的折中解決,它使幾乎所有博學的17世紀托勒密天文學家都轉向第谷體系,它就像是《天球運行論》的一個直接的副產品.第谷對哥白尼的批評和對行星問題的折中解決表明,他跟當時大多數天文學家一樣無法突破傳統的思想模式.不過,第谷高超的觀測在引領同代人走向新的宇宙論方面比他的體系更為重要.第谷在臨終前,還喃喃地說:“我多希望我這一生沒有虛度啊!”1602年,開普勒編輯出版了第谷遺留下來的觀測資料[6],并從中探討行星的運動規律.開普勒的偉大工作真正使第谷的一生沒有虛度.
5 開普勒立法
開普勒(1571~1630年),終其一生,以狂想曲般的情調,將文藝復興時期新柏拉圖主義特有的思想運用于太陽中心體系.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宇宙的神秘》(1596年出版),首次展示了為新天文學所作的數學論證的充分力量.[3]開普勒在努力使數學技巧適應以太陽為主宰的宇宙圖景,正是因為堅持這種努力,開普勒最終解決了行星問題,把哥白尼笨重的體系轉變成一項極其簡單和精確的計算行星位置的技術.得到這個結果的過程是異常艱苦的(研究火星運動大約用了10年時間)[3],開普勒一絲不茍地嘗試修改他的軌道以適應第谷的觀測數據.一長串不成功的試驗迫使開普勒做出結論,沒有任何基于組合圓的體現能夠解決問題.他設想肯定有某種別的幾何圖形包含了問題的答案.他試了各種不同的卵圓形,但都不能消除他的試驗性理論和觀測之間的偏差.然后,他偶然注意到偏差本身以一種熟悉的數學方式變化;他研究了這種規律性,發現若行星以變化的速率沿橢圓軌道運行,就可以使理論與觀測相符合.
行星沿單純的橢圓軌道運行,太陽占據橢圓軌道的兩個焦點之一;這就是開普勒第一定律.緊接著是開普勒的第二定律,完善了第一定律所表達的描述,即每顆行星的軌道速率以這樣的方式變化,使得行星到太陽的連線在相等的時間間隔內掃過相等的橢圓面積.開普勒使偏心圓、本輪、偏心勻速圓以及其他特設性裝置,都不再需要了.單獨一種非復合的幾何曲線和單獨一個速率定律就足以預測行星的位置,這還是第一次;而且預測結果跟觀測一樣精確,這也是第一次.開普勒的6橢圓體系使日心天文學生效了,把哥白尼的革新中隱含的經濟性和豐富性同時顯現出來[3].
開普勒第三定律是一種新型的天文學定律.第一、第二定律跟古代和中世紀的一樣,只決定單個行星在自己的軌道上的運動.相反,第三定律建立了不同軌道上的行星速率之間的關系.這是一條迷人的定律,因為它指出了一種過去從未在行星體系中覺察到的規律性.盡管它幾乎沒有直接的實際作用,但第三定律正是在開普勒的畢生事業中最令他著迷的.他是數學上的新柏拉圖主義者,相信整個自然都是簡單的數學規律性的例證;而發現這些規律正是科學家的任務.對于開普勒和別的具有他這種性情的人來說,一條簡單的數學規律本身就是一個解釋[3].單就開普勒在數學中的成就而論,他就足以贏得永恒的聲譽.當然他是一位數學方法的堅決擁護者,但他與早期的柏拉圖主義的哲學家相比是有差別的,這差別在于他強調要把理論嚴格地應用到觀測到的事實.哥白尼革命和第谷對星體資料的整理,對于提供一個有待于發展和證實新的、重要的數學理論來說是必要的,對于提供一套完整的資料也是必要的,而那種證實就必須在這套資料中找到.正是使用這一方法,而且也是為此目的,開普勒達到了對其三大定律的劃時代的發現[5].因其三定律,開普勒被譽為為天空立法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開普勒雖然取得那么多偉大成就,但卻一生貧困.在格拉茨大學做講師時,薪水很少,他不得不靠編制占星歷書而養家糊口.他自我解嘲地說:“如果女兒占星術不掙來兩份面包,那么天文學母親準會餓死”.后來,雖說身為宮廷天文學家,但薪水常常拖欠,以致1630年11月15日,在他去索要拖欠20余年的薪水時,染傷寒死于途中[6].
6 伽利略的望遠鏡
1609年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1564~1642年)首次通過望遠鏡觀看天空,整個星空充滿了無以數計的新成員.某些哥白尼派預設的宇宙極大的擴張甚至是它的無限性,突然變得不那么荒唐了.望遠鏡使得支持哥白尼主義的論證倍增.1609年以后,對天文學只有一知半解的人也有可能通過望遠鏡親眼看到,宇宙跟常識的幼稚告誡并不相符.望遠鏡成為一種流行的玩具,對天文學或任何科學此前從未表現出興趣的人,也買來或借來這種新儀器,在晴朗的夜晚熱切地搜索天空.一種新的文學也隨之誕生了.科普讀物和科幻小說的萌芽都可以在17世紀發現,一開始望遠鏡和它的發現是最顯著的主題.這就是伽利略的天文學工作最重要的地方:它普及了天文學,而且普及的是哥白尼天文學[3].
不同的體系被人們相信是出于相同的原因,那就是它們都為看起來重要的問題提供了似乎合理的回答.發現始于意識到反常,即始于認識到自然界總是以某種方法違反支配常規科學的范式所做的預測.于是,人們繼續對反常領域進行或多或少擴展性的探索.這種探索直到調整范式理論使反常變成與預測相符為止[4].從發現星空秩序的路線簡圖中,我們應該得到這樣的啟示:不同體系是不同時代的科學理論,科學也總是在新理論取代舊理論中進步的.
1 (法)皮埃爾·迪昂著,李醒民譯.物理學理論的目的與結構.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247
2 (美)托馬斯·庫恩著.范岱年,等譯.必要的張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07
3 (美)托馬斯·庫恩著.吳國盛,等譯.哥白尼革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7,64,69,138,126,128,165,181,196,205,207,208,212,219
4 (美)托馬斯·庫恩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70,49
5 (美)愛德文·阿瑟·伯特著.徐向東譯.近代物理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2,43
6 吳國盛.科學的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93,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