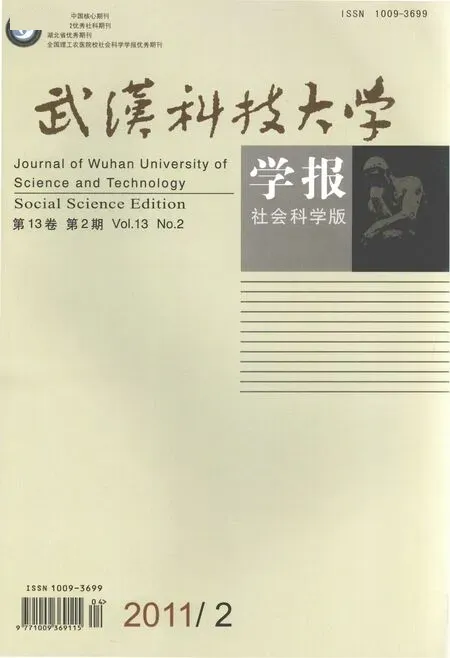荊楚文化特質平議
孟修祥
(長江大學 文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荊楚文化特質平議
孟修祥
(長江大學 文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春秋戰國時代,開放、求新、求變的精神特征為當時諸侯各國所共有,并不能說明某一地域文化的特質。荊楚文化受南方水鄉澤國、叢林山巒自然氤氳之氣而自然物產豐饒的地理環境與巫覡文化的影響,以青銅器、漆器、刺繡、老莊哲學和楚辭為代表,極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與理想主義精神,從楚人“剽輕”的風俗習性,“宏識孤懷”、“一意孤行”的思維方式,以及“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論,荊楚文化的特質應該是與藝術文化特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荊楚文化;地理環境;藝術;特質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詩圣杜甫在《江陵望幸》中以其如椽巨筆,標示出荊楚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坐標。通常所謂荊楚,系指今天的湖北地區,它是南方的“中原”,早在東周時期就有楚文化與北方的周文化逐艷爭輝。秦漢以降,這里豐厚的文化積淀和寬松的文化環境,得以成為南學的搖籃、禪宗的溫床、道學的中心和新學的重地,不僅經濟社會的發展足資稱道,而且在科學領域和藝術領域亦不乏奇思遐想和英才碩果。
為了推動荊楚文化研究的拓展精進,《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特設“荊楚文化與長江文明”專欄,陸續刊發一批高水準、高質量的學術論文,以展示荊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此乃學界之幸事。作為特約主持人,我衷心祝愿這個欄目像荊楚文化一樣,以其卓爾不群的豐采贏得學界的矚目和艷羨!
——特約主持人 劉玉堂研究員
任何地域文化現象都有其區別于其他地域文化現象的獨特之處,因此人們通常把某一地域文化最為顯著的標志稱其為文化特質或文化特征。《辭海》對“特征”(或特質)的定義為:“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特別顯著的象征、標志。”如徽州文化,其特質為商人文化,徽商以其雄厚的財力建立起為自己的經濟利益服務并體現其自身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商人文化。徽商群體熔鑄理學并雜糅宗族文化與通俗文化,包括習俗、科技、藝術乃至飲食和建筑等,所表現出的封建倫理性、社會生活的實用性等方面的特點,把中國早期啟蒙思想推到新的高度而匯入資產階級啟蒙思潮的歷史洪流,雖然先天缺乏獨立的品格,但它具有鮮明的商人文化特質。那么,什么是荊楚文化的特質呢?它區別于齊魯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的顯著標志又是什么呢?
一
綜合諸多學者的說法,荊楚文化的特質大致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諧精神[1]。這種結論性說法,與歷史事實稍作對照,便不免使人產生疑惑,且不說創業精神、開放精神、創新精神、愛國精神與和諧精神顯然是現代人總結的概念,這些說法在一些荊楚文化研究者的相關著論中,也時有所見,甚至還有改革精神、探索精神之類的說法,大同小異而已。如果說前面四個方面的總結還可以舉其歷史的事例作為依據,那么,第五點則完全與歷史事實不合,因為從春秋無義戰,到戰國大兼并,本來就是戰爭的時代,劉向早在其《戰國策》序中就說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戰國時代,是繼春秋之后更為激烈的大兼并時代,過去西周尚有“尊禮尚施”、“宜民宜人”的“德治”、“仁政”之說,在這時已完全是禮崩樂壞的大動亂了,各諸侯國之間,講的只是如何以勢相爭、以智相奪而已,何談和諧精神?《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記載的楚莊王“止戈為武”之說,在當時不過是政治家的一種策略,就在他講過此話之后的四年內,伐陳而定其亂,伐鄭而降其君,伐蕭而滅其國,伐宋而使其惟命是從,從而達到他霸業的巔峰。此外,自春秋時代始,每個諸侯國都具有創業精神、開放精神、創新精神,翻閱史書而瀏覽各諸侯國的歷史進程,就十分清楚。以齊國為例,自西周初姜太公建國起,就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直到管仲相齊后,又“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2],特別重視發展經濟,從而創造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在政治文化上,順應“寬緩闊達而足智”的原有文化,有條件地推行宗法制和集權制的結合,因其俗,簡其禮,為政簡而不苛、平易近民,所以到齊桓公時終成霸業,齊國成為名副其實的泱泱大國。可以說,戰國七雄在各自發展歷程中,都有其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創業、發展、漸至強大的過程,亦具有開放、求新、求變等特質,此可謂當時諸侯各國都具有的精神特征。至于說到愛國精神,在楚國既有身為囚徒而不忘故國的鐘儀和以橘言志“深固難徙”的偉大愛國詩人屈原,更有大批的“楚材晉用”者,以為吳所用的伍子胥而論,為強烈的個人復仇意識所驅動,不惜引吳兵入郢,“以班處宮”①《左傳·定公四年》云:“吳入郢,以班處宮。”所謂“以班處宮”,即按照不同職級居其居而妻其妻。即《谷梁傳》同年所云:“君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辱平王之墓”,以至于自古至今許多人都仍不以為是。如果拿這些“楚材晉用”者與鄭國商人弦高犒勞秦師以救鄭國、齊國名相晏嬰出使楚國不辱使命的歷史故事相比,將如何論證愛國精神一定就是荊楚文化的特質呢?
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在這一時代所形成的諸如上述之創業精神、開放精神、創新精神、愛國精神等諸多精神文化現象,已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筆者認為不能稱其為某一地域文化區別于另一地域文化的特質。
二
然而,無論歷史如何演變,社會如何進化,即或是在當今交通便捷、通訊發達、文化思想空前統一的情況下,我國不同地域的語言、習俗、民間藝術等許多方面確實存在顯明的不同之處。雖然地域文化的不同性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由多重因素形成的,但地理環境對不同地域的文化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對此,前人早有論述。《禮制·王制》說:“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班固《漢書·地理志》說:“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考工記》說:“橘逾淮而北為枳。鸜鵒不逾濟,貉逾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無論是人、物,還是民風、民俗,因地域環境的相異而產生了極大的差異性。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曾說,鄒、魯“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俗好儒,備于禮”,“猶有周公遺風”;齊人“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梁、宋“厚重多君子,好稼穡”。劉禹錫《送周魯儒序》說:“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其氣,往往清慧而為文。”《戴震文集》卷十二云:“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而居,商賈東西行營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賈者,咸近士風。”如此等等,都說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的形成不僅僅在于社會文化的作用,同時也有自然地理環境的作用。
明代有學者王士性在其《廣志繹》卷三中,以關中與川中為例云:“故其人稟者博大勁直而無委曲之態,蓋關中土厚水深,川中則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義,人性之稟多與水推移也。”所謂關中,就是函谷關以西的三秦之地,其突出的地貌形態就是由塬、梁、峁構成的黃土高原,其中以“八百里秦川”最為富饒,由于歷史上戰亂和屯墾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逐漸對黃土高原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使得原本在地理環境上就比較封閉的關中地區更加封閉,故民風樸實、本分、保守、粗獷,他們篤信“一份耕耘一份收獲”,形成了不尚玄想、勤勞務實、富于耐性的民性。川中即為四川盆地,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的四川盆地水系發達,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于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南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北部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東部有清江流域又與江漢平原相通,獨特的地理特點構成了兼融南北、“與水推移”的民性。川中人勤勞而樂觀,靈慧自信而古風不泯。
基于不同的地理環境形成不同的文化現象,故劉師培在其《南北文學不同論》中總括南北地理環境之不同而云:“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又以老、莊、列、屈作說明,“惟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及莊、列之徒承之,其旨遠,其意隱,其為文也縱而后反。寓實于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讬詞喻物,志潔行芳,符于《二南》之比興,而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事實上,我們可以繼劉師培寫出《南北藝術不同論》,從在楚地已出土的青銅器如《青銅禁》和《青銅尊盤》、漆器如《虎座立鳳》和《虎座鳳架鼓》、刺繡如《刺秀三頭鳳》和《鳳斗龍虎紋繡》等作品來看,那種浪漫、抽象、奇幻的造型與富艷繁麗的色彩,變形、夸張似乎自由無序而又無不合目的的組合,對生命力的張揚與對運動美的追求,所呈現的“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的藝術魅力,是中原之地的同類之作無可企及的,因為中原之地不僅缺少產生浪漫藝術的地理環境,而且缺少產生浪漫藝術的文化環境,當儒家思想的倡導者在意識形態層面極力推行禮樂文化的時候,統者者則從制度層面上對張揚個性、標新立異者進行著無情的扼殺。《禮制·王制》明確規定:“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嚴酷的政治制度,加上實踐理性精神,“土厚水深”的地理因素,決定了北方人務實的思維方式與個性的形成。
而南方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云:“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南方豐饒的自然環境,給生活在荊楚之地的人們以豐富想象的時間與空間,從而大大增強了人們的想象力,故王國維在其《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南方濕熱的氣候,容易形成狂放超俗和倜儻不羈的習性,而叢林水澤的氤氳之氣更易激發奇思幻想,所以,荊楚多有狂人。這與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說的“越、楚則有三俗……其俗剽輕,易發怒……則清刻,矜己諾”是吻合的,《史記·留侯世家》亦有“楚人剽疾”之說,揚雄亦云:“……包楚與荊。風剽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后服,無道先強。”①揚雄語,李兆洛選編《駢體文鈔》卷四,《四部備要》譚獻評點本。所謂“剽輕”、“剽疾”、“風剽以悍,氣銳以剛”,就是楚人性格中較易受到情感激蕩而顯得躁急、強悍的性氣,所謂“清刻,矜己諾”,是指執著而重信念的品格。可以說從哲人到文人,從最高統治者到平民百姓,雖有深淺之不同、層次之不同,但無不打上這種美學精神與文化品格的烙印。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古有屈原,今有毛澤東。屈原作為楚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他為國為民正道行直、竭忠盡智,可惜的是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因此,他以縱橫恣肆的文筆,表達強烈激蕩的情感,故袁宏道《敘小修詩》說楚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也正是針對屈原的個性特征而言的,屈原借用大量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創作出恢宏瑰麗之作“楚辭”。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云:“屈原氏興,以瑰奇浩瀚之才,屬縱橫艱大之運,因牢騷愁怨之感,發沈雄偉博之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廣譬,具網兼羅,文詞鉅麗,體制閎深,興寄超遠,百代而下,才人學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窮,史謂爭光日月,詎不信夫!”形成屈原“瑰奇浩瀚之才”的原因固然與時代風氣有關,更有江山之助,故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府奧。略語則缺,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江山之助乎?”一代偉人毛澤東融鑄古今中外各家思想之長,自成一家:毛澤東思想。然而,當我們追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歷程,毛澤東青少年時代受到以屈原為代表的荊楚文化精神濡染為最深。陳晉在其《毛澤東與傳統文藝》一書中明確指出:“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著意張揚個性和想象的詩人。他的作品在悠長久遠、汗漫綿漠的時空背景上,赫然創造了一個上天入冥、神游八極、瑰麗偉岸的人格形象,這個形象具有經天緯地之才,能扶楚國于危亡之中。這個形象太符合青年毛澤東的人格理想了。屈原的《天問》對宇宙真理、歷史起源、大地本源、善惡終極的追求,對潛心研討自然、社會、人類、宇宙的‘大本大源’的青年毛澤東來說,也是具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并以《送縱宇一郎東行》為例:“……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君行吾為發誥歌,鯤鵬擊浪從茲始。洞庭湘水漲連天,艟朦巨艦直東指。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里。丈夫何事足榮懷,要將宇宙看秭米。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壇何足理……”以此確證毛澤東“張揚意氣,馳騁想象,體現出博大的情懷、形象和時空氣勢,表現出對以屈原為代表的人杰地靈的湘楚浪漫主義文化精神的繼承和仰慕”[3]。毛澤東后來賦《念奴嬌·昆侖》將自我想象為“安得倚天抽寶劍”的巨人,俯視昆侖、胸懷世界,正是其偉岸人格的再現;《沁園春·雪》放眼大河上下、長城內外的大好河山,評點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千古英雄豪杰,可謂把荊楚文化大氣磅礴、吞吐宇宙的雄霸之氣張揚到了極致。
荊楚文化與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秦文化相比,更富有一種想象、思辨、浪漫的力度,它突出表現的是人的內在主體自覺與強盛的生命力,是卓爾不群、大氣磅礴的獨特精神。從屈原“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忽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詩句,到毛澤東“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詞作,無不體現荊楚文化中所特有的強烈的自我意識與個性張揚。
楚人奉行一種于主流之外標新立異、大膽懷疑和敢說敢當的哲學品格。從屈原《天問》一連提出170多個問題,對社會、人生、歷史和宇宙自然提出全面的追問,到唐代禪宗興起于黃梅,至明代心學的興盛,如陸九淵主政講學于荊門,李贄思考著述于黃安、麻城,三袁兄弟倡言性靈于公安,往往于主流思想之外,自創新說,對于中國哲學在不同時期的創新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其間蘊含了一種獨立創造的精神、一種敢說敢當的風骨、一種敢為天下先的氣度。熊十力先生所著《心書》云:“楚士又好為一意孤行,不近標榜,蘄黃尤甚。”[4]錢基博先生著《近百年湖南學風》指出:“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筆者按,湖南之地,水亦不少,湘、資、沅、澧四水貫通湖南全境,再加上八百里洞庭,可謂水鄉澤國也),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風氣自創,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5]荊楚文化是以兩湖為核心、輻射周邊地區有著鮮明特征的地域文化,熊十力先生與錢基博先生雖不是系統論述荊楚文化的特質,但已明確說明了荊楚地理環境與形成荊楚文化特質的關系。
三
我們不贊同“地理環境決定論”者的觀點,對此,辯證法大師黑格爾早就明確指出:“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馬詩的優美,但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6]文化特質的形成乃是地理環境、歷史條件、人口因素、生產方式、民族文化傳統等諸因素的合力而形成的,但是,“地理環境是人類從事社會生產須臾不可脫離的空間和物質——能量前提,是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經常的必要條件……普列漢諾夫說:‘不同類型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地理環境的影響后形成的。’”[7]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理環境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氣候、食物、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以持續而深刻的方式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與個性。楚人處水鄉澤國,地屬蠻荒,缺少教化,自“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始,楚人的一切都是嶄新的創造,因此,楚人高昂著一種挑戰的文化精神,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審美情趣,把自己內在的獨特個性發揮到了淋漓盡致,“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就是楚文化對北方文化的挑戰和示威,是充滿民族文化精神的宣言和昭示。
如果說早在兩千多年前,北方的孔夫子把原始文化納入到實踐理性精神的統治之下,或者說把實踐理性引導貫徹到日常現實生活、倫常情感和政治觀念之中,從而形成了“禮樂”文化[8]60,那么南方的楚人,一方面地處蠻荒、少有拘束,故張揚個性、崇尚浪漫之風,另一方面又繼承了殷商時代崇巫的文化傳統而巫風熾盛[9]。漢代王逸《楚辭章句》說:“昔楚國南郢之邑,其俗信巫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舞以樂諸神。”楚人崇巫是出了名的,前人與時賢所論甚多。巫是人們在“神秘”信仰支配下的產物,神怪思想和祭神、娛神的巫風很難為詩禮文化所限制,我國記載神話傳說的典籍多出于荊楚,是有其文化依據的。“當理性精神在北中國節節勝利,從孔子到荀子,從名家到法家,從銅器到建筑,從詩歌到散文,都逐漸擺脫巫術宗教的束縛,突破禮儀舊制的時候,南中國由于原始氏族社會結構有更多的保留和殘存,便依舊強有力地保持和發展著絢爛鮮麗的遠古傳統。從《楚辭》到《山海經》,從莊周‘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南方之強’,在意識形態各領域,仍然彌漫在一片奇異想象和熾烈情感的圖騰——神話世界之中”[8]82。崇巫的文化觀念,刺激楚人非凡的想象力,加上現實的矛盾沖突和時代的文化思潮猛烈沖擊著政治家、詩人、文學家和藝術家們的詩性智慧,他們或孤傲于世、或憤激于時,胸中如有春江之潮,狂瀾洶涌、擊石裂岸,于其時,必以“極天地古今之變動”的想象力與充沛的激情,方能吐喜極樂極、悲極憤極之情感意緒。他們代表著荊楚文化鮮明的美學精神與文化品格。故姜亮夫先生明確指出:“大抵沿江漢之民,習于水,故輕縹;而云夢緬緲,移人神思,故鬼神之事易感人。此兩事結集,故其民多巧慧,能進取,易變化,情愫特易表暴,事多創造,不守故常。人喜藝術,重義氣。故楚好多材,為一時之所重,此其大較也。”[10]
綜上所述,荊楚文化受南方水鄉澤國、叢林山巒自然氤氳之氣而自然物產豐饒的地理環境與巫覡文化的影響,是以青銅器、漆器與刺繡、老莊哲學和楚辭為代表,極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與理想主義精神,從楚人“剽輕”的風俗習性,“宏識孤懷”、“一意孤行”的思維方式,以及“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論,荊楚文化的特質應該是與藝術文化特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研究楚學的前輩張嘯虎先生曾明確指出:“在我國古代文化發展最繁榮的春秋戰國時期,各主要地區,各放異彩。如齊魯之國為經學,晉是史學發祥地,而楚則是文學藝術……這種傳統可謂歷久彌衰。”[11]當代著名作家熊召政先生于2006年11月24日在北京大學作過一次題為《楚人的文化精神》的演講,言楚文化“是一個藝術的文化,是一個把生活的快樂發揮到極致,把藝術發揮到一個靈性高度的文化”。筆者認為,一個是將畢生獻給楚學事業、成就卓著的張嘯虎先生,一個是對荊楚文化有精確把握、對荊楚文化孕育出的杰出人物之一的張居正①出生于江陵的“宰相之杰”張居正就是荊楚文化孕育而成的明代“磊落奇偉之士”,他曾云:“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衂;東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涬,一瞬皆空。”《張居正集》第三冊,卷三十七,文集九,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又云:“非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彌天下之患。”同上書,第二冊,書牘十五,《答西夏直指耿楚侗》。除張居正外,還有一大批楚人仍顯示出楚人的血性,張居正在《與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的信中說:“明興以來,國有艱巨之事,眾所巽愞觀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當之。”同上書,第二冊,書牘五。及其生活時代、文化背景與地理環境作過全面而深入探索并創作出長篇巨制《張居正》的熊召政先生,他們所得出的相同結論應該是符合荊楚文化特質的。
[1]劉紀興.荊楚文化的內涵及其創新特質簡論[J].政策,2007(2).
[2]司馬遷.史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4.
[3]陳晉.毛澤東與傳統文藝[M].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85-86.
[4]李維武.湖北地區的心學傳統及其意義[J].文史哲,2005(1).
[5]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
[6]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謝詒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123.
[7]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9-30.
[8]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9]黃靈庚.《九歌》源流叢論[J].文史,2004(2).
[10]蕭兵.楚辭文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35.
[11]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楚風補校注:上冊[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7.
Unique traits of the Jingchu Culture
Meng Xiux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020,China)
All the vassal stat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770 BC-221 BC)advocated openness,novelty,and change,which,therefore,should not be taken as the unique traits of a specific regional culture.The Jingchu Culture,influenced by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witchcraft culture,was represented by bronzes,lacquerware,embroidery,the philosophies of Laozi and Zhuangzi,and the Songs of the South.It was full of imagination,passion,romanticism,indomitable spirit,and idealism.Based on the valiantness,wild way of thinking,strong and unrestrained emotions of the Chu people,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unique traits of the Jing-Chu culture lie in its artistry.
the Jing-chu Culture;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rtistry;unique trait
G127.6
:A
:1009-3699(2011)02-0131-05
[責任編輯 彭國慶]
2010-12-22
孟修祥(1956-),男,湖北天門人,長江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