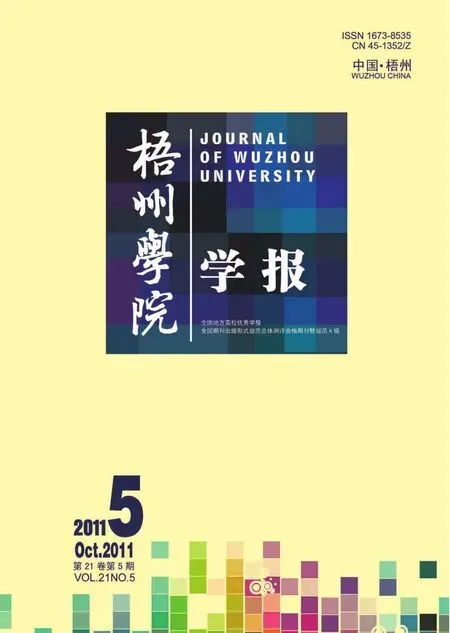歌劇《茶花女》中維奧萊塔的重要唱段解析
李陽陽,陳 潔
(1.廣西藝術學院 音樂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2;
2.梧州學院 藝術系,廣西 梧州 543002)
歌劇《茶花女》中維奧萊塔的重要唱段解析
李陽陽1,陳 潔2
(1.廣西藝術學院 音樂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2;
2.梧州學院 藝術系,廣西 梧州 543002)
歌劇《茶花女》是19世紀偉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歌劇的代表作,在世界歌劇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一部不朽的藝術作品。威爾第憑借著自己對音樂藝術的獨特理解和精湛的音樂創作技法,除了在視聽上給人們營造出所有偉大的藝術悲劇所必須要具有的“崇高”的審美感召力之外,更堅持把意大利歌劇的傳統創作技法與時代音樂風格相結合,用歌劇的藝術形式展現了《茶花女》的文本精旨。從該劇中女主人公的重要詠嘆調的角度分析歌劇《茶花女》的悲劇性,以及作曲家獨具匠心的音樂語言背后所蘊藏的美學意義。
歌劇;威爾第;《茶花女》
朱賽佩·威爾第(Giuseppe.Verdi,1813~1901)是19世紀意大利的作曲家,同時他也是西方音樂史上最偉大的歌劇作曲家之一,他一生始終都專注于歌劇的創作,共創作出26部歌劇作品。歌劇《茶花女》就是其中最能代表威爾第藝術造詣和成就的幾部重要作品之一。
歌劇《茶花女》誕生于19世紀中葉,不僅在歌劇史上是一部重要的正歌劇,而且直至今天,該劇仍然被世界各國的音樂愛好者視為藝術瑰寶,受到眾多人的歡迎和喜愛。把它置于今日的文藝百花園中,與其他優秀的作品相比,它仍然毫不遜色。這說明,它作為一部成功的藝術作品,不僅具有深刻的社會認識價值,而且還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而且對我國文藝事業也有著深遠的影響。從它為我們所提供的豐富的藝術實踐機會中,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它在歌劇藝術發展歷程中的歷史價值,這對于我們今天的文藝理論建設與文藝創作實踐,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一方面,它代表了一個特定的社會歷史時代,深刻地昭示了在時代背景下人性被束縛被摧殘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它代表了一個具有社會歷史內涵的特定的藝術時期。在這個時期音樂以及其他各藝術門類的藝術家們都逐漸在追求更加個性化的風格,他們主張藝術要真實地符合生活的現實主義,以至自然主義取代了浪漫主義對藝術領域的主導地位。威爾第就是推動這一進程的作曲家之一。“威爾第改變了他早期的創作風格不僅受到本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啟發,也接受了更多歐洲文學戲劇的影響。他的歌劇更深刻的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復雜多面和內心激烈的矛盾沖突,使意大利歌劇從形式到內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因此,歌劇《茶花女》較威爾第前期的作品更具有人性化,人物的個性更加深刻和鮮明,人道主義精神的彰顯也更為有力,同時它給人的審美感受也是無比強烈和震撼的。從文本角度講,《茶花女》的故事情節正是那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所造成的千百萬個現實悲劇中的一個,《茶花女》反映了那個時代真實的社會現狀,正如著名的樂評人沃爾夫岡·維拉切克(WolfgangWillaschek)評述的那樣:“事實上,這部‘肺結核歌劇’稱得上是一部直搗現代社會深處的神話”[2]。下面就從該劇中重要的詠嘆調和重唱解析這一偉大的作品所蘊含的藝術悲劇價值。
一、“啊,他是我渴望見到的人”——維奧萊塔的愛情詠嘆
在第一幕里,維奧萊塔在家中舉行酒會,維奧萊塔向每位來賓問好并祝他們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此時樂隊奏出一段活潑的曲調,整個歌劇宴會的氣氛頓時活躍了起來。這時男女主人公有了第一次正式謀面的機會。年輕的男主人公阿爾弗雷德被維奧萊塔的美貌和風韻所吸引,在樂隊奏起3/8拍的歡樂曲調下他唱起了飲酒歌,巧妙地向女主人表達了自己的愛慕之情,同時維奧萊塔也用歌聲回答了他。這是歌劇中男女主人公第一次正面交流,威爾第在此采用了歡快的圓舞曲節奏,使整個詠嘆調聽起來明快、熱情。到處都洋溢著巴黎上層階級的奢侈和華貴,在圓舞曲的背景下阿爾弗萊德與維奧萊塔交談,激情的短句增加了傾吐愛情的力量感,似乎沒有絲毫的不幸會降臨在他們身上,但這已經是悲劇的發端了。因為從二者的對話來看,阿爾弗雷德是為青春和美好的愛情而干杯,在座嘉賓隨聲附和。而維奧萊塔告訴人們特別是阿爾弗雷的是:“快樂不長久,青春很快就消逝。”應該像她一樣享受現在的快樂時光,不要奢求所謂的愛情。從這段對話中不難看出二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導致了他們愛情觀和價值觀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生活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更多的是兩個階級的根本對立所造成的。再從威爾第擅長的旋律曲調來看,阿爾弗雷德的旋律是陽光燦爛的,并較多地運用了大三度的音程關系,這更增加了男高音情感的明亮度和對愛情的直白表露。相對而言在維奧萊塔演唱的旋律中我們聽到的是由于身份的無奈而對愛情是不信任、不抱希望、逃避真情的聲音。她的旋律冷靜、柔和、熱情不足而躲閃有余。但將二人的旋律與眾人的合唱糅合在一起,其中以上所述論點就顯然隱藏于歡樂的宴會樂曲之中了。所以筆者認為此時的悲劇色彩不是不存在而是處于隱性地位,此時的悲劇性尚在萌芽時期。雖然此時的樂曲是歡快的,但它的作用顯然不是為描寫當時維奧萊塔的內心是多么幸福和快樂而創作的。恰恰相反,這種節奏和旋律是包含著眼淚的微笑,是女主人逢場作戲的無奈和辛酸的真實寫照。這一點從緊接著的情節就能找到顯證:她身染頑疾,面色蒼白,以至于在舞會剛剛開始的時候,就體力不支,不得不坐下休息。試問這樣的身體狀況卻要強顏歡笑討好上流資產階級的達官貴人,剛才那歡樂的曲調豈不是博得觀眾同情的最好的旋律嗎?這正是威爾第手段高明之處。
在阿爾弗雷德單獨向她吐露心聲之后,他們有一段二重唱,作曲家在用音樂的形式來塑造維奧萊塔的形象時,運用了較多的花腔,以表現她輕浮、放蕩的一面,同時也通過運用這種快速、華麗的織體形式來表現她在面對真實而激烈的感情時矛盾復雜的心情,短促的節奏表達出她內心世界的慌張,并試圖掩飾自己激動的心理。此時的歌劇并沒有明顯的悲劇性因素,但悲劇的動機卻已經顯現出來,那就是當客人們離開以后,在序曲中的第二主題發展下開始具體的描繪女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和她純潔天真的本性。她獨自一人表露了內心的情感世界,演唱了兩個世紀以來一直受人們熟悉和喜愛的獨唱曲“啊,他是我渴望見到的人”。
這首詠嘆調運用了大量的花腔技法來表現她放蕩輕浮的妓女身份,同時也表達了她在受到愛情的沖擊時內心是多么的激動和脆弱。維奧萊塔獨自一人沉浸在男主人公熱情而激烈的感情中,之后她甜蜜地唱出了阿爾弗雷德傾吐愛情的主題,此后,這便成了她的愛情主旋律,雖然此時聽起來是悅耳動聽酣暢快樂的,但在今后的許多悲劇性情節中這個愛情主題被反復運用,這樣就使得悲劇效果更加感人,為今后悲劇性的壯大埋下了伏筆。悲劇性是事物中所包含的一種特質,它能夠在一定條件的誘發下使事物向著悲劇的目標發展,并一步一步地達到這種結果,維奧萊塔的悲劇性就在于她所處的地位的卑微使其成為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玩偶,是這些人的工具,最終是會被毀滅的。而這種被毀滅的命運不是自然的,不是如人意的,它是破壞性的,是對人們的日常情感殘酷無情的摧毀,但不是說悲劇性的存在就是意味著悲劇的發生,在沒有外在條件推動和作用的情況下,它是不可能有什么超出質的變化,是達不到事物的毀滅的程度的,而悲劇也就無從生成。但悲劇性卻是潛在的,它隨時都可能因為某種情況的出現而成真,那種情況就是,在一定的外在因素的刺激作用下使悲劇性不斷得到發展強化而成為主導事物存在過程的力量,也可以說就是在悲劇性成為主導事物的發展過程的因素的時刻,就是悲劇的誕生時刻。所以,在此時,并不能得出悲劇的論斷,必須進一步隨著歌劇的發展,追隨悲劇性的腳步,才能了解作曲家是如何運用音符的力量使悲劇性成長起來的。
二、“你可是瓦萊麗小姐?”——維奧萊塔的深情詠嘆
當劇情發展到第二幕,維奧萊塔與心上人在鄉間過著幸福的隱居生活時,出現了推動悲劇性發展的重要人物——喬治·亞芒,他是阿爾弗雷德的父親,一位不屈不撓的家庭道德捍衛者。在小仲馬的原著中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省涉訟財產總管理人,一個資產階級的衛道士。在他以悲劇性的主導力量出現在維奧萊塔的面前的時候,他問道:“你可是瓦萊麗小姐”,從此引出了用嚴厲的口吻對維奧萊塔把他可憐的兒子帶到毀滅邊緣的斥責,但在聽到維奧萊塔對阿爾弗雷的真摯的愛和對過去那種墮落的生活之真誠懺悔之后,老亞芒很意外一個妓女卻有如此純潔善良的內心,于是悲劇性開始颶烈地壯大,他大起膽子要求她為自己的家庭作出犧牲。理由是他有一個象天使般純潔的女兒,而維奧萊塔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家庭蒙羞,所以為了使女兒能夠嫁給那位高尚的青年,維奧萊塔必須做出犧牲離開阿爾弗雷德,只有如此才能洗刷他們家庭的恥辱,拯救她女兒的婚姻幸福。
原以為只是讓她與阿爾弗雷德暫時分開而成全他天使般的女兒時,維奧萊塔便向老亞芒保證,盡管痛苦但她愿意這樣做。然而當喬治·亞芒提出讓他們永遠分手時,她顫栗地說出了“不!不!”,她害怕了。維奧萊塔哭泣著跪在喬治·亞芒的腳下,懇求他不要這么殘忍地傷害他們,非常激動地肯求這位“嚴父”理解他們的愛情。她自己已是重病纏身,不久于世,如果讓她與阿爾弗雷德分開,她寧愿去死。
在這充滿戲劇性的二重唱里威爾第再次大量地運用了重唱中的對比沖突,他以深刻的音樂洞察力在矛盾中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和性格,使故事情節富于戲劇性,更使整部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滿了魅力,充分調動了觀眾的審美心態。在喬治·亞芒與維奧萊塔的二重唱里,分成三個基本的部分(它們分別是:降A大調,c小調—降E大調,G小調—B大調),那有決定意義的轉折(亞芒唱:“你哭吧,可憐的人”)就在中間的一個調子中開始。這一段里悲劇性已經在老亞芒的催化作用下以顯性的姿態表露了出來,不再是隱藏在第一幕和第二幕開頭處的歡樂和幸福的外衣之下了。
三、“永別了,過去的美夢”——維奧萊塔的悲情詠嘆
在第三幕開場不久,醫生搖頭嘆息離開維奧萊塔的時候,預示著這朵曾經無比嬌艷、芬芳的鮮花最終的結局,但這時死亡對她來說是沒有恐懼的,她有的只是滿腔的無奈、失落與絕望,唯有心上的愛人才能給垂死的她一絲寬慰,這就是為什么奄奄一息的她仍然不忘給深愛著的阿爾弗雷德寫信。在飽含深情地念完她的遺言之后,她垂死掙扎地唱出了“永別了,過去的美夢”。
阿里戈·博伊托(Arrigo Boito)稱它是“垂死者最后的一記呼吸”與 “愛情回憶”的融合。在這一段富有死亡與升華的詠嘆中,歌者的創作必須與威爾第的初衷相一致,Addio(永別了)是維奧萊塔與自己以往奢華生活的告別,也是與她用生命追尋的純真愛情的告別,更是與她年輕生命的永別。在演唱這一詠嘆調時,僅僅抓住“一個垂死的妓女”形象是遠遠不夠的,她不單純是指一個生活在巴黎社會的玩具,也指有著純凈和美好靈魂的女人,更代表著這類人群的生存狀態。因此,這段演唱不是要表現她輕浮的一生終成潦倒的落魄結局,而是突出表現她臨死前對生活的渴望和對愛情的祈盼,對做一個正常人和享有正常情感生活的向往。而這些在通過女高音的二度創作表達出來的時候,應該是一個純潔、柔弱、無奈,卻有一顆無比堅貞之心的女性形象,這樣的處理要讓觀眾了解的不只是“肺結核”對她的折磨,更要剖開現象看到摧殘她的深層的社會原因。
在這首詠嘆調里有從第二幕里喬治·亞芒的旋律曲調中滲入的因子。當樂隊用笨重沉悶的音響奏出惶恐、陰暗的節奏時,似乎“死神”的腳步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可憐的女主人公,而代表“死神”的就是喬治·亞芒以及他所代表的階級。后來從這個節奏里就產生出哀悼維奧萊塔之死的音響。
巴黎狂歡節的喧鬧聲從窗外沖了進來,造成悲劇性的對比。在終場音樂里,不只一次地出現了維奧萊塔的愛情主題的回音,這些回音在她和歸來相會的阿爾弗萊德的二重唱里,表達了愛情的動機有了新的音響,在維奧萊塔死去的—剎那,它由弦樂器在高音區用Pianissimo輕輕地唱了出來。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很清晰地把這些主體性樂思聯系在一起,并明確這些主題材料之間的含義:第一幕中她甜蜜地唱出了阿爾弗雷德傾吐愛情的主題,這是悲劇的發端,而第二幕里父親亞芒的出現就暗示了維奧萊塔的悲劇性主題即悲慘的命運,安排她死刑的判決。而在終場悲劇達到頂峰之時,輕輕響起的愛情主題讓所有的觀眾都深深地陷入無盡的哀傷之中。
[1]于潤洋.中國音樂教育大系·音樂卷[M]//西方音樂通史.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273.
[2]沃爾夫岡,維拉切克.50經典歌劇[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118.
I106.3
A
1673-8535(2011)05-0067-04
2011-07-13
李陽陽(1980-),女,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聲樂教學與表演藝術。
陳潔(1982-),女,梧州學院藝術系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聲樂教學與表演藝術。
覃華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