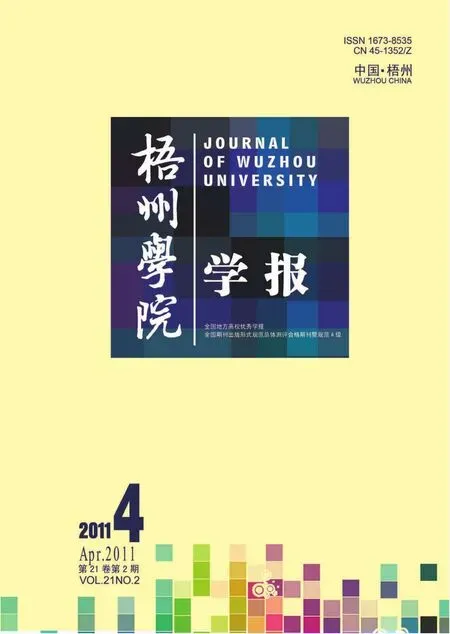構建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張云玲
(河南師范大學 法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構建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張云玲
(河南師范大學 法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近年來,刑事和解制度作為我國司法實踐部門探索的解決刑事案件的新途徑,不僅有利于有效化解矛盾,提高犯罪預防效果,還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促進社會和諧。在我國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礎、法律基礎、刑事政策基礎和實踐基礎。在此就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作一考證,以期對建構符合我國國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有所幫助。
刑事和解;可行性;必要性;和諧社會
如何既能夠使加害人順利回歸社會,又能夠有效地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是我國刑事科學領域內的一項重大難題。刑事和解制度作為一種刑事案件解決方式的新思路,成為化解上述難題的一種替代性方式,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應運而生。一方面,由于該制度以雙方當事人通過會見、溝通、協商為主要特征,充分尊重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意愿,能夠有效彌補傳統刑事案件解決方式中不太關注保護當事人雙方權益的不足,同時對于化解矛盾、促進人際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及節約司法成本、提高訴訟效率等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有構建之必要。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已經具有適用該制度的文化底蘊、刑事政策依據以及刑事立法制度基礎,有構建之可能。所以,在我國建構刑事和解制度,不僅非常必要,而且完全可行。
一、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實現犯罪人的回歸,提高犯罪預防效果
在傳統報應性司法中,認定犯罪人時很少考慮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犯罪人格,而是不加區分地對所有實施法定的危害社會行為人一律貼上犯罪人標簽,立案、偵查、起訴、審判以及刑罰的執行過程都對加害人造成了 “標簽”式影響,在社會中會受到無形的歧視。而加害人會因為犯罪標簽的強化與社會公眾的譴責,成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加害人逐漸會對自己的人格進行自我否定并且認為自己已經受到了社會的排斥,從而造成其自暴自棄,增加了其回歸社會的難度,還有可能促使其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此外,監獄刑罰的教育是告誡犯罪人若再次犯罪將會受到更為嚴厲的懲罰,犯罪人不再犯罪的原因是出自于對監禁刑的懼怕。加害人很少有機會理解或者面對他們的罪行對他人的真正影響,很少能夠將被害人也看作是人,而不是虐待的目標和客體[1]。因此,通過刑事和解,能夠避免給犯罪分子帶來的許多負面影響。刑事和解為加害人提供了對話的機會,可以尋求被害人的諒解,有利于其自身罪行的矯正。因為刑事和解能夠使加害人認識到自己行為的惡性,促使其真誠悔罪,彌補其犯罪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以求得到受害人的寬容與諒解,達成和解協議。加害人的誠懇道歉與主動承擔責任不僅緩和了被害人的憤怒情緒,避免了被害人的報復欲望,而且還恢復了加害人的尊嚴和自信,減少由于犯罪行為而招致的來自于社會的歧視,從而有利于促使其認罪和轉化,其人身危險性也將大大減小甚至消失,有利于其改造。刑事和解堅持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堅持教育、感化與挽救的方針,以加害人能夠順利地回歸社會為最終目的,這種教育是深層而本質的。
(二)有助于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與社會轉型時期,各類犯罪案件大量增加,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監獄等羈押場所人滿為患,加上刑事訴訟程序的日趨復雜化,司法資源顯得越來越稀缺。司法人員常年超負荷運轉,但仍避免不了刑事積案上漲、當事人的不滿意率增加、監獄的擁擠程度加劇、辦案效率低下、再犯罪率急劇上升、訴訟的周期延長等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種種問題。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與運行是一種更有效率、更為經濟的糾紛解決機制,通過及時、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和糾紛來預防犯罪,可以有效地減少訴訟環節和節約訴訟成本。在刑事和解制度過程中,由于這一制度采用的是一種非常規的糾紛解決程序,只要保證對達成和解協議的合意性、真實性與合法性,就能使某些案件的處理繞開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及執行程序,避免了案件在后續執行環節的司法資源支出,這樣可以促進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將司法資源主要運用在處理主觀惡性相對較深、犯罪性質與后果相對較為嚴重的各類惡性的、暴力的、對社會秩序造成較為嚴重破壞與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上,有效提高司法工作人員的辦案效率。因此,刑事和解制度不僅對訴訟程序的繁簡分流起著重要作用,而且還對全面提高訴訟效率起著積極的作用。
(三)有助于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目前,我國正處于各方面改革的關鍵時期,利益越來越多元化,治安形勢非常復雜,以致各種矛盾與沖突紛繁復雜,由人民內部矛盾激化所引起的刑事案件多發且呈上升趨勢,暴力犯罪數量也急劇增多,刑事沖突或犯罪往往對平靜、正常與和諧的社會關系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與威脅,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對業已被沖突或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予以恢復[2]。因此,倡導和諧成為當務之舉。然而,傳統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價值追求上更多關注的是國家利益;在責任承擔方法的選擇方面,主要崇尚的是重刑主義與惟刑主義,即所謂的惡有惡報、罪刑相適應。這種以牙還牙式的心態,很難使加害人產生贖罪感,而且被害人心中的忿恨也很難得以釋懷,犯罪造成的社會矛盾與對立既得不到有效解決,又有可能導致相互感染與循環報復[3]。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要妥善地解決社會糾紛、化解社會矛盾,又要穩定社會秩序,刑事和解制度正好順應了這一需求。因為刑事和解機制不是采取以牙還牙的報復形式來追求正義,而是努力為當事人雙方營造對話的氛圍與空間,要求相互對立的雙方當事人能夠積極地參與其中,充分發揮雙方在解決刑事糾紛中的能動作用,通過當事人雙方的直接交流、溝通、協商、讓步、妥協,促使其各自選擇彼此都能夠接受的方案,在相互的磨合中共同自愿地解決糾紛、化解矛盾,并把賠償損失、賠禮道歉以及刑事責任意見等作為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主要內容,讓犯罪人支付必要的代價并進行必要的反省,以彌補其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害。對受害人來說,和解協議快速及時地履行能夠使其在心理創傷得以恢復的同時得到一定的物質賠償,既有利于保障其合法權益,又有利于恢復其正常生活;對加害人來說,能夠贏得被害人的諒解和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能減少其與社會的對立情緒,減輕其犯罪標簽化的效應,從而達到多種利益之間的適度平衡,恢復業已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與沖突,促進社會安定與團結,最終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目的。此外,刑事和解中受害人與犯罪人都親自參與,可以切身體會到司法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不僅有助于消除他們對司法工作人員的各種不信任和猜疑,增強其滿意度,還有助于提高司法機關辦案的公信力,最終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二者的和諧統一。
二、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制度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礎是我國的“和合”觀念
中國歷來倡導 “和為貴”,具有 “化干戈為玉帛”的文化底蘊。儒學大師孔子云:“禮之用,和為貴。”追求和睦、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自然和諧 “天人之間合而為一”,與自身和諧“為而不爭”。中國古代和合文化十分推崇和緩、寬容的糾紛解決方式,追求一個沒有紛爭的和諧社會。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要求司法工作人員不要輕易地對糾紛進行審理和頒布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的裁決,應當對糾紛先進行調解,以尋求當事人雙方都愿意自愿地接受的糾紛解決方案。無訴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在人們的訴訟法律意識與個人權利意識中,都早已深深地烙下了無訟的痕跡,這就表明了人際關系的和諧是傳統倫理觀念和法律文化的內在使命與終極目標,而刑事和解制度正好與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不謀而合,與我國根深蒂固的訴訟觀念和期望相符合[4]。因為刑事和解強調的是當刑事糾紛發生以后,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對犯罪人的懲罰,而是積極地尋求犯罪人與受害人的和解途徑,以便能夠從根本上化解矛盾。中國自古以來所提倡的和諧、反對爭訟、和合文化的傳統思想正好與這一理論相對應。千百年來,我國運用調解的方式和平解決沖突,就是在無訟觀念下解決紛爭、化解矛盾的最常用方式。
(二)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政策基礎是寬嚴相濟
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推進,輕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漸成為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和世界性的趨勢和潮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充分適應了司法領域的新變化,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基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即 “輕輕重重、輕重結合”,懲辦與寬大的結合。具體而言,對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情節極為惡劣、后果極為嚴重的惡性暴力犯罪、恐怖犯罪、有組織犯罪和累犯等重大犯罪行為,刑事司法上應當嚴厲打擊,從重量刑;而對公共秩序與社會穩定影響不大的輕微犯罪、初犯、偶犯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上則應當采取輕緩的刑事政策。其實質就是要求我們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分別針對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在認定處理上采取寬嚴結合,有寬有嚴,不僅要有力地打擊和震懾犯罪,還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種對輕微犯罪采取更寬容的 “輕輕”刑事政策價值取向,為刑事和解制度推行提供了政策依據。當前在我國不少省市試行的刑事和解恰與上述刑事政策的精神所契合。刑事和解進一步強化對刑事案件的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進行司法保護的思想,最終實現了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間、案件雙方當事人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綜合平衡和全面恢復。其核心精神和落腳點是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在充分保護被害人利益的基礎上,兼顧保護加害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現代刑法對人權的尊重,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制度基礎是我國現行的刑事法律
盡管我國的刑事法律還沒有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規定,但我國刑事實體法以及刑事程序法中的相關規定,在一定意義上包含著與刑事和解相類似的成分,為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提供了法律依據。例如刑法中有 “侮辱罪、誹謗罪等不告不理的罪名”的規定,關于 “告訴才處理的犯罪”的規定,以及有關 “犯罪的非刑罰處理”的規定,都提倡以非刑罰方式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再比如刑事訴訟法第172條對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的規定,以及公訴案件中的輕微罪不起訴制度的規定。
(四)刑事和解制度的實踐基礎是我國非刑事處理的成功經驗
在探索替代性解決刑事糾紛方式的道路上,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于2002年將刑事和解制度廣泛應用于輕傷害類案件,其中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移送起訴的輕傷害類案件,應當聽取受害方的意見。若加害方認罪,受害方可以與加害方就賠償問題進行協商,如果能夠達成一致就能夠直接獲取相應的賠償,然后檢察機關就能夠對加害方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這一規則的出臺與運行使一些輕傷害類案件走上了和解而非訴訟的途徑。司法部于2003年就下發了 《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在全國 18個省市開始了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檢察院于2007年10月10日起正式實施 《關于辦理輕微刑事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的規定 (試行)》,并于同年的11月20日辦結了第一起刑事和解案件。據統計,從2003年1月到2004年6月,威海市公安局高區分局一共立了89起輕傷害案件,立案以后,加害方與受害方自愿進行刑事和解并由公安機關作出撤案處理的案件有43起,比例為48.1%[5]。最高人民檢察院也舉辦了關于 “刑事和解與和諧社會構建”的研討會,提出司法機關要從對抗性司法向合作性司法轉變。以上這些司法實踐針對我國具體情況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而實踐的初步成功意味著,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傳統刑事司法模式下通常由國家來行使追訴權的刑事訴訟中,具有深厚的生發土壤和廣闊的適用空間。在我國目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求下,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導下,構建中國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十分可行。
[1]博西格諾,等.法律之門[M].鄧子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661.
[2]張云玲.構建和諧社會視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J].理論與改革,2009(1):136-138.
[3]衣家奇,姚華.恢復性司法:刑事司法理念的重構性轉折[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6(2):9-12.
[4]賀衛方.中國司法傳統的再解釋[J].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0(2):199-205.
[5]傅達林.刑事和解:從“有害正義”到“無害正義”[J].社會觀察,2005 (12):25.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Conciliating System for Criminal Cases in Our Country
Zhang Yunling
(Law School,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In the present years,the conciliating system for criminal cases,a new method that is being analyzed in our country’s organizations of justice,not only facilitates settling conflicts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pre-preventing crimes but also facilitates saving judicial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There are profou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law foundation,policy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ciliating system for criminal cases to be implemented in our country.Therefore,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conciliating system for criminal cases in our country,attempting to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ciliating system for criminal cases that is suitable to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conciliation of criminal case;feasibility;necessity;harmonious society
D920.4
A
1673-8535(2011)02-0048-04
2011-02-24
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09CFX009);河南省政府決策項目(2010E456)中期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張云玲(1974-),女,河南民權人,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訴訟法學、法律邏輯學。
覃華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