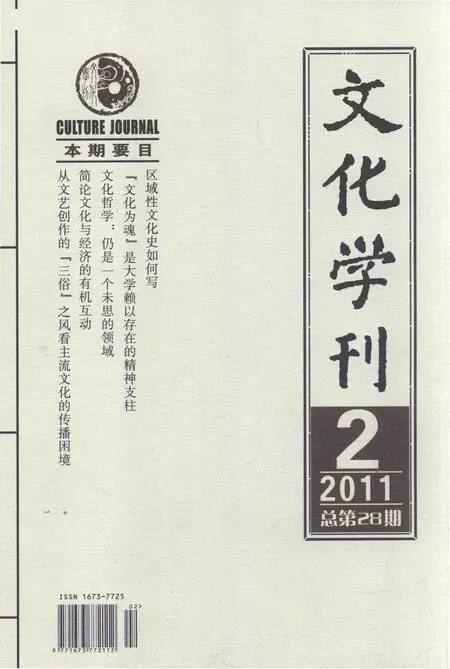村上春樹作品中荒誕背后的人性文化
王 昕
(大連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8)
村上春樹作品中荒誕背后的人性文化
王 昕
(大連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8)
村上春樹被日本文學評論家川本三郎稱贊為“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旗手”。他的作品為我們詮釋了消極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很多時候讓你沒有辦法規避其荒誕性,但在荒誕之余也不乏對人性的深入思考和人性文化的升華。
村上春樹;荒誕;人性文化
村上春樹以其獨特的故事情節和奇特的后現代敘事方式,展現了在繁華的日本都市中人們普遍的精神狀態和孤獨的心理情緒。村上春樹的作品充滿了獨特的寓意性,大量的不合邏輯的時空轉換,荒誕不經的故事情節,給讀者留下無限的想象空間。可以說村上春樹所營造的文學世界始終是離奇的,在不經意間指出生命的本質、生與死的意義、尋找自身的主體價值。
一、荒誕的敘事風格
無邏輯的荒誕是村上春樹一直沿襲的風格。閱讀村上春樹的小說,讀者都會被他奇特的想象和荒誕不經的情節所折服,他的想象不會給讀者帶來童話想象中的美好、純真和光明感,也不似神話想象般瑰麗、豐富和絢爛。作品中的荒誕情節總是在黑暗中充滿著對后現代工業社會的叛逆與反撥、否定與嘲諷。有的作品情節斷裂,各不連貫,邏輯混亂,前因后果互不關聯。其小說的敘事特點以荒誕的特性表現出來,而荒誕的表現形式首先是超時空的二元敘事風格。在村上春樹作品中經常出現“此岸”和“彼岸”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可以說是“世界的盡頭”與“冷酷仙境”,也可以說是人生的“出口”和“入口”。村上春樹曾經說,將“存在”與“非存在”進行對比是他的嗜好,而這也是他大多作品共同的特點。他喜歡在作品中并置兩個平行的世界,其一是“存在”的比較現實的感官世界;另一個則是“非存在”的虛幻的、主觀臆造的世界。例如,最具有代表性是《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出于現實中的是“冷酷仙境”這個此岸世界,在這個時空里,以東京為背景,主人公作為一名職業的計算士在接受教授的特殊數據計算任務后,經歷了一系列驚人、離奇的事件,在被“組織”、“夜鬼”、“工廠”等人追殺后,作為計算士的代價,最后自己也將面臨著只剩下24小時的生命;而虛幻的時空是“世界的盡頭”,世界盡頭是一個小鎮,和繁華的大都市東京相比較,這個小鎮寂靜、沒有戰爭,每個人都安于職守,在放棄個人的影子后,人便可以得到永生。在看似安謐、祥和的小鎮中,主人公“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面對獨角獸的頭蓋骨“讀夢”。在《且聽風吟》中,村上春樹有創造了一個此岸現實瀟灑自如的“我”和活在痛苦、自閉彼岸中的“鼠”,將“我”的生活狀態與“鼠”的生活狀態對比;而在《海邊卡夫卡》中奇數章節是一個自稱“田村卡夫卡”的15歲少年離家出走后,在4國的生活經歷,而偶數章節的主人公中田君是一位在戰時中失去記憶的、喪失閱讀文本能力的卻懂貓語的老人。在村上春樹筆下的文學世界里,這種二元世界的對比是交錯出現并行向前發展的,通過某一個物體,如“頭蓋骨”、“入口石”,或某一地點“甲村圖書館”,或者某一事件“尋找一只背生淺色星狀斑紋的羊”來將兩個“存在”和“非存在”的世界聯系在一起,從而在荒誕、無邏輯中營造出虛實相生的具有村上式的藝術世界。
二、荒誕的作品意象
村上春樹的有些小說帶有怪誕的色彩,這種風格不但出現在中長篇中,在短篇中也具有此風格。《電視人》由6個短篇組成,《眠》講述一個少婦一個月沒有睡眠,在深夜東京的街頭開車游蕩。《行尸》描述了一個暴力和血腥的夢。《加納克里他》描述兩個姐妹殺死警察,而警察變為幽靈來找“我”和姐妹兩人。《電視人》可謂是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作品,平靜的家中突然闖入小小的電視人,在給“我”裝一臺我并不需要的索尼彩電,工作開會也碰到電視人,同時“我”和妻子的關系也因此以破裂告終,妻子離家出走,電視人在“我”家的電視屏幕上一個勁地造飛機。《電視人》中出現了電視這個意象,“我”平靜的生活突然因為有了電視和“仿生人”出現而亂了套,電視人不斷打入“我”的生活,最后人無奈地看著機器,無法生活。后現代的一個特征就是由于電影、電視等可以復制的藝術出現,導致了距離感的消失,人類在可以大量復制的影像、圖片中失去了辨別真偽的能力。杰姆遜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中提出:“如果一切都是類象,那么原本也只不過是類象之一,與眾沒有任何的不同,這樣,幻覺與現實便混淆起來了,你根本就不會知道你究竟處在什么地位。”
在村上春樹的文學作品中,他所選取的意象往往都是抽象的、奇特的、詭異的,具有寓言式的。例如,《尋羊冒險記》中出現的一個叫“羊男”的小男人,“羊男把羊皮一直披到頭頂,他敦敦實實的體形同那衣裳正相吻合。四肢部分則是接上去的仿制品,頭罩也是仿制品,其頂端挺出的兩根環狀角則是真的……遮住上半邊臉的面罩、手套和襪子統統是黑的。衣裳從頸部到胯部帶有拉鏈……衣裳后部還伸出一根小尾巴”。[1]羊男的裝束實屬荒誕,但卻是為了逃避戰事而不得不以羊的面目隱身在戶外的森林里,成為一只愛好和平的羊人。在這荒誕的形象背后是作家對戰爭的諷刺,人的主體價值已經淪喪為依靠偽裝成“羊人”來維持生命。而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的“獨角獸”,出現在主人公“我”臆想的世界,也就是所謂的世界的盡頭,獨角獸的職責是將每個居住在小鎮的人的心帶出墻外。“獨角獸吸收、回收人們的心,帶往外面的世界,及至冬天來臨,便將那樣的自我貯存在體內死去。”[2]人所有的七情六欲全來源于自己的內心,人間萬物皆由心生。居住在世界盡頭的人們以丟失“心”的代價來換取永生,而獨角獸作為動物的一種,它的職責竟然是吸取人的心,這種荒誕意象的選取和附于意象的職能,可謂是在村上春樹作品中獨特的風景。類似這樣意象還有很多,如,《象的失蹤》中的“大象”,《奇鳥行狀錄》中的“擰發條鳥”,《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中被稱謂“宇宙飛船”的彈子機等等,村上春樹正是通過這些荒誕卻又獨特的意象,來使文本的內容更具有后現代的風格,同時,又借以荒誕的手法來傳達作家所要表述的觀念。另外,在村上春樹的眾多作品中還大量出現了一些沒有真實姓名的人物,如,《尋羊冒險記》的“鼠”、《海邊的卡夫卡》的“田村卡夫卡”、《奇鳥行狀錄》的“我”、《舞!舞!舞!》的“喜喜”和“咪咪”、《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我”、《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里的雙胞胎“208”、“209”等等。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是可以代表個體存在價值的姓名都已喪失,他們的主體存在已被抽象化為一個符號,作為人自身的主體價值已經不存在了。這樣的一個標識,不能不說是在消費時代所特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越是發達,人自身的價值就越是喪失,也可以說是現代文明的沖突。
三、荒誕背后的人性文化
大江健三郎在談及村上春樹時,曾經希望村上春樹上在其作品中能夠突破內閉式個體的失落、孤獨、空虛和悵惘等頹廢情緒的圖譜,賦予作品中的人物以更多的社會意義。而這種希望正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出現。雖然在村上春樹后期的作品中仍不斷以荒誕的形式表現出來,但荒誕背后的意義卻越來越深刻。加里·菲斯凱頓曾將村上春樹概括為:“在西方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日本作家……因為繼續不斷地在成長,在變化,在迷惑我們,也許一路上他自己也跟著他的讀者一樣吃驚匪淺。”[3]
村上春樹的視角是獨特的,他所創作的作品越是荒誕,就越是能揭示作品現實的本質,越是能體現作家賦予荒誕的意義。村上春樹筆下的都市青年都是出生于戰后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在科技發展、經濟增長中,人們往往片面追求物質文明,而這樣就必然導致精神文明的缺失。機器大生產給人們生活帶來無限的發展空間,同時也讓人們陷入孤獨、物化的低谷。人類的存在在無形中被貼上標簽,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消費時代。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被打破,隨著經濟發展,科技、知識的膨脹,人們的精神受到極大的壓抑,社會客體的物質化正在壓倒人類主體的精神文明。物化成為消費時代普遍的社會現象。人成了商品經濟的附屬品,人在被物化的同時也在異化。這也是村上春樹作品荒誕背后的根源。正如在《舞!舞!舞!》中“我”說到:“人們崇拜資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機,崇拜其神話色彩,崇拜東京地價,崇拜奔馳汽車閃閃發光的標志。除此之外,這個世界再不存在任何神話。這就是所謂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都要在這樣的社會里生活。善惡標準也已被分化,被偷梁換柱。善之中有時髦的善和不時髦的善,惡之中有時髦的惡和不時髦的惡……這樣的世界上,哲學愈發類似經營學,愈發緊貼時代的脈搏。”[4]誠然,人類對生活原有的期待被打破,物質文化在逐漸取代精神文明,現代人的恐慌、壓抑、絕望都是伴隨消費社會而來的。
正如村上春樹所言:“任何人在一生當中都在尋找一個寶貴的東西,但能夠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運地找到了,實際上找到的東西在很多時候也受到致命的損毀。盡管如此,我們依然繼續尋找不止。因為若不這樣做,生之意義本身便不復存在。”[5]因此,可以說村上春樹在尋找的就是精神家園的修復和彌補。村上春樹自己也說文學創作是一種“療愈”。在世紀之交的日本,“療愈”已經成為國民性的一個主題。隨處可見具有“療愈”性質的各種商品,如,音樂、漫畫、風景等。在經歷戰后的精神創傷、泡沫經濟的沖擊、阪神大地震以及奧姆真理教主導的“地鐵沙林事件”后,日本民眾的內心已經變得十分脆弱和敏感,恐懼和不安時刻縈繞在民眾的心頭。人們的內心被社會的荒誕所束縛著,壓抑著。個人與社會的距離感在日益拉大,人類對自身的存在價值感到迷惑。而村上春樹正是通過寫作來挽救民眾的精神家園,尋找失落的靈魂。正如在《神的孩子全跳舞》中,作家探索的就是這種“療愈”。日本的心理學家河合隼雄也認為,作家通過寫作得到拯救;讀者通過閱讀得到解脫。的確,在物欲橫流的荒誕社會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苦悶、困惑、孤獨的情緒,正如村上春樹筆下的都市青年“渡邊”等人,會失去人生的方向感,但即使這樣,村上春樹仍給讀者指出方向:“不錯,人人都是孤獨的。但不能因為孤獨而切斷同眾人的聯系,徹底把自己孤立起來。而應該深深挖洞。只要一個勁兒地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獨之中用墻把自己圍起來時不行的。”[6]村上春樹就這樣充滿人道主義情懷,為讀者在文學世界中點亮一盞明燈。村上春樹正是在面對人類主體價值的迷失、生存狀況荒誕的情況下,踏上尋找人性文化重建之路。
隨著日本越來越走向后現代,人類以往的生活模式已經逐漸被打破。村上春樹的小說就表現出人們在享受后工業社會高科技送來神奇創新的同時,所擁有的迷惘無助、情感失落、性愛分裂、價值崩潰,進而走向后現代的虛無和仿徨。現代城市之間的冷漠,以及內心深處對某一種純樸情感的追求,使人們沉湎于構建一種物質的可能性,來代替己經失去精神的不可靠性。村上春樹用怪誕魔幻的后現代手法,從更高層次上揭示出日本高度資本主義的嚴酷的現實和人類在潛意識中獲得瞬間的滿足和幻覺。村上春樹以其獨特的故事情節和奇特的后現代敘事方式,展現了在繁華的日本都市中人們普遍的精神狀態和孤獨的心理情緒。他重視對內心世界進行探尋和營造,同時也表現出自己希望有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無間、完整寧靜的世界,這種希冀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超越。
[1][日]村上春樹.尋羊冒險記[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214.
[2][日]村上春樹.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361.
[3][美]杰魯賓.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328.
[4][日]村上春樹.舞!舞!舞![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65.
[5][6]林少華.村上春樹和他的作品[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2.14.
【責任編輯:劉 強】
I106
A
1673-7725(2011)02-0120-03
2010-12-02
王昕(1979-),女,遼寧沈陽人,講師,主要從事日語教學和日本語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