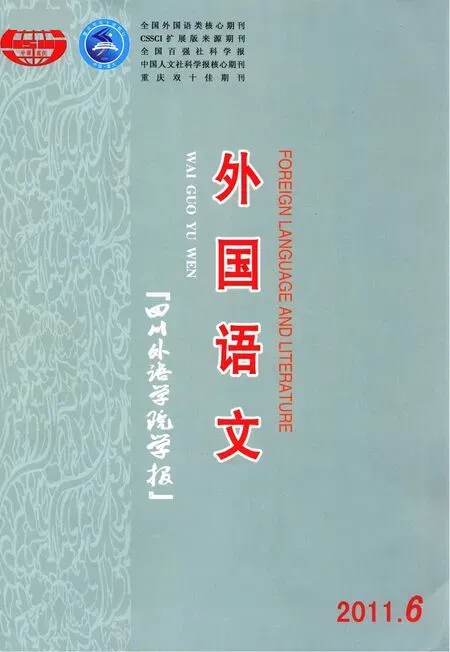《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翻譯與傳播
方 紅 王克非
(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1.引言
《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馬克思主義早期重要著作,對馬克思主義學說作了概要、系統的闡釋。《宣言》是中國人接觸到的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是被翻譯和重釋最多的對象。中國現代思想的嬗變肇始于翻譯、改寫、挪用以及其他與西方相關的跨語際交流,因此不可避免的是,相關研究會以翻譯作為其出發點(劉禾,2002:35)。自19世紀末國人初聞“康密尼人”之名直至1920年《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出版,《宣言》的翻譯經歷了節譯、釋譯、轉譯等一系列重譯過程,其傳播與接受也經歷了不同翻譯主體的選擇、闡釋、重構等一系列操控過程。思想的翻譯與傳播之初往往不是有計劃地直接和系統的全譯,而是始于選擇性的引介和節譯,而譯者的選擇不但決定了《宣言》內容進入中國的先后次序,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對《宣言》等外域思想需求的輕重緩急。勾勒出《宣言》以何種姿態進入中國,便于探尋《宣言》在中國的定位及發展方向。正如孔慧怡(2000:4)所說:“翻譯所造成的長遠文化影響并不取決于原著或譯作本身,而是取決于當時的文化環境會把外來知識引上什么道路。”作為代表和承載文化環境影響的譯者,在不同歷史語境下對《宣言》所做的翻譯選擇,不但彰顯了其時文化語境的歷史訴求,也決定了《宣言》在中國的傳播路徑。
本文將《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之前的譯介界定為早期翻譯,通過對不同時期譯文文本的梳理,深入分析《宣言》早期傳播中不同翻譯主體的選擇、翻譯策略及成因,重新審視這一重要思想文獻的翻譯傳播過程及翻譯在其中的作用和意義。從譯文反觀思想的翻譯傳播并不是要把歷史簡化為文本,而是把文本視作一種極具說服力的社會事實,探討其內容選擇和意義建構的歷史語境。《宣言》的早期翻譯傳播不但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譯介和接受過程的縮影,也為進一步探視翻譯與思想傳播的關系提供了典型的史例。下面對不同階段的《宣言》翻譯情況進行梳理,分析翻譯主體的選擇及原因,并基于文本分析對譯法及譯名加以探討,從而全面把握以翻譯為入口和載體的《宣言》早期傳播情況。
2.翻譯主體與翻譯選擇
《宣言》的早期翻譯與傳播以翻譯主體為線索可分為三個階段:傳教士與中國士大夫的合作引介(19世紀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選擇性節譯(20世紀初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翻譯評介(十月革命至1920年《宣言》第一個全譯本出現)。不同階段翻譯主體對《宣言》的翻譯選擇體現在譯文來源、選擇內容、翻譯策略及翻譯動因等方面的差異。
2.1 傳教士與中國士大夫的合作引介(19世紀末)
傳教士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尤其是19世紀中下葉,他們在傳播宗教理念的同時,也把西方社會文化中的流行因素介紹進了中國,《宣言》的思想片段最早就是通過傳教士的翻譯、介紹,經由傳教士主辦的報刊出版機構傳入中國,這使得他們無意間成為最早向中國譯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士。
《宣言》于1848年問世。1877年中國報刊中才第一次出現Communist一詞的譯名。《西國近事匯編》中記載了光緒三年(1877)由美國傳教士林樂之口譯、蔡錫齡筆述的一段文字,最早提到了“康密尼人”、“康密尼黨”,即communist的音譯①光緒三年(1877年)標注為“西歷五月九日至十五日”的原文提到:美國費拉特爾費亞省來信,謂美有數處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亂黨夏間起事,……今以體恤工人為名,實即康密尼黨唆令作工之人與富貴人為難。……美按察作色嚴諭曰:“康密尼人亂種,非可行于美國,美國斷不容也。”也有標注為“西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的文字提到:……查此事,皆由康密尼人黨而來,人皆疾惡之。……。馬克思的名字和《宣言》的觀點在中國的早期引介與傳教士李提摩太和《萬國公報》是緊密相關的。正如美國學者伯納爾(1976:38)所說:“《萬國公報》的編者經常超出其自身宗教信仰,傳播更為激進的思想。”1899年,《萬國公報》第121、123期分別登錄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蔡爾康撰文的《大同學》一書的第一章和第三章。文中提到了馬克思其人及《宣言》中的一段話,是將第一、二章內容編譯的一段話,意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世界市場而迅速發展,這樣下去財富終將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而隨著資本積累的加劇,資產階級也將逐步走向盡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窮苦百姓被逼無奈只得出其自有之權以安民而救世。”這段話是《宣言》思想中最早傳入中國的,傳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國文人蔡爾康②蔡爾康(1851~1921),光緒二十年(1894年)成為《萬國公報》華文主筆,與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合作翻譯了很多著述,有“幾合美華而為一人”之說。以“西譯中述”③傅蘭雅在《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中對此有過描述:“至于館內譯書之法,必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后,華士將稿改正潤色,令合于中國文法。”(轉引自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2001:342)。關于這種翻譯模式的弊端,馬建忠在《擬設翻譯書院議》中說:“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為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為仿佛摹寫其詞中所達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不達洋文,亦何怪夫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所鄙夷而訕笑也。”(參見馬祖毅,2001:353)嚴復也認為:“目下學習洋文(之)人幾于車載斗量,……顧其人于中國文學往往僅識之無”,“所以洋務風氣宏開,而譯才則至為寥落。……復所知者,亦不能盡一手之指。”(見《與張元濟書一》,《嚴復集》第3冊《書信》,1986:526)的合作翻譯模式,間接譯介了馬克思的《宣言》主張。
傳教士所譯介的《宣言》片語間接來源于英國的社會思想著作,是附載在進化論和社會主義思潮中,隨著“西學東漸”的歷史大背景進入中國的。翻譯的內容集中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概念及《宣言》中“概述資產階級發展過程及無產階級奮起救世”的內容,并主要從中國自有的傳統思想中選取可對應的概念來闡釋《宣言》的思想,如以“大同”、“均貧富”、“安民/養民”來譯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概念。這一階段獨有的“西譯中述”的翻譯模式使《宣言》初入中國就經歷了雙重選擇,即傳教士的內容選擇與中國士大夫的譯名選擇。可見,馬克思學說從進入中國的最初就被直接納入目的語既有的思想體系,開始了其譯介本土化的進程。而且,譯者并不追求與源文本的忠實一致,而是采用了節譯和編譯的手段,借翻譯之名表達了自己的“傳新布道”之意④李提摩太在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序言中闡述過“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策,針對中國的實際提出了一系列的變法設想。(參見熊月之,1995:603)此處可見,李提摩太并不是客觀引介馬克思學說,而是把馬克思學說納入了他所提出的“安民”策略之內,作為他宣揚的變革新學的一部分。,把《宣言》思想作為當時的流行思潮甚至一種新知識引入中國,期冀以此來教化迂腐之民,為“求變”的國人引介救世之道,告知并規勸清廷當權者接受新學和改良來強國救世。傳教士無意間間接譯介的馬克思之名及《宣言》的內容引起了當時文人的關注,引發了后來對《宣言》思想及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譯介熱情和大量討論。
2.2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選擇性節譯(20世紀初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赴外留學,尋求變革救國之路,把西方的社會思想大量引介入中國。其中尤以留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把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大量引介到中國,特別在《宣言》的日文全譯本出現后,《宣言》思想得到大量的重譯和釋譯。
中國第一位直接接觸《宣言》并認同其思想的是孫中山。他曾敦促留學生研究馬克思的《宣言》⑤參見宋慶齡《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載《人民日報》1966年11月13日。。1903年2月,東京留學生主辦的雜志《譯書匯編》第11號刊登了君武(馬君武)寫的《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并附社會黨巨子所著書記,其中列有馬克思所著《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1847)一書,這是《宣言》一書首次在中國報刊中被提及,也是國內第一個關于馬克思著作的目錄。文中譯介了恩格斯為《宣言》所作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話:“……馬克司者,以唯物論解歷史學之人也。馬氏嘗謂階級競爭為歷史之鑰。馬氏之徒,遂謂是實與達爾文言物競之旨合。……馬克司之思想華嚴界之類也。”
1903年2月,廣智書局出版了福井準造(日)撰寫、趙必振翻譯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書中介紹了《宣言》的成書目的并譯介了最后兩段話。就現有資料看,這是以直接敘述的手段翻譯《宣言》內容的最早一段譯文。1903年10月,《浙江潮》編輯所出版了幸德秋水著、中國達識譯社翻譯的《社會主義神髓》①幸德秋水是日本近代社會主義運動的著名先驅者,《社會主義神髓》是他最重要的宣傳社會主義的理論著作,也是日本明治時代水準最高的社會主義理論著作之一。原書出版于1903年7月,可見此書很快傳入中國并相當流行。后來該書再版。1906年12月,由蜀魂重譯、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社會主義研究社再版,書末附有社會主義叢書出版預告,其中列有《共產黨宣言》德國馬爾克、嫣及爾合著、中國蜀魂譯。(但是并未見到《宣言》此譯本出版)1907年3月,創生重譯、東京奎文館書局出版。后期還有兩個譯本:一個是高勞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11月出版,一個是馬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出版,由此可見此書的影響。一書,著者在自序中注明本書的參考書目中包含馬、恩的《宣言》一書,譯介了《宣言》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話,并概述了《宣言》的思想。1905年11月,蟄伸(朱執信)在《民報》第2號上發表了據幸德秋水和堺利彥的日譯本摘譯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介紹了《宣言》的寫作背景和歷史意義,并節譯了《宣言》中包括第二節十條綱領在內的部分內容及最后兩段,這是《宣言》第一次以直接的方式引介給國人。1906年9月,淵實(廖仲愷)在《民報》第7號發表了《社會主義史大綱》一文,也翻譯了《宣言》的最后一段。1907年9月,申叔(劉師培)在《天義報》第6卷發表了《歐洲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異同考》一文,對社會主義進行時期劃分時提到《宣言》一書。1908年初,《天義報》第15卷刊登了由因格爾斯著、民鳴翻譯的《宣言》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該文譯自堺利彥翻譯的日譯本,也是《宣言》序言的第一個全譯文。全文以文言形式譯出,對于專有名詞保留了其英文名稱或采用了音譯,文后附有《天義報》記者的跋,強調了《宣言》的階級斗爭學說及《宣言》是研究社會主義歷史的入門書。1908年2月,革命派的井易幕以陜西留日學生中的同盟會會員為核心,在東京創辦了《夏生》雜志,該刊曾三期連載《二十世紀之新思潮》一文,對《宣言》的主要內容也作了較系統的介紹。1912年,中國社會黨的紹興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署名為蟄伸(朱執信)譯述、煮塵(王緇塵)重治作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之學說》一文,對《宣言》中的階級斗爭學說及十條綱領進行了重點介紹。1912年9~10月廣州的《民生日報》分7次斷續刊登了署名為“陳振飛譯”的《紳士與平民階級之爭斗》,這篇譯文是《宣言》第一節的全部內容,該譯文用文白夾雜的語體寫成。至此,《宣言》引起了知識分子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其翻譯和傳播在與無政府主義的較量中形成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在反復的選擇和重譯中從眾多思想中逐漸脫穎而出。
這一階段《宣言》的翻譯主體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譯文也是間接譯自他人作品而非來自《宣言》原著,但是翻譯源頭主要是日本的社會主義著作,不但譯介數量大增而且翻譯反應速度很快。與之前傳教士把《宣言》籠統作為新思想新知識不同,資產階級對于《宣言》思想的翻譯和選擇具有更為明確的目的,即以《宣言》作為行動口號倡導改良運動和民主革命,根據翻譯主體的需要進行內容選擇和意義建構,將《宣言》納入了譯者自有的思想范疇,從而推進翻譯主體思想訴求的傳播。《宣言》的思想對當時各派力量都有影響。此時譯介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宣言》的成書背景、英文版序言中的階級斗爭觀點、十條綱領及相關內容,尤其是《宣言》的最后兩段更是被反復重譯,廣為傳播。對《宣言》成書背景及意義的介紹有利于國人了解并認可其思想的現實意義,而對英文版序言的摘譯直至后來的全譯,則是快速有效把握《宣言》要旨的實用之舉。其中階級斗爭觀點的引介在于影射中國社會亟需變革中的階級對立和矛盾,突出變法革新的條件和背景。首先選擇十條綱領并添加大量釋譯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變革的具體手段和措施,也反映了國人對《宣言》的翻譯已經從單純的理論探索進入變革實踐的思考。而《宣言》最后兩段是表明立場、號召性的宣告,具有極強的行動性,對其反復重譯是為了召喚國人奮起行動。針對如上考慮,翻譯主體采取了選擇性的節譯和釋譯手段,并附以案(按)語加以說明,而且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辦的大量報刊雜志也為《宣言》的翻譯和傳播提供了更廣泛的媒介和載體。盡管此時譯者對《宣言》的觀點并不完全接受甚至反對,理解也存在偏差,但正是在這種選擇與反復闡釋中擴大了《宣言》的傳播范圍、提升了社會關注度。這一時期的反復性、爭議性譯述,為后來《宣言》的全文翻譯及廣泛接受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是《宣言》在中國翻譯傳播中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
2.3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翻譯評介(1917年十月革命至1920年《宣言》第一個全譯本出現)
20世紀初期的社會主義傳播經歷了一段高潮后出現了暫時的平息,對社會主義的討論轉為激辯后的沉思,《宣言》的翻譯也隨之暫時沉默下來,到1919年前,再沒有針對《宣言》的專門介紹和討論。正是在這觀望與猶豫的歷史時期,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馬克思主義理論重回國人的視野并得到前所未有的信賴和重視。同時,國內的新文化運動也亟需注入新鮮的文化血液來重喚民族動力。正是在這種外有榜樣、內有需要的社會文化語境下,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積極主動介紹馬克思相關理論并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由此,《宣言》的翻譯與傳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15年,陳獨秀等人發起了以《新青年》雜志為陣地,抨擊封建主義陳腐觀念、倡導棄舊求新的新文化運動,其對“民主”、“科學”的訴求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和接受創造了契機。1919年4月,《晨報》副刊刊登了淵泉(陳溥賢)所寫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在文尾簡單介紹并評價了《宣言》。《每周評論》刊登了署名為“舍”(成舍我)摘譯的《共產黨的宣言》一文,譯介了《宣言》的十條綱領及其前后的幾段話,突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學說。5月,《晨報》副刊登載了河上肇著、淵泉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摘譯了《宣言》第一節“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大意和最后兩段,并專門探討了馬克思的歷史觀。同時《新青年》第6卷第5號刊登了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一文,文中介紹了馬克思生平及《宣言》的成書及傳播情況,并編譯了《宣言》的最后兩段。顧兆熊的《馬克思學說》在討論“唯物的歷史觀”時譯介了《宣言》英文版序言中的話,強調了“出產”(production,日人譯作“生產”)為社會基礎的經濟觀,而唯物歷史觀的應用便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并且還提到了“價值論”催生了有財產與無財產階級的對立,進而出現階級競爭論與革命論。凌霜的《馬克思學說的批評》評介了馬克思的“經濟論、唯物史觀、政策論”三個要點,指出政策論詳見“他和Engels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書》”,并選擇性節譯了十條綱領中的第一、六、七、八條。《新青年》第6卷5、6號連續刊發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①李大釗的這篇文章基本上是轉述河上肇《社會問題研究》連載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一文的有關內容。文中標明譯語源自河上肇博士,節譯部分是為了作為探討唯物史觀的研究資料。一文,文中在討論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節譯了《宣言》第一節的部分內容,所引部分與淵泉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內容大體相同,著重分析了“階級競爭學說”及第一節探討有產者發展史所揭示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11月,北大經濟系學生李澤彰根據英文版譯出了《宣言》全文,題為《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在《國民》雜志第2卷第1號上發表了第一章②后為胡適勸阻,李撤回譯文,沒有再刊登,李的全譯本也未見到。。11月11日至12月4日,《廣東中華新報》刊登了匏安(楊匏安)的《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社會主義》一文③參見林代昭、潘國華編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傳入到傳播》(下冊),1983:68 -70.,文中把《宣言》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開始和系統組成部分,認為其包含了社會主義運動論,即政策論,并把《宣言》作為馬克思經濟學說的一部分。12月1日,《晨報》副刊刊登了紹虞(郭紹虞)翻譯的《馬克思(Karl Marx)年表》,列有《共產黨宣言書》。1920年3月,在李大釗倡導下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研究會成立了專門的翻譯室,下設英文、德文、法文三個翻譯組,而且當時已有從德文翻譯的《宣言》油印本,可見《宣言》的翻譯已從轉譯開始過渡到直接從源文本翻譯④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1983:252.。雖然這些《宣言》譯本沒有流傳下來,但其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研究會從最初的十幾個人增加到后來的幾百人,而且這些會員還深入到革命運動中實踐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宣言》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陳望道翻譯的《宣言》全譯本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由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社正式出版,這是《宣言》第一個公開發表的中文全譯本。陳望道翻譯的《宣言》是應上海《星期評論》社(后該社停刊)的約稿,參照英文和日文的《宣言》版本“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譯了出來”⑤參見陳望道《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復旦學報》1980年第3期。。該書出版后即贈售一空,此后不斷再版,到1926年已印行了17版。全文用白話文譯出,以意譯為主,文中保留了一些專有名詞的英文并添加了一些相關釋意(如第一章對有產者和無產者的解釋)。如果說,之前片段、零碎的譯介和反復重釋奠定了《宣言》全譯本出現的社會基礎,那么《宣言》全譯本所引發的社會影響及后續研究才是其意義所在。它不但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資料,也深深影響了一批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宣言》該譯本的出版正值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前,對最早的一批黨員及黨的創建過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全譯本的出現,標志著《宣言》一書被正式引介到中國,也由此拉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翻譯傳播直至立足的序幕。
這一時期,以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宣言》翻譯已經從爭議辯駁過渡到認可接受,并轉為主觀渴求和主動攝取。翻譯源頭仍以日本為主,且日文社會主義著作的觀點對國人影響很大,但是也開始出現從英、德、俄語源頭翻譯和研究《宣言》,漸顯從轉譯到直接翻譯的趨勢。翻譯內容不只局限于首尾的段落和十條綱領,開始出現章節翻譯和全譯本(盡管有些譯本沒有發表),但階級斗爭學說和十條綱領仍然是譯介的重點,可見變革的手段和措施仍是國人最為關注的,這也似乎表明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實用性”而非“理論性”更感興趣(Li,1971:110)。此時最大的特點是《宣言》的翻譯不再是孤立的引介,而是將其納入了馬克思學說體系中加以評析,融入到科學社會主義、唯物歷史觀和經濟論的整個體系中,而且《宣言》翻譯與譯者評述相結合,回應了當時日益突出的民族矛盾,使其成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武器。《宣言》的翻譯與新文化運動重合,激起了思想傳播的熱議,使其成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同時新文化運動也推動了《宣言》的翻譯和傳播。受新文化運動影響,這一時期《宣言》的譯文不再是文言形式,已經使用白話文,而《宣言》中的譯詞也同時豐富了新時期的詞語用法。此時先進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創立的報刊雜志(包括期刊、副刊、專欄和專號等形式),成為《宣言》翻譯和傳播的主要載體,而且譯者主要是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學者文人,對《宣言》的翻譯和認同,使他們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而又促進了《宣言》更全面、深入的傳播。譯者與思想文化傳播者的雙重身份,使他們在翻譯選擇和思想建構方面更具有主動性和操控性,真正體現了翻譯本身就是在傳播和建構思想文化。這一階段的翻譯主體在當時社會變革中的地位和角色,及至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他們的骨干作用,都對《宣言》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的最終接受起到了決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講,譯者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決定了其所承載的思想文化傳播的成敗。
3.譯名與譯法
從節譯、摘譯到譯評結合,從單句、章節到全譯本的出現,見證了《宣言》通過翻譯在中國歷史語境下逐步建構和再生的過程。《宣言》早期翻譯中譯名的確定和對所選內容的譯法,不但體現了翻譯主體(以及其所彰顯的社會歷史語境)對《宣言》思想的定位和態度,更決定了《宣言》思想體系在中國語境下建構、平衡和融合的過程。
3.1 譯名確立
翻譯中概念譯名的確定最為關鍵,嚴復在翻譯中曾經歷“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梁啟超也曾說過:“翻譯之事,遣詞既不易,定名尤最難。”①轉引自王克非《論嚴復〈天演論〉的翻譯》一文(1992:8)。《宣言》早期翻譯中的概念譯名體現了《宣言》思想與當時中國主流思想文化的交流與調和。
如Communist一詞,最初音譯為“康密尼人/黨”,這在思想概念翻譯初期是很常見的(如新文化運動中的“德莫克拉西”、“賽因斯”之稱)。歷史上異質文化間的交流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②在引進新知識、新思想初期,譯者的目的首先是擴充和提高自身知識體系,這與后來的大規模知識傳播存在一定差別,因而主要采取的翻譯策略之一就是音譯(transliteration)。如:12世紀西班牙把大量阿拉伯作品譯入拉丁語以把異域知識納入拉丁語體系,13世紀則把阿拉伯語作品大量譯入西班牙語以普及知識并融入西班牙文化之中,這兩種翻譯考慮及其策略就是不同的(參見Delisle& Woodsworth,1995:119)。,這是目的語語境下缺乏對應概念的權宜之計。根據德國學者李博(2003:133-139)的考證,“共產主義/共產黨”的譯名則源于日本,1881年即已出現“共產黨”、“共產說”的譯名,根據在概念后添加“原則/主義”的標準,“共產主義”在1893年開始使用。漢語中公開出現“共產主義”一詞始于1903年,同年馬君武在《譯書匯編》上也列出了《宣言》一書,而“共產”之名進入中國之初是與“均產、大同”思想同義的。同樣,socialism的翻譯也是先有音譯,后出現意譯加評注的方式,譯為“大同”、“平會”、“均富”、“養民策”之名,也是從目的語思想文化中尋找相近或相似的概念進行替換,以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在思想翻譯中,譯者所采取的這種“語義借用”(semantic borrowing)策略是異質文化進入目的語文化尋求認同與接受常見的途徑,借用“已有概念”之名同時又賦予其新的內涵③譯者在自身語言文化范疇中難以找到表達源文本中異質文化的對等詞語時,要么通過引入新詞并加以解釋來補充、擴展目的語語言文化體系,要么在目的語文化體系中尋找類似詞匯來表達異質文化。英國16至17世紀伊莉莎白一世時期對后一策略的青睞也使得這一時期呈現了源文本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現象。(參見Delisle& Woodsworth,1995:203),以概念內涵轉化(transformation)的方式建構了新的概念,待這種譯名所代表的新思想已廣為接受,再借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這些外來譯名,就只是名稱的替換了。譯名替換所實現的概念構建正體現了思想傳播中借由翻譯選擇和手段使外來思想與目的語已有的概念融合、再生的過程。思想翻譯中概念的歸化策略從源語角度看,似乎是源于譯者的認識差異,而從譯入語角度反觀其過程,這正是譯者對外來思想概念的一種操控,是把異質的邊緣文化向傳統的中心文化體系引介中的翻譯立場和策略的見證,體現了思想交流與碰撞中通過翻譯實現的操控和調和。
Class struggle的譯名經歷了“階級競爭”、“階級戰爭”、“階級爭斗”、“階級斗爭”的變遷。以“競爭”譯struggles一詞是受到當時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人類社會的矛盾斗爭歸為自然界的物種競爭,同時也反映了當時譯者所代表的意識主流:新興的資產階級寄社會進步的希望于變革和溫和的競爭,沒有意識到也并不贊同階級間的斗爭。“階級戰爭”的譯名已經把對立階級的矛盾上升到了宣戰的程度。“階級爭斗”強調階級間對立的狀態,把階級對立的矛盾簡單化、普遍化。“階級斗爭”不但指出了階級對立的矛盾不可調和,也意味著階級矛盾的解決方式就是“斗爭”。第一個日譯本的譯文是“階級鬪爭”(文中也出現了“階級的爭斗”),陳望道譯為“階級爭斗”,之前譯名使用比較混亂,尤其對“爭斗”與“斗爭”似不加區分。這兩個詞在古漢語中已經存在,意義與今天不同,“爭斗”一詞強調矛盾的普遍性,包含“斗爭”的含義,而“斗爭”一詞則語義更為激烈,表示矛盾對立的尖銳性。日本社會主義文獻中最先使用“斗爭”一詞的是幸德秋水(1903)的《社會主義神髓》,宋教仁(1906)在《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一文中提到:“階級斗爭之幕既開矣”,第一次提出“階級斗爭”之名。以上可見,國人并未直接借用日譯“斗爭”的說法,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闡釋經歷了一系列的選擇和闡釋,從“競爭、戰爭、爭斗、斗爭”的更替也見證了此概念內涵的意義建構過程。
譯名確立有其從初識到熟悉的認知過程,譯名經過各種嘗試性反復闡釋,逐漸確定廣為接受的譯名,也標志著譯名所承載的思想逐步被認可接受的過程。“名”與“實”的建構,從有名無實的音譯到名不副實的轉譯和借譯,再到名副其實的概念譯名的確立,是《宣言》思想經由翻譯進入中國獲得重生的過程。思想翻譯中在目的語語境下對概念的意義重構,正是翻譯鏈接時間、空間實現思想交流和交融的過程,譯者則借翻譯途徑“必須要為自己的文化引進一種概念系統”④參見許國璋《關于索緒爾的兩本書》,《國外語言學》,1983年第1期,轉引自王克非(1992)。。
3.2 譯法調整
《宣言》早期的翻譯選擇受到源文本的限制和譯者主觀取舍的影響,不但內容的順序與《宣言》原文不一致,而且譯文也并不完全忠實于原文,譯者通過改譯、編譯、增減譯、添加按語等手段,按照自己的意圖選擇性譯介了《宣言》的內容。譯者的翻譯策略導引了中國語境下《宣言》思想體系的建構,也決定了《宣言》從進入中國之初就開始中國化進程。下面通過比照原文,對有代表性的幾段譯文進行分析,探討其譯法及翻譯效果。
3.2.1 編譯
以傳教士譯介的最早的《宣言》片段為例,先來比較Kidd原文第一章The Outlook與《大同書》第一章《今世景象》中關于《宣言》的片段:
【原文】□This has been already not only anticipated but described for us by Karl Marx.□We are told that,on the other side,we must also expect to see the smaller capitalists continue extinguished by the larger,until,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the hands of a few colossal capitalists,society at length will feel the anarchy of production intolerable,//and the end of a natural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must come with the seizing of political control by the proletariat,and turning by them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to state property.//After which,we must look forward,we are told,to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distinctions and class antagonisms,the extinction of an exploiting class within the community,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individual struggle for existence. (1894:12)
【譯文】馬克思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
通過比照,可見譯文與原文出入較大。原文表達了三層意思:《宣言》第一章中“小資產階級逐步被吞并,財富集聚到少數大資本家手中,社會面臨生產過度的恐慌”的狀況;第二章中“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中”和“消除階級差別和階級對抗,消滅剝削階級,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的斷言。譯者用“糾股辦事之人”指代“資產階級”,選擇了“其通過世界市場實現資本積累”的內容,但是舍棄了“財幣進入誰手”和“社會無法承受生產過度的后果”的信息,可見譯者認為它們無關緊要,至少與中國社會關系不大。而且譯者添加了“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的個人觀點,用“譯述結合”的方式加以提醒。同時,在說明“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前添加了“富家權盡之時”這一結果,這是譯者主觀的判斷,可見譯者在翻譯中并不是單純轉述原文,而是融入了主觀的評判。譯者選擇了“富家”和“窮黎”來代表兩個對立的階級,緣于當時歷史語境下中國資產階級尚未發展而中國社會尚無對應的階級區分,因此用中國自有的概念譯名便于讀者對新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另外,原文中“a natural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意味著“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主動性和必然性,譯者卻通過“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的譯文替之以“無奈而為之”的被動性和含蓄性,顛覆了原文的態度。而最后一層意思,譯者根本沒有選擇,說明其不符合譯者的思想主張。
總之,譯者根據自身需要放棄、添加并調整了原文中為之所用的內容,以編譯的形式為國人譯介了最早的《宣言》思想。譯者的選擇和譯法受到譯者自身意識形態及當時社會語境的限定,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對《宣言》的態度、需求和興趣所在。經過增刪手段編譯后的譯文符合國人的認知心理,以“安民救世”為目的的溫和的改良變革也順應了當時歷史過渡期的社會訴求,譯法調整所做的思想調和是思想傳播初期有效的傳播手段。
3.2.2 釋譯
《宣言》中的十條綱領是翻譯較多的內容,且譯者對個別條目都不同程度添加了解釋的內容,下面對其不同時期的譯法加以分析:
【原文】
(1)Abolition of property in land and application of all rents of land to public purposes.
(2)A heavy progressive or graduated income tax.
(3)Abolition of all right of inheritance.
(4)Confiscation of the property of all emigrants and rebels.
(5)Centralization of credit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by means of a national bank with State capital and an exclusive monopoly.
(6)Centra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7)Extension of factories and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owned by the State;the bringing into cultivation of wastelands,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il gen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a common plan.
(8)Equal liability of all to labour.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armies,especially for agriculture.
(9)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by a more equ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country.
(10)Free education for all children in public schools.Abolition of children”s factory labour in its present form.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industrial production,& c.,& c.
譯法一:1905年11月,蟄伸(朱執信)根據幸德秋水和堺利彥的日譯本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中翻譯了《宣言》的十條綱領。該譯文對部分新概念添加了長篇的解釋說明(如第二條的“累進稅”)及補充評述(如第三條的“相續者”),而日譯文是沒有的,可見譯者為了便于國人理解并使其更貼合中國語境而做了補充性釋譯。另外,譯者對綱領中的部分詞句也重新闡釋賦予了其新意,如:第二條中的“heavy”一詞,就被譯為“極端”,提升了此措施實施的嚴厲程度,而且把原文的名詞結構翻譯成“課極端之累進稅”的動詞結構,強化了其行動性。第七條“增加國民工場中生產器械”本是擴大國有資產規模的意思,但譯者卻添加了“為公眾而做”的目的,在補充了此釋義的同時舍棄了改良土地的原則,即“in accordance with a common plan”。第八條“equal liability”之前添加了“強制”一詞,強調“平等勞動”的必要性。第九條只強調“漸泯邑野之別”,卻舍棄了“by a more equ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country(通過平均分配全國人口)”的手段,或是因為這不符合國內實情,或是因為這微不足道,譯者根據社會語境做出了取舍。文尾有“蜇伸子曰”的譯者評述,是結合現實而闡發的個人觀點和評論,也是譯文的補充性解釋和分析。譯者所添加的釋譯都是日譯本沒有的,可見譯者不顧與原文的對應,根據中國的社會語境需求補充了必要的說明,把譯文和解釋評析并置,是一種典型的釋譯。
譯法二:1912年,蟄伸(朱執信)譯述、煮塵(王緇塵)重治作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之學說》一文對十條綱領進行了重點介紹,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中十條綱領的譯介基礎上添加了大量的補充性解釋。譯文以“甲-癸”的順序翻譯了十條綱領,并在每條后面添加了案語(戊、巳、庚三條的案語合并在一起),進行深入解釋和評析,闡發自己的觀點。通過補充性的釋譯,譯者一方面是為了讓這些措施更好地結合本國現實具有解釋力,另一方面,譯者也基于自己的意識主張操控了這些措施在中國語境下的意義建構,從原文分析可見,譯者認為綱領的實施就是為了“均貧富”,所以添加的信息有意建立起這樣的概念,譯者通過“釋”、“譯”結合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圖譯介了變革措施。
譯法三:1919年4月《每周評論》刊登的“舍”(成舍我)摘譯的《共產黨的宣言》一文,也譯介了《宣言》的十條綱領。與之前相比,此譯文沒有添加的大段補充性信息,但是個別語句有所調整。第二條添加了“第一條若不能積極進行”這句話,使此措施成為之前的補充;第三條本為“廢除繼承權”,但是此處卻轉譯為:“遺產歸公”,強調財物的最終歸屬在公眾,此處譯者明確指出廢除封建繼承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財產公有制;第五條和第六條的“centralization”分別譯作“壟斷”和“實行中央集權”,體現了變革生產方式的目標;第九條的譯文“對于全國國民,用同等的平均分配”與原文“by a more equ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country”有較大差異,語義模糊,沒有表達出這一措施的實施方式,存在理解有誤;第十條的“free education(免費教育)”被譯作“自由教育制度”,與原文有較大出入,但是在當時倡導“民主、自由”的背景下,這一譯法也體現了社會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和引導。總之,此節譯文的最大特點就是語言上采用了白話文,迎合了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較大。對十條綱領的重譯,是為未來革命斗爭提供可參考的行動措施,以行動上的準備再次喚起人們對《宣言》的信賴和思考。
總之,針對十條綱領這樣具有行動性的措施來說,為了使其在中國語境下具有解釋力和執行力,譯者采用了釋譯的手段,通過添加解釋性和補充性的長篇評析來建構其現實意義。釋譯的方式有針對新概念做說明,也有針對措施做評析,目的都是為了建構十條綱領的可行性。而且,對于同一措施的不同闡釋,既受限于譯者的理解和主張,也體現了不同階段社會文化語境的訴求。雖然十條綱領轉譯自日譯文,但是通過比對發現,譯者并不是簡單地采用“拿來主義”忠實傳達文字,而是結合目的語語境對每一條措施都重新解釋,通過添加釋譯或調整意義闡發了自己的主張。
3.2.3 改譯
不同譯者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宣言》的態度和理解也會有所差異,由此產生的有意或是無意的改譯也是不可避免的。改譯的涵蓋范圍很廣,對原文語句的增、減、調、換等譯法都屬于改譯。下面來看《宣言》的最后兩段,這是被譯介最多的內容,對早期多個譯文的對比,可以看出不同譯者如何對《宣言》進行改譯,并進而透視其翻譯效力。
【原文】The Communists disdain to conceal their views and aims.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 revolution.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譯文1】同盟者望無隱蔽其意見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貫徹吾人之目的,惟向現社會之組織,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階級,因此共產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勞動者,于脫其束縛之外,不敢別有他望,不過結合全世界之勞動者,而成一新社會耳。”
(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1903)
這是《宣言》最早的一段節譯。此時“Communist”的含義對于國人還是比較陌生的,用“同盟者”來代替它是為了更好“達意”,即只選取了其中“同心結盟的團體”這一含義,便于讀者理解。把“proletarians”譯為“吾人之勞動者”,這種語義替換也是基于同樣的考慮。譯文把“They”的視角轉換為“吾人”的立場,體現了譯者的自我定位和對《宣言》思想的認同。原文“the forcible overthrow”語氣堅定而手段強硬,但是譯文則改之以“一大改革”且“forcible”一詞則略去不翻,抹煞了革命的徹底性和原文的堅定語氣,此處以范圍代替程度、以“改革”代替“徹底推翻”,這些都有悖于原文的本意。這種轉換,一方面是譯者主觀不贊同或有意回避激烈的斗爭,因而選擇較為溫和的詞句;另一方面也與當時特有的文言表達形式有關,自古以來文人在表達激動、憤怒之意時也要講究內斂,多以隱晦、婉轉的措辭代替直接、尖銳的矛盾。原文的“chains”意譯為“束縛”,擴大了其語義覆蓋范圍。譯文結尾添加了“不敢別有他望”一句,把原文的果敢替換成謙卑,譯者根據邏輯推理在“world”一詞前添加了“新”字,也體現了譯者對變革求新的期待。最后一句在《宣言》原文中以大寫呈現,起到了口號的召喚作用,而在譯文中則被刪改為普通的話語,全無醒目的號召力。這樣,《宣言》原文第一次出現在國人面前就失去了其戰斗的號召力,而代以溫和的勸誡,譯者的翻譯策略決定了《宣言》的行動力度。
【譯文2】凡共產主義學者,知隱其目的與意思之爭,為不衷而可恥。公言其去社會上一切不平組織而更新之之行為,則其目的,自不久達。于是壓制吾輩、輕侮吾輩之眾,將于吾儕之勇進焉詟伏,于是世界為平民的,而樂愷之聲乃將達于淵泉。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
[蟄伸(朱執信),《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1905]
此處將“Communists”譯成“共產主義學者”,體現了譯者在建構這一概念時自身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選擇,在當時社會積極要求變革上進的人都是文人志士,因此譯者把致力于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也列為“學者”。原文“distain”譯為“為不衷而可恥”,以“羞恥心”代替“公開表明立場”使譯文具有勸誡的意味。“forcible overthrow”被譯作“去……而更新之之行為”,強調了“更新”的目的,但是刪除了堅定的行為措施,表明了譯者的態度和立場。“ruling”也只被稱作“壓制、輕侮”,明顯帶有文人的懦弱和卑微的自尊(值得關注的是日譯本的譯文也省去了“forcible”一詞,僅保留了“顛覆”之意,所以譯者的二次選擇也受到源文本的限制)。譯文放棄了“Communistic revolution”的翻譯,再次暗示譯者并不贊同革命的手段。譯者還采用了反向表達的隱喻,以“樂愷之聲乃將達于淵泉”替換了原文中“lose chains”的寓意,并添加了對未來前景的展望之意。對最后一句呼語,譯者添加了感嘆詞和設問的方式以期達到原文的效果,但是“UNITE”一詞似乎并不是一個“奮”字可以囊括全部的,在強調“行動起來”的同時卻缺失了“UNITE(團結起來)”的方式。
【譯文3】“吾人之目的,一依顛復現時一切之社會組織而達者,須使權力階級戰慄恐懼于共產的革命之前。蓋平民所決者,惟鐵鎖耳,而所得者,則全世界也。”又曰:“萬國勞動者,其團結!”
(勥齋(宋教仁),《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1906)
此段譯文比較貼切地轉述出原文的號召性和表達力度,使階級對立的矛盾凸顯出來。原文的“ruling classes”譯作“權力階級”,與平民相對,使原文基于經濟地位的階級對立關系轉為譯文中政治上的對立,這是對宣言內容的創造性建構,同時也是《宣言》在新語境中的意義重生。譯者放棄了“共產黨人公開表明立場”的內容,并添加“又曰”二字單獨引出最后的號召話語,強調了《宣言》結尾的行動性。
【譯文4】主此同盟者為麥喀氏,其宣言書之結尾絕叫曰:“萬國之勞動者團結!”
(淵實(廖仲愷),《社會主義史大綱》,1906)
僅此最后一句的翻譯可見此號召性口號在當時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宣言》最后一句話的翻譯經考證多達74種①參見高放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74種中譯文考證評析》一文,《文史哲》,2008(2):5-12。,這種重復節譯的方式體現了譯者以此感召國人行動起來的決心和規劃。譯者在此譯文之前添加了“絕叫曰”這樣的評述,譯述結合的策略加強了這句話的決心和行動動力。夢蝶生(葉夏生)發表的《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也引述了《宣言》最后一句話“萬國勞動者其團結乎!其團結乎!”,此處譯者有意添加同義反復來加強號召的力度。原文全部用大寫體書寫,漢語的語言形式很難表達出其強調的力度和隱含的決心,因此譯者多通過添加述評和修辭方法以求相同的表達效果。
【譯文5】其書大旨以為(欲實徹平生之主義,非根本上廢除現行之社會制度,出以嚴厲之手段不可。在共產派實行革命之先,非使掌權勢之人震動不可。自最可憐之平民觀之,除斷去頸上之鐵鏈而外。一無所失。以言所得,幾同得一新生之世界。最后鼓勵各地之平民,速起聯絡)。
(劉秉麟,《馬克思傳略》,1919)
譯文采用轉換的方式傳達了原文大意。以“主義”泛指“The Communists”的主張,以“嚴厲之手段”替換了原文“forcible overthrow”中的具體做法“推翻”。譯者舍棄或替換的內容,或是譯者認為不相關、不熟悉的內容,或是譯者并不認同的內容。譯者將“proletarians”譯為“平民”并在前添加了“最可憐”的修飾語,可見譯者對其的同情態度。原文中的“chains”在譯文中保留其隱喻的意象,并將之轉換為具體的“頸上之鐵鏈”,突出了平民現實處境的惡劣。譯者還添加了“新生”一詞來修飾即將得到的“世界”,也體現了當時變革求新的主流思想。因為該譯文是轉述《宣言》大意,所以采用了間接引語的表達。最后一句的譯文在形式上由直接的祈使句變為轉述的陳述句,表達效果由激情號召變為客觀描述。把“UNITE”一詞譯為“速起聯絡”,淡化了原詞“團結行動”的核心內涵,而代之以具體的行動方式即“聯絡”。譯者對原文的詞句進行了多處改譯,或以泛指替代具體,或以具體替代抽象,或以相關語義替代核心思想,通過翻譯調整再現了《宣言》主張,并建構起其在當時歷史語境下的文本形象和行動效力。
總之,《宣言》的早期翻譯中不同時期的譯者,根據自身需要和社會歷史語境的訴求采用了不同的翻譯策略,通過節譯、轉譯、編譯、釋譯、改譯、重譯等手段,選取了為己所用的內容并建構起彰顯其思想主張的《宣言》譯文。譯名與譯法的選擇受控于譯者的認知水平和社會歷史語境,反之也為探究以翻譯為載體的思想傳播特點和路徑提供了線索。盡管《宣言》早期翻譯的源頭都不是原文,譯名和譯法不可避免受到源譯本的影響,但是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發現,譯者并未完全拘泥于源譯本的譯法,而是通過譯述結合等譯法調整建構了《宣言》在中國自有的傳播模式和意義體系。《宣言》的譯名和譯法也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早期翻譯的特點和規律,并為探尋思想翻譯的規律提供了例證。
4.結語
《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是以翻譯為媒介進行的。傳播是翻譯的目的,翻譯過程本身也是傳播,因此譯文承載了《宣言》思想翻譯與傳播的歷史特點和規律。從節譯和釋譯開始,從介紹性的評述到完整的全譯,從無意的零碎譯介過渡到有目的的自主攝取,《宣言》在經歷了選擇、比較、博弈、沉寂、推進、重構這一系列過程后,終于被國人逐步接受并建構起中國語境下的理論體系。從翻譯主體看,傳教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相繼對《宣言》進行了譯介。從翻譯內容看,《宣言》思想并不是按照原文順序依次進入中國,早期零碎翻譯的內容集中在個別概念和《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內容、其英文版序言和第二章中十條綱領相關內容、《宣言》結尾部分,形成了社會主義學說、階級斗爭和系統唯物史觀的新順序。從翻譯策略看,先有“述”后有“譯”再到“譯述結合”,譯者通過多種翻譯手段調整思想概念和意義的建構。從翻譯動機看,傳教士把《宣言》作為新思想依托于進化論而引入中國,服務于知識傳教的目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基于各自的立場譯介了《宣言》中為己所用的思想,通過認同或是批判的方式釋譯了《宣言》的內容,宣揚變革求新的主張;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信奉《宣言》的思想并把其作為行動指南,譯介《宣言》就是為了實踐其革命思想。總之,《宣言》的早期翻譯彰顯了翻譯主體在思想傳播中的主觀操控力。
思想翻譯傳播早期,譯文的準確性和文本的完全性并不是最重要的,譯者的主體選擇和譯法以及由此在目的語語境中建構起來的新思想最為關鍵。思想的翻譯和傳播不是文本間的簡單轉換,也非始于按步驟、系統性地全面翻譯,而是成形于有選擇的片段性、適應性意義建構。在思想翻譯中,表面上看是為概念在目的語中尋求能指,而實質是在目的語語境下重構其所指的意義范疇,《宣言》在中國的早期翻譯正是在這種看似西化的翻譯過程中實現了化西的思想建構。
[1]Bassnett,S.& A.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Preface)[M].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1990.
[2]Bassnett,S.& A.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Bernal,M.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M].Ithaca&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4]Delisle,J.& J.Woodsworth.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UNESCO Publishing,1995.
[5]Dirlik,A.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Early Chinese Marxist Thought[J].The China Quarterly,1974(58):286-309.
[6]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Secon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
[7]Hatim,B.& I.Mason.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8]Katan,D.Translating Cultures: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M].Manchester:St.Jerome,1999.
[9]Kidd,B.Social Evolution[M].New York:Macmillan and Co.,1894.
[10]Li Yu-ning.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11]Meisner,M.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2]Pym,A.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13]Schwartz,B.Marx and Lenin in China[J].Far Eastern Survey,1949(7):174 -178.
[14]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Philadelphia:J.Benjamins,1995.
[15]Tsien,Tsuen-hsuin.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J].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4(3):305-327.
[16]Venuti,L.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17]Venuti,L.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London:Routledge,2000.
[18]陳力衛.讓語言更革命——《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版本與譯詞的尖銳化[M]//.孫江.新史學(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8.
[19]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修訂本)[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20]費小平.翻譯的政治——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21]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
[22]黃開源,等.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3]姜義華.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24]賴欽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百年[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25]李博.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M].趙倩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6]李大釗.李大釗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7]李澤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28]林代照,潘國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
[29]林霞.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的選擇性傳播[J].學術論壇,2010(10):6-9.
[30]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M].宋偉杰,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
[31]羅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的譯介[J].求索,2006(1):56-59.
[32]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33]歐陽哲生,郝斌.“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34]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M].袁廣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5]譚汝謙.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36]王秉欽.文化翻譯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37]王克非.論嚴復《天演論》的翻譯[J].中國翻譯,1992(3):6-10.
[38]王克非.中日近代對西方哲學思想的攝取:嚴復與日本啟蒙學者[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39]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40]王栻.嚴復集(第3 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1]高軍.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42]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3]許寶強,袁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44]張立波.翻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J].現代哲學,2007(2):24-32.
[45]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恩室.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6]朱執信.朱執信集(上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