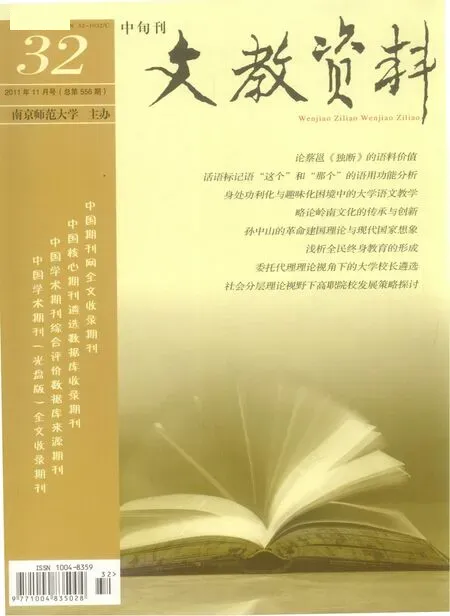略談元朝澎湖巡檢司的建置
王 紅
(新疆大學 人文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卷首云:“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于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的封建王朝──元朝的疆域是空前的,臺灣自然也被囊括其中。
寶島臺灣,在元朝時被稱為“瑠求”,或者“琉求”。《元史瑠求傳》言:“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元朝初期,元帝積極經略海外,曾派兵南征安南(今越南)、占城(今屬于越南境內)和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至于日本,由于當時的鐮倉幕府拒絕向元朝朝貢,元世祖忽必烈大為惱怒,故有兩次出兵日本之舉,而在東征的路程中途徑瑠求和彭湖。根據一般史書及《元史·外夷傳》中有關日本的記載(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可知,元世祖忽必烈遠征日本因風失敗,迂回臺灣,道經彭湖,設治彭湖,以圖進取臺灣,作為征日本之準備。事實上,臺灣對于大元王朝來說,不只是進軍日本的戰略基地,更是完成中國全方位統一的需要,故有兩次招撫臺灣之舉。
根據《元史列傳第九十七·外夷三·瑠求》所載,第一次是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冬十月,元世祖派遣楊祥、吳志斗、阮鑒等一行,“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并給銀符,往使瑠求”,并且攜帶詔書,出使招諭瑠求。其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藩罔不臣屬。惟瑠求邇閩境,未曾歸附。議者請即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來則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鑒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不效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后悔。爾其慎擇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也就是從彭湖出發,“至是日巳時”,望見有“山長而低者”,楊祥派人登岸察看,因“岸上人眾不曉三嶼人語”,被殺死三人,遂無功而返。對于此行,一行人內部出現了分歧,楊祥認為他們到了瑠求,責讓阮鑒、吳志斗出具“已到瑠求”的文字,而二人則不同意。之后因吳志斗不知蹤跡,朝廷下旨,將楊祥、阮鑒發回福建審問,后來二人遇赦,但是第一次探測臺灣之舉就這么不了了之了。如今就事理推斷此行即從彭湖出發,到達海上“山長而低者”的地方,而這里的人不曉語言,應該是番人住的地方,加之彭湖群島住的只有漢民而沒有番人,所以這里就不可能是彭湖群島的某個島嶼,因而極其可能是臺灣西海岸的某個地點。
第二次是在元成宗元貞三年(公元129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上奏:“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于是九月份,高興派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余人”。次年正月,又將所俘虜的人放回,要他們效順朝廷,但是并無下文。
雖然這兩次招撫臺灣的努力沒有結果,但是在與臺灣島相對的彭湖有所建置,設立了巡檢司,這是大陸政府在彭湖建立正式政權機構的開始,也是我國在臺灣附近島嶼設立專門政權機構的開始,標志著臺澎已正式納入中國版圖。那么元朝的彭湖巡檢司具體設置于何時呢?元朝地理學家汪大淵所著的《島夷志略》記載:“至元間,立巡檢司。”而《島夷志略》中有關彭湖的這一條,是現存元朝在彭湖設巡檢司的最早記載。但是問題在于,元代有兩次“至元”年號,一為元世祖的“至元”(公元1264—1294年),一為元順帝的“至元”(公元1335—1340年)。 《島夷志略》所謂的“至元”,又是指哪次“至元”呢?
就元朝在彭湖設立巡檢司的年代問題,就一直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解釋,有的說是在元世祖初期,有的說是在元世祖末年;還有的說是在元順帝末年。明末清初的地理學家和學者顧祖禹在其著作《讀史方輿紀要》中說:“至元末,置巡司于此。”這里的“至元末”同樣沒有說清楚具體年代,讀者既可以理解為“到了元朝末年”,又可以解釋為“至元年間的初期”。正是由于這些記載均未詳舉年份,因此自清代以來,論著甚多,考訂不一。不過在清代所修的臺灣地方志中,大部分指出元代彭湖巡檢司設于元朝末年。如曾在乾隆年間擔任過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的范咸在《重修臺灣府志》說:“元末,置巡司。”(詳見清《乾隆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建置》所載)同是在乾隆年間擔任過臺灣府臺灣縣知縣的魯鼎梅主修的《重修臺灣縣志》也說:“元末置巡檢司于彭湖。”還有謝金鑾的《續修臺灣縣志》:“元之末,于彭湖設巡檢司,以隸同安,中國之建置于是始。”(詳見清嘉慶十二年《臺灣縣志》卷一《建置》所載)均明確指出彭湖巡檢司的設置在元朝末年。另外,在元末順帝年間,汪大淵曾經兩次附搭海船,到南洋一帶游歷數年,在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就其親所見聞,寫成《島夷志略》一書,因此才可能在說到“至元間”時似乎并沒有留意到距離他生活的年代相對久遠的元世祖至元年間的問題,多少有些理所當然的意味。因此若要參照以上所說的,《島夷志略》中所謂的“至元間”,應該是就元順帝的“至元”年間而言,順帝的“至元”自然是元朝末年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朝疆域圖中,臺灣并沒有被明確標進政府的統治區域內,并非意味著臺灣不屬于元朝的版圖,只是由于該圖集的編寫是依照《元史·地理志》所編,而由于《元史地理志》本身存在的斷限問題,其中并未提到澎湖巡檢司,因此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一點更加大了彭湖巡檢司的設置時間是在元朝順帝末年的可能性。
接下來要說到的就是彭湖巡檢司的隸屬問題了。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明確指出巡檢司“地隸泉州晉江縣”(今福建泉州晉江市)。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在彭湖巡檢司的隸屬問題上又產生了模糊。比如前面提到的《讀史方輿記要》卷99《澎湖嶼》記載:“貿易至者歲常數十艘,為泉外府。至元末置巡司于此。”而清嘉慶十二年《臺灣縣志》卷1《建置》卻記載:“元之末,于彭湖設巡檢司以隸同安,中國之建置于是始。”就說到巡檢司是隸屬泉州同安縣(現為廈門市同安區)的。又如《新元史》卷253《外國五·島嶼諸國》記載:“其地屬泉州。晉、泉縣土人煮海為鹽,釀秫為酒,采魚蝦為食。至元初設巡檢司。”還有諸多文獻資料在彭湖置司的時間和隸屬這兩個問題上有不同的記載。那么,元朝的彭湖巡檢司到底是“隸同安”,還是“隸晉江”呢?
在面對不同的歷史文獻對同一事件有不同說法的時候,應該如何判斷取舍呢?雖然有最早記載的文獻未必就一定正確,但是從理論上說由于時間的跨度最小,最早的記載往往擁有相對較高的可信度。從這一點上說,探討元朝時彭湖巡檢司的隸屬問題,應該以對此擁有最早記載的《島夷志略》的說法為依據,那么彭湖巡檢司就應該是隸屬泉州晉江縣的。另外,從歷史沿革的角度來看,隸晉江的可能性更大。宋朝時,彭湖就一直隸屬晉江縣。南宋趙汝適在《諸蕃志》中有這樣的記載:“泉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可見從南宋起,彭湖地區就歸泉州晉江縣管轄了。那么元朝設置的彭湖巡檢司為了方便同樣設于晉江縣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再者,巡檢司設于晉江縣也便于泉州府的管理。元朝時晉江與同安都歸泉州府的管轄,但是泉州府城是設在晉江縣境內的(根據《元史地理志》),從政治意義上說,晉江的地位要高于同安。而且泉州港在元朝時是舉世聞名的大港口,而泉州港的出海口就在晉江,那么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晉江也比同安繁榮。綜合以上幾點,元朝彭湖巡檢司隸晉江的可能性更大。
在了解了彭湖巡檢司的設置淵源、設置時間、隸屬地之后,有必要對巡檢司做簡單的介紹:《元史·百官志》(志第四十一百官七)記載:“下縣,秩從七品,置官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則以簿兼尉。后又別置尉,尉主捕盜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巡檢司,秩九品,巡檢一員。”可見巡檢司是元代官署中品秩最低的一種,主要為州縣所屬的捕盜官。但是彭湖巡檢司作為特殊的存在形態,雖或隸屬于州縣,但依據“從道路便宜,不限境土”的原則,主要適用于沿江沿海及島嶼的巡邏管轄。由于臺灣澎湖地區多產鹽(《島夷志略》中有相關的描述),因此《島夷志略》言:“至元間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別無科差。”可見彭湖巡檢司除了維持臺澎地區的治安之外,還為政府征收鹽稅。
總之,就目前學術界對元朝澎湖巡檢司的研究成果來看,由于自身條件有限,筆者所能查閱到的相關資料很少,特別是日本和臺灣地區關于這方面的學術成果更是沒有找到,是此次資料收集方面的巨大漏洞。而大陸方面,雖然有關于澎湖巡檢司的設置時間和隸屬地區的論文成果,但也是寥寥。所以有關元朝澎湖巡檢司的建置還有很多有待進一步研究補充的地方。
[1]宋濂等.元史[M].中華書局,1976.
[2]汪大淵著,蘇繼庼校釋.島夷志略校釋[M].中華書局,2004.
[3]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中華書局,2005.
[4]范咸.重修臺灣府志[M].中華書局,1985.
[5]蔣毓英.臺灣府志[M].中華書局,1985.
[6]謝金鑾等.臺灣縣志[M].臺灣經世新出版社,1999.
[7]臺灣文獻叢刊[DB].
[8]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M].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
[9]柯劭忞.新元史[M].中華書局,1978.
[10]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M].中華書局,2000.
[11]吳幼熊.元朝澎湖巡檢司隸屬考[J].歷史教學,19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