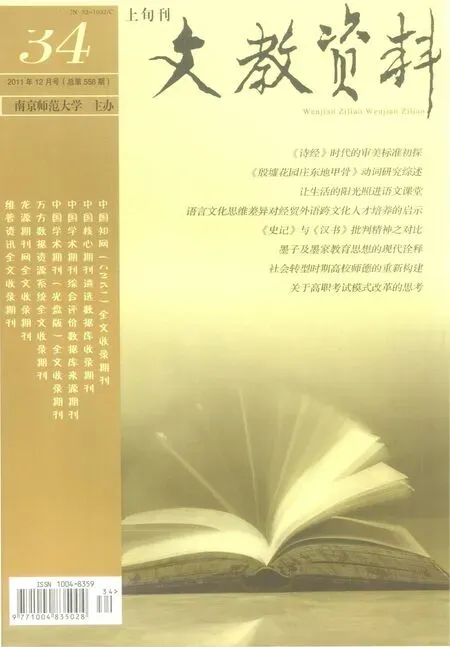閱讀教學中言語敏感性培養的策略
盧 航
(無錫市金星中學,江蘇 無錫 214000)
新的《語文課程標準》多次提到了“語感”一詞,強調“在教學中尤其要重視培養良好的語感”,要求閱讀教學中注意“有豐富的積累,形成良好的語感”。
那么,何為“語感”?葉圣陶曾說:“了解一個字一個詞的意義和情味,單靠翻字典辭典是不夠的。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隨時留意,得到真實的經驗,對于語言文字才會有正確豐富的了解力,換句話說,對于語言文字才會有靈敏的感覺。這種感覺通常叫做‘語感’。”葉圣陶提到的“對于語言文字”的“靈敏的感覺”是一種言語的心理敏銳感,是一種直覺。就語文學習來說,這種直覺無需憑借有關的知識進行理性的思考,在一聽一讀之際就能理解語言文字的含義、情味等。這種敏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反復錘煉和打磨的。因此,如何有效地訓練和培養直覺思維能力,也就是言語的敏感性,是當前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我結合執教體會,認為在閱讀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言語敏感性,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引領學生通過速讀整體把握內容
直覺思維是以反映事物之間聯系的關系表象為思維加工材料,在本質上是對事物之間關系(即內在關系)的整體把握,整體性則是直覺思維最重要的本質特征。新課標指出:“在教學中尤其要重視培養良好的語感和整體把握的能力。”將整體把握與語感培養一起放到突出的位置,這是很有道理的。在閱讀教學中,我們應將課文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要求學生把握文章部分與整體,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聯系,而不是脫離文章整體,就句子論句子,就段落論段落,甚至訓詁式地一個字一個詞地解釋,把語義弄得支離破碎。
教學一篇課文時,我一般不是急著分段分層,而是先從整篇課文出發,要求學生通過一目數行的速讀,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對所讀文字作出判斷、評價。在速讀中,主體感知的不是孤立零碎的單個文字符號,而是由字、詞、句、段所構成的篇章整體及其意義整體。速讀所憑借的,正是把事物當作整體來考查,直接迅速地觸及事物本質的直覺思維,速讀能力的核心就是直覺感悟能力。學生在速讀中,不必逐個破譯每個文字符號代碼,而是利用直覺思維簡化閱讀過程,從而敏銳地整體把握課文內容。訓練時,要求學生注意力集中,不僅迅速感知課文的語言文字,而且敏捷地捕捉重要信息,提取文義,從整體上觀察全文或全段,把握作品的特色及其內在情韻。根據不同的速讀要求,要指導學生運用跳讀、掃讀、猜讀等速讀方法。
例如在教讀《故鄉》時,我要求學生在限定的時間內掃讀課文,迅速理出小說的三要素。在分析人物形象時,我又要求學生在限定的時間內,用跳讀的方式,找出所有有關閏土和楊二嫂的描寫,運用比較閱讀,把人物作前后對比。在平時的課堂閱讀教學中,我常常要求學生迅速捕捉課文中的中心語句,迅速圈點出某一段描寫中的關鍵句、關鍵詞,或者迅速感知課文中最精彩的段落和語句,引導學生意會神攝、快速感知課文多方面的意義或特點。實踐證明,這樣的速讀訓練,對培養學生的言語敏感性,是很有意義的。悟性好的學生甚至在初讀課文后,便能從整體上捕捉到其特色和某種內在情境。
當然,初讀階段,學生對整篇課文的把握可能是混沌的、朦朧的,帶有飄忽性和猜想性,但這種從整體出發的直覺感受活動卻是充滿生氣和活力的,對培養學生言語敏感性是很有價值的。例如教學朱自清的《春》,我讓學生自由地朗讀全篇,并運用已有的生活積累和知識經驗去想象春天的畫面,談談對朱自清筆下春天特點的認識,這樣調動聽覺、視覺等多種感官的協調作用,作者筆下的春天景象喚起了他們的審美直覺,那些春草、春花、春風、春雨等已不再是零碎的詞語單個的形象,而是一幅幅和諧的春景圖,作品中那些優美的語句讓他們獲得了真切生動的感受。
劉守立先生對語文教學整體觀做了這樣的論述:“閱讀心理的發展是一個整體認知的心理活動過程,即瀏覽語言文字,形成整體印象,然后揣摩文章的謀篇布局,造詞用句,最后再回到文章整體上去,獲得發展了的整體印象。”(劉守立,《“大而化之”——閱讀教學觀芻議》)此論述對我們引領學生整體把握感悟課文,培養言語敏感性,是很有啟發的。
二、指導學生在反復誦讀中體悟情感
“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反復誦讀也是培養學生言語敏感性的重要策略之一。新課標在各學段的目標中,都明確提出“誦讀”的要求,要求學生在誦讀中獲得或體悟情感,在誦讀中提高欣賞品位和審美情趣。誦讀不但是調動學生情感,引發體悟作品的重要手段,也是訓練、培養學生言語敏感性的重要途徑。心理學專家指出,聲音信息比文字符號更具可感性,聲音出口時所負載的思想感情,比蘊含在文字之中的更為可感。誦讀,就是通過直覺思維的方式,對作品進行確切把握,綜合感受的手段,在富有情感的吟詠誦讀中,不經意間,就會對作品的語言文字產生真切、敏銳的感覺。而且,在多讀多聽的言語實踐中,學生會逐步將語言知識規律內化,形成語言直覺,形成較高的語感能力。
在平時的課堂閱讀教學中,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訓練學生“讀”的能力。
首先,通過范讀來營造課堂的情感氛圍,必要時還會配上合適的音樂。葉圣陶先生指出,教師在范讀的時候,要“把文章中的神情理趣,在聲調里曲曲折折傳達出來,讓學生耳與心謀,得到深切的了解”。教師范讀得當,學生的情感就會被充分調動,而且在聽讀的過程中,就能獲得對課文最直覺的認識,不知不覺地接受了絕妙的語感教育,就會逐漸培養出“聽的敏感”。
其次,要求學生大聲朗讀,清晰、響亮、準確地把文章讀出來, 要求他們在朗讀時,“眼到”,“口到”,“心到”,三種器官協同參與活動,充分運用言語聽覺及言語視覺去“整體直覺”地感知體悟課文,同時能從課文中找出感受最深的句子或段落,多讀幾遍,加深對課文內容、作者情感的印象。
至于一些情文并茂的課文,特別是詩歌和抒情散文,我指導學生進行美讀,也就是要求學生在誦讀時能把作者的感情傳達出來,要讀得抑揚頓挫、感情充沛。如葉圣陶先生所說,“激昂處還他個激昂,委婉處還他個委婉”,“要盡量去體驗作品中美好的內容和形式,并陶醉于其中”,倘若“美讀得其法,不但了解了作者說些什么,而且與作者的心靈相感通了”,從而激發了學生對語言的情趣敏感。
例如教學《春》時,我讓他們自由地、美美地誦讀課文,注意停頓、起伏、節奏和語速,然后用“我覺得《春》具有____美,美就美在____”的方式談談自己對課文的直覺感悟。通過誦讀,學生不但能由課文中豐富的詞語、確切的比喻、絢麗的色彩等感覺到作品語言的圖畫美,許多學生還能直覺到課文中疊詞多、短句多、“的”字短語多、兒化多等特點,感悟到作品充滿春天的韻律,領悟出作品語言的音樂美。如果我們條分縷析地去解讀作品,學生也許會知道作品用了哪些比喻,有多少排比,抒發了什么情感,但不會真正感悟到作品的語言美,言語敏感性的訓練更無從談起。
三、啟發學生通過揣摩品味鑒賞語言
要獲得言語的敏感性,還需要對語言材料進行反復揣摩、品味。葉圣陶先生指出:“一篇好作品,只讀一遍未能理解得透,要理解得透,必須多揣摩。”我認為,這種揣摩品味,應該在通過速讀整體感知的基礎上,啟發學生調動自己已有的知識和經驗,深入領悟作品的語言,把言語材料放到課文表情達意的活生生的語境中去進行,從而形成良好的語感,提高鑒賞能力。
在教學實踐中,我主要啟發學生找出文中的這樣一些言語材料來進行揣摩品味。
其一,找出特別富有表現力的詞句,體會作者遣詞造句的妙處,發掘出作品背后深藏的意蘊和情感。例如老舍在《濟南的冬天》中寫道:“小村莊的房頂上臥著點兒雪。”著一“臥”字,境界全出,形象地表現出整個村莊在暖冬里悠閑愜意的韻味。再如魯迅的《故鄉》中:“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一個“橫”字,就把故鄉村莊的零落、蕭條、衰敗的景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其二,抓住作品中言外之意最豐富的語句,品味作者匠心之所在,培養學生對語言細微部分的精細感受力。例如魏巍在《我的老師》中寫道:“我用兒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覺,她愛我們,并沒有真正要打的意思。”句中“狡猾”一詞是貶義詞,但結合語境,就能讀出一個孩子的機靈、敏感,而這種察覺,又正是源于對老師的熟悉了解和喜愛。再如魯迅的《孔乙己》中有這么一句話:“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大約”與“的確”一為估測一為確認,兩個詞放在一起,前后矛盾,這種表意方式也是超出常規的。但正是這種看似矛盾的用語,體現了作者用語的精確:“大約”是“我”的猜測,因為再也沒有見過孔乙己,根據最后一次見面的種種現象,估計孔乙己已經不在人世,但又沒有聽到他的死訊,所以用“大約”;“的確”是肯定的語氣,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中,被打折腿的孔乙己別無出路,只有死路一條。這兩個矛盾的詞語,要引導學生著重體會其豐富的言外之意。
其三,抓住作品中表達情感最強烈的語句,進行“披文入情”的真切體驗,直覺正確地把握作品語言傳達的思想感情。例如朱自清在《背影》中,以在晶瑩的淚光中再現的父親的“背影”結篇,與文章開頭回環呼應,進一步突出父親的“背影”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表達了作者對年邁的父親無限思念的感情,語言質樸,卻飽含深情,余音如縷。讀到結尾時,可以引導學生聯系自己的生活體驗進行聯想,從而更好地體會作者的感情。
此外,我還指點學生關注文章的標題、開頭和結尾,能根據標題帶著問題自覺把握文章內容;關注文章中文理特別清晰的地方,訓練學生對語言的層次和脈絡的敏銳感受力;關注文章中語言表達突破常規的地方,培養學生對語言形式變異的細致的感受力……總而言之,就是選擇教材中最適宜用來訓練語感的材料,引導他們反復揣摩、品味、吟詠,使作品的一字一句、氣韻格調深入他們的心靈。參考文獻:
[1]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
[2]倪文錦.初中語文新課程教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王尚文.語感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