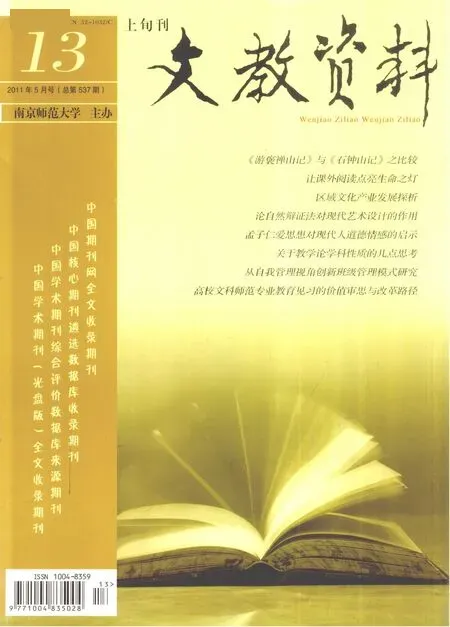重農政策的歷史悖論
袁國偉
(華東師范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241)
一、重農政策的形成
中國向來以農業立國。商鞅變法前后進行了十年,主要內容大都圍繞著農業這個層面展開。根據《史記·商君列卷》所載,其措施和農業相關的包括:“(1)致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2)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顯然,變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富國強兵,而推行以小家庭為主的自耕農是為了富國。但是秦國在實現以耕戰強國的目標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農為本的指導思想,而且清晰地表達出這樣一種特殊的國家體制,所有政策都是圍繞著以耕墾田地為出發點展開的”,社會其它方面的發展都不得與之相悖。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就是幾乎每個統一的王朝都會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中國傳統農業是在國家全力倡導、監督下得以發展成為一種進步的形態。“農為邦本”的意識非常強烈,而這種意識絕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它有一系列的政策舉措保障。這些保障在特別“照顧”農業的同時,也意味著國家的一切都將要靠它滋養支撐。正是國家——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對農業的超強控制,使農業本身受到重壓,使得發達的小農經濟所產出的剩余產品無法以合乎經濟的方式擴散、轉化、輻射到其它經濟領域,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缺乏合乎理性的自我運行機制,一切都在國家的監護之下。
隨著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興起,由于其可以為社會提供較高的糧食剩余,因此必將引發商品經濟迅速興起;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小農經濟的分解,造成貧富對立、社會分化。面對這種情況,司馬遷獨具慧眼,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的經濟政策應該是 “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爭之”。然而從富國強兵和鞏固邦本的立場出發,漢武帝在重農抑末的名義下開始壟斷天下鹽鐵,把工商虞由民間私營轉為國家官營,而農業也沒有了商品化的途徑。對這一政策的后果,馬端臨在其《文獻通考》的自序中分析得很精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采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如果農工商虞四業是由民間經營的,農民提供的剩余產品將會通過商業、手工業者的積累而在農工商虞四業中化為各種形式的產業,從而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然而由重農而抑商的政策反而限制了社會的可能發展。它一方面使得國家力量因對社會財富的過度掌握而無比強大,另一方面商人、手工業者會因這種政策而僅僅熱衷于博取一官半職或求田問舍,由于被政治權力所壓制,從而也就無法成長為一種獨立的社會階層。“在秦以后的王朝循環中,它一直成為大一統帝國的基本國策。保護小農經濟,抑制商品經濟,商業手工業的官營,這便成為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基本格局和發展定勢”。
二、重農政策導致農民素質的下降
國家政權在小農經濟的支撐下變得越來越強大,而其對社會的控制也越來越嚴密。政治權力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最強大力量。在這種強大的控制下整個社會逐漸分化為兩個極端的社會階層:一端是國家官僚和依附于這一官僚體系的地主、士大夫階層,在此泛稱之為統治階層;另一端是個體農民,在此泛稱之為被統治階層。其它社會階層則在國家控制之下始終沒有成為有影響的社會力量。這種兩極化的社會結構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它造成了農民——這個民族的大多數——素質的逐漸下降。
在這種大致一分為二的社會結構中,兩者在對立統一中結合為一個整體。由于農民一般不能直接從事精神財富的生產,他們也沒有能力思考自己的命運,精神上除去一些原始的自然崇拜之外,他們的精神風貌如何,大體總是受制于當時的統治階層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思想養料。而統治階層對待被統治階層的方式是自孔子時就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而法家所強調的控制又使農民階層變得碎片化,從而易于國家的控制。“就統治階層而言,使國民愚順是必需的,但是國家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這種代價就是由漢唐到宋以后的國力的逐漸衰弱,反過來,一個時代的國力強弱又對國民的風氣和性格發生極大的影響。中國國民性的從開放到封閉是與國力的強弱相一致并互為因果的”。由于國家運行的物質基礎完全建立在農業生產之上,國家在重農的名義下把農民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這樣碎片化的廣大農民除了提供糧食剩余就幾乎被國家隔絕了與周圍一切事物的聯系,“也幾乎割斷了他們自己之間的一切聯系,從而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徹底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隨著農民境遇及其與外界關系的變化,他們的心理和性格則隨之發生變化”。從漢唐到宋以后農民在社會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國家重農政策的保護下逐漸割裂了與社會上層之間的聯系,其生活的世界也變得越來越單調、狹小和封閉,結果則是整個農民群體素質的不斷下滑。
三、重農政策導致整個民族思想的貧乏
當大一統的帝國形成之后,思想領域的發展則逐漸消沉下去。這不能說和帝國的政策沒有任何關系,帝國時代的儒家學說不應該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沉悶的首要原因,更多時候我覺得儒家學說是帝國政策的替罪羊,否則怎么解釋孔子的“生不逢時”?顯然孔子不是在為他身后數百年的帝國創立學說,是帝國的統治者選中了儒家學說。根本原因是在統一的時候強大的國家權力強行制造的二元結構的社會模式造成了中國人在思想領域的貧乏。在這種二分對立的社會模式中,農民階層沒有能力對精神層面進行思考,他們關注的是生存的問題;而統治階層首要的任務是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進行辯護,統治階層最關心的是其統治的穩定性。形而上的精神思辨大多隱含著對絕對性、完美性的追問,這種追問是無止境的,也是不可及的,但唯其不可及,人們將會永遠處于一種對完美的追求之中。而現實總是殘缺的,即使我們認可一個不平等的制度,在以精神層面對其審視時也會感到不滿意。無論如何,這種從精神層面以絕對性、完美性為基礎的對現實的觀察都會是對現存秩序的一種消解、破壞。對本質的思辨必然是超現實的,也必然伴隨著對現實的批判,而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是拒絕這種批判的,這或許是因為習慣了霸道,或許是因為恐懼。在思想領域,人類從來就不是寬容的。在古代中國,統治階層不需要異己者,也不會允許這樣一個階層存在,這樣最有能力進行形而上思考的知識階層在國家的種種政策壓迫之下不得不依附于國家政權,從而也喪失了其獨立的人格。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之士到唐太宗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知識階層的人格精神在一路下滑。在統一的王朝時代,政權不需要有獨立見解的人才,只需要各種各樣的循規蹈矩的奴才,只許代圣賢立說,不許有任何越軌的思想。
進入帝國時代以后,三次思想活躍時期——魏晉玄學、南宋理學、明末經世之學——都是國家的不穩定時期,政治權力無法全面控制社會的時期。但是看一下這短暫的間隙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卻是如此豐富,對我們社會生活的影響又是如此綿遠。由此可知,我們這個民族不是缺乏思辨能力,而是缺乏精神思辨的現實環境。帝國的政治權力實在是太強大了,連無形的精神都無法擺脫其控制。如此一來,由于缺乏形而上的思考讓人們在習慣中變得盲目自信,以至于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 《全球通史》中寫道:“有史以來,從未有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如此缺乏根據。”
帝國政治權力的逐漸增強,知識階層的獨立人格精神的淪喪,農民素質的下滑,這三者相互影響、惡性循環,從而造成了中華文明發展的逐漸內卷化。這其中尤以帝國政治權力的過于強大為第一因素,古代社會是權力社會,而過于強大的國家政權控制了社會的一切層面,完全覆蓋了社會層面的發展,作為個體的人也逐漸被淹沒于其中。而這一切我認為都和帝國權力對農業的控制即重農政策的實行有關,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無論是權力社會還是農業社會,都有著發達的政治模式,也有著先進的農業耕作模式。權力和農業的合理結合本來應該是大力促進中華文明的進步的,可惜農業是以被權力綁架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如此一來,時間越久,兩者的相斥也就越強烈,從而在內耗中使文明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內卷化。
[1]孫達人.中國農民變遷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1,第一版.
[2]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11,第一版.
[3]馬端臨.文獻通考.文獻通考·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
[4][美]李丹著.張天虹等譯.理解農民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8.
[5]司馬遷.史記(簡體字本).中華書局,1999:1567.
[6]苑書義,董叢林.中國近代小農經濟的變遷.人民出版社,2001.
[7]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9.
[8]高壽仙.明代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合肥:黃山出版社,2006.
[9][美]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