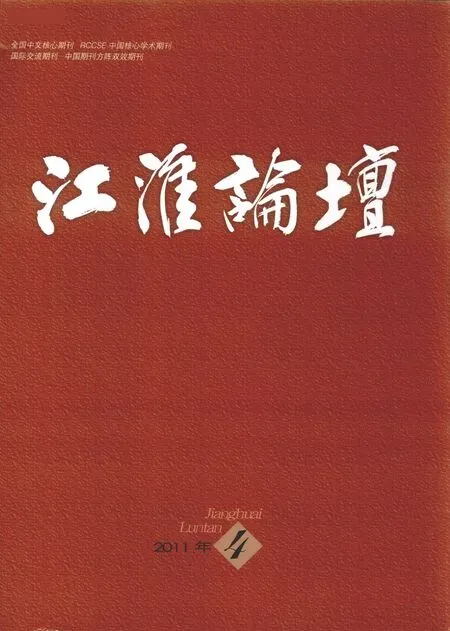誰更關心環境?*
——基于CHIPS數據的實證檢驗
王建明 劉志闊 徐加楨
(1.浙江財經學院,杭州 310018;2.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杭州 310012)
誰更關心環境?*
——基于CHIPS數據的實證檢驗
王建明1劉志闊1徐加楨2
(1.浙江財經學院,杭州 310018;2.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杭州 310012)
個體的社會經濟特征與環境關心之間關系密切。本文基于全國的城市家庭數據(CHIPS)研究了影響環境關心的個體社會經濟特征因素,同時利用城市環境污染數據控制環境關心的內生性問題。研究發現:收入差異、教育水平高低、性別差異和政黨參與是影響個體環境關心的顯著因素,年齡則與環境關心呈現U型的非線性關系。在此基礎之上,本文提出相應的政策含義。
環境關心;經濟社會特征;城市環境狀況;離散選擇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與之俱來的卻是生態環境遭受了嚴重的破壞。日益突出的環境保護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已成為我國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雖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生態環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環境污染形勢依然十分嚴峻。2009年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也顯示出世界其他國家對我國環境問題的關注,我國環境問題(特別是污染物減排問題)開始面臨著國際社會的壓力。
對于我國環境問題的研究,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研究,即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是否呈現“倒U型曲線”;[1][2][3]二是污染天堂假說研究,即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是否造成我國環境的惡化;[4][5]三是考慮環境下的生產率問題研究;[6][7][8]四是環境管制政策或管制工具研究。[9][10]上述文獻都以整個國家或某個地區為研究對象,以從宏觀或中觀視角理解和解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但這些文獻較少關注微觀個體的社會經濟特征和環境之間的關系。而這是研究環境問題的社會基礎,對研究環境問題有著重要意義。
本文基于中國城市家庭數據(CHIPS)來研究收入、教育和性別等個體社會經濟特征與環境關心的關系。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述評,主要對收入、教育、性別、年齡等與環境關心之間關系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和總結;第三部分闡述本文所利用的數據和建立相關的計量模型,從實證的角度驗證兩者之間的關系;第四部分報告模型的估計結果以及穩健性檢驗;最后一部分是結論及相應的政策含義。
二、文獻述評
個體的環境關心是環境問題的重要社會基礎,本部分主要從個體的收入、教育、性別、年齡和政黨參與等社會經濟特征與環境關心的相關文獻進行系統分析和評述,為本文計量模型提供理論基礎。
1.收入與環境關心
關于收入和環境關心的關系,多數研究的結論較為一致,即收入越高的人越關心環境。[11][12][13]這可以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解釋,即把環境看成一種“非必需品”,只有在滿足基本需求后人們才會開始關心環境問題。[14]相應地,當收入下降時,人們也會放棄對環境問題的關心,例如在經濟危機時,失業率會相應增加,從而人們的環境關心水平也會下降。[15]Franzen和Meyer基于國際社會調查項目數據(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分析發現,不僅一個國家內部高收入人群更加關心環境,而且在國家之間富裕國家的人們也更加關心環境。[16]這更加說明個體層面的問題和經濟總體的現象基本是一致的。個體收入對環境關心的影響,對于某個地區或國家而言,便呈現出人均GDP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
2.教育與環境關心
研究個體教育水平與環境關心關系的大多數文獻認為:個體的教育水平與環境關心有密切關系,即受過良好教育的個體比其他個體更加關心環境,[14]并指出這可能由于受良好教育者能獲取更多的關于環境問題的信息,知道環境污染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同時教育也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環境保護素質,從而使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更加關心環境。[17][18]同樣,在國家或地區研究層面,Dasgupta等的研究支撐了教育和環境關心的聯系,他們認為教育水平是環境關心的一個重要因素,并且發現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控制環境污染。[19]
3.性別與環境關心
很多研究都非常關注環境關心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早期的文獻沒有一致性結論,但新近文獻越來越趨于認為,環境關心存在性別差異。Arbuthnot和Lingg[20]、Arcury和Christianson[11]等在研究中并沒有發現女性更加關心環境,對此解釋是男性更加關心政治和集體事務,從而更加關心環境等社會事務。Schahn和Holzer[21]、Mohai[22]、Hunter[23]等提出了相左的觀點,他們研究認為女性更加關心環境。對此的解釋是父母身份導致女性更加關心環境對孩子的影響,從而更加關心環境問題。洪大用等[24]指出關于性別和環境關心的文獻,最新文獻研究有趨于一致的傾向。也就是說,越是最近的文獻越是報告環境關心上存在性別差異,即相對于男性而言,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更多的環境關心,而且這種關心還體現在女性對待環境友好行為上。以至于有學者指出:女性比男性更為關注環境已經成為環境社會學界日益廣泛傳播的一個結論。[25]
4.年齡與環境關心
對于年齡與環境關心之間的關系,現有的文獻觀點并未達成一致。Liere和Dunlap發現年齡與環境關心呈現負相關,即年輕人更為關心環境質量。[14]并指出這可能由于年輕人更加關心非物質生活,或者由于年輕人更容易接觸環境問題的信息。與之相悖的是Hallin[26]、Shen和Saijo[27]的研究。他們認為年齡與環境關心呈現正相關,即老年人更加關心環境。而與前兩種觀點都相異的是,Franzen和Meyer指出,年齡與環境關心呈現倒U型關系。[16]即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逐漸關心環境(這由于中年人更加關心公共事務,從而更加關心環境),但當年齡增長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關心環境問題。同時,對于我國農村地區的研究發現,年齡對環境態度積極程度的影響呈現正U型情況,即20歲以下的人和40歲以上的人更關心環境。[20]
另外,除了收入、教育、性別和年齡外,是否參與政黨也會對環境關心產生影響。[29]這由于參與政黨的個體更傾向于參與公共事務,從而更加關心環境問題。[16]
在我國,也有一些環境關心的調查和實證研究。有些研究針對特定城市居民環保意識及環保行為研究;[27][30][31]有些研究側重對農村地區環境關心進行調查研究。[28][32]在已有研究中,基于中國調查數據所進行的關于個體社會經濟特征與環境關心的系統分析非常有限,[24]并鮮有排除地區污染程度對環境關心的影響而研究中國的環境關心問題。基于此,有必要從全國來選取樣本,而不僅僅一個地區。本文使用中國12個省市的77個城市數據來研究城市居民的收入、教育和性別等個體社會經濟特征與環境關心的關系,并力圖控制地區間環境質量差異對環境關心的影響。
三、數據與基本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個體層面數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國家統計局共同收集的2002年中國城鎮家庭調查的相關數據。調查涵蓋北京、山西、遼寧、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廣東、云南、甘肅、四川和重慶等12個省市。和1988年、1995年的兩輪數據一樣,2002年的調查也是從國家統計局的年度調查樣本中抽取的。另外,本文采用的環境污染數據來源于同年的《中國城市年鑒》和《中國環境年鑒》。本研究中,我們設定的離散選擇模型(Probit model)如下:
P(environ=1)=Φ(β1lnincome+β2edu+β3gender+β4age+β5age2+β6party+β7pollution)
其中,被解釋變量environ表示是否關心環境,若是,則取1;反之則取0。解釋變量income表示個體的收入,我們對其作對數處理;edu代表個體的受教育年限;gender代表個體性別的虛擬變量,模型中男性作為參照組,取值為0;age和age2分別代表個體的年齡及其平方;party代表是否參與黨派,參與取值為1;pollution代表被調查者所在城市的污染水平。
首先對被解釋變量進行界定。在本文的研究中,模型的被解釋變量是環境關心變量,如果被調查者認為“環境問題”是當前重要的社會問題,我們將其定義為1;如果不認為“環境問題”是當前主要社會問題,我們則將其定義為0。(1)
其次,選擇解釋變量(具體數據描述見表1)。對于收入(income),我們取被調查者的個體收入,并刪除收入缺失樣本,通過描述統計分析發現,關心環境組的平均收入(12363元)要高于不關心環境組的平均收入(10856元)。對于教育(edu),我們選擇的是被調查者的教育年限,同樣也發現來自關心環境組的教育年限要大于另外一組。其總體樣本的教育情況如下:初中及以下占比33.91%;高中及大學以下占比39.28%;大學以上占比26.81%。對于性別(gender),我們定義女性取值為1;參照組男性取值為0,總體樣本中女性占比53.92%,男性占比46.08%,其中關心環境組的女性比例高于不關心組。對于年齡(age),我們剔除了18周歲以下的樣本,然后生成年齡的平方項,總體樣本中:30周歲以下占5.08%;30-40周歲占27.81%;40-50周歲占34.27%;50-60周歲占20.3%;60周歲以上占12.54%。對于是否參加黨派(party),我們設定參加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取值為1,其他為0,在總體樣本中:參加黨派的比例為35.51%,并且關心環境組比例遠高于不關心環境組。

表1 分組描述性統計
在模型設定中,我們同時控制了地區的環境差異。我們利用城市層面環境質量數據來控制環境污染對于環境關心的影響。首先,我們選擇的是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來衡量一個城市的污染狀況,描述統計顯示關心環境組的城市環境質量明顯低于不關心環境組;同時,我們選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lvhua)來作為城市環境質量變量的替代。我們假設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越高的城市其環境狀況越好,以進行穩健性分析。
四、模型分析結果
在本文中,我們使用probit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如表2中(I)、(II)和(III)列。與此同時,我們將其與OLS回歸結果進行比較,我們發現模型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都沒有明顯的變化,如表2中(IV)、(V)和(VI)列,我們在下文中主要基于probit模型的分析結果進行分析。
其中,(I)和(IV)是沒有控制地區環境差異情況下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1)收入對環境關心的影響顯著為正。這印證了發達國家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可見,收入水平提高確實可以增加國人對環境問題的關心,從而使環境質量從一種“非必需品”轉變為“必需品”。當然,這一結果是否可靠還需要剔除地區間環境質量差異的影響。比如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更高,可是工業化程度更高,環境污染更為嚴重,從而引致人們更加關心問題。因此,在沒有控制地區間環境質量差異時,模型存在遺漏變量的問題。后面我們進一步分析地區間環境質量差異對環境關心的影響。(2)教育可以增進環境意識,教育水平的提高顯著提高了人們的環境關心。這可能由于教育提供了更多的環境信息,也可能由于教育提高了人們的綜合素質,從而使人們更加關心環境問題。(3)女性傾向于更關心環境。在控制收入、教育和年齡等因素影響的前提下,女性對于環境關心仍然顯著為正,這說明性別的確是環境關心中的重要因素。(4)年齡與環境關心呈現非線性關系,隨著年齡的增加,人們對環境關心水平不斷下降,達到一定階段又會呈現上升趨勢,其轉折點大致在50周歲左右。這可能由于老年人接受集體主義教育較多,社會責任感較強,從而更加關心環境問題;[28]同時,年輕人受環境教育較多,同時環境教育對年輕人的“穿透力”更強,從而年輕人也更加關心環境。[31]與之相對,中年人較多關心其個體生計等問題(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負擔較重),相應較少關心環境問題。(5)是否參與黨派也顯著影響環境關心。參加黨派的個體,更傾向于參與公共事務,從而更加關心環境問題。[16]

表2 模型分析結果
由于模型(I)和(IV)沒有控制地區間環境質量差異對環境關心的影響,從而存在遺漏變量問題,使得估計結果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接下來本文利用城市層面的環境污染數據來控制地區間環境質量差異對環境關心的影響,分析結果如表2中(II)和(V)。與(I)和(IV)相比,我們發現:(1)環境污染程度對環境關心存在顯著影響,即環境污染越為嚴重的地區,人們越加關心環境問題,這也說明模型中如果不考慮環境污染程度對環境關心的影響會存在實質性缺陷。(2)在控制地區間環境質量差異的前提下,我們發現,收入、教育、性別等變量對環境關心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水平沒有發生變化,且其回歸系數還有所變大,這更進一步支持了上文的結論。
另外,我們又利用城市層面的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來替代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地區間環境質量狀況對環境關心的穩健性檢驗,分析結果如表2中(III)和(VI)。與(II)和(V)相比,我們發現: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越高,人們的環境關心越低,即地區間環境狀況差異的確會對環境關心產生影響,其他變量系數和顯著性并未發生顯著變化,這也為上文的結論提供了更穩健的佐證。
五、結論和政策含義
本文首次基于全國層面的CHIPS數據考察了個體社會經濟特征與環境關心的關系,并控制了城市間的環境污染差異。其主要結論如下:(1)城市環境質量的確影響人們的環境關心,特定城市或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越嚴重,越能引起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2)高收入、高教育、參與政黨以及女性更傾向于關心環境問題;(3)年齡對于環境關心呈現U型的非線性關系,即年輕人和老年人相對中年人更關心環境。
在歸納出這些基本的結論之后,我們可以總結出本文研究的基本政策含義:首先,教育能顯著提高民眾的環境意識,我國應加大對民眾環境教育的力度。特別地,相對于其他群體來說,中年人、男性、低收入者更不關心環境問題,因此環境意識教育應重點針對這些目標群體進行,從而促進全社會民眾對于環境問題的關心。其次,我國應更加重視環境管制,尤其應重視不發達地區的環境管制問題。由本文結論可知,環境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仍處于較低水平,相應地民眾環境意識仍處于較低層次。因此,通過政府驅動的方式,加強政府對環境的管制,這可以更有效地推動地區環境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對于不發達地區,民眾環境意識更弱,更應該重視加強不發達地區的環境管制。最后,我國應促進環境保護中的公共參與(如鼓勵民眾參與環保協會、進行環保抗議、投票呼吁等)。由本文研究可知,參與政黨的個體更傾向于關注環境問題,這說明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們更加關心環境問題。當然,公眾參與是以信息披露為前提的,只有首先保證了公眾的知情權,才可能實施其批評權。由此,我們應在保證環境信息披露基礎上,促進環境保護的公共參與,從而使民眾更加關心環境問題。
最后,本文不足之處在于,僅研究了影響環境關心的個體社會經濟因素,并未關注環境關心如何影響個體的環保行為和政府環境政策的制定,這將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考察的課題。
注釋:
(1)具體做法:在CHIPS數據的城鎮居民信息中有個“意向問題”,讓被調查者填出當下前三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如果被調查者選擇了“環境問題”,則認為該調查者更為關心環境,其環境關心變量取1,否則取0。
[1]Shen J.A.Simultaneous Estimation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vidence from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17(4):383-394.
[2]蔡昉,都陽,王美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節能減排內在動力[J].經濟研究,2008,(6):4-11.
[3]張紅鳳,周峰,楊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的規制績效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9,(3):14-26.
[4]陸旸.環境規制影響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貿易比較優勢嗎?[J].經濟研究,2009,(4):28-40.
[5]何潔.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中國各省的二氧化硫(SO2)工業排放[J].經濟學季刊,2010,9(1): 415-446.
[6]涂正革.環境,資源與工業增長的協調性[J].經濟研究,2008,(2):93-105.
[7]胡鞍鋼,鄭京海,高宇寧,等.考慮環境因素的省級技術效率排名 (1999-2005)[J].經濟學季刊,2008,7(3):933-960.
[8]王兵,吳延瑞,顏鵬飛.中國區域環境效率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J].經濟研究,2010,(5):95-109.
[9]王俊豪.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367-404.
[10]金碚.資源與環境約束下的中國工業發展[J].中國工業經濟,2005,(4):58-64.
[11]Arcury T A.Christianson E H.Environmental Worldview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ntucky 1984 and 1988 Compared[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0,22(3):387.
[12]Howell S E,Laska S B.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Environmental Coalition:A Research Note[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2,24(1):134.
[13]Scott D,Willits F K.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 Pennsylvania Survey[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4,26(2):239.
[14]Liere K D,Dunlap R E.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A Review of Hypotheses,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0,44(2):181.
[15]Kahn M E,Kotchen M J.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the Business Cycle:The Chilling Effect of Recession[D].NBER Working Paper,2010.
[16]Franzen A,Meyer R.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ISSP 1993 and 2000[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0,26(2):219.
[17]Jones R E,Dunlap R E.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Have They Changed Over Time?[J].Rural Sociology,1992,57(1):28-47.
[18]Marquart-Pyatt S T.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Among General Publics:A Cross-National Study[J].Society&Natural Resources,2007,20(10): 883-898.
[19]Dasgupta S,Laplante B,Wang H,etal.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 (1):147-168.
[20]Arbuthnot J,Lingg S.A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Knowledge,and Attitud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75,10(4):275-281.
[21]Schahn J,Holzer E.Studies of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Concern:The Role of Knowledge,Gender,and Background Variables[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0,22(6):767.
[22]Mohai P.Men,Women,and the Environment:An Examination of the Gender gap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Activism [J].Society&Natural Resources,1992,5(1):1-19.
[23]Hunter L M,Hatch A,Johnson A.Cross-National Gender Variation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4,85(3):677-694.
[24]洪大用,肖晨陽.環境關心的性別差異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7,(2):111-135.
[25]Tindall D B,Davies S,Mauboules C.Activism and Conservation Behavior in 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The Contradictory Effects of Gender[J].Society&Natural Resources,2003,16(10):909-932.
[26]Hallin P O.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Foley,a Small Town in Minnesota[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5,27(4): 558.
[27]Shen J,Saijo T.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EnvironmentalConcern:Evidence from Shanghai dat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8,69(10):2033-2041.
[28]宋言奇.發達地區農民環境意識調查分析——以蘇州市 714個樣本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0,(1):53-62.
[29]Dunlap R E,Mccright A M.A Widening gap: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Views on Climate Change[J].Environment: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8,50(5):26-35.
[30]趙爽,楊波.蘭州市民環境意識調查研究與對策[J].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9(5): 14-18.
[31]王建明.消費者為什么選擇循環行為——城市消費者循環行為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7,(10):95-102.
[32]譚麗榮,劉志剛.山東省農村地區居民環境意識調查分析[J].環境保護,2008,(4):47-51.
(責任編輯 吳曉妹)
F062.2
A
1001-862X(2011)04-0014-006
浙江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2010C35047);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Y6110086);浙江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YK2009080)
王建明(1979-),男,江蘇靖江人,浙江財經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環境營銷與政府管制;劉志闊(1987-),男,河北邢臺人,浙江財經學院經濟與國際貿易學院產業經濟學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產業組織與競爭戰略;徐加楨(1986-),男,安徽池州人,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農業經濟學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農村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