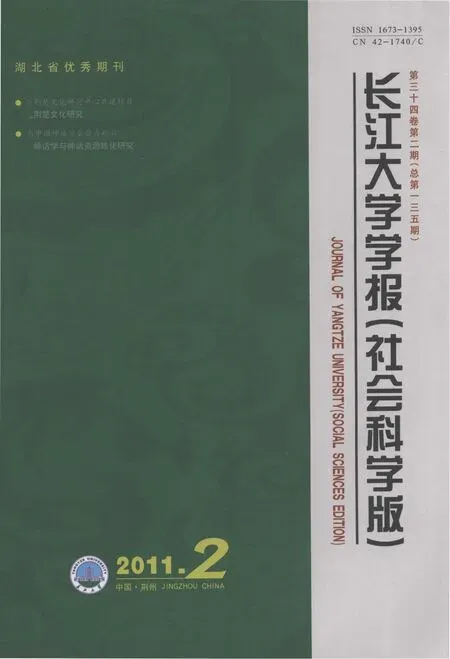屈原與《九歌》的感情寄托
李 霽
(荊州職業技術學院基礎部,湖北荊州434020)
屈原與《九歌》的感情寄托
李 霽
(荊州職業技術學院基礎部,湖北荊州434020)
屈原的《九歌》充滿了悲樂的情調,正是詩人心靈受到現實社會撞擊的結果,是詩人自己遭遇離憂、含冤被放、眼睜睜看著熱愛的國家沒落而無可奈何的自然流露,是屈原借祭神來抒發悲情之作,為歷代文人學習與借鑒的典范。
九歌;屈原;悲情;感情寄托
《九歌》本是夏朝祭祀天地的巫歌,后流傳到沅湘一帶,演唱不衰。屈原流放到沅湘后,看到民間祭祀的歌舞之樂,但歌詞鄙陋,于是在此基礎上加以潤色,創作了這一套新的歌辭。這組詩歌實質是屈原美政理想破滅后,流放沅湘之時,借當地人民祭祀鬼神的祭歌抒發自己的政治悲苦。屈原對其中的歌詞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加工、潤色、整理,使《九歌》雖是原始的祭歌而具有了原創的性質。可以說,屈原為其強烈的政治感情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傾瀉途徑。
一、《九歌》的悲情意蘊
有許多學者認為《九歌》的色調是明朗的,其中代表者有郭沫若。他在《屈原賦今譯》中認為其辭“清新”,調子“愉快”,“情調清新而玲瓏”。如果我們細細品讀這11篇短歌,不難感觸到其情感基調并非郭老所說清新愉快,而是充滿了惆悵與哀怨。
《九歌》11篇,除最后的《禮魂》外,祭祀的是十位神祗,其中《東皇太一》是天帝。清蔣驥認為“《九歌》所祀之神,太一最貴,故作歌者但致其莊敬,而不敢存慕戀怨恨之心”。《東君》祭祀的是太陽神,亦不含“慕戀怨恨”之情,充溢著對人間歡樂的留念,不乏悲涼之情和太息之聲。兩首詩所傳遞的感情都以莊敬、崇拜、頌揚為主旋律,寫得情緒熱烈,氣氛歡快。此外的八篇詩作,或寫神神相戀,或寫人神相愛,或寫為國捐軀,全都是凄婉悲涼之調。這形成了《九歌》以悲情為主的基調,構成了《九歌》的主旋律。祭祀本身就是一種對死者表達哀怨,以逝者寄以無限哀思的活動。屈原借用這種祭祀活動抒發自己郁結的悲情,表現理想的破滅、人生的悲哀,因此《九歌》的主旋律是悲情濃郁。另外,從詩詞中的用詞也可見一斑。九篇詩歌里大量使用“太息”、“悲”、“怨”、“憂”、“流涕”、“悵”、“苦”等字,從中可以看出全詩彌漫的是一種哀愁,主色調是充滿了悲情的冷色調。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指出:“《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馬茂元也說:“在《九歌》的輕歌微吟中卻透露了一種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以掩抑的深長的感傷情緒。”從基調上也說明了《九歌》的悲情色調,因此《九歌》是以悲情為主旋律,色調是冷色調,情致凄楚哀傷;而且它不是一般的哀傷,是在人間悲情之下藏含著屈原個人的政治哀傷。因此,經過屈原改作后的《九歌》所表現的悲情意蘊不再是簡單的祭祀感情,而是融合著屈原個人的遭遇與悲情。
《九歌》所描繪的神靈之戀,不是赴約失敗,就是生離別,都是沒有結果的愛情;所展示的保家衛國的戰爭,也是失敗的戰爭。其悲情濃烈,究其原因,或由佳期難遇、愛的破滅而生悲,或由生離別而悲,或由戰士視死如歸而悲哀。詩歌讓人體會到在情與愛之間總是成了一種空落,感受到愛的堅韌度,體驗著人性最本真的情感:憐憫、孤獨、焦慮、憂傷與悵惘。《九歌》如此悲苦,與詩人自身的人生經歷與體驗是分不開的。這種悲情抒發不同于《離騷》直接抒寫自己的人生凄慘,而是屈原假借神靈之手來抒寫自我人生悲苦之情。
二、屈原的唯美理想
透過屈原所創作的詩歌,我們可以看到其理想是唯美的,品性是剛正的。
這種唯美主義理想首先體現在情操上的唯美。情操上的唯美是指人的內心世界的道德與行為價值取向極高,崇尚高標,即我們常說的一種內在美。《九歌》中有“遺余佩兮醴浦”。所佩之物大都是一些古代的香草,以佩芳草香花比修煉高潔的品德情操。王逸《楚辭章句》說:“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聞一多也說:“結佩以寄意,蓋上世結繩以記事之遺。”都說明屈原通過佩飾美好來表明自己內在的唯美心情與思想。另一個“修”字,在屈原作品中出現了三十多次,可見它在屈賦中的地位了。《湘君》中有“美要眇兮宜修”,都是講的自我修養和學習。當他自己修到不得已時,只好“退將復修吾初服”,屈原思想的唯美就是通過自修與修人來達到的。
其次,這種唯美主義理想更主要地體現在他政治上的唯美。這種政治上的唯美就是人們常說的美政。他希望有一個圣君賢相。在作品中,屈原提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圣君賢相必然會出現一個清朗和平的社會,這就是屈原美政的核心思想,也正是孔子所向往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和平社會。屈原的這種美政受儒家與楚國本土傳統思想的影響,且加以革新與發揚。政治上,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與改革,建立一個和諧統一、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社會。屈原主張“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用人方面,儒家早有“選賢與能”、“為政在人”、“行有司”的觀點。屈原繼承這種觀點,反復強調“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遺則”,說明自己這樣做是取法前賢,雖然與當時世俗不合,但自己仍要堅持,不易節操。舉賢授能,遵守法度,公正無私,樹德愛民,使國家達到統一太平的境地,這就是屈原夢寐以求的政治唯美路線。
三、借祭神來抒發悲情的抒情方式
理想破滅,但流放中的屈原仍然放不下自己的國家。《九歌》悲樂的情調,正是詩人心靈受到現實社會撞擊的結果。
屈原創作《離騷》時,就創造出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用香草男女之間的關系來比喻自己與楚王的關系,從而表達自己忠心熱愛國家卻蒙受離憂的悲憤。我們解讀《九歌》時,既不能完全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來理解它,也不能離開詩人的身世來用楚地純祭祀的歌謠解讀它。如果把《九歌》完全理解為屈原借祭神的愛情悲歌來抒寫自己的政治遭遇,那就使《九歌》失去了它本身借神靈之戀表現出的審美價值與悲情意蘊;另一個方面,如果我們把《九歌》完全看成是夏王朝祭祀天地的祭歌在沅湘民間流傳的一種遺歌,那就使《九歌》失卻了詩人心靈搖蕩的審美情趣,務必落于《九歌》是抄襲的境地。所以正確解讀《九歌》的悲情,既不能離開它是沅湘人民祭神的歌謠,也不能離開它是屈原心靈搖蕩的表露。
《九歌》中的愛情基調是以悲情為主,這是與詩人的身世之悲緊密聯系的。屈原一生都執著于自己的美政,執著于自己的信念與理想。無論遭受疏遠還是遭受流放,他自始至終都不放棄自己的人生追求,直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用死來捍衛自己的唯美思想與品德。屈原這種對美政的追求,對理想的執著,都抒寫在《九歌》對愛情的歌詠里,折射在對神靈之戀的悲唱之中。
《九歌》所描寫的愛情悲歌與詩人遭遇是緊密聯系的,但詩歌里所表現的這種悲情意蘊從后人的角度來看,已超越了詩人自身的身世之悲。《九歌》抒發的這種詩人不幸遭遇的個人之悲,已經與楚國的命運,與南方楚國人民的命運聯系起來了。它既是屈原之悲,也是楚國之悲,更是先秦時期楚國人民之悲。屈原追求美政,渴望政治革新,讓自己的理想得以實現,使楚國走上富強的道路。可是楚王利令智昏,朝廷里又是奸臣當道,屈原政治革新的思路與美政的理想遭到破滅。《九歌》中有些地方在寫景時看起來似乎有明麗歡樂之樂,但這種明麗景色的抒寫實質上也是對全詩主基調——悲情的反襯。正所謂以樂景寫悲情,其情更哀。借傳說、神話、古祭祀之歌,以比興等手段抒寫個人憂憤,這是《九歌》的抒情特色,也是它之所以能流傳至今而仍為后人所頌和繼承的因素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意義巨大。參考文獻:
[1]朱熹.楚辭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潘嘯龍,陳玉潔.《九歌》性質研究辨析[J].長江學術,2006(10).
[4]潘莉.淺析《九歌》的悲劇意蘊[J].貴州文史叢刊,2007(01).
[5]李霽.屈賦中的“美人”象征[J].求索,2009(11).
責任編輯 韓璽吾 E-mail:shekeban@163.com
I207.22
A
1673-1395(2011)02-0005-02
2010 -12 10
李霽(1967-),男,湖北荊州人,副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