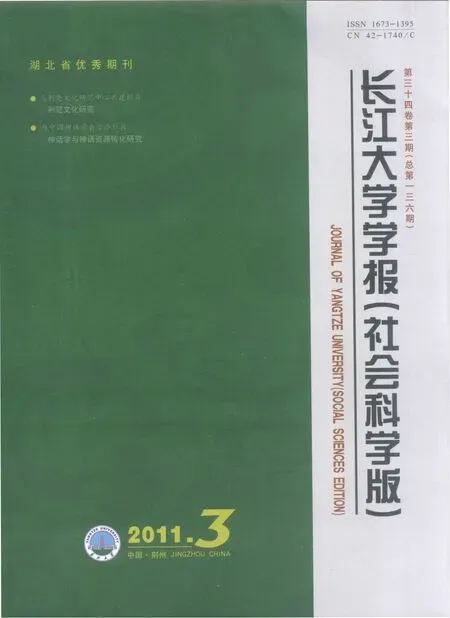試論翻譯多樣性的合理存在
吳 靜
(東莞理工學院 外語系,廣東 東莞 523808)
試論翻譯多樣性的合理存在
吳 靜
(東莞理工學院 外語系,廣東 東莞 523808)
在后現代解構主義翻譯理論中,譯者在翻譯中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譯者有著自己的意識形態、翻譯方法和創造性的表達。而在互文的網絡中,原作的意義不再確定不變。譯者主體性和互文文本相互作用而形成了多樣的譯本。
譯者;主體性;互文性;翻譯多樣性
翻譯的多樣性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譯者從自己的角度思考,不斷對作品進行新的解讀和再創造。在這個過程中,譯文讀者也可以不斷增強對原作和源語文化的了解。對于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多樣的翻譯是有益而且必要的。至于這種多樣性存在的原因,譯界往往將其歸因于翻譯標準的多樣性。古往今來,人們對于翻譯標準的討論就沒有停止過,從嚴復的“信、達、雅”到現代的“忠實、通順”,從泰特勒的三大原則到奈達的“功能對等”。這些對標準和原則的討論對翻譯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這些標準和原則的采納和使用則直接導致了翻譯的多樣性。而采納和使用這些標準的正是翻譯過程中重要的主體——譯者。翻譯的主體有三,作者、譯者和讀者,作者創造出原作,譯者通過對原作的解讀和再創造將譯文呈現給讀者。
一、譯者主體地位的確立
主體是參加社會實踐的人,那么誰是翻譯主體呢?許鈞教授歸納出以下四種答案:“譯者是翻譯主體;原作者和譯者是翻譯主體;譯者與讀者是翻譯主體;原作者、譯者、讀者都是翻譯主體。”[1]作為翻譯活動過程中的行為者和實踐者,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在傳統的翻譯理論中,譯者和譯作一直被定位為“仆人”或“女人”。德萊頓認為,“譯者是原作者的奴隸,奴隸只能在別人的莊園里勞動,給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釀出的酒卻屬于主人。”[2](P190)巴特也認為,“作者是主人。”[3](P5)法國翻譯家梅納日的那句“les belles infidelles”(不忠的美人)也眾所周知。[4]但是近年來受解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人們開始重視譯者的主體性。解構主義者認為,翻譯并不是對原文的簡單復制和模仿,它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而是一個積極參與的過程。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Venuti)從解構主義觀點出發把翻譯定義為:“翻譯是譯者依靠自己的理解,將構成源語文本的能指鏈用目的語能指鏈來代替的過程。”[5]譯者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譯者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取舍
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影響是不可回避的。翻譯之所以是兩種文化中意識形態傳遞與抗衡的活動,主要是因為譯者處于一個雙重話語、意識形態的互文關系中。福柯把意識形態看作是一種無形的權力,認為任何人文學科都是對某種權力的屈服,而翻譯更是如此,因為翻譯既涉及對原文的解讀與闡釋,也涉及對原文作者意識形態要素的解讀。譯者的翻譯策略、目的、對所譯文本的選擇以及對原文的解讀等都受到社會權力話語的制約。
(二)譯者對翻譯方法的選擇
德國古典語言學家施萊爾馬赫指出,翻譯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作者居安不動,而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居安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韋努蒂將前一種方法稱為“異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即把讀者引向原作,使讀者對原作的修辭手法、寫作風格以及內容有較直接的認識,譯者把原文形象、源語結構、語言表達形式搬進譯文;將后一種方法稱為“歸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即把一切不符合譯文讀者口味的表達法統統改變成地道的譯語表達法。對于譯者到底應該采取異化的方法還是歸化的策略,許多翻譯家或翻譯理論家常常從不同的角度,依據不同的標準和條件,提出不同的主張。而譯者則往往根據自己的翻譯目的、不同的讀者對象,偏重于其中的一種。歸化的目的是運用譯語文化易于接受的表達法,使譯文更通俗易懂,更適合于譯文讀者;而異化指盡力再現原文的色彩,以便更好地保留源語文化的異國情調,加強譯文讀者對異域文化的了解,滿足讀者對翻譯文學的審美期待。[6](P48),[7](P168)
正如《紅樓夢》的兩個最出名的英譯本,楊憲益夫婦的譯本 A Dream ofRed Mansions和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譯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各有風采。為了弘揚中國文化,楊憲益先生在英譯漢語作品時往往持原文至上的態度。他認為,翻譯必須忠于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詮釋,不應太有創造性,否則就是改寫而不是翻譯了。[8](P223)體現在《紅樓夢》的英譯本中則為異化的痕跡很多。而霍克斯則傾向于采用歸化的策略向英國的普通民眾介紹這部中國作品,使譯文讀者盡可能獲得與原文讀者同樣的感受。例如《好了歌》的第一句“世人都曉神仙好”,楊憲益夫婦的譯文為“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霍克斯的譯文是“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楊認為“神仙”是中國道教的概念,希望外國讀者對此有所了解,因此采用較為接近的“immortals”一詞;而霍則認為本國讀者可能不知道中國的道教,他認為將其轉換為他們所信奉的基督教可能更有利于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因此,他采用了基督教的概念“拯救”,人類因得到上帝的拯救而永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兩種文化發生碰撞時,兩位譯者都本著自己的翻譯目的和立場對原作做出了不同的詮釋。
(三)譯者的創造性表達
翻譯過程是譯者將其對原文文本的理解、體驗、重構、創作展現給譯語讀者的過程。在現代翻譯理論中,譯者不再是原作者的傳聲筒,不再是原作者身后亦步亦趨的隨行者,翻譯也不僅是語際轉換,更是文化上的交流。譯者不僅僅起橋梁的作用,更有在對源語文化闡釋解讀之上的再創造作用,使譯文得以符合譯語文化的語言規范。要使譯文流暢自然,譯者的創造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每一部譯文中,必然多多少少地存在著譯者苦心孤詣的創造。
還是以《紅樓夢》為例。在人名翻譯上,楊譯一般直譯其名,霍克斯則對不同身份的人名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例如,在翻譯“鴛鴦”時,楊將其直譯為“Yuanyang”,而霍則別出心裁地處理成“Faithful”,不僅體現了鴛鴦在中國文化中作為鳥對伴侶的忠誠,更點出了鴛鴦作為侍女對主人的忠心,因此比楊譯更勝一籌。
二、譯文的互文闡釋
最早提出“互文性”這一術語的是法國文藝理論家克里斯多娃。互文性研究可以分成狹義的和廣義的。前者指一個文本與可以論證存在于此文本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系,后者則指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總和之間的關系,而這些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形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網絡。[9]從廣義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遺跡或記憶的基礎上產生的,或者是在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換中形成的。翻譯過程就是一種互文過程。
互文性理論強調的是文本結構的非確定性,認為任何文本都沒有什么界限,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脫離其他文本而存在。每一個文本的意義都產生于它與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在動態的、具有互文性特征的文學環境和社會環境中,不管是作者的創作還是譯者的翻譯,在本質上都不是獨立的,也不是純客觀的,所以翻譯活動并不是物化了的活動,它同樣不能排除很多主觀因素的影響。如巴赫金所言,整個人類文化都存在著一定的互文性,因此翻譯就是打開和建立互文文本的重要媒介,而這個媒介的操縱主體就是譯者。在譯文中,我們經常可以讀到譯者獨特的表述,他的寫作風格與原文作者一樣具有個性和獨立性,譯文和原文以互文性的方式組成了一體。[10]
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原文作者的互文性寫作可以說是翻譯的第一步。無論是作者、讀者、還是譯者,都有自己的互文記憶,構成互文記憶的就是他們各自的社會、時代、文化背景以及閱歷等。作者的寫作是在互文記憶的基礎上重組前文本;而譯者的第一個身份就是讀者,以讀者身份出現的譯者對原文進行解讀,他必須傾聽出原文的互文文本的聲音,因為他不僅僅是一個讀者,同時還是下一個互文閱讀循環即翻譯的闡釋者和創造者。緊接著,譯者在對原文進行互文解讀的基礎上,調動自身所有的互文記憶,在翻譯策略中做出選擇,然后再進行創造性寫作。譯文就是譯者在互文網絡中對原文的闡釋。
三、譯者在互文網絡中的最終抉擇
翻譯不僅僅是語符之間的轉換,而且是一種釋義性的再創作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主體的譯者實際上進行著從讀者、闡釋者到作者的身份轉換。他首先要通讀原作以及大量與原作有關的注釋和評論,進行資料的收集,在這個過程中,他是讀者。在理解原文的過程中,當譯者與文本進行對話時,他總是帶著自己的經驗和認知模式進入文本,這種經驗和認知模式以及他在資料收集過程中對原作的了解構成了他的互文記憶,在這一互文記憶中,他形成了自己對原作的理解和解讀。在這基礎上,他再對原作進行研究和翻譯,作為闡釋者和作者,用另一種語言而且是一種個性化的語言,書寫出一種新的文本形式。不同的互文記憶必然使不同的譯者,甚至同一譯者在不同時期對相同文本的闡釋不盡相同。所以,作為個體的譯者的翻譯不可能與作為個體的作者的意圖完全等同,每個譯者的譯文也不可能如出一轍。譯文的多樣性正好反映了譯者在自己獨特的互文記憶中所產生的主觀能動性。譯者在某種明確的再創造動機驅使下完成的創造性翻譯行為,是通過在翻譯過程中積極地發揮和運用主觀能動性對原作進行能動的闡釋和建構。當然,譯者的主體性并不等于主觀隨意性,譯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并非沒有任何規限和制約,而是必然受到兩種語言的互文性語境的制約。
文學作品就像一個多棱鏡,從各個角度反映著我們的世界,而翻譯則像另一個多棱鏡,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原作品的風貌。正如作者的作品表達的是作者在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結構中對當時世界的理解一樣,譯者作為個體,在翻譯時難免會給譯文打上時代、歷史、民族乃至譯者個人風格的烙印,因為他必須在自己的互文網絡中做出抉擇。
從前面的分析來看,翻譯理論中經常討論的翻譯原則、標準和方法問題并不能解釋翻譯多樣性的存在。多種譯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譯者的主體性而導致的,譯者的意識形態、翻譯策略的選擇,以及在翻譯過程中創造性的運用影響到整個譯文的產生。同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于意義的抉擇又取決于原作和譯文在互文網絡中所處的位置和關系。
[1]許均.“創造性的叛逆”和譯者主體性的確立[J].中國翻譯,2003 (1).
[2]Ross Mitchell Guberman.Julia Kristeva:Interview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3]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4]楊陽,屠國元.“不忠的美人”——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傳統譯論的顛覆[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
[5]朱湘軍,陶友蘭,姜倩.觸摸英語翻譯的歷史脈搏——韋努蒂《譯者的隱身》評介[J].外語與翻譯,2004(4).
[6]Bassnett,Susan&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7]呂俊.跨越文化障礙: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1.
[8]張南峰.中西譯學批評[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9]程錫麟.互文性理論概述[J].外國文學,1996(1).
[10]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J].中國翻譯,2003(1).
H059
A
1673-1395(2011)03-0085-03
2011-01-02
吳靜(1978—),女,湖南平江人,講師,主要從事翻譯理論及應用語言學研究。
責任編輯 強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