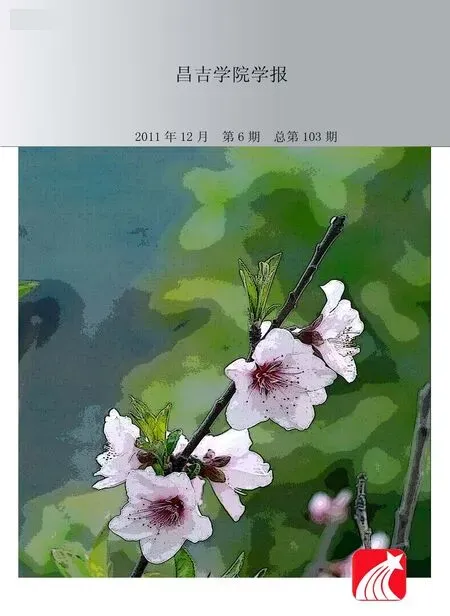諸種“文學(xué)自覺”學(xué)說的回顧與反思
李勇
(1.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北京 100875;2.咸陽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與傳播學(xué)院 陜西 咸陽 712000)
“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最早由日本學(xué)者鈴木虎雄在1920年提出,后經(jīng)由魯迅1927年的著名演講《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的介紹,成為中國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一個(gè)常識(shí)性判斷。魯迅說:“用近代的文學(xué)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gè)時(shí)代可說是‘文學(xué)的自覺時(shí)代’,或如近代所說的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此后,在陳鐘凡、郭紹虞、羅根澤等所著的“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史”中,“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都已成為審視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發(fā)展史的重要尺度。
然而,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遭遇到越來越多的質(zhì)疑與反思,“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等學(xué)術(shù)論斷紛紛被提出。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是一個(gè)前后相繼、緩慢演進(jìn)的過程,“文學(xué)自覺”亦有一個(gè)萌芽、成長、興盛的過程。那么,在一個(gè)連續(xù)的過程中,如何確定一個(gè)由量變到質(zhì)變的轉(zhuǎn)折點(diǎn),以區(qū)分文學(xué)的“自覺”與“非自覺”?以“文學(xué)自覺”的時(shí)間點(diǎn)去總結(jié)概括“文學(xué)自覺”的過程,此問題本身便存在著理論的漏洞。然而,時(shí)期劃分能夠更清晰地勾勒出中國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軌跡,“文學(xué)自覺”時(shí)間點(diǎn)的確定,對(duì)文學(xué)史寫作來說,又是不可或缺的。學(xué)者們只能勉為其難,紛紛從各自的視角出發(fā),去確定“文學(xué)自覺”的時(shí)代。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學(xué)自覺說”就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了。目前的當(dāng)務(wù)之急,是對(duì)諸種學(xué)說的理論依據(jù)進(jìn)行比較分析與反思,最終確立一個(gè)更具學(xué)理性的“文學(xué)自覺”的時(shí)間點(diǎn)。
一、“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
在質(zhì)疑“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的諸多聲音中,最具影響力非“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莫屬,而最具代表性的學(xué)者是張少康和趙敏俐。張少康在《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史》中說:“漢代文學(xué)觀念的發(fā)展與先秦相比,有較大的變化,這就是文學(xué)的獨(dú)立與自覺的逐漸形成。一般人按照魯迅的說法,認(rèn)為到魏晉方始進(jìn)入文學(xué)的獨(dú)立與自覺時(shí)代之說,其實(shí)是不確切的。文學(xué)觀念發(fā)展到戰(zhàn)國中期以后有明顯的變化。這時(shí)作為文化之‘文’的概念中,文章的含義比博學(xué)的含義在成分上大大增加了。”[2]西漢中后期,“文學(xué)的自覺”已經(jīng)清晰可現(xiàn)。
在陳述了“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的主要依據(jù)后,張少康對(duì)“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提出了批評(píng):“魏晉之際文學(xué)思想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這種變化,主要在于使文學(xué)由重視和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和社會(huì)教育作用,向重視和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作品藝術(shù)形式方面轉(zhuǎn)化。所以,對(duì)文學(xué)的獨(dú)立和自覺始于何時(shí)必須重新加以探討。”[3]既然魏晉時(shí)代文學(xué)思想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轉(zhuǎn)折性的發(fā)展,由“言志”轉(zhuǎn)為“緣情”,由注重文學(xué)功用轉(zhuǎn)向注重文學(xué)形式,那么“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為什么仍不能成立呢?張少康“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所抱持的“文學(xué)”概念與魯迅“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中的“文學(xué)”概念是有所差別的。魯迅旗幟鮮明地指出,“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是從“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視角上來建立的,“文學(xué)的自覺”是指純文學(xué)的自覺,“文學(xué)性”(即文學(xué)作品的藝術(shù)形式)本身開始受到重視。張少康拋棄了魯迅所謂的“近代的文學(xué)眼光”,側(cè)重于“文學(xué)”的獨(dú)立。在兩漢時(shí)期,“文學(xué)”概念窄化了,文學(xué)與史學(xué)、經(jīng)學(xué)開始分離,正如郭紹虞所論:“時(shí)至兩漢,文化漸進(jìn),一般人亦覺得文學(xué)作品確有異于其他文件之處,于是所用術(shù)語,遂與前期不同。用單字則有‘文’與‘學(xué)’之分,用連語則有‘文章’與‘文學(xué)’之分:以含有‘博學(xué)’之意義者稱之為‘學(xué)’或‘文學(xué)’;以美而動(dòng)人的文辭,稱之為‘文’或‘文章’。如此區(qū)分,才使文學(xué)與學(xué)術(shù)相分離。”[4]兩漢時(shí)代,“文學(xué)”開始獨(dú)立發(fā)展,但直到魏晉時(shí)代,“純文學(xué)”才浮出水面。由此可見,張少康所論及的“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與魯迅所提出的“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所探討的并非同一問題。
趙敏俐在《“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反思》一文中更為支持“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漢代文學(xué)仍處于經(jīng)學(xué)的籠罩之中,因此具有濃郁的功利主義傾向。然而,功利主義并不會(huì)成為否定“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的依據(jù)。“但是考察歷史我們卻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的文學(xué)發(fā)展,正是從功利主義的自覺走向藝術(shù)審美自覺的。”[5]正是在經(jīng)學(xué)研究和儒家功利主義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文學(xué)的審美特性被認(rèn)識(shí)得越來越清晰了,因此“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就理所當(dāng)然地成立了。但是,這一論證過程存在著學(xué)理上的漏洞。功利主義的文學(xué)觀念固然和文學(xué)的審美特性是兼容的,但是和審美主義的文學(xué)觀念卻是不兼容的。漢代文學(xué)的確極為重視文學(xué)的審美特性,尤以漢賦最為顯著,但是文學(xué)的審美特性并非審視文學(xué)的第一標(biāo)準(zhǔn),審美主義的文學(xué)觀念并未建立起來。日本漢學(xué)家青木正兒在《中國文學(xué)概說》中指出:“先德行,后文學(xué),這是孔門之教。這教訓(xùn)是萬世應(yīng)該肯定的金言。但是理解錯(cuò)了,以‘德行’為‘道德說’,以‘文學(xué)’為‘文筆’時(shí),于是道學(xué)之過信與文藝之蹂躪便要開始,文藝不容易脫離道德的桎梏了。所以此后到東漢末年,一般的都不能離開道德說而觀察文藝。文藝這東西,在道德說支配下而不敢恣意逸脫時(shí),才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像這種思想傾向,盛行起來的。”[6]由此可見,功利主義的文學(xué)觀念是否定“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的強(qiáng)力依據(jù)。另外,趙敏俐對(duì)功利主義文學(xué)觀念與文學(xué)的審美特性之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是不符合文學(xué)史事實(shí)的。在詩、樂、舞混而為一的原始文藝中,文藝的審美特性已經(jīng)受到重視。而隨著儒家“詩教”、“樂教”思想與勸誡主義文藝觀的建立,文藝的審美特性是受到了功利主義文藝觀的壓抑,直到儒家思想衰微、道玄取而代之的魏晉時(shí)代,這一局面才得以改觀。
然而,“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所潛藏的學(xué)術(shù)理念是值得特別關(guān)注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所遵行的“純文學(xué)”觀念是西洋舶來品,但卻與中國文學(xué)史中的“文學(xué)”觀念并不一致。如果一味堅(jiān)持“純文學(xué)”的觀察視角,那么就有可能歪曲對(duì)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軌跡的認(rèn)識(shí)與評(píng)價(jià)。趙敏俐說:“在討論中國古代文學(xué)自覺觀的時(shí)候,我們要有一個(gè)清醒的認(rèn)識(shí),即不能把唯美主義的追求看成是文學(xué)自覺的惟一標(biāo)志,時(shí)時(shí)刻刻記住文學(xué)應(yīng)該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是自先秦到魏晉六朝人們對(duì)于文學(xué)本質(zhì)的一種深刻理解,這也是中國文學(xué)自覺的重要組成部分。”[7]魯迅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純文學(xué)”,正是為了批判“文以載道”的儒家文學(xué)觀。“純文學(xué)”與“文以載道”的對(duì)立,實(shí)際上是道家文藝觀與儒家文化觀的對(duì)立,是現(xiàn)代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對(duì)立。在《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一文中,魯迅從中國文化內(nèi)部找尋到了對(duì)抗儒家禮教的反叛力量——道家與玄學(xué)思想所支撐的“魏晉風(fēng)度”。“純文學(xué)”觀念的引入,“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的提出,以及魏晉文學(xué)在中國文學(xué)史中地位的提升,都是為了配合對(duì)儒家禮教的批判。受其影響,在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語境中,“文以載道”似乎又受到了“純文學(xué)”的壓抑。
這種結(jié)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純文學(xué)”畢竟代表了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主流觀念。張哲俊在《東亞比較文學(xué)導(dǎo)論》中論到:“目前學(xué)術(shù)界有一種復(fù)古主義思潮,認(rèn)為文學(xué)的理論和研究應(yīng)當(dāng)建立在東亞自己的概念基礎(chǔ)上。這種主張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問題也是明顯的:一,如果回歸到雜文學(xué)的概念,那么不是進(jìn)一步使文學(xué)的概念清楚,而是回到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的界限不清的時(shí)代。這是倒退,不是進(jìn)步。二,文學(xué)研究終究不是一個(gè)人或者一兩個(gè)國家和民族的研究,是整個(gè)世界的共同研究。如果放棄現(xiàn)有的文學(xué)概念,那么顯然就無法使他人看懂。遵守世界通用的文學(xué)概念和術(shù)語,是學(xué)術(shù)研究和交流的基石。”[8]因此,最為客觀理性的審視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是二元的,是“文以載道”與“純文學(xué)”的結(jié)合;既要有古代的視角,又要有現(xiàn)代的視角,切勿將現(xiàn)代的“評(píng)價(jià)”作為古代的“歷史事實(shí)”。
二、“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與“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
在“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提出的同時(shí),“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和“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也先后浮出水面了。“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是劉躍進(jìn)在《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xué)》一書中提出的。李躍進(jìn)并不認(rèn)同“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主要基于兩大原因。第一,曹丕的《典論·論文》并不能成為“文學(xué)自覺”的依據(jù)。曹丕將文學(xué)視為“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文學(xué)依然未擺脫儒學(xué)國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控制。第二,魏晉文學(xué)是道家與玄學(xué)思想的傳聲筒,仍舊無法獲得獨(dú)立。魏晉時(shí)代,詩歌的抒情性受到了詩人越來越多的重視,文學(xué)的審美特性與審美技巧也日漸備受關(guān)注。然而,劉躍進(jìn)指出:“不無遺憾的是,魏晉詩人雖然一度擺脫了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的束縛,日益強(qiáng)烈地意識(shí)到了文學(xué)自身的特性,卻沒有再往前大跨一步,就被卷進(jìn)玄言詩風(fēng)之中,再一次簡單地充當(dāng)了時(shí)代精神的傳聲筒。”[9]因此,直到劉宋初年開始、到南齊永明前后,文學(xué)方才走上獨(dú)立發(fā)展的道路,“文學(xué)獨(dú)立一科,文筆的辨析以及四聲的發(fā)現(xiàn),這是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過程中極其重要的變化:由于文學(xué)獨(dú)立一科,使得中國文學(xué)真正從經(jīng)史附庸的地位解放出來;由于文筆的辨析,使得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觀念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突出了文學(xué)抒情寫意的特征;由于四聲的發(fā)現(xiàn),使得中國古代詩歌逐漸脫離了古樸原始的風(fēng)貌,一躍而成為近體詩的雛形。以上述三個(gè)方面的變化作為顯著標(biāo)志,中國古代文學(xué)從此真正步入了自覺時(shí)代。”[10]
支持“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的三大標(biāo)志,無疑是符合中國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事實(shí)的。然而,“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依然具有難以克服的學(xué)理漏洞。首先,“文學(xué)自覺”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既要看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又要看文學(xué)創(chuàng)作。雖然《典論·論文》對(duì)文學(xué)審美特性的發(fā)掘尚欠深入,但是“詩賦欲麗”的提出畢竟是不容忽視的觀念變革。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未免束手束腳,但文學(xué)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大踏步地邁向?qū)徝乐髁x了。曹丕、曹植的詩賦創(chuàng)作,不僅關(guān)心對(duì)個(gè)人情感的書寫,而且注重文采的華麗優(yōu)美。鐘嶸在《詩品》中如此評(píng)價(jià)曹植的詩作:“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粲溢今古,卓爾不群。”[11]然而,“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忽略了魏晉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顯現(xiàn)出來的審美主義特征,從而將“文學(xué)自覺”的時(shí)間延后了二百年。其次,“文學(xué)自覺說”的最終學(xué)術(shù)意義在于厘清中國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軌跡,它要成為對(duì)中國文學(xué)史進(jìn)行時(shí)期劃分的重要判斷指標(biāo)。不管是“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還是“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實(shí)際上都暗含著一個(gè)中國文學(xué)史時(shí)期劃分的問題。王瑤在《中古文學(xué)史論》(1948年出版)中援引了魯迅所提出的“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將魏晉文學(xué)作為中國文學(xué)史中古時(shí)期的開端。張少康在《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史》中將漢魏六朝劃定為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史的第二階段,即“發(fā)展和成熟時(shí)期”。“如果說先秦時(shí)期主要是為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發(fā)展奠定了哲學(xué)和美學(xué)思想基礎(chǔ)的話,那么,漢魏六朝則是在這種哲學(xué)和美學(xué)思想基礎(chǔ)上,發(fā)展成為系統(tǒng)的具體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12]漢代文學(xué)在經(jīng)學(xué)的影響下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在政治與教化方面的外部功用,因此文學(xué)已經(jīng)開始自覺;魏晉南北朝則緊隨其后,在道家、玄學(xué)和佛學(xué)的推動(dòng)下,將文學(xué)的審美主義與技巧理論推向高潮。因此,拋開時(shí)期劃分問題,單純地提出“文學(xué)自覺說”的問題,實(shí)際上是沒有多大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就陷入到了這一誤區(qū)。
在2010年,李永祥在《論“文學(xué)自覺”始于春秋》、《“春秋文學(xué)自覺”論》兩篇論文中提出了“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探討中國古代文學(xué)自覺,應(yīng)該用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觀從本源探討起。春秋時(shí)期文學(xué)的自覺是本源,有春秋時(shí)期人性覺醒和藝術(shù)覺醒作為滋養(yǎng)的土壤和源泉,有春秋時(shí)期的文獻(xiàn)及后世有識(shí)之士的評(píng)論作為佐證。春秋時(shí)期文的自覺,符合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中華文明發(fā)展的先鋒,為弘揚(yáng)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意義重大。”[13]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一書中發(fā)揚(yáng)光大了魯迅所提出的“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并將“人的主題”與“文的自覺”作為“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的兩大標(biāo)志。李永祥所提出的“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也沿襲了這一學(xué)術(shù)思路。春秋時(shí)代,在人性覺醒和藝術(shù)覺醒的大背景中,文學(xué)開始獨(dú)立。然而,春秋時(shí)代真的出現(xiàn)了人性覺醒和藝術(shù)覺醒的思潮嗎?“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并未對(duì)這一理論前提做出任何深入細(xì)致地解說。與此同時(shí),支撐“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的證據(jù)也很單薄。以六經(jīng)及《左傳》作為文學(xué)獨(dú)立的標(biāo)準(zhǔn),實(shí)在無法讓人信服。文學(xué)依舊被困在經(jīng)學(xué)的囹圄之中,文學(xué)理論還是先秦諸子哲學(xué)思想的組成部分。張少康論到:“(先秦時(shí)代)文學(xué)思想和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還處于萌芽和產(chǎn)生時(shí)期,它們大都體現(xiàn)在對(duì)總體文化的論述之中,而不是純粹的、單一的。當(dāng)時(shí)人們沒有把詩、樂看作為單純的藝術(shù)品,而是把它們作為政治、倫理、道德修養(yǎng)方式來對(duì)待的”,“先秦時(shí)期文學(xué)思想和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的萌芽和產(chǎn)生,和哲學(xué)、政治思想有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各種有代表性的文藝思想派別都是從著名的哲學(xué)、政治思想派別中派生出來的,不少重要的文藝思想甚至是蘊(yùn)含于哲學(xué)、政治思想體系之中,而不是以論述文藝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14]由此可見,“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是經(jīng)不起嚴(yán)密的理論推敲的。
三、諸種“文學(xué)自覺說”的反思
關(guān)于“文學(xué)自覺”,為什么會(huì)出現(xiàn)差異非常的學(xué)說呢?一個(gè)不容忽視的原因便是“文學(xué)自覺”這一詞語的曖昧不清。趙敏俐說:“‘文學(xué)自覺’這一論斷的內(nèi)涵有限,歧義性太大而主觀色彩過濃,因此不適合用這樣一個(gè)簡單的主觀判斷來代替對(duì)一個(gè)時(shí)代豐富多彩的文學(xué)發(fā)展過程進(jìn)行客觀的描述。”[15]“文學(xué)自覺”存在歧義性,這的確是一個(gè)很有見地的看法。然而,“文學(xué)自覺”并非一個(gè)“簡單的主觀判斷”,只要將其內(nèi)涵界定清晰,“文學(xué)自覺”就會(huì)具有客觀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
總體而言,“文學(xué)自覺”具有內(nèi)涵。首先,“文學(xué)自覺”是指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自覺。“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的首倡者鈴木虎雄所論述的“文學(xué)自覺”,事實(shí)上是“文學(xué)評(píng)論的自覺”。“魏之三祖即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都是作為文學(xué)家而同時(shí)以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力來推擴(kuò)、保護(hù)文學(xué)者。建安、黃初之時(shí),文學(xué)郁然興起,是不能不主要?dú)w為彼等之力的。而有關(guān)文學(xué)的議論,亦自曹丕及其弟曹植始”,“由上可見,在魏代,有關(guān)文學(xué)的獨(dú)立的評(píng)論已經(jīng)興起”。[16]可見,鈴木虎雄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獨(dú)立,其標(biāo)志是文學(xué)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的多元化,曹丕的《典論·論文》超越了儒家“詩教”的單一標(biāo)準(zhǔn),建立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多元標(biāo)準(zhǔn),既有“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又有“詩賦欲麗”和“文以氣為主”。青木正兒和導(dǎo)師鈴木虎雄如出一轍,在《中國文學(xué)思想史》中討論了“魏晉時(shí)代純文學(xué)評(píng)論的興起”。[17]而在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陳鐘凡和郭紹虞清晰地將“文學(xué)的自覺”認(rèn)定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獨(dú)立。陳鐘凡說:“中國論文之有專著也,始于魏晉。時(shí)人論文,既知區(qū)分體制為比較分析的研尋;又能注重才程。蓋彼等確認(rèn)文章有獨(dú)立之價(jià)值,故能盡掃陳言,獨(dú)標(biāo)真諦,故謂中國文論起于建安以后可也。”[18]郭紹虞則說:“迨至魏、晉,始有專門之作,而且所論也有專重在純文學(xué)者,蓋已進(jìn)至自覺的時(shí)期。”[19]他們均指出,魏晉時(shí)期是一個(gè)文學(xué)評(píng)論步入獨(dú)立和自覺的時(shí)代。
其次,“文學(xué)自覺”是指純文學(xué)的自覺。魯迅在《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中從“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視角出發(fā),提出了“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所謂“文學(xué)自覺”確定無疑是純文學(xué)的自覺。從鈴木虎雄到魯迅,“文學(xué)自覺”的內(nèi)涵悄然發(fā)生了變化,從“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自覺”轉(zhuǎn)為“純文學(xué)的自覺”。隨之而來的是,“文學(xué)自覺”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亦悄然發(fā)生了變化。“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自覺”的標(biāo)志是文學(xué)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的多元化,尤其是審美主義文學(xué)觀的出現(xiàn)。“純文學(xué)的自覺”則需要從文學(xué)或文化的宏觀視角出發(fā)去加以審定,而“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自覺”是“純文學(xué)的自覺”的標(biāo)志之一。
在置換“文學(xué)自覺”內(nèi)涵的同時(shí),魯迅拓寬了視野,把“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放在魏晉南北朝文化史中進(jìn)行考察,并將“魏晉風(fēng)度”作為“魏晉文學(xué)自覺”得以產(chǎn)生的文化背景。魯迅指出,漢末魏初的文章具有“清峻”、“通脫”的風(fēng)格,這絕對(duì)受到了以道家、玄學(xué)思想為核心的“魏晉風(fēng)度”的影響。[20]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一書中,則將魯迅的觀點(diǎn)變得更加明晰。“如果說,人的主題是封建前期的文藝新內(nèi)容,那么,文的自覺則是它的新形式。兩者的密切適應(yīng)和結(jié)合,形成這一歷史時(shí)期各種藝術(shù)形式的準(zhǔn)則。以曹丕為最早標(biāo)志,它們確乎是魏晉新風(fēng)。”[21]換言之,魏晉時(shí)代“文學(xué)的自覺”有兩大標(biāo)志,一是“人的主題”,即在道家、玄學(xué)思想的啟發(fā)下對(duì)存在的深刻體悟,二是“文的自覺”,即對(duì)文學(xué)的整個(gè)審美過程的深入探討。前者從內(nèi)容上突破,后者從形式上突破,共同迎來了一個(gè)“文學(xué)自覺”的嶄新時(shí)代。
在《中國文學(xué)思想史》一書中,青木正兒亦從內(nèi)容與形式兩個(gè)方面,論述了魏晉時(shí)代的文學(xué)新動(dòng)向。魏晉文學(xué)在內(nèi)容上掙脫了儒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控制,形成了“超脫主義”和“自然愛”等全新的文學(xué)主題。青木正兒說:“自從超脫主義和文藝結(jié)緣,在魏晉以后的文壇上產(chǎn)生巨大反響,形成了文人氣質(zhì)的一個(gè)重要的要素。從此以后,學(xué)究多由儒者充當(dāng),潛心鉆研濟(jì)世之學(xué);而文人墨客則多為超脫主義者,可見其提高處士節(jié)操之風(fēng)。這些人以風(fēng)雅相標(biāo)榜,在各種場(chǎng)合都表現(xiàn)超脫的氣味”,“超脫生活是因?yàn)閷?duì)人事交往厭棄的結(jié)果,這導(dǎo)致了同自然美的關(guān)系越來越密切的傾向”。[22]“魏晉風(fēng)度”意味著與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價(jià)值觀,意味著與名教相對(duì)的生活方式,這是魏晉文學(xué)在內(nèi)容主題上突破了兩漢文學(xué)的窠臼。而綜合衡量《典論·論文》、《文賦》等文學(xué)理論著作和魏晉詩文創(chuàng)作,魏晉文學(xué)的修辭主義特征則越來越明顯,這些都為南朝修辭主義的興盛做好了鋪墊。另外,青木正兒和李澤厚都將魏晉時(shí)代“文學(xué)的自覺”放在魏晉時(shí)代“文藝的自覺”的大背景中來展開分析。不管是“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還是“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都有意無意地將文學(xué)自覺與藝術(shù)自覺割裂開來了。
再次,“文學(xué)自覺”是雜文學(xué)的自覺。袁行霈在《中國文學(xué)概論》中說:“中國古代并沒有嚴(yán)格劃分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的界限,沒有確立純文學(xué)的觀念。古代所謂文學(xué),一方面容納了在我們看來不屬于文學(xué)的一些體裁,另一方面又沒有把我們認(rèn)為是文學(xué)的一些體裁包括進(jìn)去。因此,我們確定中國文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時(shí),既要按照我們今天對(duì)文學(xué)的理解,又要兼顧古人的習(xí)慣,充分注意雜文學(xué)這個(gè)特點(diǎn)。”[23]換言之,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研究,要同時(shí)兼顧傳統(tǒng)視角與現(xiàn)代視角。“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堅(jiān)持的是純文學(xué)的現(xiàn)代視角。而張少康、趙敏俐等學(xué)者之所以提出“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就是要回歸到雜文學(xué)的傳統(tǒng)視角,以便更加準(zhǔn)確地描述中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軌跡與基本特征。因此,“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與“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是兼容的,它們是“文學(xué)”概念不斷窄化的兩個(gè)標(biāo)志。
雜文學(xué)、純文學(xué)二元視角的建立極有意義,已經(jīng)成為審視與界說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發(fā)展史的重要維度。在《中國文學(xué)思想史》中,青木正兒從“實(shí)用主義”(或鑒戒主義)與“審美主義”(或修辭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將中國文學(xué)思想史劃分為三大時(shí)期。實(shí)際而言,“實(shí)用主義”突出的是雜文學(xué)的特征,而“審美主義”突出的則是純文學(xué)的特征。原始社會(huì)直至漢代,不管是詩、樂、舞未分化的原始美意識(shí),還是儒家的文藝觀,其文學(xué)觀念都傾向于實(shí)用主義,因此這一時(shí)期被稱為“實(shí)用娛樂時(shí)期”。從魏晉直至唐代,審美主義的文學(xué)觀念逐漸走向繁榮昌盛,在文學(xué)批評(píng)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兩方面均成績斐然,此為“文藝至上時(shí)期”。而從北宋起始,文學(xué)觀念開始復(fù)古,實(shí)用主義重新抬頭,詩歌與散文的復(fù)古主義運(yùn)動(dòng)此起彼伏,此為“仿古低徊時(shí)期”。[24]而在《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史》中,郭紹虞從類似的視角出發(fā),拓清了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史的發(fā)展軌跡。“文學(xué)觀念經(jīng)過了以上兩漢與魏、晉、南北朝兩個(gè)時(shí)期的演進(jìn),于是漸歸于明晰。可是,不幾時(shí)復(fù)為逆流的進(jìn)行,于是又經(jīng)過隋、唐與北宋兩個(gè)時(shí)期,一再復(fù)古,而文學(xué)觀念又與周、秦時(shí)代沒有多大的分別。”[25]從周秦,到兩漢,再到魏晉南北朝,是文學(xué)觀念的演進(jìn)期,從學(xué)術(shù)中析離出雜文學(xué),雜文學(xué)復(fù)窄化為純文學(xué)。而從隋唐直至明清,是文學(xué)觀念的復(fù)古期,雜文學(xué)觀念又重新占據(jù)主流舞臺(tái)。由此可見,雜文學(xué)與純文學(xué)兩大觀念的兼顧,對(duì)中國文學(xué)史的研究來說極為必要。
綜上所述,在有關(guān)“文學(xué)自覺”的四大學(xué)說之中,“春秋文學(xué)自覺說”和“宋齊文學(xué)自覺說”在理論建構(gòu)中尚有缺失,其學(xué)術(shù)價(jià)值不大;而“漢代文學(xué)自覺說”與“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綜合了傳統(tǒng)視角與現(xiàn)代視角,標(biāo)識(shí)出了“文學(xué)”概念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兩次大飛躍,對(duì)中國文學(xué)史與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史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xiàn):
[1] [20]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526,525.
[2] [12] [14] 張少康.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史(上冊(cè))[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132,87,9.
[3] 張少康.論文學(xué)的獨(dú)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6,(2):75-81.
[4] [19] [25] 郭紹虞.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31,54,5.
[5] [7] [15] 趙敏俐.“魏晉文學(xué)自覺說”反思[J].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05,(2):155-167
[6] [17] [22] [24] [日]青木正兒.中國文學(xué)概說[M].隋樹森,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29,38,220,9.
[8] 張哲俊.東亞比較文學(xué)導(dǎo)論[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29
[9] [10] 劉躍進(jìn).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xu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6:14,22.
[11] 周振甫.《詩品》譯注[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36.
[13] 李永祥.“春秋文學(xué)自覺”論[J].汕頭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2):22-27.
[16] [日]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M].許總,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37-39.
[18] 陳鐘凡.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史[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29.
[21] 李澤厚.美的歷程[M].天津: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1:159.
[23] 袁行霈.中國文學(xué)概說[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