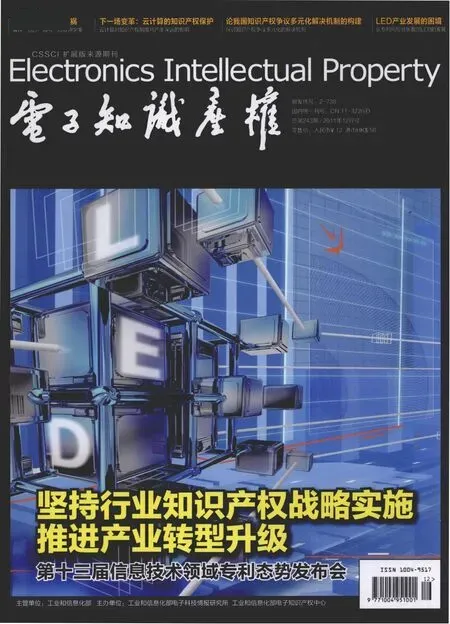迷糊的訴請 尷尬的敗訴評電影《千里走單騎》著作權侵權糾紛案
文 / 祝建軍
[基本案情] 1.具體案情詳見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2010)西民初字第2606號民事判決書,以及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終字第13010號民事判決書。
根據史料記載,“安順地戲”是我國貴州省安順地區歷史上“屯田戍邊”將士后裔屯堡人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種儺戲,是流行于我國貴州省安順地區的一種地方戲劇。2006年6月,國務院將“安順地戲”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5年7月,電影《千里走單騎》在我國公映。國家廣電總局頒發該電影的《公映許可證》顯示,出品人為北京新畫面公司,編劇、導演張藝謀,制片張偉平。電影《千里走單騎》講述的是兩對父子的故事,反映的外景環境為中國云南省的麗江。影片放映至6分16秒時,畫面出現了戲劇表演《千里走單騎》,此時出現畫外音:“這是中國云南面具戲”。影片中戲劇表演者是北京新畫面公司從貴州省安順市詹家屯“三國戲曲演出隊”所聘請的詹學彥等八位演員。在該影片片尾字幕出現的演職員名單中標示有“戲曲演出:貴州省安順市詹家屯三國戲隊詹學彥等八人”字樣。
根據上述事實,原告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認為,被告張藝謀、張偉平、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將安順市詹家屯詹學彥等8人表演的“安順地戲”劇目《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剪輯到電影《千里走單騎》中,但影片中卻將其稱之為“云南面具戲”,導致觀眾誤以為影片中面具戲的起源地、傳承地在云南,“安順地戲”屬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被告的行為侵犯了該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署名權,請求法院判令:張藝謀、張偉平、北京新畫面公司分別在《法制日報》、《中國日報(英文)》刊登聲明以消除影響;北京新畫面公司以任何方式再使用影片《千里走單騎》時,應當注明“片中的云南面具戲實際上是安順地戲”。
針對原告的侵權指控,被告張藝謀、張偉平、北京新畫面公司抗辯稱,電影《千里走單騎》的出品人是北京新畫面公司,其是電影作品的所有人,故應駁回原告對張藝謀、張偉平的訴訟請求。電影《千里走單騎》拍攝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順地戲”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2006年5月,原告無權追溯主張署名權。況且,《千里走單騎》是一部虛構的故事片,而非專門介紹儺戲、面具戲或地戲的專題片或紀錄片,原告不能要求作為藝術創作者的被告承擔將藝術虛構與真實存在相互對接的義務。綜上,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裁判]
北京西城區法院一審認為,“安順地戲”通過世代相傳、修改和豐富,形成了現有的民間文學藝術,其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依法受到國家的保護、保存,任何非法侵占、破壞、歪曲和毀損等侵害行為都應當予以禁止和摒棄。但原告作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在以自己名義提起著作權侵權之訴時,應依照《著作權法》和相關法規的規定行事。電影《千里走單騎》是一部關注人性、親情的故事影片,貫穿全劇表達的中心思想是父子情。就整體影片來說,聯系兩對父子的“儺戲”僅僅是故事的一個引子,并非該影片的重心。被告將真實存在的“安順地戲”作為一種文藝創作素材用在影片《千里走單騎》作品中,并在具體使用時根據戲劇表演的配器及舞臺形式加以一定改動,使之表現形式符合電影創作的需要,為了烘托整個影片反映的大環境與背景,將其稱為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的“云南面具戲”,此種演繹拍攝手法符合電影創作的規律,區別于不得虛構的新聞紀錄片。因此,電影《千里走單騎》未對“安順地戲”產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貶損或者誤導混淆的負面效果,其使用“安順地戲”進行一定程度創作虛構,并不違反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依照《著作權法》第三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原告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不服,向北京一中院提出上訴。北京一中院二審認為,“安順地戲”系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作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門,有資格代表安順地區的人民就他人侵害安順地戲的行為主張權利。本案中,張藝謀、張偉平不是涉案電影的制片者,故其并非本案被控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承擔主體。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主張,“安順地戲”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屬于《著作權法》第六條規定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涉案電影中將“安順地戲”稱之為“云南面具戲”,卻未在任何場合對此予以澄清,其行為構成了對安順地戲這一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署名權的侵犯,違反了《著作權法》對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署名權保護的規定。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署名權是指,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署名權的權利主體應是“作者”,權利客體是具體的“作品”,權利內容是在作品上對作者名稱予以標注。“安順地戲”作為劇種不構成作品,其既不是署名權的權利主體,也并非署名權的權利客體,同時,涉案電影在進行藝術創作時對使用的藝術元素進行相應虛構,亦有其合理性。故北京新畫面公司沒有侵犯“安順地戲”的署名權。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理評析]
本案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因電影《千里走單騎》部分鏡頭中將表演的一段《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安順地戲”劇目)稱之為“云南面具戲”,且未對此予以澄清為由,選擇以“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署名權)”受到侵害作為請求權基礎,要求追究導演張藝謀、張偉平、制片人北京新畫面公司侵害“署名權”的法律責任,結果以敗訴告終。本案與北京法院曾經審理的“烏蘇里船歌”案在案情上有幾分相近,但卻與“烏蘇里船歌”案中原告勝訴存在著巨大差異。2.具體案情詳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書。本案原告為什么會敗訴呢?其有可能勝訴的請求權基礎嗎?這些問題頗值得深思。
一、迷糊的訴請是導致原告敗訴的根本原因
一個知識產權案件發生后,當事人基于民事實體法的規定,對于被控侵權行為人的被控侵權行為可能選擇不同的請求權基礎予以救濟,從而針對一個侵權行為可能有多個請求權基礎。然而與其他民事案件相比,知識產權案件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與技術性,同時隨著社會的進步,知識產權糾紛正變得日益復雜,如此一來,當事人針對已經發生的知識產權糾紛能否進行準確的法律定性,并正確鎖定提起訴訟所要保護的實體權利至關重要,換句話說,在知識產權案件中,原告選擇的請求權以及所依據的法律規范是否適當,將直接決定其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
本案中,原告選擇以“安順地戲”是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被告的行為侵犯了該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署名權),并以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署名權之法律規范,要求被告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原告的該請求權基礎要獲得支持,其必須要首先論證“安順地戲”構成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但實際情況是,“安順地戲”是對貴州省安順地區戲劇的稱謂,其并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戲曲曲目之名稱,而是作為劇種而存在的一種地方戲劇,其代表了該地區戲曲的演唱曲調,是與其他戲曲劇種風格相區別的標志。此種情形如同湖北黃梅和安徽安慶地區的人們所表演的“黃梅戲”一樣,“黃梅戲”亦是戲曲的一個劇種,其在唱、念、做、打等唱腔設計上與京劇等劇種相區別,大家熟悉的“黃梅戲”劇目有《天仙配》、《女駙馬》等。上述事實表明,只有“安順地戲”劇種中某一個具體的戲曲劇目,比如本案中的《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才可能成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而“安順地戲”作為劇種之稱謂,絕無可能被認定為是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正因為如此,本案二審之生效判決認定,“安順地戲”作為劇種不構成作品。但本案原告在訴訟技巧上出現了失誤,誤將“安順地戲”看作是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在原告起訴存在該“致命硬傷”的情況下,由于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署名權是指,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這自然會得出本案二審生效判決所論證的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敗訴的結論,即“安順地戲”作為劇種不是作品,其既不是署名權的權利主體,也并非署名權的權利客體,因此,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的訴訟請求應被駁回。可見,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迷糊”的訴請是導致其尷尬敗訴的根本原因。應當說,二審法院對本案的裁判結論是正確的。
二、原告可能勝訴的請求權基礎
既然原告訴訟請求選擇失誤導致敗訴,那原告有可以打贏官司的請求權基礎供選擇嗎?筆者認為,就本案被告被控侵權行為的表現形式來看,原告不妨考慮以下請求權基礎之選擇:
(一)以“安順地戲”曲目《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署名權)受到侵害提起訴訟
按照WIPO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民間文藝作品是指由具有傳統文化藝術特征的要素構成,并由某一成員國或地區的一個群體或者某些個人創作并維系,反映該群體傳統文化藝術期望的全部文藝產品【1】。在“烏蘇里船歌”案中,被告郭頌在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想情郎》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再創作,改編完成了《烏蘇里船歌》歌曲,中央電視臺將表演該歌曲所制作的VCD光盤上,署名作曲“汪云才、郭頌”,原告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認為,中央電視臺和郭頌的行為,侵害了赫哲族人民依法對赫哲族民間曲調所享有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署名權和獲得報酬權),法院認定被告侵權成立,判決中央電視臺和郭頌再使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時,應當注明“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2】。
基于同樣的原理,原告可選擇以“安順地戲”曲目《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署名權)受到侵害來提起訴訟,應當說,《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是貴州省安順地區的人民在長期勞動和生活中逐漸形成的代表當地人民文化特點和精神風貌的戲曲曲目,應被認定是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在該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可能受到侵害的情況下,鑒于權利主體狀態的特殊性,為維護本區域內人民群眾的權益,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作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門,在本案中有權代表本地區人民的利益,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訴訟。北京新畫面公司作為《千里走單騎》電影的制片人,將《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的戲曲表演,剪輯到電影《千里走單騎》中,以此為引子來牽出影片所要表現的父子親情。筆者認為,電影創作時對所使用的藝術元素進行虛構,是電影常見的表現手法,但并不能一概而論,從影片《千里走單騎》使用《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的戲曲表演場景來看,其是電影主人公正在觀看電視里表演的上述戲曲節目,通過畫外音介紹該戲曲表演屬于“云南面具戲”,對于觀眾來說,會產生該戲曲節目屬于“云南面具戲”的認知。因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通常不歸屬于特定主體,而標注“安順地戲”是這類作品作者的適合署名方式,由于北京新畫面公司沒有標注“安順地戲”,故屬于對《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署名權)的侵害。鑒于此,將北京新畫面公司的行為認定為侵害署名權的行為,并責令其再使用這些戲曲表演鏡頭時,應以適當方式表示該戲屬于“安順地戲”,并無不妥,這有利于平衡雙方利益。《千里走單騎》案的一、二審判決均認為,北京新畫面公司以畫外音介紹該戲曲表演屬于“云南面具戲”,這符合電影虛構創作的手法,故并無不妥。筆者認為,該觀點值得商榷。
(二)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標示來源權益”受到侵害提起訴訟
筆者承認,以此種請求權基礎提起訴訟屬于“突破式”嘗試,但在目前的民事法律框架內對該請求權基礎進行探討是有意義的。
我國已于2004年8月28日加入了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管理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該公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權利研究最重要的國際組織,該組織制定的《傳統文化表達修訂案》和《傳統知識修訂案》兩個文件中規定的內容,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管理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規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完全吻合。而《傳統文化表達修訂案》和《傳統知識修訂案》中雖沒有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人享有的權利內容,但是其通過規定禁止不法行為,間接承認權利人享有一項“標示來源權益”,即使用或改編特殊的文化或精神價值或重要性的傳統文化表達(非言語、姿勢、名稱或符號)時,未經事先告知同意,應以適當方式告知傳統文化表達的來源地區【3】。從民法原理來看,民事權利必須由民事立法明確規定,而民事權益是由一個社會法觀念認為應予保護的利益,該利益還沒有通過民事立法予以類型化,對它的保護乃是對違反法律基本理念行為的制止。現代民法對民事權益僅僅是消極承認,這種承認主要體現為對其所受到的侵害提供救濟,而民法的一般原則是當事人提出侵權救濟的直接法律依據【4】。基于該原理,筆者認為,基于民事法律及政策的精神,在我國的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不妨參考《傳統文化表達修訂案》和《傳統知識修訂案》的規定,將與“標示來源權益”之相同或類似的內容,看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人享有的一項民事權益來保護,這完全符合我國民事立法及政策的精神,同時,這也是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事保護的嘗試。由于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具有在法律出現空白,而某特定的民事權益依據法律之精神又需要予以保護的情況下,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彌補立法漏洞或法律規定不足之功能,故該法條可以成為人民法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人正當民事權益的法律依據。
2006年6月,國務院已將“安順地戲”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該批準時間是在北京新畫面公司拍攝完《千里走單騎》電影之后,但根據《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原告有權要求北京新畫面公司再使用《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戲曲表演鏡頭時,應以適當方式表示該戲屬于“安順地戲”,既表示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來源。比如,為保持電影《千里走單騎》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可以在保留影片原有畫外音鏡頭的情況下,在片尾或其他場合標明影片中的“云南面具戲”的藝術元素來自“安順地戲”。
【1】 管育鷹.知識產權視野中的民間文藝保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
【2】邵明艷.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法律保護——《烏蘇里船歌》糾紛案法律問題探討[M]//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編.奚曉明主編.知識產權審判指導.(2009年第2輯).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125-126.
【3】李秀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保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6-80,186.
【4】劉生亮.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功能論[J].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2005:5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