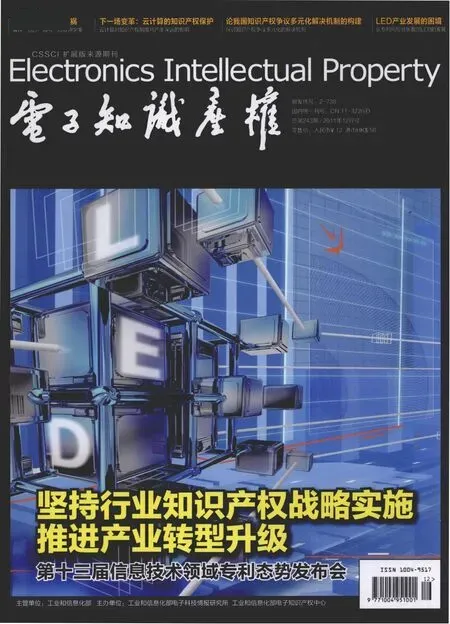知識產權仲裁制度的困境與出路
文 / 楊濤 楊斌
我國知識產權的保護實行行政執法保護與司法保護并用的“雙軌制”,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途徑主要為司法途徑和行政途徑,當事人間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則主要以司法途徑為主。知識產權的高度技術內容及其商業化本質,使得知識產權訴訟成為技巧最復雜、成本最高昂、耗費時間也最冗長的救濟程序,終而引發各界對于知識產權訴訟制度的反思,開始強調應循公平、合理、迅速、經濟、專業的糾紛解決程序來排解知識產權糾紛。知識產權仲裁作為一種“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通過對知識產權仲裁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討,以期對我國知識產權仲裁法制建設提出有益的建議。
一、知識產權糾紛與可仲裁性問題
可仲裁性是指某項爭議依法可適用仲裁方式解決。可仲裁性問題與公共政策密切相關, 是一國通過其國內立法對仲裁范圍所施加的一種公共政策限制【1】。知識產權糾紛的可仲裁性要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個層面是知識產權糾紛能否適用仲裁的問題,在起初人們認為知識產權糾紛不可仲裁,因為人們認為知識產權是脫胎于封建君主授予的“特許權”,產生之初便有“公法”性質【2】。在1994年Trips協議中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確立【3】,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的成立,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為知識產權糾紛可仲裁性疑慮掃清了障礙。
如今籠統的討論知識產權糾紛的可仲裁性意義已經不大,討論的重點在于第二個層面,即哪些知識產權糾紛適用仲裁的問題。根據仲裁法的理論及各國實踐,凡是當事人能自由處分的爭議事項或涉及經濟利益或具有財產性質的爭議事項,均可通過仲裁加以解決【4】。但是知識產權糾紛有其特殊性,其是一個外延非常廣泛的概念,從仲裁法的角度來看,需要將其進行類型化,并在類型化的基礎上討論其可仲裁性問題。關于知識產權糾紛的類型,從糾紛性質著眼,知識產權糾紛可分為權利得喪糾紛、權利歸屬糾紛、權利交易糾紛、權利侵害糾紛【5】;一般來說可仲裁性問題的討論是以糾紛性質為劃分標準,集中在知識產權權屬糾紛、知識產權合同糾紛和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三方面。
對于知識產權合同糾紛的可仲裁性在各國都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完全符合有關協議上可仲裁性要標準,具有協議上的可仲裁性。而對于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和權屬糾紛,各國仍存較大差異。
對于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否認,有人認為侵權糾紛應該排除在仲裁之外,理由是侵權關系中一方享有絕對權利,是受侵害的一方, 另一方由于實施侵害行為而有過錯,雙方地位不平等,不適于仲裁解決;另外侵權行為的侵害對象包括人身權,而人身權案件是不在仲裁適用范圍之內的。因此,侵權案件也不應該在仲裁的適用范圍之內【6】。這種否認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越來越站不住腳,從理論上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三條的規定,其并未被明文排除,而在《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明文規定著作權糾紛可以提交仲裁的,當然也包括著作權侵權糾紛;1.《仲裁法》第三條的規定為“下列糾紛不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二)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著作權糾紛可以調解,也可以根據當事人達成的書面仲裁協議或者著作權合同中的仲裁條款, 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當事人沒有書面仲裁協議,也沒有在著作權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的, 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另外,1958年的《紐約公約》第二條承認“非契約性糾紛”具有可仲裁性,2.值得注意的是,1958 年《紐約公約》還規定了商事保留條款,其締約國可以聲明“本國只對根據本國法屬于商事法律關系的爭議,不論其是否為契約性質,適用本公約。”而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即屬于非契約性糾紛,應當承認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這與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也是相吻合的。從立法和司法實踐看,以美國為例,其司法界對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所持的態度從反對逐步轉為支持。美國國會于1983年頒布的《美國法典》第35章第294節最終明確了專利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3.35 U.S .C. 294 (Voluntary arbitration)并促進了法院對版權和商標權侵權糾紛可仲裁性的承認。
關于知識產權權屬糾紛,其涉及到知識產權有效性問題,與一國的“公共政策”和行政權力緊密關聯,各國的規定存在很大差異,在加拿大、比利時、英國、美國和瑞士等少數國家,所有的知識產權爭議都可以交付仲裁,不存在否定性的障礙。而意大利、阿根廷、俄羅斯等國家在法律中規定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屬于國家法院專屬管轄的范圍,不具有可仲裁性。根據我國《仲裁法》的規定,“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不具可仲裁性,知識產權有效性問題即屬于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所以不可仲裁。我國采公私法二元制,法院尚且無權自為判斷知識產權有效性,遑論仲裁機關。
總的說來,我國知識產權糾紛可仲裁性問題在理論上業已厘清,相關的立法和實踐與國際普遍做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那些與我國制度傳統相違背的立法主張其的現實意義不大。
二、知識產權糾紛仲裁的比較優勢
知識產權仲裁作為一種獨特的糾紛解決機制,越來越受到糾紛當事人的倚重,這說明了其擁有不可比擬的優勢。知識產權仲裁屬于訴訟外解決機制的一種,和其他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相比,仲裁裁決具有很強的法律效力,根據《仲裁法》第五十七條的規定,裁決書自作出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仲裁裁決的效力體現在,當事人不得就已經裁決的事項再行申請仲裁,也不得就此提起訴訟,而且其他任何機關或個人均不得變更仲裁裁決,仲裁裁決具有執行力,這些是行政調解、民間調解等所不能媲比的。
訴訟判決固然亦有如此之法律效力,但是知識產權仲裁和訴訟相比而言,比較優勢也較為明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糾紛解決的迅速性方面,知識產權訴訟,尤其是專利訴訟,所可能耗費的金錢與時間成本龐大,為外界所詬病。專利侵權訴訟中,侵權賠償責任之成立與否乃以權利有效存在為前提。由于專利權爭議案件爭訟時,往往同時涉及權利有效性與侵權賠償的問題,而侵權賠償責任的成立與否,又以權利有效存在為前提。這使得同一糾紛在不同程序間往返,使得訴訟冗長復雜,并且可能遭有心人利用,企圖以冗長程序拖延對方產品的上市時間,或通過訴訟手段,造成對方商譽或使消費者對該產品的信心產生動搖,作為商業上的競爭方法,不當影響對方商業上的獲利。糾紛解決貴在迅速,如糾紛無法迅速獲得解決,僅是加深當事人的損害而已,此即所謂“遲來的正義并非正義”。而知識產權仲裁,由于其程序富有彈性,雙方當事人對于程序的進行能有主導的權利,故在時間上相較于訴訟程序,較為便捷、快速。
其次,在于糾紛解決專業性。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其爭議常涉及復雜的專業技術,訴訟制度于處理知識產權案件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即在于法官專業性不足【7】。而在仲裁制度中,仲裁人將從特定的名單中選任,而仲裁人能被選入該名單中,最基本除需具備公正的態度外,多半因具備所涉及爭議領域所需的背景知識或經驗。在仲裁員選任的程序中,雙方當事人可相對自主地決定將由誰來擔任仲裁人,此時雙方當事人選擇考慮的重點,除因對該仲裁員具有足夠的信任感外,多半亦同時認可其具備爭議所涉的相關專業知識、經驗與判斷能力。正因為仲裁員在專業上的知識和判斷力,其對爭議的分析能夠迅速且更深入問題的核心,進而協助雙方當事人找尋適合的解決方法。仲裁制度要求調解人的資格背景有相關的專業性,對于爭議問題能提供更深入的分析,此為仲裁制度吸引雙方當事人使用的重要誘因。
再次,在于糾紛解決的保密性。爭議解決過程中所涉及的信息與文件對于當事人的名譽、商譽或其企業未來發展可能皆有相當大的影響,當事人雙方將爭議付諸法院解決時,對于雙方當事人之時間、精力、名譽、商譽、伙伴或客戶關系等會造成一定損害,若對解決糾紛過程中涉及隱私或商業發展的信息、文件又無法提供相當的保護時,將對雙方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且無助于爭議解決。仲裁程序最為可貴且重要特點之一即在于其秘密性,以解決當事人對于此方面的顧慮。
最后,在糾紛解決的主導性方面,訴訟制度有嚴格的程序規定,從案件的受理、開庭、判決至最后階段的執行,當事人皆須遵守,無任何協商的余地。而仲裁程序十分尊重當事人意見,賦予當事人相對主動的地位,如對于仲裁員的選任等,當事人皆可展現其自主性,因此,若雙方當事人選擇仲裁制度作為爭議解決的方法時,相較于訴訟制度,在解決紛爭的過程中能享有相對主動的地位。
三、知識產權糾紛仲裁的現實困境
廈門仲裁委員會知識產權仲裁中心與武漢知識產權仲裁調解中心的成立,拉開了我國知識產權仲裁專業化的帷幕。從當前的實踐情況來看,知識產權糾紛采取仲裁方式來解決的案例還不是很多,知識產權仲裁尚未發展成為常態【8】。造成這種局面可能是社會對知識產權仲裁的認識和理解還不夠,但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應該是公眾對其接受程度較低,仲裁意愿不強。仲裁意愿不強可以說是知識產權仲裁法制發展的現實困境。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響了民眾的知識產權仲裁意愿呢?
首先,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科技和商業領域中,行為的合法與非法的劃分不是那么直觀,即使是糾紛產生后在解決時也難以確切地劃分合法與非法的界限。 對于知識產權糾紛而言,特別是侵權糾紛,往往權利人向侵權方發警告函,對方當事人又否認侵權,糾紛雙方各執一詞造成敵對情緒越來越濃,最后根本就不會有仲裁意愿了,非得在法庭上一決高低。
其次,知識產權的獨占性使得知識產權的商業戰略地位突出,知識產權權利人大多有意將其獨占性發揮到極致,通常傾向于通過訴訟將直接威脅到自己市場地位的競爭對手永遠的逐出競爭市場,或是迫使對方在法律壓力下和解、支付巨額許可費。并且許多人認為同意進行仲裁是一種示弱的表現,代表自己的案件立場并不堅強【9】。在競爭極度激烈又充分商業化的知識產權戰場上,企業絕不容許發生“未戰先竭”的形象,于是企業在面對知識產權糾紛時,寧可砸重金訴訟到底,也不愿意透過平和、便利的仲裁程序來解決糾紛。在知識產權糾紛的戰場上,通常呈現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局面,通過訴訟方式恃強凌弱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第三,知識產權糾紛主要是為市場目的而起,企業間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可能不僅僅著眼于糾紛解決程序本身或糾紛解決結果。知識產權人提起訴訟,有時是為了累積“知識產權訴訟強者”的形象,以期下次不用提起訴訟即能達到訴訟目的【10】。知識產權人通常借助訴訟方式,讓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研發能力、知識產權優勢,塑造捍衛知識產權的形象,此外,借助訴訟來釋放自己可能采取捍衛權利舉動的信息,以達到恫嚇競爭對手的效果,從而達到影響同一產業的其他潛在競爭者甚至產業鏈上中下游的各企業并左右市場的意圖,甚至當事人在訴訟中誘使對方于應對時犯下致命的錯誤,從中套取對己有利的市場信息或訴訟信息【11】。
第四,仲裁程序中的證據調查往往不能滿足當事人的需求,仲裁是一種較訴訟制度來得平易、有彈性且相對開放的程序,仲裁庭于調查證據時通常采取彈性作法,如美國仲裁協會專利仲裁規則第30條第2項即規定仲裁人無須百分百依循法定證據程序。知識產權糾紛的當事人及律師,認為在知識產權仲裁案件中如缺乏完整的證據調查規則,雙方將陷于不斷的“專家大戰”【12】。還有人認為仲裁庭在調查證據程序中,未能緊守證據方法、證據能力的要求,以至于一些于訴訟程序中經過嚴格的證據篩選程序后可能被淘汰掉的證物,于仲裁程序中還能作為有利證據使用,造成當事人無法基于對于證據法則的一般性認知,而對仲裁結果做出正確的預測,也因此對仲裁判斷的質量與可信度產生質疑。
第五,仲裁裁決與終局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其終局性可以帶來糾紛解決的高效率,這個優點向來為“非訟糾紛解決機制”(ADR)提倡者所贊揚,但仲裁判斷的終局性,對于知識產權糾紛而言是一把雙刃劍。知識產權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其權利狀態的穩定性相對較弱,尤其是專利權,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當事人還有可能通過上訴程序等途徑爭取有利的判決,倘若利用仲裁程序解決糾紛,因仲裁程序一次終結,當知識產權權利狀態發生變化后,對方當事人相對來說就失去了與訴訟中的上訴類似的補救機會。
第六,仲裁的一大特點就是“專家斷案”,仲裁員是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能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尋求個案解決的最佳方案。但是我國現有的《仲裁法》并不能有效支撐知識產權仲裁,法律規定“仲裁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中,法律、經濟貿易專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12條。這并沒有考慮到知識產權糾紛的特殊性,顯然與知識產權糾紛的技術性不甚匹配。知識產權是所有領域中專業性最強的,它的糾紛所涉及的專業知識面極其廣泛與深入,一個專利發明有可能是某個領域中的人窮其畢生精力研究出來的,所以有必要強調知識產權仲裁員的相關技術背景。
最后,隨著知識產權國際糾紛的趨多,其對知識產權仲裁的需求也越來越旺盛。但是在知識產權仲裁法律適用方面,我國沒有完整的法律,沒有關于知識產權仲裁法律適用的沖突規則,仲裁員通常根據《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的規定(即根據事實、依照法律和合同,參考國際慣例,并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則,獨立公正地作出裁決)審理仲裁案件,這無疑給知識產權仲裁的實際操作增加了困難。
四、完善知識產權仲裁制度的路徑
當前知識產權仲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就是仲裁意愿不強,除了是由于知識產權糾紛和仲裁本身的性質使然,很大程度上還是與知識產權仲裁法制不完善有關。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仲裁法制,可以從以下幾點入手。
首先,修改和完善知識產權仲裁的相關法律。無論是從國內仲裁立法、國內仲裁實踐還是從國際商事仲裁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國現有的《仲裁法》已不能滿足當前的知識產權仲裁需要,也與我國的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目標嚴重不符,所以修改和完善相關仲裁法律法規,融入知識產權仲裁的相關規則,并明確知識產權仲裁的范圍、管轄,以及配套的證據規則等。
其次,加強知識產權仲裁隊伍的建設。由于知識產權仲裁具有很高的技術性和專業性,因此就需要一批專業化的仲裁隊伍來推動知識產權仲裁行業的發展。專業化、專職化或穩定化的仲裁隊伍依靠當事人自己的選擇和實踐經驗, 為知識產權仲裁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完善的運行機制。
另外,建立知識產權行政與知識產權仲裁對接機制,積極促成仲裁機構與行政機關合作。知識產權行政保護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一大特色,實際上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知識產權局、工商局、版權局有意愿讓更多的知識產權糾紛通過仲裁方式來解決,行政機關一方面可以引導知識產權合同當事人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另一方面可以在知識產權侵權處理時鼓勵糾紛雙方訂立仲裁條款,還有就是在知識產權行政調解中鼓勵糾紛雙方訂立仲裁協議提交知識產權仲裁。
最后,加大知識產權仲裁的宣傳力度。盡管大多數知識產權糾紛都可以仲裁解決,但是現在我們能看到的知識產權糾紛采取仲裁方式來解決的案例還很少,這說明社會對知識產權仲裁的認識和理解還不夠,接受程度也較低,因此,仲裁機構和知識產權管理機構應加大對仲裁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方面的宣傳,積極引導和促使當事人選擇仲裁方式來解決雙方的爭議。
知識產權性質的復雜性決定了知識產權糾紛的多樣性,知識產權糾紛的多樣性決定了其解決方式的多元性。知識產權仲裁不同于其他糾紛解決方式,從資源配置角度來看,其為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選擇。但是我國知識產權仲裁事業起步較晚,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尚面臨不少困境,所以需要更多地借鑒國際慣例和各國的成功經驗,以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仲裁法制。
【1】王德玲.爭議可仲裁性問題探究[J].山東社會科學,2006(7): 60.
【2】鄭成思.知識產權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
【3】吳漢東.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J].法學研究,2003(3 ): 66.
【4】孫移芳.關于我國知識產權仲裁的幾點思考[J].經濟研究與參考,2010(41):69.
【5】謝銘洋.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M].臺灣:翰盧圖書出版社,2002: 16.
【6】張建華.仲裁新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98.
【7】Julia A. Martin. Arbitrating in the Alps Rather Than Litigating in Los Angeles: The Advantage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Specific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J]. Stan. L. Rev. 1997:(49)917, 937.
【8】徐妤.知識產權仲裁的理論與實踐[J].仲裁研究,2008:66.
【9】Marion M. Lim.ADR of Patent Disputes: A Customized Prescription, Not An Over-the-counter Remedy[J]. Cardozo J. Conflict Resol.2004,(6)956.
【10】陳郁婷,周延..跨國專利侵權訴訟之管理[M].臺灣:元照出版社,2007: 6.
【11】周延鵬.虎與狐的智慧·智慧資源規劃9把金鑰 [M].臺灣:天下遠見出版社,2006:331.
【12】Gregg A. Paradise. Arbitr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Encouraging the Use of Arbitration through Evidence Rules Reform[J]. Fordham L. Rev. 1995:(64 )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