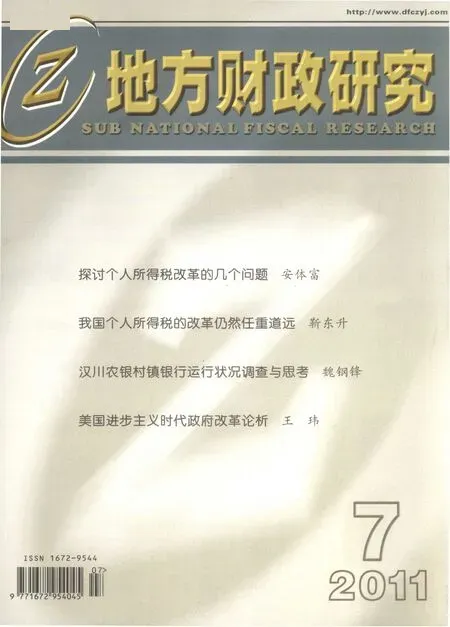美國進步主義時代政府改革論析
王 瑋 蘇云婷
(1.東北財經大學,大連 116025;2.大連交通大學,遼寧 116081)
1978以來,我國先后進行過多次大規模的政府改革,改革的力度、廣度和深度也在不斷加大。盡管如此,政府改革的相對滯后仍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之一,政府改革的實際進展仍不容樂觀,甚至在某些領域還舉步維艱。如何才能有效推進政府功能、結構及運作機制的改革,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所需要的政府形態?就像政府改革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一樣,審視、思考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當然也是多維度的。
一、進步觀念的歷史回溯與美國進步主義的時代特征
作為一種觀念與歷史、現實相互交叉的概念,“進步”觀念和哲學、宗教、歷史、政治等諸多問題千絲萬縷地交織在一起。在不同的歷史語境和意識形態背景下,它的內涵可能會迥然不同,從而增加尋求進步的統一內涵的難度。然而,這些困難不僅沒有妨礙對進步觀念性質的探討,反而進一步凸顯出對其繼續研究的必要性。在美國,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期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之所以被冠以“進步”、“進步主義”之名,顯然有其特定的精神內涵和時代特征。
早在希臘和羅馬時代,人類就萌生了進步的觀念,它的本意是自然或人類所固有的一種本質或傾向,即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循序發展過程,后面的階段總要優于前面。這一過程是對人類社會真正目的的接近,從而不斷“揭示出人類誕生之處在愚昧、悲慘和恐懼之中,爾后在科學和藝術方面,在了解自身方面,廣而言之是在知識方面緩慢而不斷地提高到更高的層次。”亞里士多德就把城邦的成長視為接近自然的、良善的過程。也就是說,城邦比家庭、村坊等社會組織形式更好,更接近人類和政治的本質。到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通過對時間觀念的神學闡釋,在進步觀念中添加進必然性的內涵。
在牛頓時空觀念和笛卡爾二元論哲學的基礎上,進步觀念獲得了近代意義,并在啟蒙運動中發展日趨成熟。這種近代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科學認識論意義上的進步觀念。進步成為一個操作性的語匯,強調通過技術上的進展、認識和探索世界能力的提高,從而促使人類的生活不斷臻于完善,“它現在被賦予了一種新近獲得的對于無限性的意識,并且隨著物質成就的不斷取得而大大強化了。”二是社會歷史觀意義上的進步觀念。孔多塞、達爾文、康德、黑格爾等思想家以近代以來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基本現實為基礎,賦予了進步觀念以社會歷史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進步就是所有國家的人民都可列入向上秩序之中的歷史,就是人類進步相互沖突的歷史,最終也是全部的發展概況的因果必然性的歷史”。三是政治生活意義上的進步觀念。在社會歷史觀意義上,進步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線性發展,而人類歷史的線性發展,又意味歷史就是趨向無限好的終極目的的過程。作為進步觀的一個政治后果,“歷史”等同于啟蒙的進步和理性,從而也成為政治合法性的一種來源。為此,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斯坦利認為,“進步觀念既是一種歷史發展的規則,一種歷史哲學,作為其結果又是一種政治哲學。它將對歷史的一種描述性分析與一種認識這種發展是正確與良善的哲學立場結合起來,而且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這種立場被用于政治目的。”
如果說科學、理性、進步等啟蒙觀念在英、法、德等歐洲國家激起的思想火焰更為熾熱的話,那么,美國這個后起的新大陸則為它們提供了天然的實驗基地。無論是洛克的自由思想、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觀念,還是潘恩的革命常識宣傳、百科全書學派等啟蒙哲學,在美國都得到了比它們的原產地更加熱烈的歡迎和實踐。美國的建國和發展史表明,“由于將近200年的擴張、持續的西進以及幾乎清一色的自由理性主義政治思想傳統,進步觀念對美國人具有特別的魔力。很少有政治家不去涉及我們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也絕少有哪個州的演講或會議基調不去談論將進步作為美國人生活的極大目的之一。事實上,美國可以說是少數這樣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之一——它們的公民仍然熱誠相信人類理性的運用可以增進人類福祉,或者每個新的發現都會有益于大眾”。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這片理性建構和進步觀念更加深入人心的國土上,最終爆發了史稱“進步主義”的改革運動。
作為一種“主義”的社會運動而言,進步主義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內涵和時代特征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首先,進步主義被理解為一套面對工業主義(或工業制度)的批判或改良態度。毫無疑問,對公司的種種犯行發泄怒火以及對工業時代冷漠的逐利行為深惡痛絕,是進步主義追求加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改革進程的最初動力。但與此同時,進步主義自身也的確存在強有力的矛盾或反諷:改革從民眾對工業主義種種壓迫、剝削的憤怒中獲得支持,卻同樣也支持那些適應甚至縱容工業主義的人們。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日漸接受了大型工業、商業和金融企業以及薪酬和工廠管理體制。進步主義的改革,并非要求取消或廢除現代經濟制度,而是謀求在工業化時代改善和提升生活狀況,要求工業主義承擔某種程度的社會責任。
其次,進步主義體現著改革者對追求社會進步的信念和決心。他們相信,人類通過有意識地行動來改善生存環境和狀況能力。這些十九世紀末期的改革者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憂心忡忡:除非采取這些重大的改革舉措,否則一切都將更加糟糕。他們堅信,改革會保護人們免受工業主義的傷害,使社會狀況更加符合人性的要求。對于進步主義時代的改革者而言,實現這些目標意味著,必須正視赫伯特·斯賓塞并駁倒它的絕對“真理”,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與演化進程并不相悖,而是自然變遷的組成部分。進步主義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們寫就了大量的普及讀物來譴責自由放任,并宣傳積極國家的觀念。
再次,進步主義強調來自公共權威諸如政府的干預是推進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首先意味著干預經濟和社會事務,以控制自然的力量,強加于它們某種程度的秩序。在那個時代的改革中,這是顯而易見的,從商業監管到禁酒法令。干預主義可能是私人的,也可能是公共的。如果可能的話,大多數進步主義者會傾向通過致力于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志愿組織,來非強制性地采取行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部分進步主義的改革只有通過立法或公共控制的途徑才能實現,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進步主義要求公共權威諸如政府對那些原本資源組織開始從事的事務承擔干預責任。這些不僅要求政府功能的調整和擴張,還意味著政府結構的優化和重組,意味著包括文官錄用、科學管理、資源汲取與開支在內的整個政府系統的改革。換言之,進步主義最終成為一種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來糾正傳統工業主義發展的種種弊病,來推進社會更加文明和進步的改革運動。在這個改革運動中,政府通過自身結構、功能的改造和重塑,成為使改革得以成功的關鍵力量。
二、美國進步時代政府改革為當代中國提供的獨特視角
對于當今世界而言,不了解中國,就無法談論世界問題。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只有深刻了解世界,才能夠更好地繼續前行。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不僅需要深刻、清醒地認識自身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還需要通過比較視野去觀察、分析和研究國外改革和發展的經驗、教訓。比較的目的并不在于對觀察和研究的對象妄加評判,更非用于意識形態的批判或否定,而是希望更充分地理解其他國家或地區社會變革的一般特征和規律,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發生的變化以及未來發展所面臨的形勢和問題。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布朗指出,中國的現代發展“之所以舉世無雙,是因為沒有其他文化、沒有別的政治制度、沒有其他民族與其相似;也因為中國現代化所處的歷史時期與眾不同。中國的現代化必將區別于任何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這一點為歷史學家所深信不疑……同時,中國告別傳統向現代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轉變,也必然會顯示出與世界其他地區(如:歐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其他亞洲國家)現代化經歷相似之處。”有著現代化經歷的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過程總會給那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或地區一定程度的“似曾相識”之感,后者總可以希望從前者的經歷和過程中獲得有益經驗或珍貴教訓。
作為解決社會需求的主要載體,政府總要不斷地調整自身的結構和功能,以適應變革時代社會需求的復雜性、動態性和多樣性。因此,“對于政府部門來說,變革與其說是一種特例,不如說是一種慣例。只要有一個不完美的政府,人們就會持續不斷地尋求理想的治理形態。”大概而論,相同或類似的歷史經歷、發展階段和變革訴求,總會孕育出相同或類似的社會需求以及改革愿望,也會推動政府改革朝著相同或類似的方向發展。亞里士多德曾說,“事物發展到后一階段是就比前一階段更充分地表現出其真正的‘本質’是什么。”顯然,從現代化國家或地區政府改革經歷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對于當代中國的政府改革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需要強調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夠取得成功,也不是所有的經驗都能夠借取和應用。美國公共行政學家羅伯特·達爾就曾指出,“對某一民族國家環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做出的概括,不能普遍化并運用于不同環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一種原則有可能適用于不同的框架,但是,原則的適用性只有在對那種特殊框架進行研究之后才能確定。”這意味著,從現代化國家或地區汲取政府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同樣需要選擇和甄別。選擇和甄別必須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可比性,即選擇的對象需要具備相同或類似的歷史經歷、發展階段、社會需求和變革訴求,對其政府改革一般特征、規律和方向的總結和歸納能夠為當代中國政府改革提供參照;二是針對性,即選擇的目的在于為當代中國政府改革的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思路,對其政府改革的進行比較研究不是把一個國家的改革經驗簡單地予以普遍化,然后應用到其他國家或地區,而是關注其改革的發生邏輯、可能性和約束條件,以及有針對性地汲取其提供的現實啟示。
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政府改革就是這樣可供選擇的研究對象。首先,進步主義時代是美國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重要時期,經濟增長突飛猛進,社會結構急劇變遷,行政效率低下,官場腐敗猖獗,國家建設和持續發展危機重重。無論在歷史階段、發展背景還是社會問題和改革需求等方面,都與當前中國政府改革的背景、現實和問題具有強烈的可比性。其次,進步主義時代的美國政府改革是一個成功的歷史案例,即通過政府改革成功地解決了國家建設和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深刻的問題,為美國政府轉型乃至整個國家20世紀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美國歷史學家赫伯特·D·克羅利指出,“美國進步時代的改革就是這樣一段歷史:面對著巨變后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形成的各種挑戰,進步時代的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國家治理結構,進而改變了美國社會,從而相對成功地應對了社會、經濟變遷所構成的挑戰。”總結改革的成功經驗,汲取改革的失敗教訓,二者雖然同樣都有價值,但前者明顯具有正向的意義。
在最寬泛的意義上,進步主義時代美國政府的改革是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尤其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移民運動伴隨著的經濟社會發展。群體利益的糾結,城市人口激增和集聚,多元文化的沖突,社會對抗的激烈和頻繁,共同呼喚采取公共權威行動,以緩解社會矛盾和沖突,并提供更多體面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務設施。所有這一切,都集中地反映在政府結構和功能的改革訴求上。為解決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應對強烈的改革訴求,美國政府在進步主義時代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對于這種轉變,羅伯特H.維貝精確地將之描述為“政府大規模且持續地卷入社會事務之中”。從政府體制到政策內容,無不反映著這種深刻的變化。在十九世紀,政府一般關注于獨具特征的群體和地區事務,經濟政策廣泛地包括資源配置以及推動企業、產業發展的特許權,而較少注意這會加重獲取收益的成本,以及補償那些由政府決策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使得另一部分利益受損的人們。雖然商業的特許管制已為人所周知,但實際執行的管制一般很少。到十九世紀末,政府開始明確地考慮利益沖突問題,并承擔起通過管制、行政和規劃來緩和沖突的責任。政府之前就是發放什么東西,但現在分配決策被管制、調整等更有意義的手段所補充。換句話說,分配和管制政策的混合改變了。在進步主義時代,許多經濟政策的重大斗爭——例如,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其實就是在爭論應該如何正確地把兩者混合起來。
政府的功能擴展伴隨著權力結構的變化。不斷擴展的功能并未托付給國會,賦予給新的行政執行部門。在當時,盡管在哪個層面上國會都是主導性的權力機構,但由于執行權力的擴張以及政府創制了大量新的委員會、委托機構等分支機構,國會很快發現他們的權力大大縮減了。20世紀初,政府機構似乎贏得了更多人的信任。正如1910年紐約州州長查爾斯·埃文斯·休斯(Gharles EvansHughes)所說的,“執行機構是從利益和分區的競爭、沖突中作為人民整體的代表脫穎而出的。”由于代表相互抵觸的選民利益,立法機構的權力天生就是碎片化,而執行機構似乎有能力把它們統一起來。在進步主義時代,各級政府通過了不計其數的進步改革措施,擴大了執行機構在任命、控制官僚過程以及創制立法等方面的權威。除此以外,傳統機構改革方面取得的創新極其重要,一些新的執行機構紛紛建立。這些執行機構、委員會配備了專家,被授予相當獨立的調查和執行權力,從立法機構那里獲得了舊有的公共職能,也承擔著新的責任。這些成立的實體機構首要的——包括那些為其他機構做鋪墊的——就是那些委員會,它們被建立起來以監管稅率、公共服務設施和交通企業。
在走向積極國家、擴展政府功能的道路上,當時的美國并不孤單。在為應對新的情勢而進行政府調整方面,一些歐洲工業化國家的確走在了美國的前面。甚至有些美國學者也認為,19世紀后期的許多時候,美國人都是在觀察和照搬歐洲的政策。然而,盡管世界范圍內的政府功能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進步主義時代美國政府改革還是具有其獨特特征,諸如對國家權威欲迎還拒的矛盾態度,總統與國會之間的權力此消彼長,以及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威并行不悖的擴張,等等。這些特征與美國建國后政治制度的設計、政治思想的傳統甚至宗教觀念都有深刻、復雜的關系,但不容置疑的是,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深深地嵌在進步主義時代美國經濟社會的轉型訴求,以及政府改革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社會精英、社會民眾的政治訴求、行動策略的復雜影響和后果當中。
總之,總結和研究美國進步主義時代政府改革的背景、過程、特征,闡明其中的改革發生邏輯以及動力、阻力等各種復雜的約束性條件,對于關注和求解當代中國政府改革難題,可以提供獨特的視角和思路。
三、美國進步時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分科化趨勢
每一門社會科學都可能與它所關注的社會現實發生相互聯系的興趣點,但某一社會歷史時期內經濟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卻從來不存在學科上的邊界。從各自不同的知識領域和學科背景出發,歷史學家、政治學家、行政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對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政府改革問題進行了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鴻篇巨制層出不窮。不同學科對美國進步主義時代政府改革研究的介入和深化,不僅反映出政府改革的復雜性以及它所涉及或引發問題的廣泛性,而且還導致學術界就此問題研究的學科歸屬乃至學術觀點等方面仍然充滿爭議或分歧。這些爭議或分歧的背后,包括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諸如理論視角、分析框架、政治立場、價值觀念甚至研究者個人的生活經歷等。但是,還有一個原因不容忽視,即不同學科在研究領域和方法論上的差異,其實質就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分科化問題。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無論是研究人類世界還是研究非人類的自然界,人們都要受制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是,在我們理解現實時,我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現實……任何現象都有數不勝數的側面,我們能夠把同一現象按照它所顯示的各個側面做出多種分析。因此,任何一種分類方法所能把握的只不過是它所拼湊的一種現象的一個片段。”這里,湯因比所謂“分類方法”的實質,就是社會科學制度化過程中的分科化趨勢。華勒斯坦指出,“十九世紀思想史的首要標志就在于知識的學科化和專門化,即創立了以生產新知識、培養知識創造者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結構。多元學科的創立乃基于這樣一個信念:由于現實被合理地分成了不同的知識群,因此系統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專門的技能,并借助于這些技能去集中應對多種多樣、各自獨立的現實領域。”“學科的制度化進程的一個基本方面就是每一個學科都試圖對它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進行界定,尤其是要說明它與那些在社會現實研究方面內容最相近的學科之間究竟有何分別。”在這一進程中,在經驗科學和理性主義的知識框架內,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作為獨立的學科紛紛得以創立并迅速發展,以探尋普遍法則為己任的社會科學家急于為他們各自的學科領域劃定范圍,并從根本上把這些領域彼此加以區分,無論在研究主題還是在方法論方面,都是如此。“經濟學家堅持ceteris paribus(其他條件均同)假設的有效性,以便去研究市場的運行機制;政治學家僅僅關注政府的結構;社會學家則著重研究那個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所忽略的新興社會領域。”從嚴格意義上講,知識的學科化和專門化是十六世紀以來就已成形的知識演進路徑,社會科學研究的分科化趨勢只不過是這一路徑到十九世紀后半期的產物而已。然而,為何十九世紀尤其是其后半期這種知識研究的分科化趨勢才出現制度化形態,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一些時候?除了知識演進的邏輯、哲學發展的趨勢之外,還需要從十九世紀后半期西方國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領域發生的深刻變化中找尋其中根源。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經濟、社會、政治乃至文化價值觀都在發生著急劇、深刻、廣泛的變化。在公共領域,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群眾運動風起云涌,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日益高漲,早前倡導改革的涓涓細流最終匯聚成聲勢浩大的改革浪潮,史稱“進步主義時代”。無獨有偶,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恰好也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行政學等社會科學諸領域創立或形成的時期,尤其是政治學和行政學,它們甚至就產生于這一時代的美國,許多著名的進步主義者本身就是政治學、行政學的開創者或奠基人。“在公共行政文獻中,有相當數量的研究關注進步時代(Gaiden,1984;Chandler,1987.;W.Nelson,1982;Stillman,1991;Ventriss,1987)。這個時期被普遍認為是公共行政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開端,著名的進步主義者伍德羅·威爾遜被看作是現代公共行政學的創始人。顯而易見,經濟社會諸領域發生的急劇、深刻、廣泛的變化對于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研究必定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政府改革的邏輯、重心和取向,在政治學、行政學以及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諸學科的研究主題、分析框架以及方法論方面,也一定會留下影響的痕跡。進而,當前有關政府改革問題之所以觀點主張各異,價值觀念叢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學科背景和知識結構之間的差異、歧見影響所致由此。因此,對進步主義時代美國政府改革問題的研究,不僅有助于理解那一時期經濟、社會諸領域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有助于后發國家從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改革邏輯和現實中得到啟示,還有助于從源頭上來認識社會科學不同學科在研究主題和方法論上的差異及其引發的理論和現實后果,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當代社會科學諸領域之間的矛盾、沖突和發展趨勢。
〔1〕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2〕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三聯書店,1997年版.
〔3〕喬治·索雷爾.進步的幻想·英譯者導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理查德·布朗.現代化:美國生活的變遷1600-1865.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
〔5〕B·蓋伊·彼得斯.政府治理的未來模式.中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7〕彭和平,竹立家.國外公共行政理論精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
〔8〕赫伯特·D·克羅利.美國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實現國家目標中的作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Arthur S.Link,Richard L.McCormick:Progressivism,Harlan Davidson,Inc.Arlington Heights,Illinois 1983.
〔10〕阿德諾·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蓋·B·亞當斯.公共行政研究——對理論和實踐的反思.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