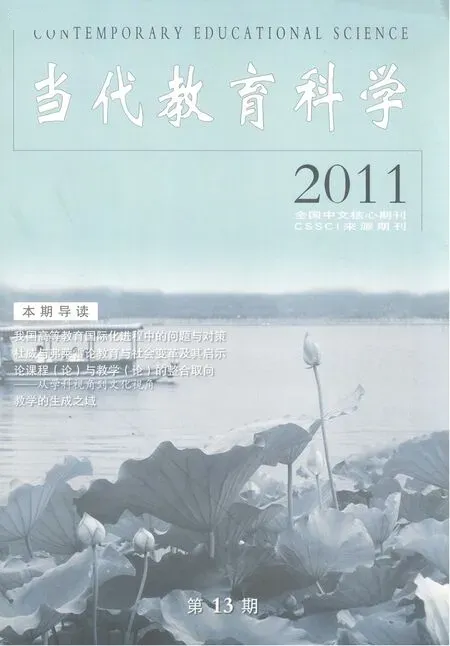論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之關系
● 伊 鑫
論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之關系
● 伊 鑫
同權論認為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同屬于憲法上的基本權利,而制度保障說則將大學自治視為對學術自由的保護,制度保障說準確界定了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關系,對我國大學法治的建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同權論;制度保障論
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是兩個關系密切而又容易混淆的概念。一項對二戰后美國高等教育的分析認為,如果被法律或公共觀點支持,學術自由可以在大學自治缺失的情況下存在。但是又有情況顯示有些外部干預會或明或暗地侵蝕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有助于維護學術自由的精神和保護這種自由免于外部的攻擊。[1]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都是建立在“傳播和創造高深學問”這一大學內在邏輯的基礎上的,但二者之間具有何種內在關系卻一直存在爭論,二者同權論和制度保障論就是兩種有代表性的看法。本文試圖在分析上述兩種觀點的基礎上澄清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之間的關系。
一、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淵源
“自治是高深學問的最悠久的傳統之一”[2],大學爭取自治是從建校時開始的,在中世紀產生之初,大學就產生了自治的訴求。大學具有國際性,其成員來自世界,主張普遍教學的自由,它的領域是基督教世界,而且沖破了城市的范圍。大學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與教會、王室甚至是普通市民進行斗爭的過程,斗爭的手段是罷課和遷校,斗爭的結果是大學有了自己的特權。
而學術自由概念的產生則要晚的多,作為大學探索真理的原則學術自由首先被德國大學接受,其思想奠基者是洪堡、施萊爾·馬赫和費希特等人,認為大學必須將研究提升到與知識傳授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要開展學術研究就需要確立學術自由的制度保障。這一思想逐漸形成經典大學的基本理念并被歐美大學普遍認同。學術自由在最初僅僅限于學校內部,是學校自身的行為,卻無法防止來自外部力量的侵害,因此需要國家法律的認可和保障。到了20世紀初期,則上升為憲法基本權利,許多國家的憲法和教育基本法開始明確保障學術自由。因此,從歷史上看,大學自治的理念和制度先于學術自由而產生。
二、二者同權論
二者同權論把學術自由視為大學的基本權利,大學是學術自由的組織體,大學自治是一種團體性的學術自由,是學術自由的合理延伸和當然結果。確實,隨著學術自由權內涵的發展,權利主體已經實現了從學者向普通公民、從個體向組織轉化的過程,許多國家將學術自由的主體擴展到了包括大學在內的機構,把學術自由視為大學的基本權利自在情理之中。同時,這種觀點立足于自由主義的精神,為大學自治提供一種自然法上的正當性,使學校在國家—社會的二元結構中能夠形成一種對峙而又互動的良性格局[3],更易于直接明確的論證大學自治的合法性依據。不過,把大學自治權直接等同于憲法學術自由權,存在許多不足:
首先,掩蓋了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之間的內在關系。大學自治以實現學術自由為旨歸,具有手段性價值,與學術自由權的實現之間是一種手段與目的的關系,而并非等同關系。相反,如果一所大學自治的主體是學校的行政系統,反而可能會帶來對學術自由的傷害。事實上,學術自由并不必然產生于大學自治,大學自治也不必然以學術自由為最終目的。大學自治不包含學者個人的學術自由等權力訴求的意義,而是指大學作為一個學術組織為避免外界干擾而提出的屬于大學整體需要的自我決策、自我管理的權力訴求。大學自治有可能損害學者個體的學術自由。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知識分子進入學院化的大學校園后,大學里煩瑣的規定成為最麻煩的學術障礙,……大大限制了學者們的獨立人格和學術自由。[4]因此,當大學自治行為損害到了教師和學生的學術自由時,應該受到限制,大學自治作為手段并不是無限的。大學自治要受到國家合法性的監督,使得大學自治在保護學術自由、學習自由以及大學成員其他憲法性權利前提下展開。
其次,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二者的內容并非完全等同。一般認為,學術自由的內容包括學術思想自由、學術研究自由以及研究成果的傳授、交流與發表自由等三個方面。而大學自治則是指大學必須由自己的機關獨自負責并且不受國家之指示以完成事務之意,亦即大學之管理、運營系委諸于大學內部之自主性決定。[5]大學自治內容上則要豐富的多,從實體和程序角度來看,大學自治分為實質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從自治權的分立和運行來看,又可以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監督權;從具體內容來看,大學的自治權包括人事的自治、學生選擇的自治、教育課程決定的自治、研究計劃決定的自治、財源分配的自治等。
再次,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二者的主體不完全相同。學術自由權的主體一般適用于全體國民,但大學自治的主體卻有很大差異。德國大學自治權的主體主要是教授,形成了教授治校的大學自治模式;而美國則形成了董事會領導下的大學自治模式。我國教育法規定辦學自主權的主體是大學,而高等教育法中主體是大學和校長,而沒有作為大學重要構成人員的教師和學生,特別忽視了學生的權利,但在大陸法系許多地區,學生一直處于大學構成主體的地位。可見,在學校這一集體之內,仍然存在著自治權主體的差別,而這一差別可能使之對學術自由的保障功能也會有所不同。
三、制度保障論
制度性保障理論最初由德國威瑪憲法時期學者施密特將其體系化,意指在憲法規范之下,某些具有特定范疇、任務及目的的制度應為國家憲法所承認,受到憲法的特別保護,立法者不能通過立法而將其廢棄。制度性保障的功能在于避免某些先存性法律制度免受立法者廢棄,這是一種消極的制度性保障。制度性保障理論的內涵可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制度性保障的目的在于保障特定的法律制度,而非保障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制度性保障是以一定法律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其所保障的乃是一種被形構、組織乃至被界分的具體法律制度。制度有別于自由權利本身,制度對于個人自由的保護與強化則具有補充的功能,因此制度性保障的結果可形成對某些自由權利的連接性、補充性的保障。其二,制度性保障的客體是既存的法律制度,是現行憲法制定之前即已存在的法律制度。這些制度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制度文明建設的結晶,運行多年,且有組織、結構上的表征,并得到某種程度上的法律保障,其核心部分必須予以尊重。其三,制度性保障的前提是相關法律制度必須有憲法連接點。傳統的法律制度只有被憲法納入時才能獲得制度性保障。“經由憲法法律的規范,特定制度可以獲得特殊的保護。此種規范的目的在于使立法者無法以單純法律的方式廢除此等制度。”[6]其四,制度性保障的內容是立法者不能對已經納入憲法范疇的法律制度的典型特征加以侵害。立法者在對某一法律制度進行改革時,必須尊重現存法律制度的核心價值,如需廢棄該法律制度,則必須啟動修憲程序。當然,憲法對該類制度的保障并非保障這些制度的現狀,而是保障這些制度的本質內容,國家可根據立法對這些制度的周邊部分進行界定和變更,但不可侵害其核心部分。
依據制度性保障理論,大學自治在作為傳統制度受到憲法保護的同時,又成為憲法基本權利,從而得到憲法的雙重保護:在消極層面,防御立法者創設法律侵害大學依據學術本質需要而應享有的自治制度的核心部分;在積極層面,則可以要求立法者積極創設法律對大學自治進行確認,并通過具體的制度去實現和保護大學自治。基于學術自由的制度性保障理論,德國傳統的大學自治制度與作為基本權利的學術自由建立了緊密的連結。按照積極性制度保障理論,一方面要求立法機關創設的法律不得侵害大學依學術本質需要而應享有的自治權利,另一方面則要求立法機關積極創設法律對大學自治進行確認,并通過具體的制度去實現和保護大學自治。
還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種制度性保障,大學自治不僅是對大學構成人員學術自由的保護,而且是對大學作為一個獨立主體的學術自由的保障。學術自由為基本權之一,其權利主體除從事學術研究之個人外,還包括大學本身。倘使只有從事研究個人享有學術自由基本權,而大學并不擁有此項權利,則國家對于大學干預,例如限制大學圖書館收藏圖書種類,僅能當其直接影響個人研究活動時,個人才可以主張學術自由的保護,而大學本身并不能直接、立即地援用基本權防御功能,不啻為國家提供一個間接、但是極為有效干預學術研究自由的途徑,顯然悖離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精神。而且由于現代學術研究工作早已非研究者憑借自己毅力和天分所能完成,而往往必須透過研究機構各種設備與人力的支持始得進行,大學自然而然地就成為學術研究工作得以開展實現的必要場域,國家除了應消極地不干預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活動外,更應創設制度以協助保障學術自由之實現,而大學自治,正是為達成此一目標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性保障功能。
四、對我國大學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制度保障說在德國的大學自治的法理理論中目前處于通說的地位,也得到了聯邦憲法法院的認可,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憲法理論與實踐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日本,二戰前,大學自治制度被視為一種慣行,在戰后則被視為與學術自由的憲法規定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系,而受憲法的保障。而我國的臺灣地區在相關的法律文件中更是明確認定了制度保障說,如在380號解釋理由書中明確指出,“講學自由之規定,以保障學術自由為目的,學術自由之保障,應自大學組織及其它建制方面,加以確保,亦即為制度性之保障。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應承認大學自治之制度,對于研究、教學及學習等活動,擔保其不受不當之干涉,使大學享有組織經營之自治權能,個人享有學術自由。”[7]在大法官林永謀、楊慧英的協同意見書中也指出,“大學自治既系源自學術自由之本質,則‘憲法’第十一條關于講學自由之規定,在實際問題上,當系指大學講學之自由,故就此意義言,大學自治可謂系對于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從而其侵害大學自治者,即為侵害‘憲法’第十一條講學之自由;且此一制度性保障并不變更大學教師基本人權保障之意義,要屬當然。‘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并在法律規定范圍內,享有自治權。’即系上開憲法對講學自由即學術自由以及由此衍生之大學自治所為保障之積極的法律性宣示。”[8]
當然,對制度保障說也有不同聲音。在日本,制度性保障受到嚴厲批判之處在于,制度性保障過分強調制度的核心內涵,反而對于不是核心內涵的制度會傾向于讓法律任意更改,弱化了所想要保障的制度或基本權,另外制度性保障的概念過于模糊,有人為操作的空間。在我國臺灣,有學者指出大法官引入制度性保障并沒有充分的理論基礎,而是面對現實的結果,因為在臺灣公立大學并沒有獨立法人地位,無法從法人基本權利保護的角度來維護大學的學術自由,只好改用制度性保障這種說理方式。[9]制度保障說并非是對等同論的修正和發展,事實上二者之間并沒有內在的聯系。制度保障說是德國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有一定應急的功利目的,不過,制度保障說相比于等同論正確界定了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之間的手段和目的關系,對于學術自由的保護具有重要價值,這也是制度保障說雖遭非議但卻沒有被代替的主要原因。
我國雖然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學術自由權,但在建構具體的權利保護制度方面卻存在很多不足,使得學術自由權有淪為紙面權利的危險。特別是對大學學術自由的保護方面,沒有建立一種制度性保障措施來實現學術自由,甚至沒有提到大學自治,只在高等教育法中規定了辦學自主權,自主權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高等教育事業性質認識的一種延續,是政府在有限的范圍內讓渡給高等院校的一部分教育行政管理權,甚至只是國家默認的一種恩賜。所以,在人們的意識中,它是下放的而非大學應有的權利。[10]更為致命的是,這種自主權并不是出于對學術自由的保障,而是為了維護學校秩序的管理權,正是辦學自主權與學術自由的這種疏離,使得自主權反而可能傷害學術自由權。比如在鄒柳娟訴教育部一案中,法院認為華中科技大學未評聘鄒柳娟為教授屬該校行使自主權的行為,不是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11]因此,在我國大學法治的建設過程中,應當借鑒制度保障說,將辦學自主權視為教師和學生學術自由的保障手段,并以此為基礎來配置學校權力,并將學術自由的實現作為判斷辦學自主權的正當性的依據。
[1]Altbach,Philip G.etc.(ed.)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Prometheus Books,1994:57,70.
[2]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鄭繼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0.
[3]湛中樂等.論大陸公立大學自治權的內在結構[J].教育管理研究.2005,(3).
[4]鄧光平.如何識讀現代大學組織特性:羅伯特·伯恩鮑姆的大學組織結構觀[J].復旦教育論壇,2005,(2).
[5][8]臺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380號解釋大法官林永謀 楊慧英協同意見書[EB/OL].法源法律網.http://fyjud.lawbank.com.tw.
[6]李建良.“制度性保障理論”探源——尋索卡爾史密特學說的大義與微言[G].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集:公法學與政治理論.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222.
[7]周志宏.學術自由與大學法[M].臺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53.
[9]李建良.論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的憲法保障[J].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8卷第1期:280-281.
[10]熊慶年.對落實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再認識[J].復旦教育論壇.2004,(2).
[11]評教授是高校的自主權不是具體行政行為[EB/OL].北大法意.http://www.lawyee.net.
伊 鑫/山東政法學院人事處師資職稱科科長,法學理論碩士,講師
(責任編輯:劉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