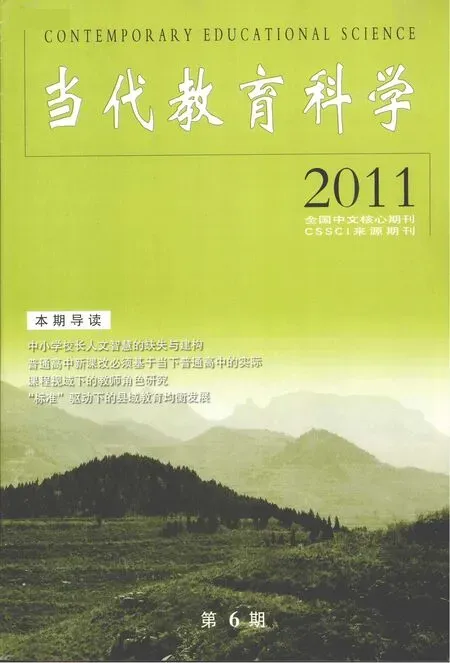課堂烏托邦:泛娛樂化時代課堂教學怪相批判
● 蔣福超
課堂烏托邦:泛娛樂化時代課堂教學怪相批判
● 蔣福超
當今課堂教學有走向泛娛樂化的趨勢,在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教材解讀上都有所體現。消費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對課堂教學的影響和浸染是課堂教學泛娛樂化產生的時代背景。泛娛樂化課堂教學將課堂視為市場、學生視為上帝、學習視為輕松和快樂,這些隱喻忽視了學校和課堂的相對獨立性,使教學失去了靈魂。
泛娛樂化時代;課堂教學;消費主義;后現代主義;隱喻
一、笑聲與熱鬧:當今課堂教學中的泛娛樂化傾向
毋庸置疑,課堂是課程變革的主戰場。課堂教學直接反映新課程理念能否被正確理解和實施。在我們欣喜地看到當今的課堂教學一改往日的沉悶和單調時,我們同時也發現課堂教學有滑入另外一個極端的傾向,泛娛樂化在當今課堂呈現綿延趨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泛娛樂化的手段
以多媒體科技為代表的現代教學手段大大提升了課堂教學效率和趣味性,但在當今課堂教學中存在濫用的現象(甚至有的評課竟然將是否使用先進的教學手段作為評價的標準)。課件設計越來越精美,大段大段的視頻占據了許多課堂教學時間,精美設計的圖片、音樂、聲音、動畫吸引住了學生的眼球,讓學生眼花繚亂,“饒有興趣”地“觀看”課堂。許多老師嚴格按照課件設計的程序按部就班地教學,離開課件就完全不會講課(比如有的語文課上,課文范讀改為放錄音,播音員讀得標準,板書改為放投影,打印的字體比手寫的規范,該講的也不講了,看屏幕,看動畫等),教師完全變成了多媒體的“被支配者”。
(二)泛娛樂化的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上的泛娛樂化是指教師往往過多地采用多種時尚、熱鬧的教學活動,營造濃烈的課堂氣氛。在許多課堂,特別是“公開課”和“示范課”,一改往日的沉悶,將活動、游戲、表演等作為課程的主要呈現方式和評價方式,課堂變成了 “星光大道”“開心辭典”“超男超女”等等,課堂成了穿著華麗衣裳的木頭人,絢麗多彩卻華而不實。比如,在某市級教學比武中,有教師教《“神舟”五號飛船航天員出征記》一文,一開始上課就為大家先唱了一節《歌唱祖國》,在教學過程中為了讓大家能體會航天員訓練時的艱辛,找了一個學生模擬航天員,到黑板前閉上眼睛轉20圈,師生一起為他數數,場面十分熱鬧。轉圈結束后就是記者招待會,問到訓練那么累、那么苦為什么還要訓練,學生答曰:為了國家的利益,這點苦、這點累算什么。下面掌聲雷動。在師生集體高歌《歌唱祖國》后兩節后,這堂課結束。在筆者參與過的英語優質課評選中,也發現許多老師將課本內容一帶而過,然后圍繞課文內容極力發揮,或去辯論、或去游戲競賽、或去唱歌舞蹈,整堂課變成了學生和老師的才藝表演。
(三)泛娛樂化的教材解讀
課堂教學的娛樂化還表現在對傳統、嚴肅話題和經典的解讀上。歪說、戲說、搞怪、低級幽默等充斥許多課堂,淺嘗輒止的理解加上搞怪的動作和低級趣味的油腔滑調式的幽默,造就了許多“最牛某某老師”。在這些課堂里,歷史、經典、傳統被庸俗化的語言表現出來,唐詩宋詞可以變成打油詩,白毛女可以成為商界精英,李白可以搖身變成古惑仔。
二、消費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時代背景對課堂教學的浸染
消費主義是當今消費社會的一種基本消費觀念、人生觀、生活方式。它奉行的是快餐和速食、宣泄和快感,以及消費所帶來的虛榮。毫無疑問,消費文化以其及時享樂和縱欲狂歡的現代生活新理念,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固有的精英主義文化觀,大眾文化愈來愈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影響著人們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取向。這也就是布爾迪厄分析的“批量化的文化生產場(以通俗、娛樂為核心的趣味標準)”戰勝“有限的文化生產場(以崇高、深刻、神圣為核心的趣味標準)”的過程。
這個過程體現在消費行為上就是,消費行為在量上日益膨脹,但在“質”上卻趨向平面化。其突出表現是:取消深度的傾向;追求同質化的時尚、奢侈、快感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大眾傳媒對文化消費的強烈介入和深入影響。以先進的信息科技為支撐的電視、電影、報紙、廣播、互聯網等傳媒,往往屈從于商業的利潤法則,去迎合大眾的消費需求,同時,“大眾媒介不僅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再生產工具……在消費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大眾媒介充當了最佳孕育者和助產士的角色”。[1]大眾媒介讓“快樂”放棄了意義追問和現實思考,這種快樂,沒有理性的光芒,沒有詩意的纏綿,而只是大眾文化流水線上的一道工序而已。
所以,當教育走向市場,成為可供買賣的商品時,為了迎合消費者的旨趣,教育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都力圖走向大眾化。在課堂教學上就體現為以娛樂來消解學習的枯燥和深刻,用輕松的感性方式代替理性方式,從而逃避學習過程的單調與艱辛,深思與批判,為學生構造了一個沒有苦惱、只有快樂的課堂“烏托邦”。
同時,大眾傳媒的觸角也深入到了校園,讀圖時代下的課堂也充斥著諸多“屏幕”,圖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在讀圖時代,學生建構心智的主要方式是讀圖,而不是文本閱讀,學生迷戀通過卡通片獲得思想教育,通過漫畫了解古典名著,通過電腦游戲認識歷史人物。他們視覺第一、趣味為重,成了習慣于圖像化、故事化敘事方式的一代人,或者稱為“圖像人”。為適應“圖像人”的興趣愛好,教師的課堂教學也受到了影響。想給學生講述古典的美,可是學生卻不愛聽,學生喜歡的是周星馳的無厘頭;想讓學生了解歷史名人的成長歷史,但學生喜歡的是韓國明星和周杰倫的成長經歷以及奇聞軼事……對此,教師只能降低要求,改變教學方式,力圖成為學生心目中的“麻辣教師”。教師為逗樂學生煞費心思(特別是在某些培訓機構),那些儼然成為學生偶像教師的課堂教學充滿著笑聲,即便課堂教學內容和講笑話的比例達到 3:7。
此外,當代各個領域不同程度的娛樂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后現代思潮的外在表現。政治娛樂化、科學娛樂化、宗教娛樂化、學術娛樂化,當然包括教育(課堂)娛樂化等,都是對原有領域話語權威和游戲規則的一種質疑和顛覆。具體到課堂教學上,結合后現代思潮的特征,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做出理解。
首先,后現代主義奉行對中心權威的質疑和反叛。傳統教學本質上是教師單向、獨白式的權威教學,維護教師在知識傳授中的中心地位,學生始終處于被動的弱勢群體地位,教師有著至高無上的話語霸權。而后現代主義主張消解教師的話語霸權,鏟除對秩序和權威的服從,鼓勵在課堂教學中以師生平等對話代替教師的灌輸。教師、學生的概念產生了變化,甚至像弗萊雷所說的那樣:“通過對話,學生的老師和老師的學生之類的概念不復存在,一個新名詞產生了,即作為老師的學生和作為學生的老師。”[2]后現代主義下的娛樂化課堂正是反映了教師權威和話語霸權的消逝,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學生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一切圍繞著學生轉,泛娛樂化的教學方式正是這種思想的極端表現。
其次,后現代主義主張對現代性的元敘事和深度的解構。后現代主義把矛頭直接指向現代性,對其進行反思和批評,認為它依賴元敘事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并主張深度的消失,后現代主義文化不再提供現代、前現代經典作品具有的深度價值和意義。體現在知識觀上,后現代主義對“旁觀者”的現代知識觀進行抨擊,認為每個人因為獨特的經驗而有不同的看問題的視角,教師不能充當一個知識的解釋者的角色,而是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大膽思考,表述自己的任何觀點和想法。由此,教育中的神圣、莊嚴的一切東西,被善于調侃、娛樂、反嚴肅、反崇高、淡化是非觀念的學生所解構。喜兒做黃世仁小三的幸福生活等類型的對經典和傳統的惡搞在課堂中大為流行,并被賦予“開發學生創造性、想象力”的正當理由。學生長久的課堂壓抑變成了漫無邊際的課堂暢想和狂歡。
三、快樂地學習與學習的快樂:課堂教學泛娛樂化的隱喻與批判
“隱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不僅體現于語言,而且貫穿于我們的思維及行動”[3]隱喻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基于我們自身的經驗,隱喻又是一種映射關系,將我們的抽象概念通過隱喻來具體化,以加深對抽象概念的理解。
泛娛樂化的課堂教學也有其對課堂、學習、學生、教師等抽象含義的映射性理解即隱喻。大致來說,在泛娛樂化的課堂里,課堂是市場,教師是服務者,學生是上帝,學習等于輕松、快樂。
(一)課堂是市場
泛娛樂化的課堂是買賣交易的市場,其交易的對象當然是知識。教師擁有學生未知的知識,成為市場中的賣方,學生是知識的后知者,需要通過教師的講解和指點才能獲得知識,屬于市場中的買方。
在市場交易中,如何尋求買賣雙方的價格契合點,以盡快達成交易,獲取利潤(或獲得使用價值)是市場的核心問題。因此,在泛娛樂化課堂里,從教師的角度講,能夠讓學生比較容易地學習知識,以便于達成知識的“出售”,是教師關注的核心問題;從學生角度講,學生希望貨物(即知識)能夠“物美價廉”,能夠不需要通過太多努力就可以獲得較多的知識。而娛樂化的教學方式恰恰符合兩者的需求,成為主宰課堂的不謀而合的潛在精神。
課堂是市場的隱喻將教學理解為知識在師生之間的傳遞,如何快速、容易地獲取知識是課堂教學的關鍵。然而,課堂教學不僅是知識的學習,教學還是一項富有“教育性”的活動,知識負載的教育意義在游戲、圖像和玩笑中很難被深刻理解,相反,卻往往會被遺忘。同時,課堂是市場的隱喻也容易降低課堂教學的效率和水平,造成課堂教學的“虛假繁榮”,教師和學生貌似快樂高效地學習知識,其實形式大大超過了內容,或者有時形式根本不能反映內容,與內容背道而馳。
(二)學生是上帝
泛娛樂化課堂里的師生關系是“消費至上,利益為先”的消費思想之下的畸形關系。在消費主義影響下,教師褪去了“神圣”“威嚴”的光環,變身為學生學習的“服務者”,學生成為具有“上帝”稱謂的“消費者”和“顧客”。教師必須要一切以學生為先,唯學生是從,為迎合學生的需求或努力做出讓步,或努力改變自己本真面貌,或插科打諢地造作拿捏。他遵循的是商業法則,即沒有學生,就沒有老師的飯碗,要想獲得學生喜愛,就要符合學生口味,就能獲得某種利益(比如“學生評教”中的高分等)。
不論是“學生中心”、“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還是師生雙主體說,各種不同的師生關系說在教育學歷史上都曾出現過,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承認教師和學生平等的人格關系。“學生是上帝”的隱喻恰恰將教師和學生的平等人格關系畸形化,刻意提高學生的地位,貶低教師的主體地位,同時也帶來了學習主體的迷茫。教學主體角色的沖突和混亂使得師生關系異化為“工具”和“手段”的關系,從而造成課堂教學的方向性和指導性不強。
(三)學習等于輕松、快樂
泛娛樂化課堂盛行的是快樂文化。對“快樂”的極度膜拜,讓“學習”的含義發生了異變,學習就是要輕松、快樂。教師也誠惶誠恐地改變以前舊有的教學模式,將娛樂生拉硬扯地填到課堂里,好像這就體現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學生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一樣。
然而事實是,學習絕不是一項易如反掌的事情,也不會永遠充滿快樂。痛苦并快樂著,感受知識的巨大,更感受靈魂的盛大,這乃是“學習”的本源,更是“學習”的旨歸。學習的真正快樂來自于思考的愉悅,而不是來自于技術興趣。快樂的學習只是學習的一部分而已,泛娛樂化的課堂夸大了學習的快樂,用笑聲代替了思考,使學生“快樂”有余,“體驗”不足。正如有學者在批評臺灣校本課程改革時所說的那樣:“全民麻醉在嘉年華的歡樂氣氛和大賣場式的聲光刺激中,誤以為這就是‘快樂學習’,這就是‘體驗’,這就是‘改革’。但誰去覺醒:大賣場式的市場邏輯強調將多元的、編制過的文化產品放在學生的手上,學生就以非常膚淺的方式消費這些產品。”[4]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一本名為《教學:一種保護性的活動》中,詳細分析了電視圖像和學校這“兩種課程”的獨立性,并且提出,學校(包括課堂)是幫助年輕人從圖像和娛樂中解脫的最好方式。學校因其自身性質的特殊性,承擔了這項任務,并將一直承擔下去。當后現代、消費主義與泛娛樂化的時代成為教師的生存背景,教師應該深思教師的精神向度和教育姿態如何呈現?波茲曼的話給我們很大的警醒,學校和課堂的確應該保持其相對的獨立性。捍衛教學的思想性和教育性,打造有靈魂的課堂教學,應該是浮躁時代教師的歷史使命,要記住赫胥黎曾說的一句話:“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5]
[1]燕道成.論大眾媒體對消費文化的建構作用[J].中州學刊,2005(11).
[2]Freire.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M].New York:Continuum,1970.67.
[3]Lakoff&Jo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11.
[4]歐用生.披著羊皮的狼——校本課程改革的臺灣經驗[J].全球教育展望,2002(7).
[5]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26.
(責任編輯:劉君玲)
蔣福超/泰山學院教師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