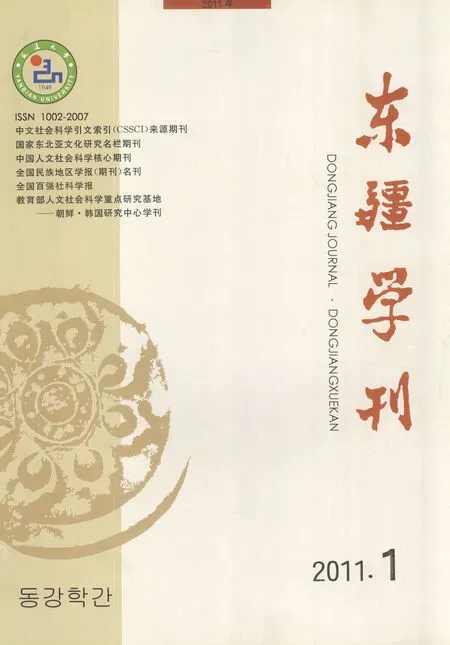從日本宗教論日本影視動漫中唐僧的女性化變異
高 晨
從日本宗教論日本影視動漫中唐僧的女性化變異
高 晨
中國古典文學(xué)名著《西游記》中懦弱短視的“御弟”唐僧在當(dāng)今一些日本影視動漫版《西游記》中被大膽變異成女性,并成為愛情的主角,引發(fā)了中國觀眾的強烈反感。但其在日本高居不下的收視率不禁引發(fā)人們深層次的思考。分析唐僧形象女性化變異的原因可以看出,是日本神道教與佛教介入其中,將唐僧形象加以分解后進行集體再創(chuàng)造和重新詮釋,從而形成了女性唐僧這一形象變異體。
唐僧;女性化;日本宗教
在《西游記》的眾多人物中,唐僧(玄奘三藏)是故事主線“西天取經(jīng)”的始作俑者,也是全書中唯一真實的人物。作為高僧,他歷時十九年從印度取回佛教原著千余部,入寂時完成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經(jīng)的翻譯,并留下一部稀有的地理志《大唐西域記》,可謂創(chuàng)下了佛學(xué)界的豐功偉績。然而,他堅強勇敢、執(zhí)著智慧的高僧形象卻在經(jīng)歷了百年流傳的《西游記》中被改變成溫良、愚昧、軟弱的俗僧形象。他昏庸莫辨的低俗形象成為火眼金睛的孫悟空的反襯;食之可以長生不老的肉身佐證了孫悟空“齊天大圣”的本領(lǐng)。他愚蠢的仁善和不能自保的低能成就了孫悟空的英雄名節(jié)。在《西游記》影響下的潛移默化中,唐僧由堅強無畏開創(chuàng)佛學(xué)歷史之先河的圣僧不知不覺地就被改變成性格柔弱模樣英俊的僧人了。
早在日本的飛鳥時代(公元550年—645年),唐朝玄奘三藏西天取經(jīng)的故事就已經(jīng)遠播到日本。玄奘以其圣僧形象被日本佛教尊奉為祖師,并流傳著大量有關(guān)玄奘三藏與日本僧侶友好交往的傳說。因此,在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佛教文學(xué)作品中,出現(xiàn)了將唐僧取經(jīng)路線改道日本的變異現(xiàn)象,以求玄奘三藏的神跡降臨日本。江戶時期在對《西游記》進行翻譯、加以通俗化改編之后,《西游記》中的師徒四人形象開始在平民階層廣泛流傳。自此,孫悟空不畏強權(quán)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玄奘三藏也由佛教神話中的圣人先賢轉(zhuǎn)變?yōu)楹廊A貴族(御弟唐僧)的文弱形象。隨著《西游記》在日本的普及,日本文學(xué)作品也竭盡所能地對《西游記》大加改編,以期適合本國民眾的欣賞口味,變異出與中國的《西游記》大相徑庭的唐僧形象。
1936年,上海的《電影周報》報道,“日本拍攝《西游記》電影,將唐僧變?yōu)榕?并與孫悟空談戀愛”[1](1),在當(dāng)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1978年,日本播出電視劇《西游記》,轟動一時,唐僧由當(dāng)紅女星夏目雅子出演,三位徒弟已擺脫《西游記》設(shè)定的原型,以人形出現(xiàn)。此后的1993年、1994年和2006年版都延續(xù)了這一特點。1979年,松本零士創(chuàng)作的日本TV動畫《SF西游記》,只是以“西游記”為片名,只能從人物的外形和飾物上看出西游記的些許痕跡。作品以銀河系戰(zhàn)爭為背景,描寫了外星公主(唐僧)與三位隊員(三位徒弟)駕駛大型宇宙飛船在銀河系與敵人作戰(zhàn)以維護和平的故事。2000年出品的日本TV動畫《パタリロ西游記》,雖然延用原著主題,但以女性化唐僧(美少年唐僧)吸引人們的眼球,并帶有色情情節(jié)。2008年出版的日本漫畫《大猿王》中,唐僧是不折不扣的成熟女性,并忍受悟空的虐待,兩人以殺死釋迦為共同目標(biāo),踏上了前往西天的道路。日本影視動漫將玄奘改編成女性形象不僅可以取得高收視率和高票房收益,更是捧紅了大量女明星。
中國影視在汲取學(xué)習(xí)日本版《西游記》的過程中,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的女性化的玄奘,卻在日本成為高收視率、高票房收益的保證。為什么會把玄奘變作女性?日本人如何接受女性化的玄奘?筆者將在本文中予以分析和解惑。
一、唐僧與日本神道
神道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是風(fēng)土習(xí)俗,它沒有嚴(yán)格意義上的教義,是日本人對自然萬物的崇拜。它以原始神話的形式流傳于世,可以說它是深植于日本人思想血液中的情感,任何傳入到日本的外來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與神道結(jié)合起來發(fā)生變異。作為描寫佛教高僧西天取經(jīng)故事的中國古典文學(xué)名著《西游記》,也不可避免地在日本與神道相遇并迸發(fā)出日式火花。
日本的神話故事多以女性為主角,并生動地體現(xiàn)出對女性——母親的熱愛和尊重,帶有明顯的母系社會的痕跡。例如,日本神話中的天照大御神(太陽神)是女性,而日本天皇家族就是天照大御神(女性太陽神)的后代,這足以說明日本神話中女神的地位之高。
建立在神話基礎(chǔ)上的日本神道,尊崇女性天照大御神的旨意,選取女巫作為神意的傳達者。女巫由與天皇有著血緣關(guān)系的處女擔(dān)當(dāng)。她們崇高的血統(tǒng)和純潔的身心使人們相信,只有她們才會將神的旨意傳達給人間。有史書記載,日本早期的國家統(tǒng)治者多為女性,她們以女巫的身份統(tǒng)治國家,行使權(quán)利。日本女性天皇的數(shù)量也遠遠地超過了同為中華文化圈的中國和朝鮮,這不能不使我們聯(lián)想到日本對女巫的崇拜。
唐僧身為高僧,貴為“御弟”,其俊美的外表、溫柔的性格和高貴的血統(tǒng),使玄奘的形象與日本女巫的形象有諸多相似之處。正因為有如此相近的身份地位和行為舉止,由高僧變?yōu)榕椎奶粕谌毡竞芸炀捅淮蟊娝邮鼙悴蛔銥槠媪恕H毡緦⑿首兩頌榕灾蟮淖畲髣?chuàng)新之一,是將崇高的母性也賦予給唐僧。《古事記》中記載,風(fēng)神速須左之男哭鬧著要見母親伊耶那美命,而被父親伊耶那岐命驅(qū)逐出國。他的姐姐天照大御神母親般地憐惜他,對他的種種惡行不予追究。當(dāng)?shù)艿艿娜涡允顾龤鈵罆r她便躲入石洞,拒絕出來。神話中對母愛的依戀在當(dāng)今日本依然延續(xù)著:
每天夜晚,成千上萬的日本商人避開“經(jīng)濟奇跡”躲進有時取名“母親的趣味”或僅僅標(biāo)為“母親”的小酒吧里。他們借助威士忌和礦泉水,又退回到童年時代,并尋求那些被他們稱作“媽媽桑”的女人們的傾聽。這些“媽媽桑”以一種精神病醫(yī)生的職業(yè)耐心,聽他們傾訴各種問題:妻子如何嘮叨糾纏不休,公司的科長如何壞,要么是無人重視他們的繁重的工作。這些日本的經(jīng)濟英豪,在得到“媽媽桑”的些許溫和的建議和種種寬心的鼓勵后,又東倒西歪地走回家。他們相互攙扶著,不時撲在同伴的肩上,為重新回到八歲的童年而高興地歡叫。[2](19)
這種母親情結(jié)在日本版玄奘身上也有所體現(xiàn)。日本動畫《SF西游記》中的外星公主(唐僧),以領(lǐng)導(dǎo)者身份與其他三個人(三個徒弟)組成小隊。她用溫柔的舉止、包容的胸懷接納受難的隊員,一次又一次地幫助其他三個人處理難以預(yù)料的各種事情。日本電視劇《西游記》系列中的唐僧也以溫柔莊重示人,并以堅強果敢的導(dǎo)師形象貫穿整個搞笑劇。
日本的神道是樸素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一直沒有擺脫孩童任性的自然天性,因此保留著那份原始的粗糙與直接。受到日本原始信仰的影響,女巫在現(xiàn)實生活中具有風(fēng)流多情的一面。在日本書籍中記載了大量書寫女巫與愛人相會情景的和歌和物語。《萬葉集》中的《和銅五年壬子夏四月遺長田王子伊勢齋宮時山邊御井作歌》中寫道:
山邊御井在,見此已欣然,伊勢良家女,相逢在井邊。時雨從天降,見之似水流,心情常寂寞,處處多煩憂。遙望立田山,相思路幾千,何時能越度,得見妹身邊。[3](22)
《伊勢物語》中也寫道:
從前有一個男子,當(dāng)了天皇的敕使,到伊勢參謁到此來修行的皇女。有一個在皇女處當(dāng)差的女子,經(jīng)常愛講色情話,她偷偷地寫了一首歌送給這敕使,歌曰:“癡心欲看花都客,神圣齋宮跳得過。”那男的便回答她一首道:“男女相逢神不禁,多情倩女早來臨。”[4](70)
以淫穢美艷著稱的日本傳統(tǒng)藝術(shù)——歌舞伎,是由一位叫阿國的女巫開創(chuàng)的。因此,女巫們的情愛在日本不但沒有被排斥,反而被廣為流傳。日本影視動漫作品中大量出現(xiàn)女性化玄奘的愛情情節(jié),這在日本神道中即可窺見一斑。
日本的神話推崇暴力性極強,性欲發(fā)達的男性英雄,這是早期父系社會的審美遺留。《古事記》中記載道:
速須佐之男命毀壞天照大御神所造的田塍,填塞溝渠,并且在殿堂上拉屎,但是天照大御神并不譴責(zé)他,替他解說。他的胡作非為卻不止歇,而且加甚了。當(dāng)天照大御神在凈殿內(nèi)織衣的時候,他毀壞機室的屋頂,把天之斑馬倒剝了皮,從屋上拋了進來。天衣織女見了吃驚,梭沖陰部,就死去了。[5](14)
據(jù)《日本人的色道》一書分析,認(rèn)為《古事記》“這一記載顯然是被修飾過的,真實的故事或許就是被所謂的‘大神’強奸了之后被異物傷陰而死”[6](26)。這種極端的性侵犯行為,在抗戰(zhàn)時期的日本軍人身上得到了最大發(fā)揮。在日本漫畫《大猿王》中孫悟空變身強悍霸道的妖怪,以殺死釋迦為目標(biāo),捆綁虐待女性唐僧前往西天,一路斬殺好色風(fēng)流的天神和暴力淫亂的怪物。其間充斥著血與性交織的情節(jié),這正與在神道觀念浸染下的現(xiàn)代日本人的色情觀念相吻合,形成具有日本傳統(tǒng)性和后現(xiàn)代性雙重特征的《西游記》傳奇。
三、唐僧與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在與神道不斷磨合的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它在中土大地上的原本面貌。玄奘高僧的形象也隨著佛教在日本的變異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紗。
梅原猛在《世界中的日本宗教》一書中,對日本佛教中凈土真宗的由來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日本佛教始于圣德太子。作為在家人的太子的佛教是法華佛教,這種在家法華佛教貫穿于日本的佛教。最澄繼承了太子的傳統(tǒng),并引入了6世紀(jì)中國的學(xué)僧天臺智的天臺佛教,建立了日本天臺法華宗。親鸞繼承了法華宗的佛性論、戒律論和法然改革后的凈土教,可以說,親鸞的凈土真宗是日本佛教的核心。[7](98-106)
日本凈土真宗的開創(chuàng)者親鸞,在發(fā)揚最澄的佛性論和戒律論的基礎(chǔ)上,提出人人可以成佛的佛性論、“還相回向”的凈土論和否定戒律的戒律論。這些思想與神道不謀而合,從而奠定了凈土真宗在日本佛教中的核心地位。在他的著作中,大量書寫佛變?yōu)榕詾樯顺韧捻灨?
親鸞夢記云 六角堂救世大菩薩示現(xiàn)顏容
這是藏于三重縣津市專修寺中《親鸞夢記》中的《女犯偈》。主要說觀音化身高貴的女性拯救僧侶。更有傳說,如意輪觀音變?yōu)榕詫樾杂嗟纳畟H帶到極樂凈土,這種說法并不是只在親鸞文章中可見,中世的僧侶都有摘錄,例如,東密的《覺禪抄》中的《如意輪末車去車》,就記載有“本尊佛變成玉女的故事等等”[8](107~109)。
這是日本佛教對日本神話中神圣高貴女神形象的引用,而且日本佛教中的女性不僅具有美麗純凈的身心,還可以為僧侶洗刷丑惡。
《西游記》中的取經(jīng)故事,是三個被天庭懲罰的罪人,受神佛的指派保護唐僧西天取經(jīng),以此謝罪。《西游記》的主題與《女犯偈》的主題相似,由唐僧(觀音)帶領(lǐng)三人(需要洗刷罪惡的僧侶)到西天(極樂凈土)成佛。唐僧由堂堂大男人變身為美麗女性也是與日本佛教流傳的神跡記載相符的。
日本電視劇《西游記》中唐僧由女演員扮演,但一路行來對徒弟算是嚴(yán)加管教,不失諄諄教導(dǎo)之功,雖然三人滿身陋習(xí),但唐僧救人于水火,得到不少夸贊,留下不少感人的故事,既有現(xiàn)代版搞笑的成分,也有勵志情節(jié)。另外,《SF西游記》中四人的相互配合與情感交流也成為SF類動畫中的經(jīng)典,那不失溫柔的公主(唐僧的外星身份)和三位隊員拯救弱小星球上的生靈,得到銀河系的嘉獎。
然而,我們不禁要氣憤日本人將高僧改編成愛情的主角是對佛教和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莫大侮辱。日本的佛教傳承自中國,但在日本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日本人作了自主創(chuàng)新。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日本僧人可以結(jié)婚生子,而且可以子承父業(yè),這是現(xiàn)代日本和尚與其他國家和尚最大的不同。凈土真宗的創(chuàng)始人親鸞就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結(jié)婚和尚,但結(jié)婚生子并沒有影響他在日本佛教中的地位。《日本人的色道》中提到:“在日本的色情文學(xué)歷史記載中,最淫蕩的角色往往是和尚。”[9](57)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女》中曾書寫一位妓女經(jīng)人介紹到寺廟中服侍和尚的故事,書中這樣寫道:
和尚仿佛說夢話似地說:“你非用不可的墮胎藥的制作方法,我昨天晚上從一個人那里學(xué)到手了!”他糊里糊涂脫口而出,自知說走了嘴,再去掩口已經(jīng)來不及了,著實可笑。然后是一通大吃大喝,從廚房里飄來的葷腥味一直不斷。商量妥帖,每一晚上的過夜錢是兩步金子,按這個價碼我轉(zhuǎn)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廟宇,沒有一處寺院不歸于女色之道,這一宗一派,沒有哪個寺院的和尚沒有破色戒。后來,一個寺院的住持對我特別癡心,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內(nèi)給三貫銀子。這樣,我就成了這寺院住持的姘頭。在這樣的生活過程中,也就懂得了這個藏污納垢的寺院許多可笑的事情。[10](30)
從平安時代的道鏡到室町時代的一休,無不云雨風(fēng)流一生,他們的風(fēng)流心態(tài)也被毫無保留地流傳開來。這些被載入日本佛教史中的高僧,受到信徒的景仰,自然,和尚的風(fēng)流也被民眾所接受。所以電視劇中與孫悟空談情說愛的女性唐僧,或與盤古大神偷情的女性化唐僧,不但沒有遭遇唾棄,反而一度掀起了日本觀眾的追捧狂潮,成為標(biāo)志性的影視形象,具有日本佛教的特征。[11](16)
三、結(jié)語
形象變異是國與國文化交流過程中必然發(fā)生的現(xiàn)象,它的產(chǎn)生基于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沖突與融合。日本引進中國古典文學(xué)《西游記》,經(jīng)過長時間的發(fā)展,產(chǎn)生與原著偏差極大的日本影視動漫版《西游記》,這看似偶然,其實卻是必然。尤其是對唐僧形象的女性化變異現(xiàn)象,曾引發(fā)了中國觀眾一次次的爭論風(fēng)潮。日本神道教與佛教介入到《西游記》中將唐僧形象加以分解,從而形成女性唐僧這一新穎的形象變異體,體現(xiàn)出當(dāng)代日本民族對于唐僧這位中國佛教史上偉大人物的集體再創(chuàng)造和重新詮釋。
[1]舟子:《日本攝制西游記》,《電影周報》,1936年。
[2][荷]布魯瑪:《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李曉凌、季南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
[3][日]無名氏:《萬葉集(上)》,金偉、吳彥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年。
[4][日]無名氏:《伊勢物語》,周作人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5年。
[5][日]安萬侶:《古事記》,鄒有恒、呂元明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9年。
[6]郝滿祥:《日本人的色道》,長沙: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7][日]梅原猛:《世界中的日本宗教》,卞立強、李力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8][日]西口順子:《中世の女性と亻厶教》,京都:法藏館,2006年。
[9]郝滿祥:《日本人的色道》,長沙: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日]井原西鶴:《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王啟元、李正倫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
[11]石美玉:《日本“觀光立國戰(zhàn)略”的效果評價及啟示》,《東北亞論壇》,2009年第6期。
[責(zé)任編輯 叢光]
J954
A
1002-2007(2011)01-0045-04
2010-08-16
高晨,女,四川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