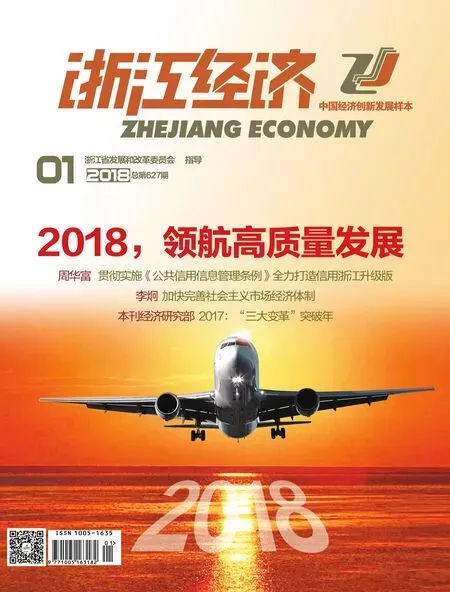2018,領航高質量發展
2018-02-07 17:40:45新華社
浙江經濟 2018年1期
圖/新華社
錨定新方位,領航新時代。
高質量發展既是新時代的風向標,
也是浙江經濟發展的新主題。
浙江要在高質量發展上走在全國前列、
成為排頭兵,
須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
瞄準“兩個高水平”建設目標,
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
低收入百姓增收、污染防治”
三大攻堅戰,
著力推動
大灣區大花園大通道大都市區建設,
以理念轉換、動能轉換、結構轉換、
效率轉換、環境轉換占得先機、贏得優勢。
2018,高質量發展的新起點。
新理念引領新發展,新引擎激發新動能。
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上,
浙江定能實現
“有沒有”到“好不好”華麗蛻變,
走出一條獨具浙江特色的
高質量發展道路。
猜你喜歡
當代陜西(2022年5期)2022-04-19 12:10:12
當代陜西(2021年1期)2021-02-01 07:18:02
當代陜西(2020年20期)2020-11-27 01:43:10
非公有制企業黨建(2020年9期)2020-09-26 13:22:18
人大建設(2020年1期)2020-07-27 02:47:06
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19年3期)2019-05-28 23:47:21
人民調解(2019年1期)2019-03-15 09:27:16
華人時刊(2017年21期)2018-01-31 02:24:16
領導決策信息(2017年12期)2017-05-17 04:49:18
中國衛生(2016年7期)2016-11-13 01:0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