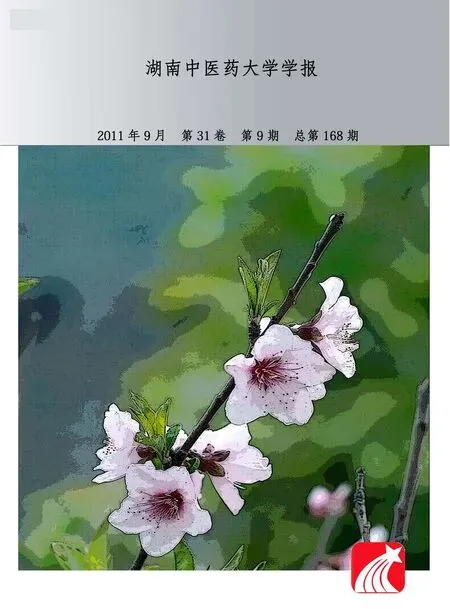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醫證型研究進展
劉 輝,劉柏炎*
(1.湖南中醫藥大學2009級碩士研究生班,湖南 長沙 410208;2.湖南中醫藥大學省部共建教育部重點中醫內科實驗室,湖南 長沙 410208)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又稱非潰瘍性消化不良,系指除器質性疾病而見的持續性或反復發作性上腹疼痛、食后飽脹、腹部脹氣、噯氣、早飽、厭食、惡心等上腹不適癥狀的一組臨床癥候群[1],大多由于情志內傷、飲食傷胃、勞倦傷脾所致。根據最新的羅馬Ⅲ標準[2],將 FD分為運動障礙樣型、潰瘍樣型、非特異性三種類型,伴隨著現代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FD是一種身心疾病,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和生存質量。FD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其發病機制涉及因素較多,目前公認胃腸運動障礙,內臟敏感性增高,社會心理因素和生活事件與FD的發生、發展有關[3]。中醫強調辨證論治,只有在辨證的基礎上對癥施治,才能達到治病求本的效果。由于功能性消化不良中醫分型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統一對其證型的認識,才能更好的發揮中醫藥的治療優勢。
1 病因病機研究
中醫古籍中沒有功能性消化不良這一病名,但根據臨床癥狀,多將其歸屬于“痞滿”、“胃脘痛”等范疇,其中痞滿證與ED癥狀最為相似。痞滿病名最早見于《黃帝內經》,稱之為“否”、“否塞”、“否隔”等。《素問·五常政大論》:“備化之紀,……其病否”、“卑監之,……其病留。”《傷寒雜病論》中明析:“滿而不痛者,此為痞。”《醫學正傳·痞滿》云:“故胸中之氣,因虛而下陷于心之分野,故心下痞”,則指出了痞證在心下胃脘部的病變特點。
中醫學認為本病病位在胃,涉及肝脾兩臟,多因飲食不節、外邪內侵、情志失調等,使脾失健運、胃失和降,導致中焦氣機阻滯、肝郁氣滯、脾胃虛弱、運化失職、胃失通降,脾胃升降失常、胃腸運動功能紊亂而發病。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升胃降,氣血調暢,氣機不息。因此,脾胃氣機失常為發病的中心環節。當代名醫董建華教授認為:FD的發病基本病理是脾胃納運失常,氣血瘀阻不暢,即所謂“不通則痛”,認為本病的發生與情志郁悖、外邪內積、脾胃虛弱有關。病因病機不離肝、脾、胃三臟,脾虛是發病的基礎,肝郁是致病的條件,胃氣不降是引發癥狀的原因。《丹溪心法》曰:“痞者,與否同,不通泰也,由陰伏陽蓄,氣與血不運而成,處心下,位中央……皆土病也。”由此可見當時已經認識到氣血運行不暢是痞滿產生的主要病理基礎。相關學者[4]認為中焦氣機失常是 FD發病的中心環節。現代醫學研究發現FD是由于情志精神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引起腦-腸功能紊亂,從而導致胃腸道對各種應激運動反應增強和內臟敏感性增高。
2 辨證分型
參照2001年中華中醫藥學會內科脾胃病專業委員會第13次會議通過的“功能性消化不良中醫診治規范草案”,將該病分為肝郁氣滯證、肝郁脾虛證、脾虛痰濕證、飲食積滯證、寒熱錯雜證。2003年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消化系統疾病專業委員會通過了《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醫結合診治方案(草案)》[5],將 FD分為肝氣郁結、脾胃氣虛、肝氣犯胃、濕熱滯胃4型。2009年10月中華中醫藥學會脾胃病分會再次討論與修改了消化不良中醫辨證證型,認為功能性消化不良證侯分為:脾虛氣滯證、肝胃不和證、脾胃濕熱證、脾胃虛寒證、寒熱錯雜證[6]。脾虛氣滯證癥狀表現:胃脘痞悶或脹痛,食少納呆,泛酸惡心,噯氣呃逆,疲乏無力,舌淡苔白,脈細弦。肝胃不和證癥狀表現:胃脘部脹痛,攻撐作痛,兩脅脹滿,每因情志不暢而發作或加重,痞塞不舒,心煩易怒,善太息,舌淡紅,苔薄白,脈弦。平素情緒易郁或易怒。脾胃濕熱證癥狀表現:脘腹痞滿或疼痛,或嘈雜不舒,惡心嘔吐,口干不欲飲,口苦,納少,身重困倦,小便短黃,食少納呆,舌紅苔黃厚膩,脈滑數。脾胃虛寒證癥狀表現:胃寒隱痛或痞滿,脘腹滿悶,時輕時重,喜溫喜按,泛吐清水,納呆便溏,神疲乏力,少氣懶言,手足不溫,語聲低微,舌質淡,苔薄白,脈細弱。寒熱錯雜證癥狀表現:胃脘部痞滿,或有燒灼樣痛,遇冷加重,肢冷便溏,泛酸嘈雜,厭食噯氣,口干口苦,或口干黏膩,舌淡,苔膩或黃膩,脈弦細滑。
但國內眾多學者對本病有不同的辨證分型。楊海波[7]總結FD為脾胃虛弱、痰濕內盛型;飲食傷胃、食滯腸胃型;肝氣犯胃、氣滯血瘀型;胃陰不足、虛火內盛型;寒熱錯雜型。高守庭[8]將FD分為肝郁氣滯型、肝郁脾虛型、脾虛痰濕型、飲食積滯型、寒熱錯雜型5個證型。張聲生[9]等提出以“寒、熱、虛、實”為綱,認為 FD應該可以分類辨證為脾虛氣滯證、脾胃濕熱證、寒熱錯雜證、脾胃虛寒證及肝胃不和證。陳暉[10]等將功能性消化不良分為肝氣郁結證、濕熱阻胃證、痰濕中阻證、飲食內停證、瘀血阻絡證、胃陰不足證、脾胃陽虛證、脾胃氣虛證8個證型。繆育坤[11]對FD進行辨證施治,分為肝胃不和、濕熱內阻、飲食積滯、脾胃虛弱、胃陰不足5個證型。楊蓓[12]等對臨床130例FD患者進行辨證分型研究,發現脾胃濕熱型、肝胃不和型、脾胃虛弱型、飲食停滯型及寒熱錯雜型分別占35.4%、33.8%、14.6%、9.2%、6.9%。劉汶[13]等對1 000例 FD患者進行辨證分型研究,發現主要分為肝郁氣滯型、肝氣犯胃型、脾胃虛弱型、濕熱滯胃型,分別占25.8%、26.2%、23.2%、24.7%。岳在文[14]將FD辨證分型為脾胃虛寒、肝胃不和、脾胃濕熱、寒熱錯雜、脾虛氣滯5個證型。陳貞[15]等根據相關文獻將FD分為脾虛氣滯證、脾胃濕熱證、脾胃虛弱(寒)證、寒熱錯雜證、肝胃不和證、飲食積滯證、胃陰不足證、痰濕中阻證。管松[16]將FD分為脾胃虛弱證、脾胃虛寒證、飲食停滯證、痰濕中阻證、肝脾不和證。趙麗丹[17]總結FD分型有濕熱內蘊型、肝胃不和型、肝郁胃熱型、肝郁脾虛型、飲食傷胃型、食積停滯型、脾胃虛弱型、脾胃虛寒型、脾胃陰虛型、濕濁中阻型、肝郁氣滯型11型。《實用中醫消化病學》把FD分為脾胃虛弱證、食滯傷胃證、肝氣郁結證、肝氣犯胃證、濕熱滯胃證、寒熱錯雜證、痰氣交阻證、痰火阻胃證和胃陰虧虛證9型。綜上各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脾胃濕熱型及肝脾不和型為FD的主要證型。
3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胃腸激素研究
辨證是中醫內科學的精髓,是中醫診斷疾病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卻因其缺少客觀指標的衡量標準,辨證分型難以統一。因而如何在中醫內科臨床辨證中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使中醫內科的“證”有明確的客觀指標,即中醫內科辨證的客觀化、規范化、標準化[18]。劉芳[19]等認為膽囊收縮素(CCK)可作為脾虛證的一個客觀性和特異性指標,其通過實驗研究表明脾胃虛弱證早期生長抑素(SS)在胃腸組織中含量降低抑制作用減弱,而CCK在組織及血漿中含量升高。劉松林[20]等研究發現肝胃不和型FD患者胃竇iNOS增加,5-HT、P物質表達顯著降低。張仲林[21]等通過實驗表明六君子湯治療脾虛證模型大鼠顯著升高血漿中胃動素(MTL)、SS的含量,明顯降低血漿血管活性腸肽(VIP)含量,有升高血清胃泌素(GAS)的趨勢。黃穗平等[22]研究發現肝郁氣滯型胃電圖表現為胃電節律紊亂為主(占62.5%),脾胃虛弱型胃電圖表現為胃動過緩為主(占57.1%),并且脾胃虛弱型血漿胃動素含量又低于肝郁氣滯型。朱方石[23]研究表明胃熱陰虛型、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血漿胃動素明顯高于脾胃虛弱型。潘志恒[24]等研究發現肝胃不和型和肝胃郁熱型FD患者的餐后2 h胃竇面積較大;餐后2 h的胃排空率明顯小于正常對照組和脾胃虛弱型。方盛泉[25]等研究發現患者脾胃虛弱型胃動力障礙明顯高于肝胃不和型、脾胃濕熱型。邵文全等[26]研究發現肝胃氣滯型主要表現為GAS、MTL、CCK血漿濃度的偏高;寒邪犯胃型主要表現為GAS、MTL、CCK血漿濃度的相對偏低。劉汶[27]等探討發現肝氣郁結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胃排空減慢,胃動素水平較正常降低,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升高。王麗[28]等研究發現肝脾不和證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血漿中VIP含量高于其他證型,胃泌素、胃動素降低;脾胃濕熱證患者血漿中CCK濃度偏高。
4 展望
FD其發病多因飲食、勞倦、情志所傷,形成食積濕熱、痰瘀等病理產物,阻于中焦,使胃的氣機阻滯,升降失常,影響胃的受納與和降。即《內經》所謂“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脾胃為人體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肝體陰而用陽,主疏泄、藏血。故肝、脾胃功能失調,導致全身氣血生成運行功能異常。結合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八綱(主要考慮陰陽寒熱虛實)辨證,可以將FD證型大致歸納為脾胃虛弱(氣虛、陰虛、陽虛)證、肝脾不和證、脾胃濕熱證、肝郁氣滯證、痰濕阻滯證、飲食積滯證、瘀血(氣虛所致、氣滯所致)停滯證七個證型。目前已有相關學者[29]從肝脾理論進行相關研究,亦有少數學者[30]提出從心胃相關理論進行探索。大量的臨床試驗研究表明,中醫藥可以通過腦-腸軸來調節、改善、治療FD的相關癥狀,效果明顯優于單純的西藥治療。但是中醫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中醫辨證分型標準及療效評定標準尚未統一,多為各醫家根據自己臨床經驗擬定證型,使得許多資料與資料之間缺乏可比性,應進行對中醫循證醫學的研究,為中醫在研究和治療FD提供確切依據;其次,FD辨證分型方法多種,應綜合分析辨證分型,如微觀、宏觀辨證法等。再次,許多證型之間名異實同,或者各個證型之間又相互交叉。中醫強調整體觀念,辨證論治,只有規范FD辨證分型的標準,才能更好的進行辨證施治。
[1]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消化系統疾病專業委員會.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醫結合診療方案(草案)[S].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5,25(6):539.
[2]魏 瑋,史海霞,樊麗娜.功能性消化不良羅馬Ⅲ診斷標準與中醫辨證分型的關系[J].環球中醫藥,2009,2(4):253-254.
[3]姚筱梅.姚樹坤教授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思路與方法[J].四川中醫,2007,25(1):5-6.
[4]馮敏曉,顧 勤.中醫對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認識[J].中醫藥信息,2010,27(2):97-99.
[5]張萬岱,危北海,陳治水,等.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醫結合診治方案(草案)[S].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04,13(1):42.
[6]中華中醫藥脾胃學會分會.消化不良中醫診療共識意見(2009)[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0,30(5):533-537.
[7]楊海波.中醫辨證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J].中華臨床醫學研究雜志,2008,14(7):1 024-1 025.
[8]高守庭.中醫辨證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療效觀察[J].中國中醫藥咨詢,2010,9(2):220.
[9]張聲生,陳 貞.中醫藥診療功能性消化不良若干問題的思考[J].環球中醫藥,2009,4(2):245-248.
[10]陳 暉,陸喜榮,陶鳴浩.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醫診治[J].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25(6):845-846.
[11]繆育坤.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醫辨治[J].中國中醫急癥,2009,18(7):1 177-1 178.
[12]劉 蓓,葉 楓.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醫證候研究[J].北京中醫藥,2008,27(1):1-2.
[13]劉 汶,范 萌,王仲霞,等.功能性消化不良中醫辨證與西醫分型的調查研究[J].北京中醫藥,2008,27(10):764.
[14]岳在文.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痞)中醫癥候特點及臨床研究[J].內蒙古中醫藥,2010,29(3):32-33.
[15]陳 貞,許文君,張聲生,等.功能性消化不良中醫證候及癥狀分布特點的研究[J].北京中醫藥,2008,27(11):841-843.
[16]管 松.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辨證施治分析 [J].醫藥論壇雜志,2008,29(1):71-72.
[17]趙麗丹.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醫辨證治療[J].光明中醫,2007,22(12):20-21.
[18]符為民.中醫內科臨床辨證客觀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J].2009年中華中醫藥學會內科分會中醫內科臨床科學研究專題研討會論文匯編,2009:169-172.
[19]劉 芳,任 平,李月彩,等.脾虛證與膽囊收縮的關系[J].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02,10(5):262-264.
[20]劉松林,梅國強,趙映前,等.疏肝和胃湯對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胃竇iNOS、5HT及SP表達的影響[J].湖北中醫學院學報,2010,12(4):3-5.
[21]張仲林,臧志和,鐘 玲,等.六君子湯對脾虛證大鼠胃腸激素影響的實驗研究[J].中成藥,2010,32(4):659-661.
[22]黃穗平,李 葉,羅云堅,等.功能性消化不良中醫證型與胃腸動力及激素的相關性[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002,19(4):26-269.
[23]朱方石,張旭東,朱海杭,等.非潰瘍性消化不良證型與胃動素及胃電參數關系的研究[J].遼寧中醫雜志,1996,23(7):291-292.
[24]潘志恒,黃冬梅,閻 平,等.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中醫證型與胃排空功能關系的研究[J].中醫雜志,2002,43(3):213-214.
[25]方盛泉,朱生梁,倪紅梅,等.功能性消化不良中醫證型與胃動力學的關系及其臨床意義探討[J].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2005,19(2):27-28.
[26]邵文全,莊曉丹.胃脘痛證型與胃腸激素相關性研究[J].江蘇中醫藥,2007,39(5):25-26.
[27]劉 汶,范 萌,周 呂,等.柴胡疏肝散對功能性消化不良肝氣郁結證患者胃動力及胃腸激素的影響[J].中醫雜志,2010,51(1):30-33.
[28]王 麗,朱飛葉,石燈漢,等.功能性消化不良與胃腸激素的關系及中藥調節胃腸激素的研究[J].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08,32(4):554-556.
[29]李 花,蔡光先,劉柏炎.中醫“肝脾相關”理論闡微[J].天津中醫藥,2010,27(3):210-212.
[30]王洪京,趙 明.中醫心胃相關理論探討及臨床應用[J].中醫研究,2010,2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