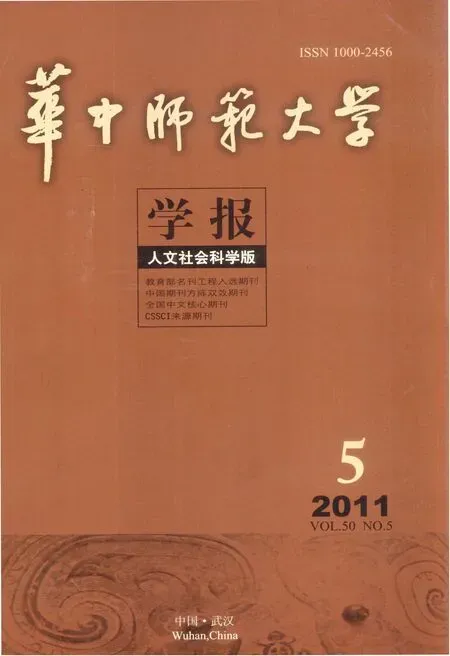南高學派與現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
——以孔子觀為中心的探討
許小青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漢430079)
南高學派與現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
——以孔子觀為中心的探討
許小青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漢430079)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北大新文化派的激烈反傳統主張激起了南高—東大師生的熱烈回應,催生了以“學衡派”為主體的南高學派。其后,南高學派以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為中心,并擴展到南北多校,形成一個廣泛而延綿的學術文化網絡,造就了現代中國的一個學術社會。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南高學派在柳詒徵、吳宓、郭斌龢、張其昀等倡導下,以《學衡》、《國風半月刊》、《大公報?文學副刊》和《思想與時代》為陣地,重塑孔子形象,發起“新孔學運動”,倡導“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并在60年代臺灣復興孔學,成為現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一支重要派別。20世紀南高學派的演變歷程,不僅表明后五四時代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自始至終交織在一起,而且也顯示出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與北大新文化派的激進主義如影隨形,成見與心結俱深。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南高學派的民族主義與政治上權威主義經歷一個由分到合的復雜過程,顯示出現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
南高學派;孔子;新孔學運動;人文主義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以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為主體的“學衡派”,激烈地批評新文化派的反傳統主義,高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旗幟,在學術文化與北大新文化派立異,形成了中國現代學術史思想史上“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成為20世紀20年代學分南北的一個突出現象。長期以來,在新文化主流派的話語支配下,南高學派這段歷史并不彰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的研究取向發生了重大轉變,圍繞近代中國思想上的激進與保守爭論激烈①。在這一背景之下,有關南高—東大與北大學術文化之爭重新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并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②。不過,檢討相關成果,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五四時期的“學衡派”,且對于南高學派和北大新文化派的研究和看法,或多或少將派分的成因——往往是他指和后認——人為地當成事實,并滲入相關的史實與論斷之中,容易造成先入為主和倒敘歷史的弊病③。本文擬從歷史主義的角度,以孔子觀為中心,初步梳理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的流變,進而探討現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與激進主義及權威主義的相互關系。
一、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與孔子形象重塑
20世紀30年代初,周谷城就對五四時期的北大與南高進行過評論,稱:“從前北大曾新極一時,凡奉行新教育主義的,當然到北大去。與北大對抗的有南高。那么反北大,而且專拜古典主義的,當然到南高為好。”④周氏觀察雖有可商之處,但大體上揭示了五四時期北大與南高學分南北的歷史。
北大與南高在學術文化上的分歧,主要表現為北大的《新青年》同仁與南高《學衡》諸友之間的文化主張對立。《學衡》是由南京高師-東南大學⑤一批反對北方新文化運動的教授于1922年1月創辦的一份綜合性文化雜志,直到1933年出版至79期停刊,前后共存在11年。其編輯部設在東南大學內的時間共二年半,即從1922年1月到1924年6月,共出了1-32期。東南大學時期的《學衡》是一份具有明顯地緣特色的文化雜志,其主要編輯和撰稿人大部分為東南大學教授,尤其以文史哲學科為主。其核心成員有吳宓、梅光迪、劉伯明、柳詒徵、胡先骕,尤其以吳宓為自始至終的中堅。東南大學中主要撰稿人還有:蕭純錦、徐則陵、繆鳳林、景昌極、張其昀、徐震諤、束世徵、向達等。這些學者就知識背景和人脈關系而言,有一個大至相同的特點,要么從清華學校畢業、留學美國而執教于東南大學,如劉伯明、梅光迪、吳宓;要么執教于東南大學或就學于東南大學,如柳詒徵、繆鳳林、張其昀、景昌極等。二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師友關系,因此可以判斷出《學衡》是東南大學的同仁雜志。《學衡》開篇即點明辦刊目標:“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的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⑥其宗旨是站在中西文化融合點上,致力于國學和西學兩個方面,并特別提倡“以吾國文字,表西來思想”⑦。這里所言的“吾國文字”即明確指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思想的提出是直接針對當時國內的文化研究現狀而言的。湯用彤指出當時國人的文化研究有三種不良傾向:“誹薄國粹者”、“輸入歐化者”、“主張保守舊文化者”,他認為這三種傾向的共同缺點是“淺”與“隘”,如主張“輸入歐化”論,他認為其缺點是對于西方文化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常以一得之見,以偏概全,“于哲理則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戲劇則擁戴易卜生、蕭伯納諸家”,“似乎柏拉圖盡是陳言,而莎士比亞已成絕響。而激烈反傳統者,則不值得一駁。”⑧文中所及杜威、尼采、易卜生等西方現代思想家,顯然矛頭所向是針對北大新文化派。《學衡》雜志成立后在文化觀念與北大新文化派發生了激烈的論戰。如文學的新舊、文白的優劣和新人文主義與實驗主義之爭等,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以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派,具有相當的反傳統精神,雖然還談不上“全盤性”,但是在儒學及禮教領域卻表現得相當激烈,“打倒孔家店”更是成為一個最簡潔的口號和象征。北大新文化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尤其在孔子評價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承認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認定其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正是孔子與儒學造成今日中國的腐敗與落后;2.孔子之道不適應現代生活;3.孔子之道與歐化背道而馳⑨。
與北大新文化派不同的是,南高的學衡派在孔子問題上,主張以批評的精神研究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本來面目,尤其應該剔出后來統治者強加在孔子身上的附會成份,他們提出兩點值得注意的區分:一是“真孔”與“假孔”問題;二是孔子與儒學制度化后的中國。針對新文化運動者將中國今日的衰落歸咎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學之類的文化傳統,學衡派主將之一柳詒徵便明確指出,中國社會衰落只是由于社會動蕩和歷史事件的無常,而不能將之歸結到孔子和儒家身上。他說:“中國今日之病源,不在孔子之教……在滿清之旗人,在鴉片之病夫,在污穢之官吏,在無賴之軍人,在托名革命之盜賊,在附會民治之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諸人固皆不奉孔子之教。”⑩他開出以儒家思想為救治中國近世之病的藥方,就是從中國病象的表征中總結得來的,其矛頭是直接針對新文化運動者以啟蒙的姿態批判中國傳統。在柳氏看來,孔子的真正價值在于他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所在:“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點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下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在此,他極力表彰孔子的人格:“孔子以為人生最大之義務,在努力培養其人格,而不在外來之富貴利祿,即使境遇極窮,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蕩蕩之樂。無所歆羨,自亦無所怨尤,而堅強不屈之精神,乃足歷萬古而不滅。儒教真義,惟此則已。”?
為重塑孔子的文化偉人形象,學衡派有意將孔子時代與希臘文明起源進行并列比較,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諸多契合之處。《學衡》雜志創刊號上將孔子與蘇格拉底畫像并列編排在一起,以示中西文化巨子的同等地位。胡先骕認為孔子是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齊名的世界文化偉人,其“學說為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胡稷咸論證說希臘文明的性質與中國文化頗相仿佛:“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所研究之主要問題,厥為人類道德之增進,與我國孔孟所討論者同。”?郭斌龢也指出孔孟之道的“中正和平正”是一種人本主義,“與古希臘人之態度頗相似,平易近情,顛撲不破。”?
學衡派作為一種與新文化運動相悖的文化派別,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與《新青年》大不一樣,劉伯明認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斷不能一筆抹殺,“自歐美之風東漸,吾國學子率喜趨向實利,……而以舊有文化為不屑研究,或無補于救亡。”?同樣在東南學術界有很大影響的柳詒徵,在討論大學生的責任問題時,對于學者的文化態度提出了三原則:一對于今人的責任主要為“改革”和“建設”;二對于前人的責任主要是“繼承”和“擴充”;三對于世界之責任,主要是“報酬”和“共進”?。這種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態度,也是學衡派的基本文化立場。學衡派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也表現對國學的研究方法與新文化派大異其趣。《學衡》創刊時就宣稱,“本雜志于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后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矛頭所向無疑是針對胡適“整理國故運動”及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疑古思潮。梅光迪直接指責胡適的國學研究方法,認為“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異義,以期出奇制勝。且謂不通西學者,不足與言‘整理舊學’。又謂‘整理舊學’須用“科學方法”,其意蓋欲嚇倒多數不諳西洋文未入西洋大學之舊學家,而彼等乃獨懷為學秘術,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風頭’,即有疏漏,亦無人敢與之爭。然則彼等所傾倒者,如高郵王氏之流,又豈曾諳西文、曾入西洋大學者乎?”?明顯對胡適等人提倡的“整理國故”的方法、動機和學術根底提出質疑。
由此可見,與新文化派激烈地反傳統不同,學衡派對傳統懷有很深的敬意。學衡派這一主張對于東南大學學風的形成影響深遠。何謂學風?正如時人所講,“學風這個名詞,也就是同一時空之教者與學者的行為、意態、思想、傾向,同時同地教者學者內外生活之綜合的表現,就是學風。”?在柳詒徵、徐則陵、竺可楨等直接指導下,南高-東大的學生創辦了《史地學報》、《文哲學報》等刊物。《史地學報》宣稱:“近來自號新文化運動者,大都浮浮在信,稀為專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談之文哲諸學,亦僅及表面,而于專門學科,益無人過問;循是不變,將使名為提倡文化,而適以玷辱文化。”故他們決定組織中國史學會,“促進實學之研究”?。而《文哲學報》則取中西互采的立場,“本刊以研究文學哲學為旨,國故西學齊重互見,古言今說兼取并論,于哲學不宗一派,惟真是歸,于文學不拘一格,惟美是尚,誠以學術本無畛界,而哲學示真理之廣溥,文學寓情思之潛通,尤為至公無私之物。”?其基本學術理念與《學衡》相通,甚至外界批評者稱其為“《學衡》的孫子”,以致南高學生公開辯駁:“譬如晨報上某君,罵《文哲學報》是《學衡》的孫子,無論《文哲學報》和《學衡》的主張未必盡同,就是《文哲學報》內部的主張,也未必彼此無異,發刊詞內已經一不進則退聲明。請問罵的人可得有罵的理由,或者罵的人自己承認是《新青年》、《新潮》等等雜志的孫子,所以步亦步,趨亦趨,發出那一口同聲的議論,以為《文哲學報》,也是這樣的,這也勉強算是一個理由了。”?在東南學風的熏陶下,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鄭鶴聲、景昌極、王煥鑣、向達等學生輩迅速成長起來,成為南高學派重要傳人。
對于五四時期南高學派的尊孔主張,也不斷被后來的南高人所總結與肯定。郭斌龢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說:“當舉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國舊有文化之日,南高諸人獨奮起伸吭與之辯難。曰中國舊文化決不可打倒,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決不可打倒。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南高師生足以當之。”?到了40年代,中央大學有人總結校史時,將郭氏的評論稍加變通,進一步加以發揚:“猶憶民國八九年間,當舉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國舊有文化之日,本校學衡諸撰者,獨奮起與之辯難曰,中國舊有文化決不可打倒。孔子中國文化之中心,決不能打倒。迨其后新說演變而為更荒謬之主張,其不忍數千年之文化,聽其淪喪者。又一反其所為,乃大聲疾呼:宏揚固有道德,建立本位文化,排斥浪漫思想者。”?到了20世紀60年代,張其昀回憶說:“民國八年(1919年)以后,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范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
……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可見,五四時期以“尊孔”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張,成為南高學派的核心理念,也為這一學派不斷繼承和發揚。
二、“九一八”后“國難”下的“新孔學運動”
1925年發生東大易長風潮后,南高學人紛紛離開了大本營東南大學,北上清華、東北大學等地。經歷北伐、遷都等系列政治變動后,20年代末30年代初,“南高學派”重要成員柳詒徵、張其昀、繆鳳林等以中央大學為根據地重新聯結。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國的民族主義再度興起,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文化民族主義的高漲并走向成熟,其中文化復興問題成為一個共識: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或前提,復興民族文化關鍵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尊重本國的歷史和文化?。
在“國難”下,南高學人紛紛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重樹南高學風,分處南北各地的南高同人,相互配合,發起了一場“新孔學運動”。
在北方,南高學派以清華的吳宓為主要聯絡點,以浦江清、張蔭麟等為助手,以《大公報·文學副刊》為宣傳陣地,倡導孔子的人文思想,率先發起“新孔學運動”。新孔學運動最早倡導者是學衡派西學思想導師哈佛大學的白璧德,白氏在《中西人文教育談》中,特別希望以一種“人文的君子的國際主義”、“以中和禮讓之道聯世界為一體”,“吾所希望者,此運動若能發軔于西方,則中國必有一孔教運動。”?這一思想在后五四時期經白氏的中國信徒吳宓、梅光迪等不斷宣傳,成為學衡派成員的思想支柱之一。五四時期由于康有為、陳煥章等的“孔教運動”不得人心,南高諸人并沒有發起“孔學運動”。不過到了九一八事變后,在“國難”之下,“新孔學運動”最早是由中央大學教授郭斌龢提出。
九一八事變后,郭斌龢在北平華文學校發表英文演講,專門指出“孔學非宗教,而是一種人文主義。”認為中國一向以孔學立國,孔學是中國的國魂,“而近三十年來,孔學開腔重創,使國人失去信仰,思想無序,造成外患日重。”他為新時期救國開出藥方就是發起“新孔學運動”。具體而言,“新孔學運動”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應發揚光大孔學中有永久與普遍性的部分,如忠恕之道、個人節操的養成等等,而鏟除受時空間的影響所產生的偶然部分,如繁文縟節易流為虛偽的禮儀,及后人附會的陰陽家言等等;(二)應保存有道德意志的天之觀念。(三)應積極實行知、仁、勇三達德,提倡儒俠合一、文人帶兵的風氣,如中國歷史上諸葛亮、文天祥、王陽明、史可法,及清末之曾國藩、胡林翼等,皆以文人而握兵權。知恥近乎勇、殺身成仁、士可殺不可辱等古訓,應盡量宣傳,成為全國國民牢不可破的信條。(四)應使孔學想像化、具體化,使得產生新孔學的戲劇、圖畫、音樂、雕刻等藝術?。可見,“新孔學運動”的目標,就是要將此前孔子形象的重塑發展到一個綜合的文化運動階段,且與“國難”下的救亡運動聯系起來。
郭斌龢的《新孔學運動》演講稿由《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顯然得到該刊主編吳宓的欣賞,且與吳宓的一貫主張相契合。早在20年代《學衡》早期,吳宓就大力宣傳孔子的價值與孔教的精神,就是到了北方的清華后,他仍不改斯志,1927年還專門撰文,力陳孔子的價值和孔教的精義,批評“自新潮澎湃,孔子乃為攻擊之目標,學者以專打孔家店為號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輕薄尖刻之筆,遍致底譏。盲從之少年,習焉不察,遂共以孔子為迂腐陳舊之偶像,禮教流毒之罪人,以謾孔為當然,以尊圣如誑病。”?此時,郭氏“孔學運動”也激發吳宓的孔學觀,吳宓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孔誕小言》一文,指出現在研究孔子,首要就是對孔子要持了解與同情的態度,“孔子之更為人認識崇敬,亦文化昌明學術進步必然之結果矣。”?言下之意,北大新文化派一系對于孔子的批評,乃是學術不進步的結果,也是造成中國今日難局的原因之一。
郭斌龢的“新孔學運動”號召得到中央大學南高學人的積極回應,中央大學同仁刊物《時代公論》先后組織發表了多篇尊孔文章,對郭文進一步發揮。其中張其昀在《時代公論》第十三號發表《教師節之日期》專文,主張以孔子誕辰日為教師節紀念日,為新孔學運動提出了一個切實的紀念方法。其后又在第十四期再著長文,再述教師節與孔學的關系,提出以孔子為誕辰日為教師節紀念日的四大理由:1.中國講學之風始于孔子;2.中國以教授為職業始于孔子;3.中國教育宗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大綱始于孔子;4.中國文化統一始于孔子。張其昀在文中公開支持郭斌龢的“新孔學運動”,稱:“吾友郭斌龢君,嘗有《新孔學運動》,略謂中國向以孔學立國,孔學為中國國魂。近三十年來,為新派摧殘抨擊,孔學遂一蹶不振。國人根本信仰已失,思想界產生一種無政府狀態。對此種無政府狀態,在內政與外交上,完全暴露,長此不改,外侮將源源而來,此正愛國志士所深切憂慮,而亟思挽救者也。又謂孔學非宗教,而為一種人文主義,以人為本,不含神學與超自然之理論;此階級之優秀者,每愿犧牲孔學犧牲生命與物質上之享受,則孔學實含宗教性;謂之為廣義宗教,亦無期不可。又謂中國目前最要者,為一新孔學運動。此種新孔學運動,應為一切改革之原運動。哀莫大于心死,中國國心,已瀕死境,新孔學實為使此將死之國心復活之恮良方。”?
對“新孔學運動”倡導最為有力的是《國風半月刊》,該刊也是九一八之后民族主義高漲下的產物。1932年9月1日《國風半月刊》在南京正式出版發行,核心成員有四,社長柳詒徵,編輯委員張其昀、繆鳳林和倪尚達。其主要撰稿人為中央大學教授如范存忠、張江樹、熊慶來、景昌極、盧于道、汪辟疆、胡煥庸、劉咸、謝家榮、鄭曉滄、鄭鶴聲、蕭一山、劉永濟等,同時也吸引當時的一些國學大家如章太炎、歐陽漸、蒙文通和科學界的秉志、竺可楨、嚴濟慈等為之撰稿。
柳詒徵在發刊辭中對創辦背景作了清楚的交待:“張繆諸子倡為《國風半月刊》,囑余為發刊辭。余曰:嗚呼噫嚱!吾儕今日尚能強顏持吾國之風而鳴于世耶!淞滬之血未干,榆熱之云驟變;雞林馬訾,莫可究詰;仰列強之鼻息,茹仇敵之揶揄。此何時,此何世,尚能強顏持吾國之風而鳴于世耶!”?正是在這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柳詒徵認為,時局比現在有人所擔心的“季宋晚明”的歷史重演更為嚴重,因為那時戰伐媾和、蒙塵割地等一切還可以自主,但現在情勢完全操之于外敵之手,“有史以來無此奇恥”。更為嚴重的是,“雖以總理遺教,昭示大經,欲復民族之精神,盛倡政治之哲學;而喪心病狂者,依然莫之或革,社會之震憾,風化之污濁,直欲同人道于禽獸,而一以飾以異域之所嘗有,遂莫之敢非。”文中“一以飾以異域之所嘗有”等語,實際上暗指曾以《嘗試集》為名鼓吹西化的胡適等新文化派,柳氏對于新文化派猛烈批評,認為只有從民族歷史文化之中,才能尋求救國之道,即“以炎黃胄裔之悠久,擁江河山岳之雄深,寧遂無奮發自強為吾國一雪此恥乎。”因此他明確地提出《國風半月刊》的宗旨:“本史跡以導政術,基地守以策民眾,格物致知,擇善固執;雖不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見,要以降人格而長國格為主。”?到第二年,《國風半月刊》在封面上以更為直接的方式,標明其宗旨為“一、發揚中國固有之文化;二、昌明世界最新之學術。”?從這一點而言,該雜志與東南大學時期的《學衡》有不少共通之處。
與《學衡》尊孔主張一脈相承,對于民族精神的恢復集中表現在:《國風半月刊》創刊不久就專門出版了紀念孔子的“圣誕”特刊(第三號),可以說這是該刊宗旨的一個明顯標志。這一期共刊九篇紀念孔子的文章,這些文章首先回擊社會上對于孔子的各種攻擊。梅光迪在文章中禮贊圣教,力排諸子,他發現孔子平易近人,盡管在基本的原則上不讓步,卻并非不茍言笑的假道學。他批評“今日開口進化、自由平等博愛科學方法”的假道學、新名流,也不過是過去孔子所批評的“德之賊也”的鄉愿而已。對于新文化運動以來,社會上猛烈批評孔子的現象,梅光迪認為“今日之乳臭未干兒,皆挾其一知半解之舶來學說,以揶揄孔子、掊擊孔子者,此非僅孔子一人之厄運,實亦吾民族文化之厄運也。”?
柳詒徵先后撰有《孔學管見》和《明倫》兩文。他批評近年對于孔子的兩種態度——無論是打倒孔家店,還是以孔教號召天下,均是對于孔學的曲解,他認為“近年來有所謂專打孔家店呵斥孔老頭子者,固無損于孔子毫末,實則自曝其陋劣。然若康有為陳某某等以孔教號召天下,其庸妄亦與反對孔子者等。真知孔子之學者,必不以最淺陋之宗教方式,欺自欺人,且以誣蔑孔子也。”?并重申人倫、倫理、禮教為今日研究中國學術、道德、思想和行為的根本問題,他反對新文化者的意見,重新以明五倫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對于改變世風和穩定社會仍然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其后,他又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化的根本,便是就天性出發的人倫,本乎至誠。這種精神方能造就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有過去幾千年光榮的歷史。”只有一步步地發揮人倫的作用,“使中國文化的精神,從新發揚起來,那便是中國民族復興的良藥見了功效了。”?
繆鳳林批評“今人卻專以禮教詬病孔子”的現象:“現在一般對于禮教,非鄙不屑言,即談虎色變;孔子也就被視為拂逆人性的禮教制造者或吃人禮教的代表。”繆鳳林認為這實對于“禮”的誤解,就其本質而言,“禮是社會的習慣,亦是社會的秩序。人類既已有了社會,自然有這些習慣和秩序。人既與人相處,為社會中一分子,自然須履行這些習慣和秩序。鄙夷固屬不可,畏忌尤可不必。歸罪孔子,更無是處。”?此外,《國風半月刊》的同仁對于孔子與民族精神的關系加以發揮,強調孔學依然是救國的良方。這如同郭斌龢所言,一年來外患雖深,而民族精神反趨消沉,國人迷途知返,“深信倡明孔學為起衰救弊之惟一方針”?。當然,在融合中西的旗幟下,他們也努力將孔子的思想與西方近代思想進行比較,以此證明孔子的思想不僅未過時,而且與西方思想有諸多暗合之處。
“南高學派”成員在南北報刊同時紀念孔子,倡導“新孔學運動”,既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孔反孔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有意識批判,也是民族危機時刻對傳統文化的重新反思,“孔子”成了傳統文化認同的最大象征,“新孔學運動”成為該學派借以重新集結的旗號。這一動向遭到北大新文化派胡適諸人對《大公報·文學副刊》的關注與批評。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大學文學院的一批文史教授所倡導的以“尊孔”為主旨的“新孔學運動”,后人往往將之與國民政府要人和地方大員倡導的尊孔讀經運動聯系在一起,認為這是中央大學保守主義的表現?,有意地將學統與道統聯系起來,這一看法不僅失之于籠統,而且是將后來觀念移加到當時人身上的誤讀。應該注意到《國風半月刊》的一批學人(主要是人文學者)當時倡導的“新孔學運動”,主要是以文化為出發點。事實上中央大學倡導的“新孔學運動”不僅早于當時官方尊孔文化政策的出臺,而且待到官員輿論一致“尊孔”之時,他們卻有意地保持低調,并時時提醒與官方保持應有的距離。郭斌龢1935年專門提到:“廿一年秋季,南高舊人曾就國風雜志刊印圣誕特刊,提倡尊孔。翌年而尊孔之說洋洋盈耳,見諸命令,形諸祀典,與新生活運動相表里,而此諸人者,力避挾策干時之嫌,退藏于密,惟恐人知,不敢應聲附和以嘩眾而取寵。此獨往獨來不慕榮利之態度,真吾所謂南高精神篤實而有光輝的一種表現也。”?顯然南高學人此時重樹“尊孔”之旗,是想與“政統”劃清界限的,中央大學人40年代回憶這段歷史時,多引用上述文字,并加以改造,說明大學的獨立性,“及二十一年秋間,本校舊人,曾就國風雜志刊印圣誕特刊,提倡尊孔。翌年而尊孔之說大行,且見于命令,崇諸祀典,與新生活運動相表里,而本校諸先進首倡此論者,類皆退藏于密,不以自多,斯非顯而易見者乎。”?其本義與官方所宣傳的文化統制的出發點還是有相當的區別。但到了抗戰時期,南高學派的獨立文化主張卻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日漸與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結合在一起。
三、從“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到孔學復興
20世紀30年代初,北大新文化運動主將羅家倫出長中央大學,社會上便有“北大戰勝中大”之說,“南高東大中大校友總會”更采取不合作態度,并發起驅羅運動,雖未成功,但卻埋下日后沖突的種子。特別是在在紀念南高成立20周年和遷校問題等問題上,羅家倫與南高舊人矛盾公開化?,致使1936年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以張其昀、郭斌龢為首的一批南高學人移席浙江大學;胡先骕出長中正大學,帶走王易等一批南高學人,抗戰中,南高成員借助于貴州的《思想與時代》、重慶的《中國學報》和江西的《文史季刊》繼續宣揚一以貫之的尊孔主張。
1941年,張其昀更在浙江大學西遷遵義后創辦《思想與時代》雜志,其創辦有著明顯的官方背景,竺可楨在1941年6月14日的日記中記載:“曉峰來談《思想與時代》社之組織。此社乃蔣總裁所授意,其目的在于根據三民主義以討論相關之學術與思想。基本社員六人,即錢賓四(穆)、朱光潛、張蔭麟、郭恰周、張曉峰等六人。”?其中南高出身的張其昀是關鍵人物,不僅是刊物的主要創辦者,更在刊物發展及與學人、官方的聯系中起作舉足輕重的作用?。先后為刊物撰稿的南高出身的學人除張外,還有郭斌龢、景昌極、梅光迪、樓光來、吳宓、繆鳳林、陳訓慈、胡先骕、范存忠等。其他重要骨干錢穆、朱光潛、張蔭麟亦為同道之人,且自20年代以來與南高學人交往圈子來往密切,甚至有人認為,他們也屬于保守主義或南方學人圈子?。
雖然《思想與時代》沒有發刊詞,并不等于沒有宗旨,這可從其每期中刊登的“歡迎下列各類文字”中也透露出基本傾向,胡適在美國看到后認為其中前兩項即是他們的宗旨,第一,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第二,我國固有文化與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特別是1947年復刊后,作為主編張其昀明確其宗旨為:“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他解釋說:“科學的文化是現代教育的重要問題,也是本刊的努力方向。具體說,就是融貫新舊,溝通文質,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導,為現代民治厚植其基礎。”?除了科學外,更主要落腳點在人文主義的宣揚上。
郭斌龢撰文特別禮贊孔子為代表的“儒行”,“吾國固有文化,以儒家學說為中心。而儒家學說中,尤以理想人格之提示,最為具體,最為實效。人類行為之推動力,究極言之,非感情,非理智,而為想像。”“儒家所長,即在善用想像,提示其理想人格。”這種理想的人格,在古代或以成人、君子、士、賢等不同的名稱稱之,他細致區分了實際生活中的“小人儒”和“君子儒”之別,以“君子儒”為立國之精神,而“君子儒”正是孔子所首但是和實踐的,“要其最終鵠的,在勉力求為智仁勇三方面平衡發展之完人。而‘儒’之一字,實際上尤為提示此理想人所通用之名稱。”?在郭氏看來,如果能將孔子所倡導的君子儒發揚光大,就可以解決中國當下以及未來的重大難題。對于儒家文化的倡導,是《思想與時代》的一大主題,謝幼偉專門發揮了孔子的孝道思想,論證以孝作為中國社會重建的基礎。郭斌龢在文后附有一篇“附言”,對于意義作了引申,認為“孝”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具有恒久的價值:“生產工具,經濟制度,可因地制宜,隨時更改。此一點人性,一點真純優美之民族道德,斷不當令其隨家庭生產工具,家庭經濟制度而俱去也。”他極力倡導孝文化,認為這是一個民族文化中應當的部分,即“一民族有一世族之中心思想,中心信仰。個人有風格,民族亦有風格。生活方式可變,獨特之風格,不能盡變,亦不宜盡變。變當其所變,而守其所當守。”[51]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期另外兩份南高學人雜志《中國學報》和《文史季刊》先后創刊,前者由汪辟疆在重慶主編,后者由王易在江西泰和主編,均極力宣傳儒家文化與孔子思想。《中國學報》,除了繼續像《學衡》、《國風半月刊》刊登舊體詩外,一個主要的內容則在于倡導“尊孔”。創刊號中首篇登載的李翊灼長文《中國學術與中國學報》,編者題記稱:“至本篇樹義立文,迥異時尚,讀者幸勿以尋常文律視之矣。”故完全可視為《中國學報》的發刊詞(本沒有發刊詞,編者稱之為“循例之文,無關宗旨”。)李氏認為孔子的偉大形象來源于中國傳統的六藝:“中國之學,重道德仁義之大經大本,而了輕術數方技之枝末。務得其精神,而遺其糟粕,其由來蓋久矣。故孔子之于六藝,必達諸成人,如其言。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而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也;潔靜精徹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屬辭此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52]其后李翊灼更將重點放在“禮學”復興上,他論證在“國難”下“復興中國民族,應自復興中國之固有文化。”他力陳“中國文化的源泉,實以禮學為出發點,舍禮無所謂文化也。”所以,他將“禮學”復興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文中細致地回答了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復興禮學是否為中國所必需要?第二,今日中國如何復興禮學?[53]盡管《中國學報》堅持時間不長,出版期刊不多,許多活動亦無法真正展開,但從其文化思想傾向來看,無疑是直接繼承南高學風,也成為南高學派在戰時中國宣揚其文化民族主義的重要分支。
1949年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以意識形態統一思想界,而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島內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論爭仍在繼續。1954年南高學人張其昀出任臺灣“教育部長”,引起胡適在美國對南高的老校長郭秉文戲言:“南高征服了北大”,郭秉文卻嚴正地回應:“學術為公,再不可有門戶之見。”[54]胡、郭二氏一諧一莊,重提南高北大這一學術公案,不能說完全與人事變動無關。旅居香港的曹聚會仁則在回顧南高學派與北大新文化派的歷史,進行了一番綜論:“直到蔣氏天下窮居小島,張其昀任‘總統府秘書長’,又轉任‘教育部長’,這才是東南系稍抬頭之時。北大系不甘示弱,其間斗爭之跡,稍知世務的,一定看得很明白的。”[55]曹氏以局外人的身份,從張其昀出任臺教育部長來觀察南高學派與北大新文化派勢力的消長,與北大派胡適所論如出一轍,集中反映出近代學派問題多與人事的糾纏在一起的復雜歷史。
事實上,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張其昀主政臺灣島內教育后,在不同的場合,以其特殊的身份,撰文、演講,紀念與宏揚南高的精神,而且在行動上恢復中央大學、創辦中國文化學院,重樹南高大旗。
張其昀在臺灣多次南高中大的紀念演講和撰文中,重申南高的歷史悠久和學脈相傳,特別指出與北大對峙的歷史,在中大六十周年紀念演講中,他稱:“歷史上幾度成為國立大學的所在地,薪火相傳,學統綿延,達一千七百年之久。這種光榮的歷史,古今中外各國的大學,實未見其比。”“南高、北大,南北齊名。世人以為這是中國文化正宗與激烈派的對峙,固有其理由。事實的真相,則是北大為文學革命的起源地,南高為科學研究的大本營。”[56]對于南北學派的學風也進行了歸納:“世人或以為民國以來學風有南北兩派,北以燕都為中心,南以金陵為大宗,北派趨于細針密縷,南派趨于崇樓杰閣。”[57]
在整個回憶中,張其昀將重點放在南高-東大-中央大學對于現代儒學復興的重要意義,他宣稱:“國立中央大學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儒學復興的一個策源地。在五四運動以后,對中國歷史文化持懷疑與抨擊態度者,滔滔皆是。當時南京的我校,則屹立而不動搖,所謂‘鐘山龍蟠,石頭虎踞’,真為中流砥柱的氣概。我校所倡導的新學術,雖深受西洋思想的影響,而不為所轉移,而益充實光輝。這種儒學復興運動,經過四十年的時間,由發軔而漸趨成熟,以期成為吾國學術的正宗,中國真正的文藝復興。”[58]張其昀在60年代憶恩師劉伯明時,重提南高與北大20年代的歷史,“他(指劉伯明——引者注)對五四以后的新文化運動,持批評的態度。新文化運動很多治史學的人,但他們指史學狹窄化,甚至只成為一種史料學,他們往往菲薄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為保守,是錯誤的。歷賢前史,惟有民族主義才是國家民族繼繼繩繩發榮滋長的根本原因。當時南京高師,就學風而言,的確有中流砥柱的氣概。”[59]有意思的是,北大派領袖胡適看到張其昀這一回顧時,還專門去信,談及不能認同張氏這一評價[60]。顯然,南高學派與北大新文化派之間的分歧與心結,在臺灣時代還沒有完全解開。
在實踐南高學風方面,張其昀最重要的行動就是1962年創立了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學院其重要的源頭就是“南高”,張其昀在《華岡學園的萌芽》一文中,首先將中國文化學院的“萌芽”其歸結于“南高”,他寫道:“南京高師,雖然只是國立高等師范之一,可是它的地位很高。民國十年左右,南高與北大并稱,有南北對峙的形勢。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而南高是人文主義的大本營,提倡正宗的文化。Classics一字,一般譯為經典,南高大師們稱之為正宗。從孔子、孟子、朱子、陽明,一直到三民主義,都是中國的正宗。本人在南高求學期間,正當新文化運動風靡一世,而南高師生,主張融貫新舊,綜羅百代,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神,儼然有砥柱中流的氣概。面高北大成為民國初期大學教育的兩大支柱,實非偶然。”[61]
中國文化學院的前身仍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之初,他在答記者問時,談及辦學理想,稱:“華岡講學,承中原之道德,陽明風光,接革命之心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必有真知,方能力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不得,反求諸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62]中國文化學院的辦學理念更是繼承南高的精神,張其昀對于華岡興學,他在多種場合有大致相同的表述,他稱華岡的理想為四個“綜合”:(一)東方西方的綜合;(二)人文與科學的綜合;(三)藝術與思想的綜合;(四)理論與實用的綜合[63]。
中國文化學院的創立,其中的立足點,就是恢復傳統的敬意,其中尊孔是其要點。張其昀接續20年代初學衡派的尊孔主張和30年代的新孔學運動,繼續重申孔學大義,特別將孔子思想與人文主義聯系起來,張其昀明確提出:“孔子是中國人文主義的創立者。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師,他的誕辰已成我國的教師節。孔子學說與人文主義可視為同義語。孔子往矣,精神長存。孔子認為精神力較物質力為強固,故統治世界實為思想。孔子學說經無數者之闡述,而益發揚光大,稱為近代孔學或新孔學。吾人深信中國人文主義精神,為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這是一種最偉大的道德與精神永無窮盡的潛勢力。”[64]對于社會上批評尊孔與復古的保守傾向,他力辯孔子學說與現代文化的緊密聯系,對于中國文化復興更是不可動搖,“孔子學說為中國思想之主流,中國文化之大動脈。自孟子曾子以降,二千年來,薪火相傳,皆以繼承孔子之業為職志。歷代儒者,抱負宏偉,態度積極,思博慮遠,崇論宏議,務期見諸實踐,造福人類,幫能使孔子學說益為發揚光大,從精神上、教育上創造中國長期統一之光榮史跡。”[65]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他在辦理臺灣教育時特別強調孔子思想在現在大學中的地位,認為孔子思想是文化復興的基礎,他在《大學教育與文化復興》一文中強調:“孔子之學說對中華民族影響至大,孔子不朽的教澤,便是他集大成的方法與精神。”[66]所以其后在論及華岡精神時,他明確宣布:“華岡精神,即為大學精神。大學精神是什么呢?那是本校第一座建筑物所標榜的大成二字,也就是融貫古今,會通新舊,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遠溯孔子所倡導的集大成精神。”[67]在科學的時代里如何發表孔子的精神,張其昀特別擇時出,“現代人文主者必須了解科學的方法與精神,與時偕進。”[68]
由此可見,在五六十年代的臺灣,南高學派張其昀將其一貫的文化民族主義主張與國民黨當局的文化民族政策結合在一起,在島內宣揚儒家文化復興運動,同樣引起了文化觀察家曹聚仁這樣的評論:“過去三十年的‘世變’,真是偉大,其波瀾之壯闊,比法國大革命、蘇聯大革命還要奇麗些,從文化的波瀾,好似今日的中國大陸,乃是‘北大’系的天下,而臺灣則是‘東南’系的世界,因此,學衡派的思想正在左右草山的風雨。”[69]曹氏評論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到文化民族主義在島內的復活,顯示出南高學派在20世紀后半期的生命力,更表現出自40年代以來,南高學派與官方權威主義密切合作的歷史,這種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的結合,集中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臺灣的政治文化生態。
四、結語
在現代中國,以文化民族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南高學派形成于五四時期,其成員的文化活動卻長達大半個世紀。在現代中國的風云變幻的時代大潮中,南高學派以大學為主要基地,通過創刊刊物來聯絡同仁,極力宏揚民族文化,視孔子為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象征,不斷發起孔學復興運動,成為現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重要一支。透過南高學派文化民族主義演變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作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一支,它有著這樣一些突出的特點:
1.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并非是一種嚴格意義上“保守”
正如美國學者史華慈先生對“保守”所作了的定義:“凡是未經反省地保持固有的行為、感受與思考之方式,這種慣性傾向可稱為‘保守的’。”[70]顯然,那種將“保守”視為一種落后、反動的貶義詞的定性,不太適合南高學派的文化觀。因為,從歷史和比較的角度看,20世紀的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開明的保守,一方面,對于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多重反思,視中國文化為承接新文化的主體,肯定了傳統文化中蘊藏的現代意義,特別將孔子為代表的倫理道德和人文精神視為拯救現代西方文明病的良方;另一方面,主張中西文化的學習與互融,并不排拒以現代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且這個學習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可從他們所辦刊物的宗旨中表現出來。不過南高學派強調的是在批判西方現代文明弊病下向真正的西方文明正宗學習,其中在他們看來,西方文化的內核應以哈佛白璧德為首的“新人文主義”為中心。因此,從這種角度來看,南高學派的學人的文化立場是一種開放式的,民族本位與世界眼光二位一體的,更多地表現出一種人文主義的色彩,這也是后五四時代文化民族主義的整體時代特征。
2.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或明或暗所針對以胡適為首的北大新文化派
五四時期,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與北大的激進主義進行了從文化到學術各方面的論戰,形成了南北學術文化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格局。20世紀30年代,南高學派倡導“新孔學運動”,同時倡導文言與“讀經”,遭到北大派胡適等人在《獨立評論》上的嘲諷。到了40年代,胡適對南高學人創辦的《思想與時代》進行了或明或暗的批評。在五六十年代臺灣島內,南高學派與北大新文化派的人脈與思想之間的競爭或隱或顯地交織在一起,其文化立場也多表現出歧義的一面。因此,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發展歷程,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與近代文化激進主義(尤指北大新文化派)相對抗的歷史,亦表明,“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區分的、相互依賴的。它是保存與革新這樣一個同等到重要的過程的兩個方面。”[71]過去學者多以新舊來區分南北[72],這種簡單的二元化區分容易遮蔽許多歷史真相。其實北五四后學分南北的歷史,實與北大派與南高學派有著復雜的人脈關系,且化作成見與心結,雖然南北各有新舊,但觀念差異與人事糾葛之中,雙方明爭斗,且有意氣用事在其中[73]。故而,南高學派的保守主義與北大的激進主義還如同硬幣的兩面,既有思維的同一性,又包含著復雜的人事糾結。雙方圍繞“孔子”的論爭可以說貫穿于整個現代中國,反映出文化危機下尋找文化出路的不同方法與路徑。可以預見,在中國的文化危機沒有徹底化解前,這一爭論還將以各種方式長期存在下去。
3.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關系微妙
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其誕生、傳播、流轉大半個世紀,不絕如縷,影響顯然超越出學派的范圍,個中緣由,還在于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與民族主義的不斷高漲。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所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優越意識,因此,有可以將其稱為文化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一般意義上而言,文化民族主義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是文化取向與政治取向的背離[74],不過,在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演變史來看,卻經歷了一個由與政治保守主義關系由離到合的過程,文化與政治表現得十分微妙。在五四時期,南高學派的文化主張與政治之間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們批評北大新文化派“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75]實際上點明了五四文化激進主義的強烈政治取向。[76]北大新文化派隨著國民革命的興起,在20年代后逐步取得主導的地位。但國民黨上臺后,政治上文化上卻一步步向保守主義退卻,九一八后國民黨文化政策的轉向,在文化統制之下,尊孔讀經和新生活運動日漸熱鬧,似乎與南高學派的“新孔學運動”合上了節拍,但此時的南高學派卻努力保持文化的獨立性,有意地與官方的文化政策保守距離。然而,抗戰軍興,《思想與時代》不僅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授意和資助,其文化立場與政治主張日益交織在一起,張其昀、錢穆、張蔭麟等由文化的保守轉向政治上的保守,表現出極端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建國、國防、領袖與建都等政治問題上主張擁護集權,[77]北大新文化領袖胡適批評它有“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和“擁護集權的態度”[78],更是有所本。到了臺灣時期,張其昀復興儒學主張更是成為國民黨官方政治保守主義在文化上的實踐。南高學派的文化民族主義演變的歷史,表明在民族主義高漲的現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關系復雜而微妙。
注釋
①爭論文章可參考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的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研究綜述可參考鄭大華、賈小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學界已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五四時期的學衡派,代表性的成果有沈松僑的《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年),以五四時代為歷史背景,側重與新文化派的比較中來探討學衡派的文化見解與歷史地位。鄭師渠的《在歐化和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從文化觀、史學思想、諸子學、教育等不同等方面對學衡派的文化思想進行了專題研究。高恒文的《東南大學與“學衡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研究了學衡派在東南大學的成長歷程,注意到學衡派與東南大學內其他派別(如中華教育改進社、國學研究會)之間的聯系與區分,特別指出不能將學衡派與東南大學等同視之。不過,近期已有學者注意從較長時段和相互脈絡中來研究這一學派,著作方面的代表為沈衛威的《“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從長時段歷史中選取五個相關刊物——《學衡》、《史地學報》、《大公報 ?文學副刊》、《國風半月刊》、《思想與時代》,來分別探討學衡派的文化整合、歷史尋根、文學批評、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察的表現;論文可參考彭明輝的《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形成(1911-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9期,2008年5月,第51-84頁)則從學人交往網絡來展示一個不同于北方的學人文化圈子。
③桑兵:《中國思想學術史上的道統與派分》,《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并收入氏著《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北京: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70-102頁。
④周谷城:《官場似的教育界》,《社會與教育》第5期,1930年12月13日。
⑤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成立于1915年,簡稱“南高”,東南大學成立于1921年,簡稱“東大”。1921年-1924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與東南大學乃是一所學校,兩塊牌子,只是學生分屬兩種不同體制。1924年南高取消,該校統一為國立東南大學。
⑥?《學衡雜志簡章》,《學衡》第1期,1922年1月。
⑦《學衡雜志簡章》,《學衡》第3期,1922年3月。
⑧湯用彤:《評近人文化之研究》,《學衡》第12期,1922年12月。
⑨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第 224頁。
⑩柳詒徵:《論中國近世病源》,《學衡》第3期,1922年3月。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卷),北京:東方出版中心 ,1988 年 ,第 231、234-235 頁。
?胡先骕:《論批評家之責任》,《學衡》第3期,1922年3月。
?胡稷咸:《敬告我國學術界》,《學衡》第23期,1923年11月。
?郭斌龢:《新文學之痼疾》,《學衡》第55期,1926年7月。
?劉伯明:《杜威論中國思想》,《學衡》第5期,1922年5月。
?柳詒徵:《論大學生之責任》,《學衡》第6期,1922年6月。
?梅光迪:《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學衡》第2期,1922年2月。
?陳東原:《養士制度下的學風問題》,《學風》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
?陳訓慈:《組織中國史學會問題》,《史地學報》第1卷第2號。
?《發刊要旨》,《文哲學報(南京高師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第1冊,1922年3月。
?景昌極:《隨便談談》,《文哲學報》第2期,1922年7月。
??郭斌龢:《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二十周年紀念之意義》,《國風半月刊》第7卷第2號,1935年9月。
??馬騄程:《國立中央大學校史》,《國立中央大學概況》(二十九周年校慶紀念),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編印,1944年6月,第5-6頁,第6頁。
?張其昀:《吾師柳詒謀先生》,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 9 冊),第 4712 頁 。
?鄭大華:《九一八事跡后民族主義的新變化》,見《“20世紀中國社會思潮及大陸赴臺知識分子——紀念殷海光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交流論文集》(2009年12月5日,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第 85-102頁。
?轉引自張其昀:《中國與中道路》,《史地學報》第3卷第8期,1925年10月。
?《新孔學運動》,《大公報?文學副刊》第199期,《大公報》1931年11月2日。
?吳宓:《孔子之價值與孔教之精義》,《大公報》1927年9月22日。
?《孔誕小言》,《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47號,《大公報》1932年9月26日。
?張其昀:《教師節與新孔學運動》,《時代公論》第15號,1932年7月8日。
??柳詒徵:《發刊辭》,《國風半月刊》創刊號,1932年9月1日。
?《國風半月刊》第2卷第1號封面,1932年1月1日。
?梅光迪:《孔子之風度》,《國風半月刊》第3號,1932年9月28日。
?柳詒徵:《孔學管見》,《國風半月刊》第3號,1932年9月28日。
?柳詒徵:《明倫》,《國風半月刊》第3號,1932年9月28日。
?柳詒徵:《對于中國文化之管見》,《國風半月刊》第4卷第7號,1934年4月1日。
?繆鳳林:《談談禮教》,《國風半月刊》第3號,1932年9月28日。
?郭斌龢:《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國風半月刊》第3號,1932年9月28日。
?如有學者在總結民國時期北京大學與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思想、學術傳統的差異時,認為:“可以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做簡單的概括,也可以看做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對立。”(沈衛威:《“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第43頁。)這種概括多從思想文化上立論,雖切近主旨,但仍失之于過簡、過偏。既漠視了二三十年代政治激變情勢下,圍繞政治中心南移,黨派政治與制度安排對于這兩所大學的巨大影響,也忽略了這兩所大學本身內部思想學術文化的多樣性及階段性特征。
?參見拙作:《張其昀與南高學派》,《近代史學刊》(第7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 515頁。
?[77]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2008年。
?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見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129頁;彭明輝:《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形成(1911-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9期,2008年5月。
?胡適1943年10月12日日記,見《胡適全集》(第3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4頁。
?張其昀:《復刊詞》《思想與時代》第41期,1947年1月。
?郭斌龢:《讀儒行》,《思想與時代》第11期,1942年6月。
[51]郭斌龢:《〈孝與中國文化〉附言》,《思想與時代》第14期,1942年9月。
[52]李翊灼:《中國學術與中國學報》,《中國學報》第1期,1943年。
[53]李翊灼:《復興禮學之管見》《中國學報》第2期,1943年。
[54]張其昀:《敬悼胡適之先生》,見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學會編:《張其昀博士的生活與思想》,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部1882年,第324-325頁。
[55][69]曹聚仁:《學苑思故》,見《天一閣人物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280-281頁,第216頁。
[56]張其昀:《中大六十年紀念》,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十七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年“文教類二”,第8710頁。
[57][58]張其昀:《國立中央大學的學風》,見中國文化大學華風學會編:《張其昀博士的生活與思想》,第441頁,第440頁。
[59]張其昀:《中華五午年史?自序(一)》,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冊,第10837-10838頁。
[60]張其昀:《敬悼胡適之先生》,見《張其昀博士的生活與思想》,第327頁。
[61]張其昀:《華岡學園的萌芽》(1972年5月3日),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冊),“文教類二”,第9038頁。
[62]張其昀:《答記者問》,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冊),“文教類二”,第8883頁。
[63]張其昀:《華岡興學的理想》,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冊,“文教類二”,第9049頁。
[64]張其昀:《孔學大義》,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冊),“序跋函札類二”,第11297頁。
[65]張其昀:《〈孔子學說與現代文化〉前言》,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 20冊),“序跋函札類”第 10771-10772頁。
[66]張其昀:《大學教育與文化復興》,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冊),“文教類二”,第8994頁。
[67]張其昀:《大學精神》,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冊),“文教類二”,第9003頁。
[68]張其昀:《新人文主義》,見《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0冊),第 5062頁
[70]史華慈:《論保守主義》,見傅樂詩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年,第19頁。
[71]美國《人文》雜志社編、多人譯:《人文主義:全盤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3頁。
[72]如王汎森曾指出,新舊轉換的時候,“新”與“舊”的微妙分別滲透到每一種領域中。見氏著:《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見《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5頁。
[73]桑兵:《金毓黻與南北學風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74]鄭大華:《現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潮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4期。
[75]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1922年1月。
[76]陳來:《二十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東方》1993年創刊號。
[78]胡適1943年10月12日日記,見氏著:《胡適全集》(第 33 卷),第 524 頁 。
2011-05-07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首都遷移與學術文化的分合”(07CZS018);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自由關系研究”(07JJD770100)
責任編輯 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