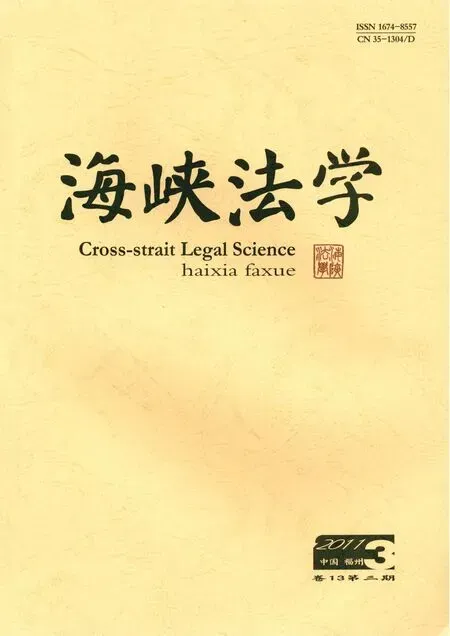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開發傳統文化產業的結合路徑
丁麗瑛
(廈門大學法學院,福建廈門 361005)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開發傳統文化產業的結合路徑
丁麗瑛
(廈門大學法學院,福建廈門 361005)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存在于現代的活態傳統文化表征,它的存在和傳承形態與現代傳統文化產業或產品密切相關。面對商業開發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現實問題,應當“警惕危機更看重機遇”,必須克服過于依賴政府而忽視市場的觀念,找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開發傳統文化產業的結合路徑,具體包括:產業扶持與市場準入的結合;文化傳承與產品創新的結合;公權管理與私權保護的結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文化產業;結合路徑
一、不容忽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存在和傳承形態
按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2條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或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2005年3月我國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第2條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作為國內第一個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題的地方性立法,《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回避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般性定義,僅在第2條以列舉的方式規定條例所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范圍。雖然學界基于上述條款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界定有不同的理解,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概念的基本特征基本形成共識,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口頭性”、“集體性”、“傳承性”、“環境依附性”和“變異性”。[1]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包括:(1)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2)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3)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4)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5)傳統體育和游藝;(6)其它非物質文化遺產。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實物和場所,凡屬文物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
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應當明確其概念以界定其所指對象,還應當從現代社會關系出發,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存在于現代的傳統文化表征。法律對因它而產生的社會關系的調整以及對它所采取的具體保護措施必須根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生活的存在形態,特別是對它的價值性的認識不能脫離現實生活需要及傳統文化產業開發的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博物館珍藏的文物,它與物質性文化遺產的不同在于它是活態文化,既有歷史積淀下的特定“文化基因”,也反映現代生活的動態發展和變革。因此,筆者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生活中尤其是在傳統文化產業開發中所顯現的存在和傳承形態是值得歸納和關注的,而這些形態特性恰恰是影響處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開發傳統文化產業的關系的重要因素。
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口頭傳承、動態變異,并融合于現代傳統文化產品中。任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孤立于現代文化構成之外來看待而形成的觀點都是不適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為一種“遺產”,但是從它的存在形態上分析,卻是融合于現代的傳統文化之中的,是構成現代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形式上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不具物質性表現載體而主要借助口頭傳承,是一種抽象的文化現象,因而具有彈性的變異空間。基于這樣的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目標在于保障文化多樣性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脈”即文化特質提供保護,維護其不發生質的改變,但不應禁止在此前提下產品的多樣性發展和傳統文化產業的開拓。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貫徹保存與可持續性發展相結合的原則,才能體現法律保護的價值。
其次,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成為支撐地方特色經濟的傳統文化產業的重要來源,文化傳承與產業開發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具有十分突出的經濟價值:它有助于地方特色經濟的形成,可以孵化和培育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新產業;有助于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目的的實現;具有可循環使用、無污染的經濟特征,有助于實現節約型、環保型的經濟發展模式。[2]著眼于當前及未來經濟發展趨勢,文化產業被確定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成為一個地區乃至國家重要的支柱產業。而文化產業的競爭和推動核心之一在于文化產品的附加值。我國的許多地區擁有個性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間文化藝術優勢,傳統文化資源豐富,因此應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項重要的文化產品的高附加值來看待,并通過適當的制度設計使它的商業利用價值轉化為財產或市場競爭優勢。
最后,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歷史形成上看雖具集體性,但在現代傳承中卻有相對確定的代表性傳承主體,而且該傳承主體又往往作為市場主體參與了文化產業活動或經營。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成和傳承不僅具有鮮明的地方性,而且是滲透著共同祖先的靈魂和凝聚著群體智慧的集體記憶,從這一意義上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體性是不可否認的。另一方面,從當前的現實出發,保有和守護著特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卻往往是一個特定的主體,該主體可能是一個團體、組織,也可能是一個家族,甚至可能就是一個自然人,現有的規范將他們歸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或“代表性傳承單位”。對于這些傳承人或傳承單位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構成他們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而不僅是興趣愛好或副業,也非公益事業。這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往往是在傳統文化產品的開發、提供和消費活動中進行的。因而,僅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視為一種社會公益是不夠的,必須重視傳承人或傳承單位的市場主體地位和經濟發展需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設定的政策或措施不僅應當包括公權管理上的扶持、搶救和弘揚等,而且也應當包括私權保護措施的強化。
二、商業開發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問題
面對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沖擊,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面臨現實的流失與淡漠。在我國,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產業在我國許多地方的發展緩慢,尚未發揮助飛地方經濟的動力,卻成為流失海外的娛樂產業或產品的高附加值。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傳承是與文化市場的需求緊密相關的,因此,我們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現實問題以及應當采取的對策或措施,都離不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綜合目前的資訊及研究,筆者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現實問題主要體現如下:
第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觀念上,未能處理好保存與發展的關系,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開發傳統文化產業脫節、失衡。這主要反映為兩種極端:一是在商業開發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品化現象越來越嚴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貌逐步被扭曲和改變,致使其內涵和價值最終被扭曲,因此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異化”;[3]二是未能充分重視市場的調節作用和正確處理好保留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特性與創新傳統文化產品形式及開發傳統文化市場的關系,忽視傳統文化市場的需求和價值,因此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僵化”或與現代生活需要的“格格不入”。
第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式上,過于強調公權管理而忽視私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的私權利益未獲得適當的彰顯。這主要反映為兩個問題:一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中衍生的傳統文化產品的知識產權利益重視不夠;二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的私權主體定位不清,也制約了傳承人傳承及創業的積極性。
第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上,重視宣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忽略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怠于其創新和發展。一方面,政府的政策高調,但資金上的鼓勵和扶持力度有限,難以滿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與發展所需要的經濟支撐,許多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在觀念上過于依賴政府,往往面臨經費籌措困難之制約發展瓶頸;另一方面,現實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模式散亂,管理與利用政策彈性或張力過大,適當的利益分享機制未能獲得很好的引入或引導。
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開發傳統文化產業的結合路徑
為了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決策或制度設計中,應當“警惕危機更看重機遇”,必須克服過于依賴政府而忽視市場的觀念,找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開發傳統文化產業的結合路徑,并將它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之規定中。具體而言,筆者認為以下的結合方案是值得考慮的:
(一)產業扶持與市場準入的結合
既然承認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活態文化,就應當給它適當的發展空間,并且該發展空間又是與市場需求緊密相關的。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上,應當貫徹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原則。政府扶持體現的是政策導向、產業引導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具體的措施包括財政經費支持、稅收優惠、融資幫助等等。同時,值得重視的另一舉措是傳統文化市場準入上的管理。2007年6月文化部正式批準設立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這是中國首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可以預測,在未來,文化生態保護區可能成為各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整體性保護的一種重要模式。
為了防止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商業開發過程中被“異化”,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手段就是通過市場準入管理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傳播。在市場準入管理中應當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作為考察合格市場主體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在文化生態區建設中,必須將保護和扶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放在優先的位置,予以重點關注;二是尊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和傳承的歷史脈胳和客觀規律,承認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生活中繼續存在的重要性和固有價值,維護其原生態下的傳承、利用和發展。應當盡可能地保障任何合法、正當的商業開發不會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異化”或“變相流失”;三是保障傳統社區的生存和發展權利,建立發源地參與和適當的利益分享機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可以采用多種模式進行,[2]必須重視和加以思考的關鍵性問題是通過這種商業開發,代表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定利益群體或主體的傳承人或傳承單位基于這種商業利用獲得哪些利益,該利益的實現是否足以維護其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否足以保證其獲得與其他人群同樣的生活質量和發展空間的可能性。在這樣的要求下,首先需要優先考慮的是在市場準入上突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在保存和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傳統文化產業或產品上的優勢利益;其次在前一種情形明顯存在事實上的障礙或困難,需要考慮借助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以外的其它主體之力量加以傳承并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有效和正當的利用時,則需要給予必要的制度約束,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得以參與決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利用,并以適當的方式分享因此所獲得的經濟利益。
(二)文化傳承與產品創新的結合
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保護傳統知識并非僅僅為了使某些可能已經過時的知識不致消滅,更不是為阻止現代社會的人們利用那些有價值的傳統知識;恰恰相反,保護的目的正是為了更好、更積極地利用。一方面,在全人類共同走向現代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與傳統的多樣性;另一方面,積極挖掘傳統知識的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特有的作用和價值,使其服務于現代社會與現代文明。”[4]同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和價值也不在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文物考古”,而在于發展性保存和可持續性利用。所謂的發展性保存,就是應當維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態發展和革新,使之在保持自身傳統文化特質的同時服務于現代社會發展。所謂的可持續性利用,就是應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視為一種資源,一種需要人為的挖掘和利用才能發揮經濟價值的財產,而不是鎖在保險箱里也能增值的珠寶或文物。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應當處理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保護與利用的關系。
首先,應當正確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保護與利用的關系。誠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理念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正價值不是創新,而是保留”,[3]但是無視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生活中的存在和傳承形態,脫離現實的文化市場需求,這種理念的堅持無異是“紙上談兵”。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中,保留與創新完全是可以處于協調而不矛盾的和諧態勢的。一方面,應當保留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文化特質;另一方面,應當以該傳統文化特質為基礎,創新文化產品的內容和形式。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可持續性的利用本身也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方式。
其次,以傳統文化產業開發帶動和激勵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除了信仰、民俗外,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以民族或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或工藝來體現的,而這種表達或工藝又是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的生存和發展緊密相關的。換言之,文化傳承本是傳承人或傳承單位謀生之手段,而文化市場的認同和需求則是他們重要的經濟出路。單靠政府的扶持或救濟是難以維持傳承人或傳承單位的生存和經濟發展的,而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死汰留存”也不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精神和政策;因而應當調動傳承人或傳承單位開發傳統文化產業的積極性,在保留文化命脈和不改變文化基因的同時,變革傳承方式和創新傳承產品,以開發傳統文化產業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來帶動和激勵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最后,在文化傳承、文化認同中培育傳統文化產品的消費市場,使文化欣賞與文化消費相結合。要使文化傳承與文化產業開發相結合而成為地方經濟的支撐或亮點,并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就必須重視消費市場的培育。雖然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自我繁衍”的功能,但是在當前的經濟浪潮下,失去文化認同和市場需求,就很難擺脫“斷代失傳”或“加速消亡”的瀕危命運。因而,無論是政府就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所采取的具體措施,或是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的傳承活動,不僅應當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宣傳、弘揚,使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得以延續,而且應當重視市場運作規律,變革和開拓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途徑或方式。
(三)公權管理與私權保護的結合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前期工作中,我們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發揮政府的管理職能和支持作用,采取普查、認定代表作、建立名錄、確定和命名代表性傳承人或傳承單位,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利用予以一定的經濟救助或扶持。毫無疑問,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來說,這種具有公權介入屬性的行政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私權保護模式的運用也是十分重要和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中。
將知識產權制度的運用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是私權保護的一種重要選擇。知識產權制度是對非物質性的知識信息提供財產權保護的法律工具,因而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雖然由于存在許多現實的制度障礙及國際環境的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最終并沒有如部分學者所期望的直接賦予非物質文化遺產私權保護,而是明確排除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私權保護模式,但同時也在第44條規定“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知識產權的,適用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據此可以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衍生品可以納入現行知識產權的對象范疇。
第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活動中延伸和創作出的文學藝術新作品可以依法獲得著作權保護,即使它們已經被視為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的代表作品,同樣具有私人物品屬性而得以主張私權利益。
第二,利用地理標志保護和商標注冊制度,彰顯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源地的地源價值。在這種模式的運用上,“銅梁火龍”商標注冊就是一個典范。[5]
第三,利用專利權制度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提供消極性和積極性保護。消極性或防御性保護主要體現于制止不適當專利權的授予,即對于那些利用公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傳統工藝)作出的發明創造獲得專利獨占權的行為進行規制。這種保護模式不僅需要依托于專利權制度的完善與變革,而且制度的實際運行也需要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或傳承單位的積極主張。積極性保護主要體現于就未公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利用提出專利申請和獲得專利權保護。當然,采取這種保護模式必須考慮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利用成果是否符合授予專利權的條件。
第四,重視傳統文化產業開發中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作用。在以下兩個領域中,反不正當競爭法可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保護:一是對符合商業秘密條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反不正當競爭保護;二是對傳統文化產業開發中采取不正當手段從事市場交易,損害競爭對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制止。
第五,創設與現行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并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權保護模式最具突破性與開拓性,但需慎行且具配套措施。我國臺灣地區在2005年2月5日公布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3條中規定“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并促進其發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此后,在2007年12月7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與之并行的還有“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目前尚未頒布)。這些法案的立法思路便是按照特別權的模式對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成果(相當于大陸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和生物多樣性知識(相當于大陸的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提供私權保護,這樣的立法思路雖存在一定的施行障礙,但仍具其一定的創新與合理,值得大陸的借鑒。[6]
[1] 齊愛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與構成要件[J].電子知識產權,2007(4):17-21.
[2] 齊愛民,趙敏.非物質文化遺產商業開發中的利益分享機制之確立[J].電子知識產權,2007(8): 21-24.
[3] 李曉秋,齊愛民.商業開發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異化”與反“異化”[J].電子知識權,2007(7): 38-40.
[4] 唐廣良,董炳和.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547.
[5] 齊愛民,趙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標權保護模式[J].知識產權,2006(6):63-66.
[6] 丁麗瑛.臺灣地區原住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保護立法評價[J].臺灣研究,2010(2):37-41.
G122
A
1674-8557(2011)03-0012-06
*本文系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地方文化生態區建設中的知識產權問題研究——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和保護為中心》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為:09BFX003;系2008年福建社科基金項目《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中的知識產權保護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為:2008B117。
2011-08-19
丁麗瑛(1965-),女,江蘇宿遷人,法學博士,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 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