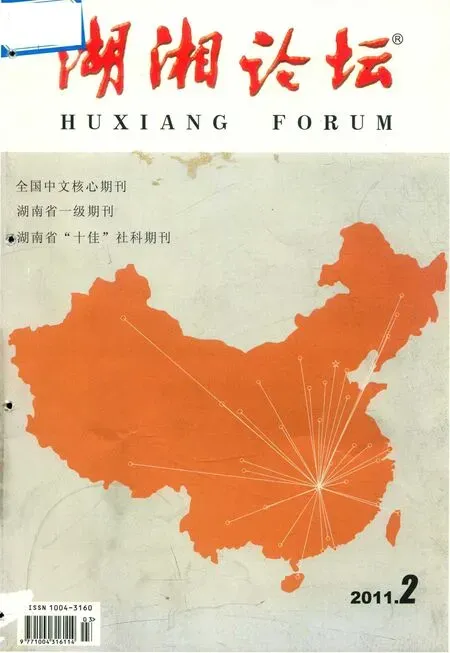馮友蘭哲學與中醫之關系
徐儀明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 長沙 410081)
·文史哲·
馮友蘭哲學與中醫之關系
徐儀明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 長沙 410081)
作為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醫曾為馮友蘭所關注,他沒有停留在一般性的評判層面上,而是將其作為形上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確定了中醫理論的哲學性質,為中醫哲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馮友蘭哲學;中醫;形上學
馮友蘭先生曾甚為關注中醫中藥學,并為此寫有多篇專論。在論述形上學問題時也曾專門論及中醫學理論。作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著名哲學家和哲學史家,馮友蘭以其擅長的理論思維方式剖析中醫學這一中國文化的重要層面,將中醫理論研究上升到哲學形上學的高度來加以認識,開了中醫哲學研究的先河。而且,如果能通過對馮友蘭所總結出來的中國哲學的優長之處來反觀中醫理論的話,應該能夠更為深入地理解和認識中醫,并對中醫哲學的發展走向會有較為明確的把握與判斷。
一
與馮友蘭同時代的不少著名學者對中醫都抱著懷疑甚至貶斥的態度,這似乎在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成為很流行的觀點。比如像傅斯年就說:“我是寧死也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1]P434持這種極端觀點的還有丁文江等人。陳寅恪自謂其家學即為中醫,自己卻轉而“不信中醫,以為中醫有見效之方,無可通之理”[2]P188。甚至一貫崇尚儒學,被視為“玄學派”重鎮的梁漱溟也說:“中國說是有醫學,其實還是手藝。……十個醫生有十樣不同的藥方,并且可以十分懸殊。因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藥,都是沒有客觀標準的。”[3]P354這顯然是近代西方科學 (包括醫學)傳入中國以后,對本土固有傳統文化所帶來的強大沖擊,使得中醫在西醫面前顯得黯然失色,不少人心靈天平的重心也滑向了西醫。
馮友蘭對中醫的看法似乎和陳寅恪基本一致,同樣認為盡管中藥是有效驗的,中醫理論則是荒誕不經的。他說:“從現代生理學的觀點看,中醫的理論,有一部分是荒誕不經底。如以五行配五藏,以五行的生克,講藥的效用等。這些理論,在現代是很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底。中醫理論的另一部分,雖不能說是荒誕不經,但亦是很模糊底。例如寒熱風火等,其確切底意義,是很難令人捉摸底。有人說:所謂涼藥者,即能治所謂‘是熱’底病之藥也;所謂熱藥者,即能治所謂‘是寒’底病之藥也。所謂‘是熱’底病者,即涼藥所能治愈之病也。這是開玩笑底話,即所謂熱涼等觀念,確是很不清楚底。”[4]P384顯然,站在所謂“現代生理學”的立場上來看,中醫的理論要么是“荒誕不經”,要么是“很難令人捉摸”,
馮友蘭所持的否定態度是很明顯的。但同時他又指出中國的藥還是有效的,說:“中藥,至少有一部分中國藥,是有效驗底,是能治病底,這是現在用新方法研究中藥,提煉中藥底人,所都承認底。”[4]P384然而,為什么說中醫的理論不通,而中藥卻能治病,這又是什么緣故呢?馮友蘭認為,我們對于中藥的知識,并不是從中醫理論得來的。就是說并不是先有了中醫的理論,然后照著那個理論去找藥。這是因為知識起源于經驗,中國自古以來便有神農氏嘗百草之說。“所以第一步底知識,都是經驗底知識。人積了許多經驗,而知有某現象之后,常繼有某現象。這是一個知識。這種知識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人知某現象之后,常繼有某現象,而不知其所以如是。不知其所以如是,即不敢說它必如是。因為經驗只能追溯既往。而不敢保證將來,”[4]P384例如人吃了大黃即下瀉,這是憑經驗便可以知道的。但這種經驗的知識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因此就要將其上升為理論。馮友蘭指出,中醫的理論,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一套,予以解釋。他以為有此解釋,我們即可以說,人吃了大黃必要下瀉。又如在傳染病流行之時,中醫也知道病人可以傳染不病的人。不過他說這是由于“四時不正之氣”。這也是一種解釋。不過這種解釋屬于一種空想,實在不能算是解釋。馮友蘭說:“經驗底知識是不完全底知識。人對于已知其然者,必求有以解釋。對于已知其然者,如有了解釋,則人即覺又已知其所以然。以前他只知其是如是者,現在他又覺可說其必如是。不過這些解釋,可以只是空想底。如只是空想底,則其解釋實不能算是解釋。”[4]P385就是說,氣化學說、陰陽五行觀念等中醫學的主要理論,用來解釋中藥的藥效和疾病的成因,在馮友蘭看來其基本上屬于一種空想,這是因為其不是科學的解釋,“科學底解釋與空想底解釋不同者,即科學底解釋是以實驗為根據,而且可以實驗證實底。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是不能用證實底。‘四時不正之氣’,亦是不能用實驗證實底。但如說大黃能使人下瀉,是因其中有某種化學原質;說傳染病之所以傳染,是因病菌的傳播:這都是可用實驗證實底。所以科學的解釋,是真底解釋。”[4]P385應該說,馮友蘭作為受到近代科學精神洗禮的學者,具有這樣的認識不足為怪,科學實驗、化學分析等方法的運用,確實使人們對疾病的認識清晰、精確了很多 ,甚至對中藥的有效性,他也是從西醫理論的立場來認識的。因此中醫固有的思維路徑和認識方法,在馮友蘭眼里顯得那樣蒼白無力,只能以“空想”二字來加以概括了。
可以說,這種“廢醫存藥”的思想在馮友蘭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他認為:“我們現在應當研究中藥,而不必研究舊醫。所謂不必研究舊醫,是不必研究舊醫的理論。至于舊醫的經驗底知識,仍是要研究底,不然我們何以能知某中藥能治某病而加以研究呢?”[4]P385這一認識顯然存在著內在的矛盾,他一方面說不必研究舊醫的理論,同時又說要研究舊醫的經驗知識,盡管在他看來,中醫 (即他所謂的“舊醫”)的理論和中藥的經驗知識可以截然分開,但事實上幾千年來兩者已經渾然一體,根本不能分出彼此來,在一部中藥學史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氣化學說和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中醫學的經典《黃帝內經》對四氣五味、升降浮沉、五臟苦欲等中藥學的基本理論均有綱領性的闡述。顯然,中藥的實效雖然并非根源于其理論,但卻已蘊涵于理論之中,中醫和中藥是不可分開也不能分開的,只是在馮友蘭看來,中醫是不能用科學來加以解釋的,所以其理論就應該廢棄。這顯然是一種“唯科學主義”的觀點,在今天這一觀點雖然仍有一定的影響,但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人們從不同的方面闡發了中醫藥學的歷史地位和輝煌成就以及它的臨床價值。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馮友蘭,并沒有持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而是從哲學演進的路線上對包括中醫學在內的中國舊文化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就因為中國有一條內向的路線,即是說墨家、荀子等的科學思想萌芽沒有得到長足發展,而且進入宋明時期以后,中國思想的人為路線,幾乎再也沒有出現了,“中國哲學史的這個時期,與歐洲史上現代科學發展的這個時期,幾乎完全類似,類似之處在于,其成果越來越是技術的,具有經驗的基礎和應用的方面。惟一的、但是重要的不同之處是,歐洲技術發展是認識和控制物質,而中國技術發展是認識和控制心靈”[4]P48這也就是說,西方是從科學層面上認識和控制物質,中國則是從形上學層面上來認識和控制心靈的,技術發展的路徑是截然不同的。盡管這一說法不無偏頗,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學術見解還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這對于今天如何深入理解中國哲學與中醫藥學之間的關系仍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作為哲學家和哲學史家的馮友蘭,他對中國哲學的特質和精神的獨特認識,能夠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中醫學的理論特點,進一步了解中西醫之間的差異,消解籠罩在中醫學上面的種種迷霧,更清晰更準確地弄清中醫學理論的根本性質。中醫、中國哲學和中醫哲學之間的內在關聯,將會通過深入研究馮友蘭哲學而能夠得出新的和更為深刻的理解。這也是馮友蘭能夠超邁他的同時代學者的優長之處。
二
在馮友蘭看來,盡管中醫藥學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其仍然屬于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理論雖然以科學來考量的話就會顯出其種種缺點,但又遠遠優于宗教巫術,它應該是哲學 (形上學)所研究的領域。馮先生這些見解都發表在距今七十年前,真正屬于哲人的遠見卓識,不能不使我們對此給予高度關注。
在馮友蘭《貞元六書》之一的《新知言》中有這樣的一段論述,其云:“就醫學說,說傳染病的病源是一種微生物,這是可以實驗底方法從經驗中證實底,這是科學的理論。說傳染病的病源是‘四時不正之氣’,這是‘想當然耳’,是不能以實驗底方法,從經驗中證實底。這是‘先科學底’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雖是‘想當然耳’,但亦是對于傳染病的病源底一種比較合理底解釋。比如說,傳染病是上帝降罰,或鬼神作祟,這種理論,已經是進步得多。說傳染病的病源是上帝降罰或鬼神作祟,是宗教的說法。說傳染病的病源是‘四時不正之氣’,是‘先科學底’科學的說法。說傳染病的病源是一種微生物,是科學的說法。從宗教的說法,到科學的說法,是一種進步,是人的知識在醫學方面底進步。”[4]P147在這里,馮友蘭指出了盡管中醫學是‘先科學底’科學理論,但仍是一種較為進步、較為合理的說法,因為它是介于科學與宗教之間的一種哲學的說法。將中醫學理論視為哲學,這一認識無疑是正確的。
馮先生進一步論述道:“‘先科學底’科學,有些人稱為形上學。孔德說:人類進步,有三階段:一、神學階段;二、形上學階段;三、科學階段。他所謂形上學,正是我們所謂‘先科學底’科學。如所謂形上學是如此底性質,則形上學只可于‘無佛處稱尊’,于沒有科學的時候,此所謂形上學,在人的知識中占現在科學在現在人的知識中所占底地位。換句話說,此所謂形上學,就是那個時候的人的科學。于既有現在底科學以后,此所謂形上學,即應功成身退,將其地位讓與現在底科學。如既有現在底科學,此所謂形上學,仍不退位,則即與現在底科學沖突。此等沖突,嚴格地說,是現在底科學與以往底科學的沖突。是進步底,好底科學,與落伍底,壞底科學的沖突。”[4]P147就是說,形上學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曾經起到現在科學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在馮友蘭眼中形上學就是這一時期的科學。中醫藥學特別是中醫學理論顯然就是這一時期的形上學或科學,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如馮先生所說:“中國的醫學藥學,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凡是中國文化所到底地方,也就是中國醫藥所到底地方。在一百年以前,東亞到處都是中國文化,也到處都是中國醫藥。”[4]P383中醫藥學的影響已經遠播中外,中醫學理論也隨著中國哲學一起傳播到東亞諸國甚至更遠。這說明馮先生是承認中醫藥學曾經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同時也是指出中國哲學曾經有過像今天的科學一樣的崇高地位。不過,馮友蘭認為作為形上學的中醫學理論,應該讓位于近代以來的西方科學,因為前者是“落伍底,壞底科學”,而后者是“進步底,好底科學”。然而,近代科學的進步和發展,并沒有能夠讓形上學徹底“退位”,兩者之間依然存在著激烈的沖突,在馮先生看來缺少現代化環節的中醫藥學尚停留在古代的水平,“一般人常以中醫西醫中藥西藥對比。中醫西醫的對比是錯底。因為普通所謂中醫西醫之分,其主要處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異。中醫西醫,應該稱為舊醫新醫。”[4]P383顯然,馮友蘭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這和五四以來“科學派”的認識有著不少一致性。
然而,馮友蘭客觀地看到近代以來的科學并不能完全取代形上學,這是因為科學有著其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另外一種方法亦即形上學的方法,所以哲學的維度是永遠不可或缺的。他說:“形上學的問題,雖與科學的問題,是一類底,但并不是所尚不能解決底問題,而是科學所永不能解決底問題。形上學于科學之后,專撿拾科學所永不能解決底問題,以另一種方法解決之。所以,它只是‘后科學底’科學,不是‘先科學底’科學。”[4]P48盡管馮先生舉出的科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多是西方哲學史中所謂上帝存在、靈魂不滅和自由意志等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其實人體中所存在的問題也不是西方科學所能全部解決的。在筆者看來,經絡學說、陰陽五行學說和氣化觀念等中醫學的根本理論問題,也不是西方科學所能解決的。而這些問題恰恰符合馮友蘭所謂“真正形上學底命題,可以說是‘一片空靈’”[4]P54的說法。在其看來,歷史的命題是實而死的;科學的命題是靈而不空的;邏輯學、算學中的命題是空而不靈的。只有“形上學底命題,是空而且靈底。形上學底命題,對于實際,無所肯定,至少是甚少肯定,所以是空底。其命題對于一切事實,無不適用,所以是靈底。真正底形上學,必須是一片空靈。哲學史中底哲學家底形上學,其合乎真正底形上學的標準的多少,視其空靈的程度。其不空靈者,即是壞底形上學。壞底形上學即所謂壞底科學。此種形上學,用禪宗的話說,是‘拖泥帶水’底。沾滯于‘拖泥帶水’底形上學底人,禪宗謂為‘披枷帶鎖’”[4]P155若以中醫學理論來較之于馮先生這個“真正形上學命題”的標準,可謂若合符節。試以中醫“氣”論做一剖析。清喻昌《醫門法律》在祖述《內經》以來的氣論時說:“氣有外氣,天地之六氣也;有內氣,人身之元氣也。氣失其和則為邪氣,氣得其和則為正氣,亦為真氣。……人之所賴,惟此氣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帝曰:氣內為寶,此誠最重之辭,醫家最切之旨也。”[5]P43顯然,中醫的“氣”范疇源于中國哲學的“氣”觀念是無庸質疑的,然而由于其更切近于人,其“空”與“靈”則尤為生動。“氣”非固體非液體,似霧似露又似風,可謂“空”;但其又能夠流動、發散、游走、灌注、充溢、聚散 ……,可謂“靈”。當然,這“空”與“靈”還表現在其性質和作用上。“氣”既可為天地之外氣又可為人身之內氣;既可為正氣又可為邪氣。其形態的改變又可以決定人的生與死。所以說,“氣”命題決非是一個科學的命題,近年來以所謂科學手段來研究“氣”命題為什么全告失敗,就足可證明其“空”而非“實”。至此,我們能夠理解馮先生為什么在討論形上學的問題時,特別要提出中醫學理論來加以分析的深刻含義。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馮先生在《新理學》中把“真元之氣”理解為亞里士多德所謂“絕對的料”,這就消解了“氣”的能動性和多樣性,也就消解了它的空靈性,從而出現了與中國傳統氣論的分離,因此造成了矛盾和誤解。這一點已為不少學者所論及。但是,在大多數場合下,馮先生對“氣”的論述還是“接著”宋明理學講的,那就是“氣”有陰陽動靜、聚散開合等特性。特別是到了晚年,馮先生對中醫學說及其氣論贊許有加,比如他說:“中醫治病,講究‘扶正祛邪’。‘正’就是病人的陽,‘邪’就是病人的陰。如果他的陽勝他的陰,他就盛。如果他的陰勝過他的陽,他就衰。如果他的陰全勝他的陽,他的情況就嚴重了,就相當于 (六十四卦 )《圓圖 》中《坤 》卦 ,它就死亡了。”[6]P77以中醫的核心理論陰陽觀念既解釋了人的生命現象,又創造性地闡發了易理,可謂神來之筆。
因此,按照馮友蘭這里的論述,我們可以認識到中醫學理論既然是真正的形上學,那么就不可以老在那里拿西方科學的標準來衡量它苛求它評判它否定它,更不能將其視為科學的對立面。馮友蘭說:“因為科學與形上學,本來沒有沖突,亦永遠不會有沖突。最哲學底形上學,并不是‘先科學底’科學,亦不是‘后科學底’科學,亦不是‘太上科學’。它不必根據科學,但亦不違反科學,更不反對科學。所以它與科學,絕不會發生沖突。”[4]P146這段話非常適合論述中醫學與科學的關系,我們要補充的是,中醫學的理論盡管有著諸如“明晰不足,暗示有余”之類的模糊性,但不會像某些具體的科學命題那樣會過時和被淘汰,它以“不中不遠”的方式至今依然指導著中醫的臨床實踐,并在經驗性的知識配合下,常常會取得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這一“真正形上學”的理論魅力,卻往往并不被人們所理解,通過研究馮友蘭學說我們方能夠揭示這一學術奧秘。
三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馮友蘭將中醫理論稱為“空想”,流露出貶斥或否定的意思;但他又在論述形上學的特點時,又拿出中醫理論作為例證,使我們認識到其具有真正形上學的“空靈”性質,則顯示出褒揚或欣賞的態度。兩者顯然是矛盾的。這恐怕是因為馮先生討論問題時,由于角度不同而得出的結論就會出現差異。當然,馮友蘭并不以科學名家,當他站在近代以來的西方科學的立場上論述中醫時,難免會因為隔膜而得出一些偏頗的認識。但是,作為現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的馮友蘭,他將對中醫理論的研究納入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之中,從而得出許多真知灼見。這是由于在他看來,中醫理論就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馮友蘭先生曾親口對筆者說:宋明時期的中醫學屬于宋明理學的組成部分。),中國哲學的一些重要特點也就是中醫理論的特點。因此,以馮先生對中國哲學研究所得出的深刻見解來認識中醫理論,可以使一直困惑我們的疑難問題得以豁然開朗,迎刃而解。下面,我們擇其要者,做一些較深入的探討。
馮友蘭認為,在中國哲學中有一種“形上學的負的方法”,其主要以道家和禪宗為代表。所謂負的方法,是指對于理智所不能描述的界限彼岸的東西,只用語言說它不是什么,而不說它是什么。馮友蘭說:“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討論形上學的對象,這成為哲學研究的主題。負的方法的實質是對要探討的形上學的對象不直接討論,只說它不是什么,在這樣做的時候,負的方法得以顯示‘某物’的無從正面描述和分析的某些本性。”[7]P310比如,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語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義,而在于他的暗示,引發人去領悟道。而在理學,這種方法被稱為是直觀的“體認”,“就是說由體驗得來的認識,這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種經驗,是一種直觀,不是一種理智的知識。”[8]P496這些中國哲學中習見的暗示、直覺、領悟、直觀、體認等的負的認識方法,均被靈活地運用于構建中醫學的理論體系中去了。比如,中醫診斷學中的切脈,其原本就是望、聞、問、切四診中之最難者,因此往往被蒙上種種神秘霧幔,諸如什么“索線診脈”,則更為神奇。這主要是因為診脈的過程無法運用邏輯分析,只能靠一種直覺的體認。晉代王叔和 (210—285?)《脈經序》云:“脈理精微,其體難辨。絃緊浮芤,輾轉相類。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沉為浮,則方治求乖;以緩為遲,則危殆立至。況有數候具見,異病同脈者乎?”[9]脈象給人的感覺撲朔迷離、錯綜復雜,不僅指下難明,而且口中也難明,因此只有賴心的了悟。所以,《內經》強調診脈時需要“慧然獨悟”、“俱視獨見”、“昭然獨明”(《素問·八正神明論》),認為“持脈有道,虛靜為寶”(《素問·脈要精微論》),即強調切脈時要“必清必靜,上觀下觀”(《素問·方盛衰論》)。這種清虛守靜,返觀內照,慧然獨悟的方法恰似馮先生所揭示的道家的負的認識方法。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老子·第十六章 》),“滌除玄覽”(《老子 ·第十章》);莊子說:“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莊子·養生主》)等,都是指的這種微妙深遠的直覺體認方法。而醫家可以在“絃緊浮芤,輾轉相類”的紛擾中排除許多無用之“知”,由此方能達到所謂的“無知之知”。馮友蘭說:“‘無知’是人的原初狀態,而‘無知之知’則是人經過‘有知’而后達到的‘無知’階段。人的原初狀態的無知是自然的恩賜,而人達到‘無知之知’則是心靈 (亦即靈性)的成就。”[7]P106和道家哲學一樣,中醫哲學所獲得的“無知之知”也是心靈 (靈性)的成就,古人所謂“醫者意也”即此謂也。馮先生對負的方法的論述,是對中國哲學也包括中醫哲學(中醫理論)認識方法的肯定,也是對中國文化的推崇。當然,馮友蘭最終還是主張正、負兩種方法的有機結合的。那就是既強調邏輯分析又強調直覺體認,他說:“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應當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于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后頂點。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7]P311如果把中醫理論作為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這種正負結合的方法論的確為中醫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正確的思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馮友蘭強調情感在哲學中的地位與作用,因此有論者稱馮友蘭哲學為“情感哲學”。早在 1935年,馮友蘭在以人生術為題的講演中這樣說:“人生術很多,今天只講一個,就是應付情感的方法。情感包括喜怒哀樂,雖然幸福的整個問題不完全在情感上,可是喜怒都與人生有大關系。如《三國》上三氣周瑜,一下子給氣死了;《說岳》中的牛皋捉住了金兀術,把金兀術氣死,牛皋樂死了。這都是情感的作用。我們怎么對付它,就是現在要講的。”[8]P123情感的問題直接關乎人的生死,不能不使人感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此種認識顯然和中醫學理論是十分一致的。中醫認為人之所以病其內因就在于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突然、強烈或長期持久的情感刺激,影響人體正常的生理功能,致使臟腑氣血竄行紊亂,導致疾病的產生甚或生命的危殆。《素問·疏五過論》說:“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從中醫學的情志理論中的確可以找出周瑜、金兀術氣死,牛皋樂死的原因。在中醫學看來,任何情志只要發生偏執,就會產生疾病,《素問·舉痛論》說:“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就是說,怒能使人肝氣上沖,重者可引起昏厥;喜能使人心氣緩散,傷精敗神;悲能使人肺氣耗傷,意志消沉;恐能使人氣陷于下,二便失禁;驚能使人心無所依,神無所附;思能使人氣機阻滯,運化失常。總而言之,過度的精神刺激,皆能導致內臟功能嚴重損傷。針對這種狀況,《內經》提出了以“情”治“情”的方法,《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說:“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以情志之間的相互制約,來調整各個臟腑的功能。這種方法自有其可取之處,但情志的發作難于掌控,往往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后果,臨床上也會經常遇到這樣的難題。馮友蘭顯然是熟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七情說的 (其中自然包括中醫的七情說),他指出:“王陽明說:‘七情不可有所著’,著即累,即七情不可有所累。講《大學》‘心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他所注重在‘所’字,一有所憂患忿懥,即是有了對象的累于物了,即有所苦了。”[8]P725即是說不要被七情所掛累,而墮入傷苦之淵。這種擺脫情感束縛的方法,源于先秦儒道兩家,而由王弼、程顥等人加以發揮,至馮先生方得以闡揚。至于《素問》中所說的以“情”治“情”方法,雖然未有明確論及,但馮先生似乎是不同意的,這是因為“情之使人在整個底心理和生理方面,起非常劇烈底變化者,如把一池清水,從底攪起。”[10]P423所以根本的問題是不讓情海翻起波浪。那么,怎樣才是對付情感的最關鍵的辦法呢?在馮友蘭看來那就是“以理化情”。“以理化情”的實質就是平衡情感與理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就是馮友蘭反復強調的“有情不為情所累”,不為情累就需要理智的調控,越是激烈的情感越需要高度的理智來加以制約。他以儒家對待喪葬的態度為例說:“我們對待死者,若純依理智,則為情感所不許;若專憑情感,則使人流于迷信,而妨礙進步。其有折衷于此二者之間,兼顧理智與情感者,則儒家所說對待死者之道也。”[11]P136孔子強調的“哀而不傷”就是能夠“折衷于此二者之間”的中庸之道。馮友蘭還指出:“根據現代心理學,情感是依附于心理活動的基調,所謂哀樂都是情感,以知識駕馭情感,不用外力強抑。我們如果對引起情感的事物有充分的認識,有相當的理解,則情感自然減少。”[12]P82顯然,這里的“知識”和“理解”就是理智的別稱。由此看來,馮友蘭提出的處理情感的方法,既符合現代心理學的原理,又能夠匡正或補充中醫的情感治療方法,更凸顯了中國哲學所特有的實用性和現實性品格。
當然,馮友蘭正負結合的方法和對付情感的方法,都不是針對中醫學理論而提出來的,如果要真正運用于中醫臨床過程中,恐怕還需實踐的反復檢驗。
結語
馮友蘭的一生幾乎和二十世紀共始終,而這也是中醫學命運最為坎坷的一百年。中醫學在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下,大有岌岌危殆之勢。而作為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哲人,馮友蘭并未一味責難甚至完全否定中醫,而是客觀冷靜細致地分析中醫的歷史成因和學術內涵,從整個中國哲學的特點入手深入研究中醫理論,正確地指出中醫理論的形上學性質,從而將其納入中國哲學的研究范圍之中。這樣,通過對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馮友蘭實質上也為中醫哲學提出了新的認識方法。顯然,中醫理論即中醫哲學其命運和中國哲學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馮友蘭曾有一個預言:中國哲學將來一定要大放光彩。這也包括了對中醫哲學未來命運的展望。盡管目前中醫哲學的研究尚在初始階段,但由于馮友蘭等老一輩學人已經做出了篳路藍縷的開創工作,中醫哲學一定能夠得到深入、持續、長足的發展,一定能夠大放光彩。
[1]傅斯年.傅斯年全集 (5)]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2]陳寅恪.寒柳堂集 [M].北京:三聯書店,2001.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1)[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4]馮友蘭.三松堂全集 (5)[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喻昌.醫門法律 [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
[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 (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馮友蘭著趙復三譯.中國哲學簡史 [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8]馮友蘭.三松堂全集 (13)[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9]王叔和.脈經[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
[10]馮友蘭.三松堂全集 (4)[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11]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12]馮友蘭.三松堂全集 (11)[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肖琴
B2
A
1004-3160(2011)02-0069-06
2010-12-24
徐儀明,男,湖南開封人,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