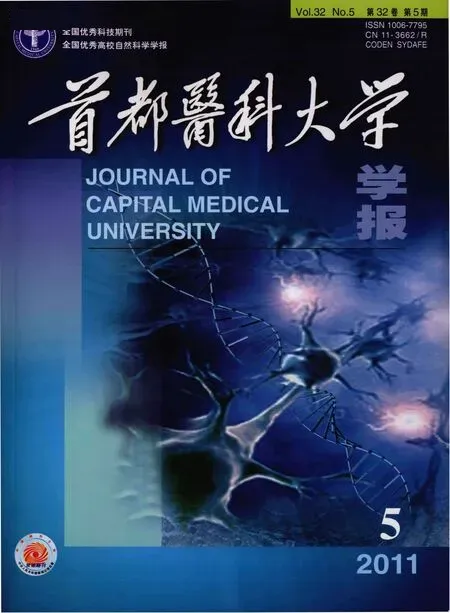正確認識高鹽和高血壓
華 琦 任海榮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心臟科,北京 100053)
高血壓是由多基因遺傳和多個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1],在基因和環境因素共同影響下,已經成為影響全球三分之一成人的嚴重公共衛生問題和沉重負擔[2]。作為高血壓發病的主要環境因素之一,鹽對于高血壓的發病起到重要作用。以往流行病學和大量臨床實踐證明了食鹽(或氯化鈉)的攝入量與高血壓發病率、平均血壓水平的密切關系。Dahl于1960年成功建立了鹽敏感性高血壓遺傳大鼠,隨后Kawasaki和Luft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先后提出了血壓鹽敏感性概念,使針對鹽和高血壓發生發展機制關系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3-4]。
1 定義和診斷標準[3-4]
高血壓有多種分型方法,如果按照鹽負荷或限鹽后血壓反應可以分為鹽敏感性高血壓、鹽不敏感性高血壓和中間型。其中鹽敏感性高血壓是指攝入高鹽飲食后導致血壓明顯升高,限制鹽的攝入使升高的血壓下降的高血壓類型。在臨床工作中也可以分為高腎素型、低腎素型、正常腎素型。還有根據紅細胞膜離子轉運缺陷進行的分型。
在動物實驗中,常常以給予大鼠高血壓模型高鹽(含8%氯化鈉)飲食2周或以上,血壓較正常鹽(含1%氯化鈉)飲食大鼠顯著升高>10%,為鹽敏感性高血壓,否則為鹽拮抗型高血壓。在臨床研究中,采用鹽負荷試驗和鈉敏感指數等進行判斷。
鹽負荷試驗包括食物和靜脈注射2種方法,前者采用逐步增大飲食含鹽量,比較高鹽后較之低鹽后血壓升高大于10%或10 mmHg(1 mmHg=0.133 kPa)即鹽敏感性高血壓,否則為鹽拮抗性高血壓或非鹽敏感性高血壓,也有應用24 h動態血壓監測對比低鹽和高鹽2次的血壓均值,如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即為鹽敏感性高血壓,否則為鹽拮抗性高血壓;后者對比靜脈輸入0.9%氯化鈉注射液(增加鹽負荷)和次日低鹽飲食及利尿(減少鹽負荷)的平均壓,如果平均壓下降超過10 mmHg為鹽敏感,下降低于5 mmHg或者不降反升者為鹽拮抗或鹽耐受,處于2者之間(6~9 mm-Hg)為不確定。
鈉敏感指數是指平均壓的變化值和尿鈉排出量變化值之比,即先分別測定高鹽負荷和低鹽負荷時平均壓和尿鈉排出量,再計算2者變化值,如果大于0.05 mmHg·(mmol-1·d-1),即為鹽敏感。
2 流行病學研究
高血壓的發病機制非常復雜,難以用單一的遺傳因素、環境因素或其他因素來解釋,很可能是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多個環境因素中,高鹽是最常見最重要的環境因素之一。以往調查發現,食鹽攝入量低的地區的人群其平均血壓也偏低,食鹽攝入量高的地區人群平均血壓也增高,同時血壓水平也隨著年齡增加而升高,食鹽入量和血壓水平呈線性關系。于1988年完成的INTERSALT大規模橫斷面研究證實,平均24 h尿鈉排泄量與血壓隨年齡增長呈顯著相關;個體排鈉量與血壓顯著相關,在部分研究中心此關系獨立于體質量指數和飲酒量;人群的24 h鈉排泄量(反映鈉攝入量)每減少100 mmol,收縮壓和舒張壓也分別相應減少6.0和2.5 mmHg,同時顯示血壓隨年齡升高的程度與大量食鹽攝入密切相關。在排鈉量極低的人群中,血壓中位數和高血壓患病率也低。該研究[5]有力地說明了鈉鹽與血壓的關系。
在我國,食鹽攝入和高血壓發生率呈現明顯地域性,例如居住在北方和寒冷地區的居民,鈉的攝入量明顯高于南方和沿海地區,而且高鹽攝入人群的平均血壓水平和高血壓患病率也相應較高,鹽的攝入與血壓水平明顯相關。在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鈉和鉀的生物學作用機制起著突出作用[6]。調查發現在過去30年間全國范圍的高血壓患病率增加了近3倍,但鹽的攝入量并沒有平行增加。在同一時期,由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成年人中出現超重或肥胖的比例明顯增多。可見在中國,高鹽攝入與高血壓患病率相關,此外近些年來高血壓發生率的增加,與肥胖比例的增多也有一定關聯[7]。
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流行病學、遺傳學和動物實驗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臨床實踐表明,在食鹽攝入量與高血壓發生之間存在密切的因果聯系。我國有研究[8]認為僅僅8周的高鹽飲食即引起大鼠基因表達的變化。流行病學研究表明,每天攝入食鹽不到3 g的人群,高血壓的發病率很低,而每天攝入20 g以上的人群,高血壓的發病率很高。對于每天鹽攝入量在3~20 g之間的不同人群,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隨著鹽攝入的增加,血壓會隨之升高,但如果每天攝鹽量大于3 g,那么隨著年齡的增大患高血壓的風險將逐漸增加,鹽攝入的越多這種現象就越明顯。現代社會人們的平均攝鹽量約為每天10 g,在我國,北方人每天吃12~18 g鹽,南方人為6 g以上是很常見的現象。中國六成的高血壓患者都屬于“鹽敏感性高血壓”,即服用高鹽后血壓會隨之增高,這已經大大超過腎臟排鹽的正常能力范圍,是造成我國一部分地區高血壓發病率明顯增高的重要原因。
3 發生機制
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盡管高鹽飲食會引起血壓升高,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或人種出現對于鹽的耐受性,即在高鹽攝入后不發生病理性血壓上升,表現為血壓對鹽的不敏感,即在高鹽攝入的同一人群中,僅部分個體發生高血壓,提示鹽對血壓的影響存在個體差異性[9]。鹽攝入過多使血壓升高的機制目前認為是由于各種原因導致部分人群細胞膜離子轉運缺陷和腎臟排泄鈉功能異常,在高鹽環境下發生鈉鹽代謝異常,出現多種病理生理改變并引發高血壓的發生。目前已知誘發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環境因素就是鹽過度攝入,而個體血壓對鹽敏感性則為遺傳因素。例如非洲裔美國人比美國白人更易發生高血壓,提示非洲裔美國人對鹽敏感性高于白色人種,而且其血漿腎素活動水平和醛固酮較低,有著更高的腎臟對鈉的重吸收率[10]。而在一項日本進行的研究[11]中發現,相關的等位基因頻率在日本人和白人出現情況不同,在日本人中出現的頻率明顯高于白人,也說明鹽敏感性高血壓發生率在不同種族之間的明顯差異。在高血壓患者和血壓正常人群中,51%的高血壓患者和26%的正常人鹽負荷后出現血壓升高,即表現為鹽敏感性。但是高鹽飲食者不論是鹽敏感性還是不敏感性 ,鹽對機體靶器官都可能產生重要影響。研究[12]表明,腎臟和中樞神經系統是和鹽敏感性有密切關系的2個主要器官和系統,尤其以腎臟的作用更為顯著。遺傳性細胞膜鈉離子代謝異常、腎排除鈉功能障礙、血管反應性異常增高都是鹽敏感性高血壓發病的重要原因。當腎臟不能及時將過量攝入的鹽從體內排出,就會出現體內水鈉潴留,細胞外液和循環血量均明顯增加,并導致動脈血壓升高,即需要更高血壓才能保持一定量的鈉排泄,以致不能有效抑制血漿腎素活性;同時水鈉潴留和體液明顯增加還刺激腎上腺和下丘腦釋放哇巴因樣物質,抑制血管平滑肌細胞和心肌細胞Na+-K+-A T P酶活性,導致細胞內Na+離子和游離Ca2+離子濃度的升高,使血管緊張性增加,對升壓物質的敏感性增加,心肌收縮力增強。也有研究[13]認為由急性鹽容量擴張導致低腎素性高血壓時可以刺激內源性哇巴因的假設不成立,而且內源性哇巴因也不是低腎素高血壓時主要的利鈉因子,在這種狀態下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可能是調節內源性哇巴因分泌的因素,而內源性哇巴因的作用可能是醛固酮的調節因子并且減弱了這種鹽容量依賴性高血壓狀態下的防衛機制。所以通過減少食鹽入量,可以抑制或中斷哇巴因,也許是一項有效的降壓措施[14];高鹽還可引起交感-腎上腺髓質活動增強,血管內皮受損,一氧化氮釋放減少,內皮素分泌增加,使血壓進一步升高[15]。
高鈉能誘導成纖維母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肥大,使血管平滑肌細胞AT1mRNA表達增多,AT1受體密度增加,介導AngⅡ引起的血管收縮和心臟肥厚;高鈉負荷可使血壓晝夜節律性改變 ,血壓變異性增加,導致靶器官損害。所以,近端小管對鈉的重吸收并且引起血鈉濃度增高是高血壓的獨立預測因素[16]。由于血壓升高,腎臟的壓力性利鈉、利尿效應增強,從而排出多余的體液。因此可以把高鹽引起的血壓升高理解為防止過量的水鹽在體內進一步積聚的機體的自我保護意義的反應。但是由于血壓升高甚至出現高血壓引起的一系列病理性后果,例如動脈管壁增厚、動脈硬化,左心室肥厚、左室增大,內分泌系統功能發生紊亂等等因素,導致心腦血管疾病的大量增加,嚴重威脅人類健康,所以應當引起廣泛關注。
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可能是以下幾種機制的共同作用結果:
1)遺傳機制:目前已知的遺傳性鹽敏感包括Liddle綜合征、Gordon綜合征和非調節型高血壓等。另外已知有多種基因可能參與了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例如血管緊張素原基因、血管緊張素轉化酶基因、ADD基因、腎素基因、多巴胺受體基因、胰島素受體基因、ANP基因、鈉泵基因、β22腎上腺素受體基因(β22AR)等等。其中ADD是一種異源二聚體細胞骨架蛋白,在膜連接和膜骨架的形成以及細胞內信息傳遞中起重要作用。研究[17]認為α-ADD的460位的Gly突變為Trp后可以導致鹽敏感性高血壓,且其突變個體對利尿劑的降壓反應優于對照組,但是該突變與高血壓的相關性具有地域和個體人群的差異,在一項針對α-ADD和WNK1-NEDD4L通路影響鹽敏感性高血壓調節的研究證實,ADD1,WNK1和NEDD4L存在等位基因時可以共同影響腎臟鈉轉運、血壓調節和對噻嗪類降壓的反應。有學者[18]認為單核苷酸多態性(SNP)的診斷方法的使用對于早期檢測鹽敏感性和及時介入鹽敏感性高血壓發生發展的預防有重要意義。ANP是由心房分泌的一種多肽,可通過利尿、利鈉、控制血容量在血壓的調節中起重要作用,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血漿ANP水平顯著低于鹽不敏感性高血壓患者,但是在一項對照研究[19]中發現,只有ANP的5'端非翻譯區(C-664G)的多態性與高血壓有明顯的關系,而其他多態性與高血壓均無關,但是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的結論并不一致。在日本最近進行的研究[20]中發現,鹽負荷在鹽敏感性動物中引起腎臟交感神經活動增強,從而導致β2腎上腺素能受體(β2-adrenergic receptor,β2AR)興奮,引起活化Na+-Cl-協同轉運蛋白(Na+-Cl-cotransporter,NCC)的WNK4基因表達下降,最終導致鈉滯留和發展為鹽敏感性高血壓,并且預言存在于腎臟的β2AR-WNK4-NCC通路是治療鹽敏感性高血壓的重要目標靶點。
2)離子轉運機制:紅細胞內鈉含量升高,鉀含量降低,高鹽攝入使細胞內鈉和鈣離子濃度上升,水進入細胞,導致血管內膜水腫 ,血管腔狹窄;血管平滑肌細胞內鈉也增加 ,使鈉鈣交換增加,胞內鈣增加,促進血管平滑肌收縮;過量鹽負荷可以使蛋白結合鈣變為離子鈣,使細胞游離鈣增加,游離鎂減少,這也是服用鈣劑治療鹽敏感性高血壓有效的機制之一;過量鹽負荷導致鉀缺失,所以補充鉀可以減輕高鹽導致的高血壓。
3)內皮功能障礙機制: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內皮功能受損程度較鹽不敏感性高血壓嚴重,表現為一氧化氮生物活性減弱,血漿vWF升高、尿中內皮素-1排泄減少。我國學者[21]提出在正常血壓時,內皮功能障礙也會導致鹽敏感性人群長期高危的靶器官損害和高病死率。
4)腎臟機制:除了前述腎臟在鹽敏感性高血壓發生當中的主要作用以外,腎臟還參與多種血壓調節機制,而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中多有腎功能異常或腎臟疾病,腎臟排鈉受到動脈壓力乃至腎灌注壓的調節,正常情況下腎功能正常,排鈉功能強,血壓正常。鹽負荷時尿排鈉反應延遲,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腎臟對鈉負荷血流動力學的適應性異常,出現尿微蛋白排泄量增加。由于腎小球前血管阻力增加引起血壓升高為鹽拮抗型高血壓,腎小球濾過面積減少、腎小球濾過膜通透性下降和小球數量下降導致腎臟濾過系數下降和腎小球鈉重吸收率增加引起的血壓升高可以產生鹽敏感性高血壓。可見鹽敏感性高血壓反映了腎臟在排泄氯化鈉方面的生理性缺陷[22]。
5)交感神經機制:鹽和應激都是高血壓發生的環境因素,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進高血壓的發展。有研究[23]表明交感神經系統活動可能在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中起重要作用。鹽敏感性高血壓常常伴有交感神經系統活性增加,比如有鹽敏感性高血壓父母的正常血壓子女在高鹽攝入時對精神應激產生的血壓增高反應更加明顯,同時伴有交感神經活性增強。鈉能促進交感神經末梢釋放去甲腎上腺素。機體對應激反應的程度代表了交感神經活性,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鹽負荷時血漿兒茶酚胺濃度明顯增加,對應激的升壓反應增強。神經節阻滯和交感神經抑制劑可顯著減低高鹽導致的血壓升高,也表明交感神經系統活性增加和高鹽導致的高血壓有關。另外,多巴胺和腎上腺素能受體也參與了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機制。研究[24]證實大腦和交感神經系統活性氧增加可以導致鹽敏感性高血壓和肥胖性高血壓。高鹽食物的早期效應主要影響夜間動脈血壓,也提示交感神經系統活動的晝夜節律性可能影響了這一鹽敏感高血壓反應的調控。
6)中樞神經系統機制:鹽敏感性高血壓伴有交感神經系統活性增加機制可能和中樞神經系統有關。有Coruzzi P等[25]學者研究顯示在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中盡管其鹽敏感性僅有輕度升高,也和心血管自主控制的改變相關,提示在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中發生鹽敏感性的病理生理學的機制中神經機制的重要作用。
7)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機制:在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中,血液中腎素活性比較低(但是非調節型鹽敏感性高血壓腎素水平正常或升高),鈉促進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激活,鹽敏感性高血壓常常伴有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功能異常。有Chamarthi B等[26]研究表明高血壓患者在高鹽飲食時對于血管緊張素II有反常的血管反應,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活動失調可能在此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為進一步研究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病理生理學機制增加了新的亮點。醛固酮和鹽皮質激素受體體系在鹽敏感性高血壓以及相關的器官損害發生發展中也發揮了重大作用,正常的醛固酮和鹽皮質激素受體體系是人類生存必需的水電解質平衡的最基本調節機制,過量的鹽攝入的結果是醛固酮-鹽皮質激素受體軸受抑,導致高血壓、心血管受損和腎衰竭[27]。
8)內分泌機制:內分泌系統也參與了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和發展,至少在絕經期后女性當中進行的實驗[28]觀察表明,在絕經期后的女性鹽敏感性高血壓和隨后的終末期靶器官損害的發病機制中,雌激素、一氧化氮、血管緊張素II和血管壁以及腎臟當中的活性氧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臨床上可以導致由于雌激素缺乏,鹽敏感性增強,使那些遺傳上較為敏感的絕經期女性更容易發生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腎臟疾病。
9)胰島素抵抗:高鹽飲食可能誘發胰島素抵抗,主要是改變胰島素代謝途徑必需的酶的活性而發揮作用,但是目前還缺少證據證明胰島素抵抗是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
還有許多其他機制可能參與了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例如WNK激酶的發現就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WNK激酶是連接血管緊張素Ⅱ、醛固酮和腎臟鈉鉀轉運的極其重要的分子通道,其和其他重要的轉運酶組成的體系一起調節遠側腎單位中鈉鉀轉運蛋白,包括噻嗪類敏感的Na-Cl協同轉運蛋白和腎ATP-調節型鉀離子通道(ROMK channels),如果探究其發生機制,可能會進一步揭示鹽和高血壓發生發展的關系[29]。Mazor R 等[30]研究表明 TNF-α 水平在鹽過度負荷和高血壓時升高,這種細胞因子可能在激活NADPH氧化酶以及在鹽敏感性高血壓模型中提高氧化應激中起作用。也有學者[31]認為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可能是由于依賴20-羥甘碳四烯酸的排鈉機制的削弱所致。主要由腎上腺和下丘腦分泌的內源性鈉泵抑制因子哇巴因在高鹽時增多,抑制腎小管上皮細胞、血管內皮細胞和交感神經末梢的鈉泵,使細胞內鈣離子濃度升高,血管張力增加,血壓升高,所以也參與了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其他如前列腺素、激肽釋放酶等可能都參與了鹽敏感性高血壓的發生機制。
4 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查
除了原發性高血壓共同具有的特點以外,鹽敏感性高血壓的臨床特點還包括鹽負荷后血壓明顯升高,限鹽或縮容后血壓降低,這已為動物實驗和臨床觀察所證明,并作為鹽敏感性測定的經典方法;血壓的晝夜差值縮小、夜間谷變淺,鹽負荷后更加明顯;血壓的應激反應增強,鹽敏感者于精神激發試驗和冷加壓試驗后血壓的增幅值明顯高于鹽不敏感者,且持續時間較長;腎臟靶器官損害出現早;尿微白蛋白排泄量增加;鹽敏感性高血壓屬于代謝性高血壓,可以同時伴有多種胰島素抵抗表現,特別在鹽負荷情況下鹽敏感者的血漿胰島素水平均較鹽不敏感者明顯升高,胰島素敏感性指數降低,血三酰甘油水平和膽固醇水平均較高;左心室質量增加等等。其中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左心室質量增加主要表現為室間隔和左心室后壁增厚,而且鹽攝入被認為是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發生左室肥厚最重要的明確原因之一,其原因與鹽敏感者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對飲食的攝入反應遲鈍,血漿醛固酮水平相對升高、血漿兒茶酚胺升高(特別于鹽負荷后)、鈉的轉運異常、鹽敏感者血壓的晝夜節律改變、夜間谷變淺等有關。另外,有代謝綜合征的患者其鹽敏感性高血壓發生率也增高,而且其血壓增高的大部分應該“歸功于”食鹽[32]。
高鹽所致不良反應除導致血壓升高和左室肥厚外,還有:使原有的鈉、水潴留加重;高鹽可使腦卒中發生率增加;可能加速腎功能和腎疾病惡化,甚至有學者把過量的鹽稱為“尿毒癥毒素”(uremic toxin)[33];高鹽使尿鈣排泄增加,繼而骨脫鈣和骨質疏松,易發生骨折等等。
5 治療
5.1 常規治療
1)限制氯化鈉的攝入量:限鹽是鹽敏感性高血壓防治的核心。對于鹽敏感者,我們可通過減少氯化鈉的攝入量達到控制血壓及減少降壓藥用量的效應,即便是血壓正常者,由于普通膳食中的鹽攝入量遠遠超出生理需要量,也應該適度減少鹽攝入量。人類對食鹽的生理需要量很低,成人每日攝入1~2 g氯化鈉就足以滿足一般人體的生理需要。WHO建議一般人群平均每日攝鹽量應控制在6 g以下,美國建議輕中度高血壓患者每日攝鹽量應控制在4~6 g。這個標準對我國高血壓患者也是適宜的。我國人均攝鹽量遠高于其他國家,尤其在我國北方,每日攝鹽量可高達14~26 g之多。如果人群收縮壓下降5 mmHg,即可使高血壓的患病率下降5%。另外,限鹽和降低膳食中的鈉/鉀比值都是高血壓飲食治療的關鍵。盡管INTERSALT的研究結果還有待進一步去解釋,但鹽的攝入與血壓隨年齡增長而增高的斜率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鈉的平均攝入量低會對血壓隨年齡的改變產生良性影響,從而有利于減少心血管患病率。由于我國人平均攝鹽量遠高于其他國家,提倡適當減少鈉的攝入量,可以有助于降低高血壓的發病率。研究[34]表明,過量鈉鹽攝入也會拮抗降壓治療,大幅度降低鈉鹽入量應該成為高血壓尤其是難治性高血壓治療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2)補充鉀離子及鈣離子:鈉和鉀的排泄有相互促進作用,增加鉀的攝入能促進鈉的排泄 ,反之亦然。鈉負荷會造成尿鈣和尿鉀的排泄增多,產生條件性的鉀和鈣的缺乏;增加鉀的攝入通過促進鈉的排泄、遏制容量擴展,阻止鹽介導的血壓升高。研究[6,35-36]報道,無論在動物實驗、流行病學研究還是隨機對照實驗均證實,高鈉低鉀飲食和高血壓的發生密切相關。給Wistar大鼠喂以高鹽飲食后,動物的預期生存時間縮短,但如同時補充鉀鹽則不受影響,血壓也因鉀的補充而降低,高鈉飲食造成的其他影響也不復發生。在我國北方農村進行的GenSalt(the genetic epidemiology network of salt sensitivity study)研究[37]對 1 906名年齡超過16歲的成人進行研究后也發現,血壓對于冷加壓試驗的反應與鹽敏感性和鉀敏感性有關,在對于冷加壓試驗有高反應的人群來說,低鈉高鉀飲食有更好的降壓效果。另外,在人群間和人群內的調查及實驗研究[38]取得的結果也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血壓與尿鉀排泄量及尿鉀/鈉比呈相反關系;鉀鹽攝入不足使血壓升高 ,而增加鉀的攝入則會使血壓降低,盡管結果在不同人群及種族之間不完全一致,鈉鉀比值增高和未來發生心血管病危險性增高相關,鈉和鉀的動態平衡在維持動脈血壓及內皮依賴性血管擴張中起著重要作用。鹽敏感者大劑量補充鉀鹽不僅能夠有效拮抗高鹽導致的血壓升高,而且還能夠促進NO合成和釋放,提高血、尿NO水平,提示鉀通過拮抗鈉的作用,改善血管內皮功能,從而可能減輕靶器官損傷,降低心血管風險[39]。高血壓人群防治除主張限鹽外,還應積極推動補鉀。一項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研究證實給予輕度高血壓患者補鉀飲食(氯化鉀或碳酸氫鉀),雖然沒有有效降壓,但有效改善了動脈僵硬程度和內皮功能,顯示了補充鉀飲食對心血管系統的保護作用[40]。另外適量補充鈣和鉀鹽能促進對鹽敏感性少年兒童尿鈉的排泄,并明顯延緩這部分少年兒童血壓隨年齡的增長幅度。因此 ,在年齡早期階段對那些鹽敏感者適當增加鉀和鈣的攝入,將有利于延緩血壓隨年齡的增長,減低人群的血壓水平,從而達到預防高血壓的作用。有證據表明,飲食鈣的攝入量與血壓水平呈相反關系,但不同人群間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卻非常不一致。后者可能與人群鈣的攝入水平有關,鈣攝入低的人群,鈣攝入量與血壓的相關性更強一些。多數鹽敏感者屬于低血漿腎素活性類型,血清游離鈣水平多偏低,飲食鈣的攝入和血壓之間有著穩定的負相關關系,血壓高者必然鈣的攝入低。同樣,此型高血壓患者可能呈現尿鈣相對或絕對排泄增多現象。鹽負荷使血壓升高越多 ,血清鈣水平受抑制越明顯。根據現有的認識還不能肯定增加鈣的攝入一定會對所有人群產生顯著地降壓效應,但對于那些既有飲食鈣攝入不足且為高血壓易感人群者,適當補充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或延緩高血壓的發生,特別是對于年老個體和鹽敏感者。
3)研究開發低鈉替代鹽:限鹽是鹽敏感性高血壓防治的關鍵因素。但是 ,在實際生活中,從高鹽攝入轉為低鹽飲食不僅表現在口味咸淡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人們根深蒂固的飲食文化和生活方式、習慣的改變。同時,雖然高鈣鹽有顯著降壓作用 ,但加入鈣劑量過多或時間過長 ,可使尿路結石患病率增加。如果在食鹽中添加鉀 ,盡管可使高血壓病患者的血壓下降,但鉀過多又會影響味覺。因此,研究開發出一種不影響味覺習慣,但又能減少鈉鹽攝入、補充鉀、鈣的復合離子鹽可能成為新的防治手段。
5.2 降壓藥物治療
1)治療原則:起始采用最小有效劑量獲得應有療效后,根據年齡和用藥后患者的反應再決定是否逐步增加劑量,使患者得到最佳治療的同時不良反應最小化;鼓勵24 h平穩降壓,避免在清晨血壓突然升高而出現心腦血管事件,降壓藥的谷峰比應該大于50%;可以采用2種或2種以上藥物治療。
2)調節型鹽敏感性高血壓:此型患者在增加鹽的攝入或鹽負荷時血壓升高,而限鹽及縮容時血壓降低;血漿腎素活性低且對鹽的負荷反應遲鈍;血清游離鈣水平多偏低。減少鈉攝入和增加鈣的攝入有助于降低血壓。利尿劑和鈣拮抗劑是首選藥物。其中利尿劑主要用于輕中度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特別是老年和伴發心力衰竭者。宜從小劑量開始,避免低血鉀、糖代謝異常和心律失常、血脂異常等不良反應。痛風患者禁用,已確診糖尿病和血脂異常者慎用。以氫氯噻嗪和吲達帕胺首選,呋塞米可用于伴有腎功能不全的高血壓患者。由于利尿劑可以導致嚴重低鉀血癥,為避免此類不良反應,可行的策略是利尿劑與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或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ARB)聯合使用,發揮各自的優勢同時又避免了低鉀血癥發生。由于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有細胞內鈉、鈣及鎂的代謝異常,服用鈣拮抗劑有助于對抗鹽介導的細胞內離子改變和升壓反應,另外,鈣拮抗劑還有利尿鈉作用,可見鈣拮抗劑對鹽敏感性高血壓具有良好降壓效果。由于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容易較早地發生腎損害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增加。在給予鈣拮抗劑降低血壓的同時,能有效減少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保護腎臟,所以鈣拮抗劑不論急性服用或長期應用,均使腎血流量(RBF)和腎小球濾過率(GFR)升高,腎血管阻力降低,產生利鈉、利尿作用,以二氫吡啶類的效果最顯著。可以用于各種鹽敏感性高血壓,特別適用于有著高卒中風險的人群,例如亞洲人以及老年單純收縮期高血壓患者和穩定性心絞痛患者。但是嚴重心臟傳導阻滯和心力衰竭禁用非二氫吡啶類,較嚴重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以下簡稱冠心病)患者如不穩定心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禁用短效二氫吡啶類鈣拮抗劑。首選長效緩釋制劑。
3)非調節型鹽敏感性高血壓:是與低腎素型高血壓相反的一種高血壓類型,腎上腺素對限鈉的反應減弱。鈉的攝入在這類高血壓病患者既不調節腎上腺也不調節腎血管對血管緊張素的反應,由于缺乏鈉介導的靶組織對血管緊張素的反應所以稱為非調節者。這類高血壓病患者血漿腎素水平增高或正常,有遺傳性腎排鈉缺陷。因為服用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可以糾正這類高血壓病患者的血壓升高和其他異常改變,所以應該首選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主要用于合并糖尿病患者,或者合并心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合并蛋白尿者,但是妊娠、腎動脈狹窄、腎衰竭者禁用。另外,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也同樣適用于此類患者。
5.3 其他治療
1)Omapatrilat:為血管肽酶抑制劑,通過神經內肽酶5抑制作用增加血管舒張作用,可以有效治療鹽敏感性高血壓。
2)血管舒張素(激肽釋放酶):可以增加緩激肽,使血管舒張,達到降壓目的。
3)選擇性內皮素受體拮抗劑:例如波生坦。
4)抗高血壓疫苗:目前主要重點在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的作用環節上,還未達到臨床應用的標準。
5)基因治療:高血壓的基因治療主要包括增強舒血管基因,即將正常舒血管基因DNA序列導入細胞,使血管舒張基因過表達,或者抑制縮血管基因,即將反義DNA序列轉入細胞,抑制血管收縮基因表達。
6 預防
有學者[41]指出,鹽敏感性高血壓和非杓型晝夜節律變化應當作為心腎疾病重要預測因素而加以重視,因為鹽敏感和非杓型晝夜節律血壓變化反映了腎功能儲備的缺失和高血壓的嚴重程度,而這些損害程度依靠諸如血壓本身、危險因素和靶器官損害等等常規方式是無法進行預測的,同時,鹽敏感性高血壓發生心血管病事件的危險比鹽拮抗性高血壓高出3倍[42]。盡管進行了大量實驗,對于有關鹽的攝入量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仍然有著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比如如何進行鹽敏感性的正確評價,食物中鈉含量測量的方法,研究人群中人口統計學數據的差異,怎樣鑒別降壓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各種新藥如腎素抑制劑的開發和應用等[35,43]。在經過大量流行病學調查后,研究[44]證實如果每天進食食鹽減為3 g,美國每年可以減少新發冠心病60 000例,腦卒中32 000例,心肌梗死54 000例,對于特殊人群如鹽敏感性高血壓患者受益更多。研究[45]表明代謝綜合征明顯增強血壓對鈉鹽攝入的反應,在患有代謝綜合征的多種危險因素患者中限制鹽攝入對于此類患者的降壓治療尤其重要。鹽負荷過重也會在短期內明顯增加血管脈搏波速度和血壓[46],而且短期的鈉鹽飲食波動就可以明顯改變高血壓患者心電圖電壓以及左室肥厚的心電圖表現,在通過心電圖來判斷高血壓患者左室肥厚時包含鈉鹽攝入評價可以改善心血管危險度評價標準[47]。
著名的The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DASH)-Ⅱ研究[48]當中表明,限鹽結合新鮮水果蔬菜、低脂乳制品飲食能夠有效降壓,而且容易實現,每日鈉攝入量減為1.6 g的降壓效果已經等同于單用一種降壓藥物的療效,所以有意識的改變飲食習慣是很好的預防措施,例如盡量少吃腌制食品,同時將補鉀列為重要的非藥物干預措施。我們每日攝入的鉀主要來源是新鮮瓜果和蔬菜,綠葉菜如菠菜、油菜等含鉀較多;豆類食物和甜薯、土豆含鉀也很豐富;此外蘑菇、紫菜、海帶、木耳也多含鉀;從保鉀的角度最合理的烹飪方法是在烹調時減少加工程序,避免長時間煮沸和過度煎炸,不輕易丟棄溶有鉀的菜湯。另外,補充鈣攝入可增加尿鈉排泄,在部分具有鈣代謝異常的高血壓病人中,補鈣降壓較好,而且在鹽敏感者中,缺鈣也是促成因素之一,故在限高鹽攝入的同時適當補鈣還是可取和有益的,例如養成每天喝牛奶的習慣等等。美國公共健康協會已經向食品制造商和飯店建議在10年內將食品中的鈉鹽含量降低50%并且已經得到著名的第7次美國預防、檢測、評估與治療高血壓全國聯合委員會的支持[49]。在歐洲高血壓協會和歐洲心臟病學會共同發布的2007年《高血壓防治指南》中也明確指出過量的食鹽攝入可能是頑固性高血壓的原因之一,并且建議將每日氯化鈉攝入量目標降至 3.8 g(盡管短期內難以達到)[50]。所以,在我國改變高鈉、低鉀、低鈣的飲食習慣,也應該作為高血壓一級預防的重要措施。
然而最近國外學者在進行研究[51]后發現,在收縮壓和鈉排泄之間確實存在橫向和縱向的關系,但這種關系不會解釋發病率和生存率的變化,而舒張壓卻和鈉排泄沒有關系,基礎鈉排泄量也并不預測高血壓的發生,相反,較低的鈉排泄可以預測更高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同時不支持在全體人群當中不加分別的進行限鹽措施,當然也不否認在高血壓患者當中進行限鹽所帶來的降壓效果。可見,在高鹽和高血壓之間關系問題上還有很多疑問有待解答。
總之,在當今社會中改善高鹽飲食早已經不僅僅是改變飲食習慣和輔助降壓的問題,已經涉及公共健康、經濟發展等諸多領域,為了進一步扭轉高血壓防治工作當中的被動局面,需要政府公共管理部門、醫療和科研機構、社區工作者以及患者和患者家屬共同努力。
[1]Hamet P,Pausova Z,Adarichev V,et al.Hypertension:genes and environment[J].J Hypertens,1998,16(4):397-418.
[2]Kearney P M,Whelton M,Reynolds K,et al.Global burden of hypertension:analysis of worldwide data[J].Lancet,2005,365(9455):217-223.
[3]劉力生.高血壓[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512-544.
[4]孫寧玲.高血壓治療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280-286.
[5]Intersalt Cooperative Research Group.Intersalt: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electrolyte excretion and blood pressure.Results for 24-hour urinary sodium and potassium excretion[J].BMJ,1988,297(6644):319-328.
[6]Adrogue H J,Madias N E.Sodium and potassium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ypertension[J].N Engl J Med,2007,356(19):1966-1978.
[7]Liu Z.Dietary sodium and the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a review of nationwide surveys[J].Am J Hypertens,2009,22(9):929-933.
[8]Gu J W,Young E,Pan Z J,et al.Long-term high salt diet causes hypertension and alters renal cytokin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in Sprague-Dawley rats[J].Beijing Da Xue Xue Bao,2009,41(5):505-515.
[9]Weinberger M H.Salt sensitivity of blood pressure in humans[J].Hypertension,1996,27(3Pt 2):481-490.
[10]Chun T Y,Bankir L,Eckert G J,et al.Ethnic differences in renal responses to furosemide[J].Hypertension,2008,52(2):241-248.
[11]Katsuya T,Ishikawa K,Sugimoto K,et al.Salt sensitivity of Japane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gene polymorphism[J].Hypertens Res,2003,26(7):521-525.
[12]Orlov S N,Mongin A A.Salt-sensing mechanisms in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and hypertension[J].Am J 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2007,293(4):H2039- H2053.
[13]Balzan S,Nicolini G,Iervasi A,et al.Endogenous ouabain and acute salt loading in low-renin hypertension[J].Am J Hypertens,2005,18(7):906-909.
[14]Manunta P,Maillard M,Tantardini C,et al.Relationships among endogenous ouabain,alpha-adducin polymorphisms and renal sodium handling in primary hypertension[J].J Hypertens,2008,26(5):914-920.
[15]Lorenz J N,Loreaux E L,Dostanic-Larson I,et al.ACTH-induced hypertension is dependent on the ouabain-binding site of the alpha 2-Na+-K+-ATPase subunit[J].Am J 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2008,295(1):H273- H280.
[16]He F J,Markandu N D,Sagnella G A,et al.Plasma sodium:ignored and underestimated[J].Hypertension,2005,45(1):98-102.
[17]Manunta P,Lavery G,Lanzani C,et al.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α-adducin and WNK1-NEDD4L pathways on sodium-related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J].Hypertension,2008,52(2):366-372.
[18]Rhee M Y,Yang S J,Oh S W,et al.Novel genetic variations associated with salt sensitivity in the Korean population[J].Hypertens Res,2011,34(5):606-611.
[19]Kato N,Sugiyama T,Morita H,et al.Genetic analysis of the 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gene in essential hypertension[J].Clini Sci(Lond),2000,98(3):251-258.
[20]Mu S,Shimosawa T,Ogura S,et al.Epigenetic modulation of the renal β-adrenergic-WNK4 pathway in salt-sensitive hypertension[J].Nat Med,2011,17(5):573-580.
[21]Liu F Q,Mu J J,Liu Z Q,et al.Endothelial dysfunction in normotensive salt-sensitive subjects[J].J Hum Hypertens,2011 Feb 24[Epub ahead of print].
[22]Ehmke H.Neurogenic mechanisms and salt sensitivity[J].Hypertension,2005,46(6):1259-1260.
[23]Strazzullo P,Barbato A,Vuotto P,et al.Relationships between salt sensitivity of blood pressure and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a short review of evidence[J].Clin Exp Hypertens,2001,23(1-2):25-33.
[24]Ando K,Fujita M.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salt-sensitive hypertension:possible relationship to obesity-induced hypertension[J].Clin Exp Pharmacol Physiol,2011,Mar 9.doi 10.1111/j.1440-1681.2011.05510.x[Epub ahead of print].
[25]Coruzzi P,Parati G,Brambilla L,et al.Effects of salt-sensitivity on neural cardiovascular regulation in essential hypertension[J].Hypertension,2005,46(6):1321-1326.
[26]Chamarthi B,Williams J S,Williams G H.A mechanism for salt sensitive hypertension:abnormal dietary sodium mediated vascular response to angiotensin Ⅱ[J].J Hypertens,2010,28(5):1020-1026.
[27]Shibata S,Fujita T.The kidneys and aldosterone/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 system in salt-sensitive hypertension[J].Curr Hypertens Rep,2011,13(2):109-115.
[28]Hernandez Schulman I,Raij L.Salt sensitivity and hypertension after menopause:role of nitric oxide and angiotensinⅡ[J].Am J Nephrol,2006,26(2):170-180.
[29]Hoorn E J,Nelson J H,McCormick J A,et al.The WNK kinase network regulating sodium,potassium,and blood pressure[J].J Am Soc Nephrol,2011,22(4):605- 614.
[30]Mazor R,Itzhaki O,Sela S,et al.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a possible priming agent for the polymorphonuclear leukocyte-reduced nicotinamide-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oxidase in hypertension[J].Hypertension,2010,55(2):353-362.
[31]Laffer C L,Laniado-Schwartzman M,Wang M H,et al.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natriuresis by 20-hydroxyeicosatetraenoic acid in human salt-sensitive versus salt-resistant hypertension[J].Circulation,2003,107(4):574-578.
[32]Hoffmann I S,Cubeddu L X.Increased blood pressure reactivity to dietary salt in patients with the metabolic syndrome[J].J Hum Hypertens,2007,21(6):438-444.
[33]Ritz E,Koleganova N,Piecha G.Role of sodium intake in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J].J Ren Nutr,2009,19(1):61-62.
[34]Pimenta E,Gaddam K K,Oparil S,et al.Effects of dietary sodium reduction on blood pressure in subjects with resistant hypertension: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trial[J].Hypertension,2009,54(3):475-481.
[35]Jones D W.Dietary sodium and blood pressure[J].Hypertension,2004,43(5):932-935.
[36]Whelton P K,He J,Cutler J A,et al.Effects of oral potassium on blood pressure.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J].JAMA,1997,277(20):1624-1632.
[37]Chen J,Gu D,Jaquish C E,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blood pressure responses to the cold pressor test and dietary sodium intervent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J].Arch Intern Med,2008,168(16):1740-1746.
[38]Cook N R,Obarzanek E,Cutler J A,et al.Joint effects of sodium and potassium intake on subsequ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the trials of hypertension prevention(TOHP)follow-up study[J].Arch Intern Med,2009,169(1):32-40.
[39]Fang Y,Mu J J,He L C,et al.Salt loading on plasma asymmetrical dimethylarginine and the protective role of potassium supplement in normotensive salt-sensitive Asians[J].Hypertension,2006,48(4):724-729.
[40]He F J,Marciniak M,Carney C,et al.Effects of potassium chloride and potassium bicarbonate on endothelial function,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and bone turnover in mild hypertensives[J].Hypertension,2010,55(3):681-688.
[41]Kimura G,Dohi Y,Fukuda M.Salt sensitivity and circadian rhythm of blood pressure:the keys to connect CKD with cardiovasucular events[J].Hypertens Res,2010,33(6):515-520.
[42]Morimoto A,Uzu T,Fujii T,et al.Sodium sensitivity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J].Lancet,1997,350(9093):1734-1737.
[43]Egan B M.Reproducibility of blood pressure response to change in dietary salt.Compelling evidence for universal sodium restriction[J].Hypertension,2003,42(4):457-458.
[44]Bibbins-Domingo K,Chertow G M,Coxson P G,et al.Projected effect of dietary salt reductions on future cardiovascular disease[J].N Engl J Med,2010,362(7):590-599.
[45]Todd A S,MacGinley R J,Schollum J B,et al.Dietary salt loading impairs arterial vascular reactivity[J].Am J Clin Nutr,2010,91(3):557-564.
[46]Chen J,Gu D,Huang J,et al.Metabolic syndrome and salt-sensitivity of blood pressure in non-diabetic people in China:a dietary intervention study[J].Lancet,2009,373(9666):829-835.
[47]Vaidya A,Bentley-Lewis R,Jeunemaitre X,et al.Dietary sodium alters the prevalence of electrocardiogram determined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 hypertension[J].Am J Hypertens,2009,22(6):669-673.
[48]Sacks F M,Svetkey L P,Vollmer W M,et al.Effects on blood pressure of reduced dietary sodium and the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DASH)diet DASH-Sodium Collaborative Research Group[J].N Engl J Med,2001,344(1):3-10.
[49]Chobanian A V,Bakris G L,Black H R,et al.The seventh report of the joint national committee on prevention,detection,evaluation,and treatment of high blood pressure:the JNC 7 report[J].JAMA,2003,289(19):2560-2572.
[50]Mancia G,De Backer G,Dominiczak A,et al.2007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rterial hypertension:the task for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rterial hypertens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hypertension(ESH)and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J].Eur Heart,2007,28(12):1462-1536.
[51]Stolarz-Skrzypek K,Kuznetsova T,Thijs L,et al.Fatal and nonfatal outcomes,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and blood pressure changes in relation to urinary sodium excretion[J].JAMA,2011,305(17):1777-1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