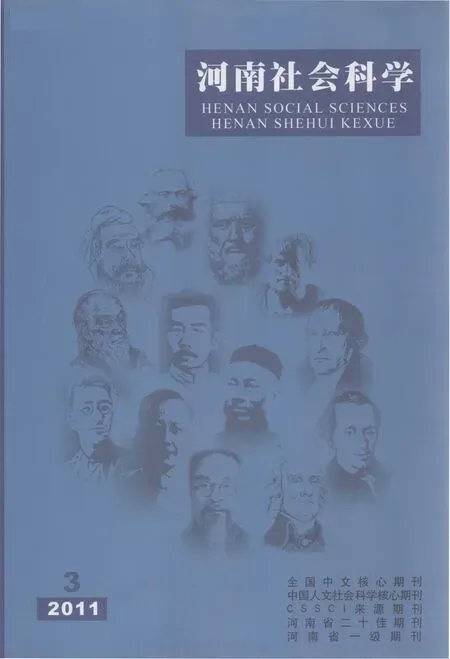“以意逆志”:文學閱讀學的再闡釋
蘭拉成
(寶雞文理學院 中文系,陜西 寶雞 721013)
“以意逆志”:文學閱讀學的再闡釋
蘭拉成
(寶雞文理學院 中文系,陜西 寶雞 721013)
孟子的時代,《詩經》充當“達政”、“專對”等政治場合的特殊語言的功能消失,“不學詩,無以言”也就成為過去。與之同時,也結束了“斷章取義”的用詩方法。也就是說,孟子時代的人們已開始把《詩經》中的作品當做一個整體來讀并重視對詩義的探求了。他在《孟子·萬章上》中針對咸丘蒙拘于字面的讀詩法說:“是詩也,非是之謂也。”指出文學作品語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不應當這樣理解,首次注意到了文學語言的特殊性。進而,他指出了正確的文學閱讀方法:“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從漢代以來,歷代學者對“以意逆志”有過不同的闡述。明人王嗣爽說得明了:“以意逆志,孟子讀詩法也。”[1]他明確指出“以意逆志”是關于文學閱讀的方法。因此,本文試圖將“以意逆志”置入文學閱讀視野中,并將其視為一個完整的閱讀過程,以期對“以意逆志”作出新解。
一、讀者擁有的知識:“以意逆志”的前提保障與桎梏藩籬
“以意逆志”的主語是“說詩者”,即讀者。也就是說,讀者是閱讀的主體。“以意逆志”是文學閱讀的高級形式,只有擁有知識才能保證閱讀活動順利進行。所謂“知識”既包括了閱讀基本能力、閱讀技巧等基本條件,也包括了嚴肅的閱讀態度以及哲學、史學等影響閱讀層次的各種知識,涵蓋了可能影響閱讀的道德、情感、藝術素養等各種要素。在閱讀活動中,一個讀者擁有的知識既為進行“以意逆志”的閱讀提供了前提保障,同時又是束縛閱讀進行的桎梏藩籬。
一方面,每個閱讀者作為個體,所擁有的知識情況差異很大。一個讀者擁有的知識越多,“視域”越廣,就越有利于閱讀,他的閱讀就越能接近真正意義上的“以意逆志”。因而,閱讀者的人生閱歷、思想境界、文學閱讀基本能力和技巧及其對哲學、歷史等相關知識的占有程度無不影響其閱讀的質量,決定其閱讀層次。從具體閱讀技巧來說,中國古代文論將“知人論世”納入閱讀系統中,要求閱讀者在閱讀作品時,必須結合作者的時代文化背景、思想、閱歷等,并將它們作為進行有效的“以意逆志”閱讀理解的技術保障。對作者時代的文化背景、思想、閱歷等知識及與作品相關的知識了解越多,讀者就越接近作者的創作意圖,其閱讀層次就越高。因此說,知識是進行“以意逆志”閱讀的保障。
另一方面,讀者擁有的知識又是進行閱讀的桎梏藩籬。外國文論將讀者擁有的知識稱為“視域”。既是“域”就有一個界線,給讀者的視野劃定了范圍,制約著其視野的擴展。因為一個人所擁有的知識武裝了這個人的頭腦,卻形成了其固定的思維定勢,他所能見的也只能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閱讀的最高追求卻是超越自己,打破思維定勢,走出自己“視域”所劃定的圈子。從這個角度講,閱讀所面對的,與其說是作者、作品,不如說是讀者自己。在閱讀中,作品的“真諦”一直存在于作品中。每回閱讀均有收獲,但均不是文學作品的“真諦”。掩蔽作品“真諦”的并不是作者或作品,而是讀者自己擁有的知識,是讀者自己的“視域”制約著自己的認識。因此說,讀者擁有的知識又是“以意逆志”閱讀的桎梏藩籬。
簡言之,進行“以意逆志”的閱讀必須擁有知識,讀者自己的知識一方面是閱讀的前提保障條件,另一方面卻是閱讀的桎梏藩籬。但需要強調的是,這里說的知識主要指人文知識,并不指文化教育程度。民眾文化教育程度愈來愈高,但閱讀質量卻不見得提高,相反,正如丹尼爾所說:“文化大眾的數量倍增,中產階級的享樂主義盛行,民眾對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時尚本身的這種性質,已使文化日趨附粗鄙無聊。”[2](p37)受教育程度不僅沒有提高閱讀質量,反而影響了審美趣味。此種情形說明了當前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呼喚強化人文教育。
二、詞義——“以意逆志”的起點
對“以意逆志”的“意”的理解目前尚未有定論,代表性說法有三:第一種說法認為“意”是古人之意。以清人吳淇“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詩論詩,猶之以人治人也”[3](p37)論斷為代表。第二種說法認為意是學者之意。這種說法最早是由漢人趙岐提出來的:“意,學者之心意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4](P2735)后有宋人朱熹、今人朱自清繼承并發展了此說。還有一種說法是:“意為作家作品之意與評者之意的結合。”[5](P117)當前學界支持第二種說法的呼聲最高。但是,筆者以為以上三種說法與閱讀經驗都不相吻合。因為在閱讀之始,根本不可能知道作者之意,也不可能知道作品之意,用不知道的“意”去逆不知道的志,根本沒有可能。如果說讀者在閱讀之前,心中已有一個意,用這個已有的意去逆的那個“志”到底是讀者之志還是作家作品之志呢?若是讀者之志,閱讀還有什么意義呢?“以意逆志”分明說用“意”去“逆志”,意是閱讀的起點。根據一般的閱讀經驗,閱讀理解起點為詞義。因而,將“以意逆志”的“意”理解為詞義,更妥當些。
閱讀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交流。《莊子》云:“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6](P245)在人與人的交流中,語言只是交流的工具,“意”的交換才是目的。但是,語言文字是作家留下來的作品的唯一形式,所要傳達的“意”并不是顯于外,而是蘊藏于語言之中。讀者必須通過語言才能獲得意。語言的最小表意單位是“詞”,正是一個個詞的能指義與所指義誘導讀者的思路,使讀者由詞聯想到與之相類、相關甚至相反的事物,從而進入規定的情景。因此,所有的聯想都是建立在詞義的基礎之上的,離開最基本的詞,就失去了理解的對象,也就無所謂理解,再高明的解釋也只能是空穴來風。
劉勰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7](P397)清人吳淇:“詩有內有外。顯于外者曰文曰辭,蘊于內者曰志曰意……”[3](P36)辭是“波”,“顯于外者”;情感意志才是“源”,是“蘊于內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正是說閱讀前人作品以“顯于外”的文辭為起點,由外及里去探究作品蘊于內的志意。西方解釋學也認為,“無論什么時候,意義總是依附于一系列詞”。但他們由此推導出的結論是“回避作者是不可能的”[8](P5)。但是,作品一旦完成,成為獨立的文本之后,它與作者的關系無論密切到何種程度,任何批評家所標榜的自己得到的文本原意、作者原意,總是無法擺脫讀者自己的影子,有時甚至與作者根本沒有絲毫關系。因此說,只有“意義總是依附于詞”的論斷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在一篇文學作品中,詞是最小的意義單位。一部完整的文學作品正是由不同數量的最小意義單位組成的。讀者在閱讀一篇作品時,正是從破解它的第一個有意義的單位開始,進入詞匯的森林迷宮,積詞成句,積句成段,積段成篇,完成對文章的整體感知,進而完成閱讀。因此說,詞義是閱讀的起點。
章句之學,訓釋詞語意義,揭示句子結構,是中國最早的解釋方法,也是后世最常見的解釋方法。因此,有大批專家學者,不惜精力為古人的書作注,為廣大讀者和初學者掃除文字詞語障礙,也有力地證明了詞義是文學閱讀的起點。那么,“意”作為“以意逆志”的閱讀理解起點,完全可以理解為詞義。這是對讀書而言,對當代文藝未必適應。然而,在后現代主義那里,人們卻不斷消解經典的意義,以至于無詞歌曲、只是發泄的《忐忑》也受追捧,事實上這是對語言交流的否定。雖然無法否認狂吼可以暫時緩解情緒,但是,如果只有狂吼,沒有語言交流,絕不能真正疏導情緒,只能將人引向自閉。因此,在人與人的交流中,要別人真正理解自己,使用語言追尋意義才是正道。
三、去蔽——“以意逆志”的過程
如果說“以意逆志”的“意”是閱讀的起點,那么,“逆”就是閱讀的過程。前人對“逆”的解釋為迎。如朱熹說:“逆是前去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說:“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里,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9](P1359)也有人解釋為鉤考。周裕鍇先生認為如果把“以意逆志”解為“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那么“迎取”僅僅意味著讀者和作者之間的心靈接觸,理解和解釋還未開始,此時不能說“得之”,真正的理解和解釋有待于“鉤考”[10](P44)。還有人解釋為猜測、揣度。《漢語大詞典》“逆志”條解釋云:“猜測其志,揣度其原意。”有些學者對這幾種解釋之間的差異辨析很是精細,但是,我們認為,無論是“迎取”,還是“鉤考”或者是“猜測”,它們的主語都是讀者。讀者為什么要“迎取”、“鉤考”、“猜測”,又怎么去“迎取”、“鉤考”、“猜測”更為重要。
孟子說得清楚:“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之所以要讀者去“迎取”、“鉤考”、“猜測”是因為閱讀時常常會出現“以文害辭”、“以辭害志”的情況。所謂的“以文害辭”中的“文”指文學的修辭手法,“害”意為妨礙,“辭”是指詞義。文學修辭手法本來是幫助作家表達思想的,但是,借助文學修辭的表達多具有一種不確定性,讀者不同,對它的理解也就會有差異。因此,文學修辭就會產生對詞義理解的妨礙,即“以文害辭”。所謂的“以辭害志”的“辭”為詞義,“志”為思想。因為文字詞匯只是表達思想的符號,并不等于思想。各人的表達習慣、對語言詞匯的掌握運用等情況,所用的詞意與思想具有差距,就會出現語言表述妨礙思想表達亦即“以辭害志”的情形。咸丘蒙針對《詩經》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提出“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的疑問,雖也是依詞解《詩》,卻不懂文學表達的特點,只作機械字面理解,才認為《詩經》敘事與事實不符。顯然,是文學修辭遮蔽了咸丘蒙對詩的理解,才不能迎取《詩》之“志”,即“以文害辭”、“以辭害志”——由此,“文”對“辭”的遮蔽、“辭”對“志”的遮蔽是閱讀的障礙,閱讀過程就是要剔除一切遮蔽,使辭、志等明朗起來。簡言之,文學閱讀過程就是去蔽的過程,“以意逆志”的“逆”就是去蔽。
那么,文學閱讀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具體如何去“逆”,如何去蔽呢?
根據文學閱讀經驗,讀者常常從第一個詞、第一句話進入作家所構筑的語言城堡,于是,讀者漸漸進入作品情景,當專心致志時,將忘記自己周圍的現實,完全沉浸于故事中。初級的讀者往往還會將自己認同為作品的某個主人公,與他/她同悲喜。當然,更多的讀者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讀作品的,在閱讀時,總是尋尋覓覓,剝開層層掩蔽,尋找與自己理解相契合的東西。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在閱讀時無論發揮多少,他們總是認為,他們自己所得到的正是作者要傳達的,也是作品要表達的。然而,每回閱讀所揭去的掩蔽不同,所得也都不一樣。就這樣,讀者常常在矯正上次閱讀的“失誤”,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具體一下,則為:
文學閱讀從辭開始,揭去掩蔽,把握詞義;再積詞成句,揭去掩蔽,把握句意;如此層層揭下去,直至把握全篇之意。在掌握全篇之意后,全部文字的整體掩蔽被揭開了,真正的閱讀需再回過頭來,再逐層矯正對段意、句意、辭意理解的偏差。在矯正了辭意之后,再回到句意、段意、篇意逐層矯正。如此往復矯正,像剝洋蔥一樣,揭去一層又一層,雖然永遠到不了中心,卻慢慢靠近“中心”。
由此,揭示文字下被掩蔽的“意”、“志”的過程就是文學閱讀過程。“以意逆志”的“逆”就是去蔽。讀者要真正“迎”得作品之“意”和“志”,需要反復研讀。但是,在影視圖像發達的當前,許多人用看影視劇等代替原著閱讀,就不可能做到對原著“以意逆志”。換句話說,“以意逆志”這一去蔽的閱讀過程,要求當代讀者必須閱讀原典。
四、明志——“以意逆志”的暫時終極
如果單單從“以意逆志”這個詞來看,“志”就是閱讀目的、閱讀的終點。閱讀者把握了“志”,他的閱讀就獲得了意義。因此,只有正確把握閱讀的意義,才能解釋“志”和“以意逆志”。
前人對“以意逆志”的“志”有三種解釋。漢人趙岐說:“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4](P2735)朱熹也說:“當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11](P385)清人吳淇則說:“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為輿,載志而游,或有方,或無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詩論詩,猶之以人治人也。”[3](P37)今人朱自清的《詩言志辨》也持這種看法,他們將以意逆志的“志”均解釋為作者之志。李澤厚和劉綱紀在《中國美學史》中就指出,“詩人的‘志’不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的,而是蘊涵在詩人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之中”,孟子所說的“志”就是“詩人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12](P194);陳望衡則說:“如果把‘志’訓作記載,把《詩經》的本質看做史,孟子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就好理解了。”[13](P146)郭英德則說:“‘志’的本義是記憶、記錄,‘詩言志’的原始意義即是向神明昭告功德、記述政治歷史大事,而不是指抒發個人志意、情感。在孟子的時代,盡管‘志’已經有懷抱、情志之意,已經有‘詩以言志’、詩‘可以怨’、‘盍各言其志’(《論語·公冶長》)等說法,但‘志’的記事之意和‘詩言志’的原始意義仍然保留著,將詩歌創作真正看成個人志意的表達,還是孟子以后的事情。孟子本人的說詩方法……恰恰是著重于詩對歷史或現實現象的說明,即詩的記事之義。”[14](P27)志則被解釋為對歷史事實的記載。
我們不否認所有的作品中均含有作者的情感思想,但是將其完全等同于作者之志是不妥當的。首先,正如袁宏道所說:“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15](P693)作品所表現的未必就是真實的作者,因而,有什么理由將“以意逆志”的“志”全部看做是作者之志,并將它視為讀者閱讀的終極追求呢?除非我們相信作品表現的就是作者的真實志向。如果不能輕信或者不能全部相信,作品之志就不能與作者之“志”畫等號了。其次,假設“以意逆志”的“志”就是作者之志的話,在當代有許多作家都在世,叫這些作家出來講講就行了,還為什么要那么多的文學批評來研究它們呢?顯然,閱讀并非只是迎取作者之志。由此,“以意逆志”的“志”作為閱讀的暫時終極,就不能將它簡單地解釋為作者之志。
根據閱讀經驗可以看到,讀者經歷不同,擁有的知識程度不同,所處時代不同,閱讀同一作品的所得就不同。事實上,就是同一讀者,在不同時間、地點,閱讀同一作品所得也不盡相同。即使專業讀者(文學批評工作者)各自極力搜求最適當的理論,試圖對文學作品作出最合理的解讀,但是,不同專家所作出的“合理解讀”的結果也不盡相同,甚至差異極大。顯然,在文學閱讀中,作者、作品均是客觀的存在,相當于數學中不變的常數并不變化,變化無窮的是讀者及其閱讀結果。因而,閱讀的意義、“以意逆志”都只能在讀者及閱讀結果中探求。
讀者群十分復雜,他們的道德、情感、藝術等文化素養及思想閱歷等不相同,閱讀目的不同,因此,閱讀的意義也就各不相同。一般讀者閱讀的出發點或者只是對故事好奇,或者只是對優美的語言感興趣,或者只對其中的哲理感興趣,或者是對前幾種情況程度不同地兼而有之。因此,在閱讀后,他們或者了解了故事,或者記住了幾句名言警句,或者吸納了自己生活、工作所需的某些哲理。這些獲得也就是他們閱讀的全部意義。文學批評者對作品作出的“合理解讀”,無論其“合理性”如何,對批評者本人來說也是閱讀的全部,是他所得到的“以意逆志”的“志”。
這樣說來,每個讀者的閱讀所得,無論它是新奇的故事、優美的詞句、所謂的哲理,還是批評家的“合理解讀”,盡管各不相同,對讀者自己的閱讀來說都是全部,都是所“逆”的志。這些東西為作品所固有,一直都存在,所得之所以不同,不在作家、作品,而在讀者自身。讀者在閱讀中之所以得出如此結果,首先是在于這些是他擁有的知識視野能夠認識到的,其次是讀者自己認為重要的,或者是自身所缺乏或所忽視的,還有一種情況是與自己的思考相同或相左的。在整個閱讀過程中,讀者揭開的“掩蔽”,實際上是自己擁有的知識等造成的,作者、作品都只是讀者擴充知識、認識自己的工具,是與自己相對照的鏡子,讀者閱讀有意義的所得主要是彌補自身的缺失,在交流中堅定自己的思考。最終它們又化為讀者的知識的一部分固定下來,從而擴大了讀者的知識視域,進而取得認識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感、藝術素養等)效果。因此,所有閱讀者的閱讀與其說是讀書,不如說在閱讀自己。讀者的興趣取舍與其說解讀了作品,不如說明確了自己,展現了自己的志向。即是說“以意逆志”的“志”是閱讀者自己之志,明志才是每個個體“以意逆志”閱讀的暫時終極。這一揭示不僅說明了文學閱讀的意義,更強調了讀者在文學閱讀中對知識視域的突破及價值觀、審美觀的修正等。因此,它要求讀者要讀書,還要根據自己需要選擇優秀的經典書目,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交流之目的,并實現提升自己的意義。
基于以上分析,從文學閱讀角度可以對“以意逆志”作出新的解釋:以讀者自己擁有的知識為基礎,從作品的詞義出發,由詞積句,由句成段,由段成篇,逐層揭去掩蔽,直到實現閱讀目的——認識自己、提高自己。換一句話來說,閱讀活動與其說是讀書,不如說是在讀自己。重新解讀“以意逆志”對今天的啟示意義有:呼喚人文教育,強調閱讀要追尋意義達到交流,一定要閱讀原典,讀書要選擇優秀經典等。另外,有一個問題需要補充:每個讀者情況的差異,導致閱讀結果千差萬別,閱讀結果是否有統一的標準?西方文論中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已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兩個“一千個”前者強調讀者間的差異,后者突出的是閱讀結果的差異,“哈姆雷特”卻是具有差異的閱讀結果中的相同點,亦是眾多閱讀結果中唯一真正的結果。趙岐在解釋“以意逆志”時說:“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所謂“人情不遠”強調的是文學閱讀中讀者與作者交流的基礎,正因為如此,閱讀才得以可能并順暢進行。這一交流基礎,在讀者與讀者之間同樣適應,從而,不同讀者對同一作品的閱讀必有一定的重合,即相通的閱讀結果。因此,文學閱讀中盡管讀者不同,閱讀結果不同,但這并不表明文學閱讀沒有規范。閱讀差異是文學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學解釋學的價值所在,消除差異則是文學解釋學的目標。因為讀者的差異,文學閱讀結果的差異永遠不可能消除,并由此形成文學閱讀的層次——愈得到更多讀者認可的閱讀結果則愈優秀。
[1]王嗣奭,杜臆.杜臆原始(卷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丹尼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北京:三聯書店,1992.
[3]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趙岐.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影印本).
[5]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王夫之.莊子解[M].王孝魚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85.
[7]趙仲邑.文心雕龍譯注[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5.
[8]施赫.解釋的有效性[M].北京:三聯書店,1991.
[9]朱子語類(卷五八)[C].
[10]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1985.
[12]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13]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4]郭英德.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5.
[15]錢仲聯,等.元明清詩鑒賞詞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
2011-02-10
寶雞文理學院重點科研項目(ZK082)
蘭拉成(1966— ),男,陜西寶雞人,寶雞文理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元明清文學及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責任編輯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