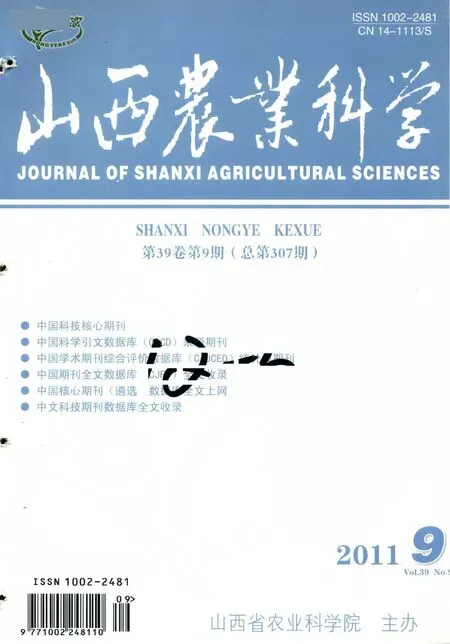山西省工礦區土地復墾現狀及發展對策研究
暢功民,李建華,張 強
(1.山西省農業科學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31;2.山西省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資源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
山西省礦產資源豐富,特別是煤炭資源,已探明儲量居全國首位。近年來,山西省原煤的產量一直居全國首位,外調煤炭占全國省際外調總量的80%,供應出口占全國出口量的74%[1]。但煤炭的大量開采,對土地利用產生了巨大負面影響。據初步統計,截止1998年全省累計塌陷、破壞和煤矸石、尾礦等壓占土地已達7.56×105hm2,并以每年5×103hm2的速度遞增,平均每生產萬噸原煤破壞土地0.058 hm2,其中40%為耕地[2]。然而,與這些破壞不相符的是全省的土地復墾率只有2%左右。因此,山西省工礦區土地復墾迫在眉睫,這對山西省農業生產、環境保護、生態建設以及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山西省工礦區土地復墾現狀
1.1 山西省工礦區土地待復墾面積大
目前,山西省待復墾面積大、分布廣,遍及全省多個地市,以大同、朔州、晉中、晉城、長治、臨汾、陽泉、呂梁、太原等地為主。位于太原市的西山煤電集團直屬9個礦,2006年產原煤3 200萬t,年產煤矸石550多萬t;目前,全礦矸石綜合利用不到20%,待治理矸石山120多hm2。位于陽泉市的陽泉煤業集團直屬8個礦,2006年產原煤3 500萬t,年產煤矸石600萬t;該礦現有28座煤矸石山,已治理3座。位于大同市的大同煤業集團煤礦開采歷史悠久,對生態與環境的破壞較大,加上當地自然條件較差,水資源嚴重缺乏,對當地大氣、土壤、水源等造成的污染相當嚴重,由于礦區復墾剛剛起步,礦區生態治理和植被恢復任務相當艱巨[1-3]。
1.2 山西省工礦區復墾率低、復墾周期長
山西省復墾率低,只有2%左右,復墾周期長,平均需要5 a時間。以對生態破壞最嚴重的露天采礦為例,采礦前對覆蓋層全部剝離—堆置—采礦后復墾與生態重建整個過程短則數十年,長則上百年[3]。同時,山西省礦區復墾的歷史欠賬尚未還清,每年新賬又在產生。山西省4個大型國有礦區,已治理矸石山約占總面積的1/4。較好的陽泉礦58.7 hm2矸石山已治理24 hm2,占40.9%;大同煤業集團所屬云崗礦18.7多hm2矸石山治理4.7 hm2,占25%。山西煤矸石平均約占煤炭產量的15%左右,若按全省年產6億t煤計算,每年新產生的矸石將達9 000萬t。而目前煤矸石綜合利用還不到總量的20%[4-5],山西省工礦區土地復墾工作任重而道遠。
1.3 礦區復墾后不穩定
矸石山復墾3~4 a后出現二次復燃現象嚴重。煤矸石中含有硫、碳、水分。其中,硫為可自燃物質、碳為可燃物質,二者構成矸石山的自燃基礎,而氧氣和水分則是矸石自燃的必要條件[6-8]。復墾后如果地面覆蓋度不高,矸石與空氣中的氧接觸,再加上微生物的作用便發生氧化,這樣日積月累,矸石山內部的熱量不斷累積,溫度不斷升高,當溫度達到煤的燃點時,便可使矸石山自燃。這對于井工開采的煤礦,復墾后地表仍有可能會出現二次沉陷,導致地表再次不平,甚至會出現裂縫,影響土地的生產力。
2 山西省工礦區土地復墾工作存在的問題
2.1 政府雖出臺許多相應的政策,但可操作性差,執行力度不夠
長期以來,我國的環保一直側重于空氣與水污染的防治。復墾要求常常籠統地散見于相關法律、法規中。在實際操作中雖然以“誰破壞,誰復墾,誰受益”的原則為指導,但是《土地復墾規定》既沒有明確界定破壞者的責任與義務,也沒有明確復墾者應享有的權益,特別是在土地復墾后的利益再分配和所有權問題上。這些不利因素大大挫傷了那些意欲復墾者的積極性[9]。同時,土地管理、環境保護以及工業管理等部門都有義務執行國家復墾政策,然而,交叉重疊的目標與任務往往導致重復管理,或是互相推諉責任,最終導致環境政策執行不力。
2.2 企業對復墾認識不足,復墾沒有積極性
企業對礦區復墾認識不足,土地復墾作為一個緩慢而長期的過程,不能立即顯現價值,所以一些礦山企業不愿長期大量投資,擔心收不回成本。當土地復墾后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時,還需要有人繼續進行生產性投資和經營管理,否則礦山土地復墾只能產生環境效益,這樣會使礦山負擔日益加重,也會影響礦山復墾積極性[10]。
2.3 復墾資金渠道不暢,難以保證
我國現行的礦區復墾資金缺乏強有力的保證措施。在將礦區廢棄地復墾成耕地的過程中,涉及土壤的改良、坡度的減緩和土地的平整等重大復墾工程,成本比較高。如平朔安太堡礦區43 000 hm2廢棄地的土地復墾工程費用投資平均3.8萬元/hm2,其中,土地整治費用2.6萬元/hm2,植被恢復及生產力提高費用為1.2萬元/hm2[4]。現在國家雖然設有土地復墾資金,但相對面積較大的復墾土地仍是杯水車薪。迄今為止,大部分地方仍然要求礦產企業對礦產破壞土地先行征用,而后進行復墾。換句話說,采礦企業必須先行支付耕地征用費,然后再承擔土地復墾費,這種做法不利于鼓勵企業實施復墾。修訂后的《土地管理法》第31條規定,沒有條件復墾或復墾達不到要求的,應繳納復墾費用作復墾基金。但是缺乏具體金額的規定,可能導致復墾資金支付遲緩或籌措困難。
2.4 待復墾土地產權界限不清,出現扯皮現象
礦區待復墾土地有2種所有制形式: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國家征用的塌陷地屬于國家所有,但這部分土地仍由原集體、村民占有和使用,國家也沒有對其授權,所以,造成所有者缺位。這就阻礙了復墾后土地進入市場的流轉。根據國務院《土地復墾規定》,土地復墾實行“誰破壞,誰復墾”的原則。但現實中由于待復墾土地的產權界限不清,使有能力進行土地復墾的煤炭企業也無法進行復墾。按照目前的征地規定,煤炭企業對所征用的土地經采煤后形成的塌陷地無使用權。現行的管理模式是:煤炭企業征地→采煤→塌陷地→土地主管部門→劃撥給地方使用。如果企業需對塌陷地進行復墾以作他用,則必須對塌陷地進行二次征地;如果企業在不進行重新征地的情況下進行復墾和使用,則將招致地方政府和農民的強烈干預。也就是說,“誰破壞,誰復墾”與“誰復墾,誰受益”不統一,造成企業不愿意出資進行土地復墾工作[9]。
2.5 復墾研究滯后,技術支持不足
近30 a來,山西省的礦區土地復墾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然而,從總體上來看,有關煤礦區土地復墾的理論研究仍落后于復墾的實踐要求,使土地復墾工程因缺乏理論指導而帶有一定的盲目性。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對塌陷地的利用方式、工程技術措施等的總結、歸納上,對土地復墾過程中所涉及的政策、法規、經濟問題及技術研究不足。
3 山西省工礦區土地復墾對策
3.1 政府應繼續完善現行的法律法規制度,提高其可操作性
政府應借鑒美國等復墾工作開展較早的國家,實行年度環境執行報告書、礦山監察員巡回檢查制度、礦區土地復墾保證金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同時應加大對重點礦區環保執法與監督力度。由環保部門運用法律手段和現代科技手段,在全省重點礦區設立生態與環境因子動態監測網點,定期發布監測數據以及生態重建與環境污染綜合治理進展情況,督促礦區依法履行“誰污染,誰治理”的責任和義務,以此作為評價地方政府政績和企業效益的主要依據,激發社會與民眾參與監督的熱情。
3.2 加強宣傳力度,明確“誰破壞,誰復墾”的原則,提高企業對復墾的認識和積極性
加強對《土地復墾規定》的宣傳和學習力度,提高企業對礦區復墾工作的認識,并將其作為企業工作的一部分。嚴格按照“誰破壞,誰復墾;誰治理,誰受益”的原則,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礦山環境治理。各地政府和企業可研究組建專業化礦區治理公司,依托其研究制定礦山治理規劃并組織實施,積極開展有計劃的礦山土地復墾。根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礦產資源勘查規劃和土地開發整理專項規劃,合理安排以土地復墾為主的土地開發整理項目。進一步調動各企業的復墾積極性,加大礦山廢棄土地的復墾力度。
3.3 疏通融資渠道,加大資金投入,加強資金監管力度,保證復墾費專款專用
礦區廢棄地可以借鑒德國通過拍賣和招標的方式得以復墾,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同樣,也可以通過財政補貼、代征補償、稅收優惠等政策傾斜來幫助廢棄礦區再利用的啟動,比如減征土地使用稅、允許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等來疏通融資渠道。對于原有礦與新開礦,可以實行復墾保證金制度。原有礦可以按產量或銷售量繳納保證金,新開礦的保證金應該在申請開采許可時繳納。保證金額度應由國家環保局本著合理、適當的原則確定,既要保證足額支付目前的復墾費用與長期維護的費用,又要確保保證金額度不使未來投資者望而卻步。同時,應加強資金監管力度,建立一種有效機制來保證復墾專項基金的合理使用與專款專用[10-11]。
3.4 加強復墾科研投入力度,減少復墾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復墾效率
在國家統一領導和協調下,以礦區復墾為契機,加強礦區復墾的科研投入力度,建立企業、環保、林業、水利、農業、氣象等多方合作的平臺,形成以煤業集團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長期合作機制,減少復墾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復墾效率,推進礦區植被恢復和生態重建,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持續發展。
3.5 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積極倡導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加快山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一方面要延伸以煤為主,電力、氧化鋁、建材并舉的黑色產業鏈;另一方面要圍繞復墾土地開展生態重建,種養殖一體化發展的綠色生態產業鏈。利用復墾的土地資源建立苗圃基地、中藥材、飼料種植基地,開展蔬菜、食用菌種植和牛、羊等家畜養殖等,以后還要實現復墾土地農副產品的深加工。同時,要加強對礦區周邊環境的詳細調研,根據地理、環境、氣候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復墾計劃和方法,將改善生態環境作為土地復墾的主要目標,達到礦區的環境、經濟、社會三者的效益最優化,走科技與生產相結合的路子,不斷把相關領域的新技術引入礦山復墾中;倡導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分批分期分重點地建設扶持一批重要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的綠色礦業公司,把復墾工作推向產業化,促進山西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提高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
4 結束語
“十一五”期間,由山西省農業科學院環境與資源研究所主持的山西省科技攻關重大專項“山西省礦區土地沉陷防治、復墾與生態重建”,已取得了階段性研究成果。建立了地表沉陷預測預報模型,煤矸石山綠化造林的實用技術模式,形成礦區復墾和快速培肥技術,研制開發出沉陷土地快速培肥微生物菌劑和生土熟化專用肥料,建立了礦區土地復墾數據庫以及基于3S技術和地面核查相結合的礦區土地復墾和生態重建信息系統等,為山西省礦區復墾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技術支撐。
[1]蔡登谷.關于山西礦區復墾的考察報告 [J].林業經濟,2008(4):36-38.
[2]李素清,張金屯.山西生態環境破壞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及對策研究[J].干旱資源與環境,2005,19(2):56-61.
[3]白中科,趙景逵,段永紅,等.工礦區土地復墾與生態重建[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2000.
[4]曹銀貴,程燁,白中科.安太堡露天礦區土地景觀格局變化及土地復墾的原則[J].資源與產業,2006,8(5):7-11.
[5]李建華,郜春花,盧朝東.山西省礦區土地復墾的初步探討[J].山西農業科學,2008,36(3):69-72.
[6]張晶.我國礦區生態環境修復法律制度研究 [J].環保科技,2008(1):13-15.
[7]李華,李永青,沈成斌,等.風化煤施用對黃土高原露天煤礦區復墾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研究 [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08,27(5):1752-1756.
[8]胡振琪,康驚濤,魏秀菊,等.煤基混合物對復墾土壤的改良及苜蓿增產效果[J].農業工程學報,2007,23(11):120-124.
[9]劉越巖,劉成付.礦區土地復墾與土地生態重建研究[J].環境科學與技術,2005(28):154-156.
[10]趙巧香.對烏海市耕地現狀及土地復墾的幾點思考 [J].內蒙古農業科技,2003(S2):199-200.
[11]瞿春艷,劉寶華.海州露天煤礦排土場土壤空間變異性分析[J].內蒙古農業科技,2011(2):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