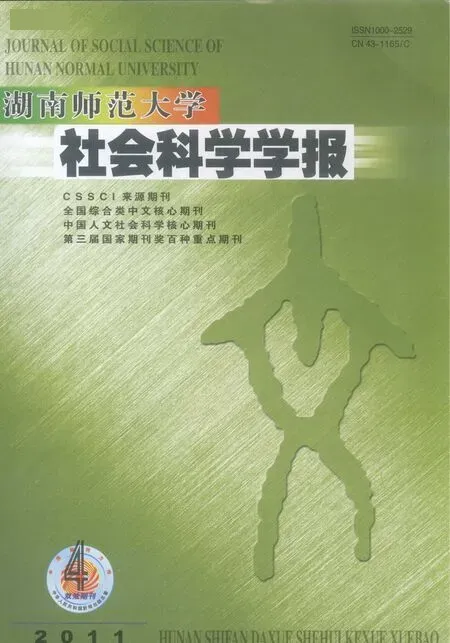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建構的應有視域
李培超
(湖南師范大學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1)
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建構的應有視域
李培超
(湖南師范大學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1)
環境倫理學本土化建構是對我國環境倫理學三十年發展歷程反思和對其未來走向的理論自覺,體現的是對中國環境倫理學在滿足現實需要的基礎上獲得話語權和強化其實踐效能的強烈要求,這也決定了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的建構應當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上同時展開。
環境倫理學;本土化;話語權;實踐效能
近年來,關于我國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建構的吁求受到廣泛關注,這種吁求表達了理論界對中國環境倫理學現狀的冷靜反思和對其未來發展路向的期許,本文擬對此問題做出回應。
一、環境倫理學本土化主張的提出
環境倫理學是20世紀中葉前后在西方生成并得到迅速發展的一種理論思潮。這種理論思潮的出現既有豐沛的思想理論基礎,也有現實的客觀環境。現代西方哲學和倫理學的理論轉向以及生態學的發展為環境倫理學的萌生直接提供了思想資源,而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和人們對解決生態危機的迫切呼喚則是環境倫理學發展的現實動力。
西方環境倫理學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以后,已經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并且在生態問題已成為全球性問題的背景下,也迅速地向其他國家傳播。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就是在20世紀初70年代末從譯介西方的環境倫理學論著開始起步的,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環境倫理學進展非常迅速,但是模仿和移植的痕跡比較嚴重。這種情況在起步階段時其局限性并未充分現露,但是隨著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對其實踐性要求的提高,缺乏本土化視角和價值立場的環境倫理學的局限性就開始充分暴露出來了。因為,任何倫理學都應該是實踐的,缺乏實踐效能的倫理學只能是不結果實的“思辨的花朵”,難以擔當對人們進行價值引導的作用。而我國環境倫理學目前就面臨著這樣的窘境:學界的理論建構與國家的環保決策之間有過大的張力,學術研究與環保實踐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距離,學者思想與民眾意識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我國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問題開始受到了重視。
實際上,從全球的范圍來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的訴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就表達得越來越強烈,因為在經歷了激進的環境主義的喧囂后,許多國家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抽象孤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對自然的認識總是要受到具體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制度安排等社會因素的影響,所以必須在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來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惡化的原因以及探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途徑,因而許多學者都提出了他們各自的環境關懷的本土化主張。
這些主張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可以稱之為“批判性”的思路,即主要反思和批判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局限性,反對將西方環境倫理思潮的價值理念在全球推廣。印度學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在《激進環境主義與荒野保護:來自第三世界的批判》(Radical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Wilderness Preservation:A Third World Critique) 一文中所表達的觀點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認為,以“深生態學”為代表的西方激進的環境主義以普遍主義的面目出現,但實際上它的思想基礎和現實背景都是來自西方社會,或者確切地說“深生態學是獨一無二美國的”,所以這種學說用在像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在印度這樣人多地少的國家推行它的價值觀念和環境保護策略是一種“荒野強迫癥”,是一種帝國主義情結的表現方式,必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侵害:“這種坦率的帝國主義宣言,集中體現了深層生態學熱衷于荒野保護的多重危險。正如我所表明的,它大大加劇了美國運動忽視第三世界內部更為緊迫的環境問題的傾向。但是,或許更重要、也更為陰險的是,它也為西方生物學家及其資助人、組織(如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國際自然與自然資源保護聯盟)的帝國主義渴望提供動力。把一個在文化上植根于美國保護史的運動批發、移植到地球上其他地區,只能導致那里的人群在社會中背井離鄉。”[1]古哈指出,把激進主義的環境保護理念在印度強制推行最終只能造成惡果,因為印度是個長期定居高密度人口的國家,農業人口占國家人口的多數,長期的農業生產活動使得人們與自然之間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平衡關系,但是激進的環境倫理學卻以保留荒野為目的,秉持這種價值理念的環境保護主義如果在印度強制推行,就會導致自然資源從窮人直接轉移到富人手里。如被國際保護團體歡呼的老虎項目的公園網建設被當成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它假設老虎的利益和住在保護區及四周的貧窮農民的利益是沖突的。因而老虎保護區的設計要求村莊和他們的居民搬遷,保護區的管理要求長期地把農民和家畜排除在外。很明顯,在印度,為老虎和其他大型哺乳動物如大象和犀牛建立公園的初始動力,主要來自兩個社會群體,一是大部分印度聯邦衰落中的上層人士,他們由以前的獵人搖身一變為保護主義者,二是他們所謂的國際機構的代表,如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和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他們試圖把美國自然公園的系統植入印度土壤中,而不考慮當地人口的需要,就像在非洲的許多地方,標明的荒野地首先用來滿足富人的旅游利益。而涉及到大部分窮人生存的環境問題——如燃料、飼料、水資源短缺、土壤侵蝕、空氣和水污染,卻沒有恰當地處理。
盡管在有些人看來,古哈對深生態學批判主張或許有些極端之嫌,但是他主張環境保護倫理觀的確立和環境保護措施的實施應當以具體國家的國情為基礎,特別是要顧及社會大多數的人的利益,而不是帶有上層社會悠閑情調和避免生態殖民主義的侵害的主張并非僅僅是道德義憤的宣泄,而是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其現實意義不容低估。
另一類可稱之為“建設性的”的思路,如由維杰卡·梅農和坂元正吉主編的由16位來自亞洲政界、學界、商界和民間組織人士撰寫的《天、地、與我——亞洲自然保護倫理》(Henaven and Earth and I:Ethics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n Asia)一書則分別立足于亞洲不同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國情,提出了自然保護倫理的本土化問題,雖然在本土化的路向選擇方面各自闡述的視角不同,如有主張發揮本土宗教傳統在民間的影響和作用,有主張通過NGO組織來傳播自然保護倫理,還有主張通過發掘傳統文化中的民間生態智慧來形成適合本國的自然保護倫理,等等。但是他們的共識則是“自然保護倫理必須依托于本民族的文化環境和社會條件才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國外學界的這些主張雖然沒有直接涉及到中國環境倫理學本體化的問題,但是這些觀點還是有重要啟示的。
近年來,國內學界針對這一問題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①,國內學界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有:第一,通過反思中國環境倫理學的進程,提出中國環境倫理學的未來發展必然是要體現出本土化的視野或中國本土特色,要建構中國的環境倫理學;第二,在分析批判西方環境倫理學所表現出的西方中心主義或生態殖民主義色彩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要正確把握環境問題的普世性和特殊性問題,既不能忽視人類在應對生態環境問題上需要責任共擔、利益共享,但是又不能忽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解決生態問題上的固有權益;第三,提出了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建構的一些基本設想,如如何實現傳統生態智慧與現代生活的對接與活化問題,如何發揮環境倫理學的實踐效能,等等。
毫無疑問,這些觀點為我們進行環境倫理學本土化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也留下了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二、環境倫理學本土化訴求的實質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似乎“全球化”的呼聲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有人認為它代表著開放的視野、寬容的胸襟,相形之下,“本土化”則似乎是不時髦的話語表達,它難以與保守、封閉等觀念和思想劃清界限。那么,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建構是不是“不合時宜的思想”?
要回答這一問題,至少需要廓清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訴求所針對的問題是什么?其二是,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只能是彼此對立還是可以并行不悖?其三,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訴求是不是當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偶然或孤立的現象?
首先,關于中國環境倫理學本體化訴求緣起的分析。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的吁求絕不僅僅是針對該領域學術成果的匱乏或學術上的冷清局面。
實際上,倫理學這門古老的學科在20世紀中葉以后隨著應用倫理學的興起而顯現出了勃勃生機。盡管目前學界對應用倫理學的學科屬性尚未完全達成共識,但是研究者大都認同,應用倫理學并不是倫理學某個原理在生活中的套用,它代表的是倫理學范式的“革命”。這種范式的“革命”所體現出的是倫理學理論和價值呈現方式的重大變化:首先,面對日新月異的現實世界,舊有的道德理論已經乏力或“失語”,不足以為現實生活提供有效的價值應對,因而倫理學必須改變不關注現實生活而沉醉于玄思妙想的“高雅”姿態。其次,道德判斷和價值引導應當體現出現實性、境遇性,換言之,絕對主義的道德價值立場應當作出妥協或調整。再次,倫理或道德在新的時代中應當成為應對現實問題的一種有效的機制,因而它不應該僅僅表現為個人的情感、德性,而且也應該成為一種社會統籌性資源。
毫無疑問,應用倫理學的這種變革為倫理學實現與現實生活的有效互動提供了重要的平臺,也極大地促進了倫理學學科的發展,甚至有學者斷言,“新世紀倫理學的發展和演變將主要體現為各種應用倫理學思潮的潮起潮落。”[3](總序)時至今日,應用倫理學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學科群落,而環境倫理學是這個學科群落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分支,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力量發展非常迅速,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加。可以說在一定時間內,環境倫理學成為了應用倫理學群落中的“顯學”。
但是在這種繁榮背后卻暴露出了我國環境倫理學的另外的“貧乏”:一是本土化話語的貧乏,二是實踐力量的貧乏。前者所指涉的是,我國環境倫理學是在直接譯介西方環境倫理思潮的基礎上起步的,直到今天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明顯改變。也就是說,我國環境倫理學基本上還處于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概念、話語、派別的介紹的層面上,即便有比較性的研究也多是用西方環境倫理思潮某一流派的理論框架來容納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或模塑當代人的思維,這顯得中國環境倫理學與國際學術界的接軌和對話是建立在沒有自主的話語權的基礎上的。過于明顯的模仿性痕跡使得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的進展顯得或多或少有些“不自然”。后者所反映的則是,通過移植而形成的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缺乏理論反映現實、影響現實的應有“效能”。一方面,環境倫理學理論與我國的文化傳統、人們的價值心理、現實的國情缺乏有效的互動關聯,從總體上顯得理論漂浮于現實生活之上,與現實生活存在著明顯的距離。另一方面它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理論現象而受到部分專業研究人士的關注,而并沒有實際地走向現實生活,沒有走入人們的內心世界,沒有轉化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的調控力量。甚至有人指責它淪為了學者間用于相互贊賞或攻訐的文字游戲。
其次,對于全球化和本土化能否并行不悖的問題,解答的關鍵就是對這兩個概念實質的把握。全球化在今天雖然是一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概念,但是并沒有形成一個“封閉性”的闡釋體系,也就是說對其理解或把握也呈現一種開放的言說格局,人們大多是立足于具體的領域來談論全球化的內涵。如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當今世界的許多經濟活動已經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了全球范圍運作的經濟整體,簡言之,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系的一個整體,不同國家共同凝聚成一個經濟實體。如文化全球化則是指在經濟全球化的帶動下,當今世界的各種文化元素以各種方式,在“融合”和“互異”的同時作用下,在全球范圍內的交流與碰撞,從而表現出全球共享的癥候。除此之外,還有科技全球化、傳媒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等不同概說。如果要在這多種不同的全球化闡釋中尋求共同性,不難發現,所謂全球化實質上是指當今世界的一種動態開放、多元包容、跨越時空限制的節奏或態勢,它并不意味著齊一性或無差別性。與全球化這一概念相似,本土化的內涵也不是封閉的,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本土化闡釋維度,如企業本土化戰略、語言本土化、教育本土化、風俗習慣本土化,等等,從總體上看,本土化的核心成分即是凸顯出人類生存方式的具體性或現實性,并在此基礎上展現出對人類文明整體的不同的體認空間。
從表面上看,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易生齷齪,但實質上二者之間的關聯性是更加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本土化的關注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開并強烈表現出來的,可以說全球化既為本土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也予以了限制,即真正意義的本土化并不是隸屬于關門主義的或山頭主義的;另一方面,本土化的進程為全球化的落實提供了實踐機制,即任何全球化的吁求只能通過本土化的方式才能得到落實。
再次,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訴求并不是當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偶然的孤立現象。它體現的是理論對現實需求的自覺反映,也只是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本土化“和聲”中的一種元素。從大的背景來看,當今我國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訴求并非是對綿延已久的東西之爭或體用之辯等命題的重新提起,也不能單純地理解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力圖打破學科壁壘,集體主張自己的話語權,以期擺脫學術依附地位的純粹學理化運動。實際上,哲學社會科學的脈動盡管有其內在的規律,但是并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或流入一種任意化的理論沖動,表現為一種從理論范式到理論范式的自動轉換。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變化的根本基礎在于現實生活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哲學家并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里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人民的產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正是那種用工人的雙手建筑鐵路的精神,在哲學家的頭腦中建立哲學體系。哲學不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腦雖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體之外一樣。”[3](P219-220)也就是說,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說,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訴求是對我國當代社會發展所呈現出的“中國現象”的一種自覺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所出現的許多新的具體問題以及應對全球普適性問題的特殊視角都說明了,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簡單地移植追隨或硬性地嫁接某些概念和理論模式會面臨著難以解脫的尷尬和無奈:學術研究的“熱”與現實關切的“冷”形成對照,論壇上的“唇槍舌劍”與面向現實生活的“失語”產生反差,詮釋的豐富與原創的貧乏對比明顯……這種狀況必然會促動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直接主動地面對現實生活,擺脫與傳統“體用之辯”、“中西之辯”相伴隨的被動、焦躁、情緒化的文化心態,自然而綿密地進行自主性的理論創造和學術對話,敏銳地審視和把握當前我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同層面所發生的問題,或是提出有針對性的應對之策,或是做出明確而切實的價值引領,因而本土化的建構成為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共識。所以,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訴求并不“孤獨”。
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看,中國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的訴求是具有合理性,不能以全球化的話語對其加以貶低或壓制。而由此也可以申明,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問題研究是一個既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又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的課題。中國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訴求同許多學科的本土化要求在目標指向上是一致的,概括地說即主張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要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或體現“中國氣派”,具體來說則是強調中國環境倫理學要有一種本土化的研究定向(Indigenous Approach),應當與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人們的價值心理相契合,在對本土社會有更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增強在本土社會的應用性,形成具有本土特色(話語表達方式、價值理念、教育和實踐路徑等等)的環境倫理學體系。也就是說,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是指陳這樣一種學術研究向度:它不是簡單地模仿和照搬外來的研究成果,而是將關注的視角投向自身;它不滿足于“外激型”的發展軌跡,而秉持自我認同和個性張揚;它也并非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理念出發對于他國相關學術研究成果予以無端貶損或否棄,而是強調學術研究的一種現實主義的理路和自主創新精神。
實質上,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并非是中國環境倫理學獨特的要求或屬性,在許多“流行的”環境倫理學思潮中都不難“檢出”本土化的成分。
環境倫理學這種理論思潮在歐美率先興起以后,雖然長期以來以“普世主義”的姿態示人,但是實際上它也仍然走的是本土化的道路,即它的產生和發展既有特定的理論基礎,也有具體的現實背景。從理論基礎上來看,現代西方哲學倫理學的轉向、自然科學特別是生態學的發展以及受生態學帶動所形成的龐大的學科組群,都為環境倫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合宜的理論環境。如,西方現代哲學對形而上學、理性主義、主體主義、二元論、機械論、科學至上論的批判,直接構成了環境倫理學理論建構的重要支點;現代西方哲學在轉折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對世界和人類發展的價值關懷和憂患意識為環境倫理學所汲取;現代西方哲學發展過程中所提出的許多觀點對環境倫理學的轉折產生了重要啟迪作用。從后現代主義與環境倫理學的關系來看,兩者的直接結合已經成為一種理論現實,后現代主義的有機整體論和關于自然的“祛魅”與“返魅”的理論都取得了與環境倫理學的密切結合,當代西方倫理學對規范的重新重視、對人的具體道德境遇和道德應用性的關注等等,也為環境倫理思潮的生發提供了直接的學科支撐。從現實基礎上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以后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從而導致人與自然的關系緊張,各種環境公害對民眾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環境保護成為社會焦點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諸多浪漫性思考必然讓位于實際的應對舉措,在強調市場調控、科學決策、法律規范作用的同時,人們深刻地意識到了道德價值導向的不可替代性。因而環境倫理思潮在西方的崛起充分說明了,它并非是一種應對現實生態危機的“權益之計”,是沒有理論基礎的“主觀臆想”。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西方環境倫理思潮始終是按照一定的路向來向前發展的,從總體上看并沒有完全脫離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目的論、義務論等西方哲學的思維范式。盡管環境倫理學潮的出現在西方的思想舞臺上也存在著“合法化危機”,但是它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啟導仍然是人們所熟知的,因而環境倫理學能夠迅速地成為許多“草根”環保組織所高舉的旗幟,也能夠為社會民眾所內化。即便是為古哈所強烈抨擊的深生態學所倡導的“保護荒野”的價值理念,實質上也是一定文化、環境下的產物,也是具有本土化的基本內涵的。
所以,應當對西方環境倫理學進行具體的把握分析,僅僅以普適性的理論和實踐姿態加以對待是有失偏頗的。
三、中國環境倫理學本土化建構的四重維度
中國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建構首先要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風格、氣派的環境倫理學體系,為此必須做好這樣三個方面的工作:
1.應當樹立正確的自然價值觀,以克服抽象自然觀在環境倫理學理論中的泛濫
自然價值觀的闡發是環境倫理學的核心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環境倫理學的革命性或顛覆性就體現在它所主張的自然價值觀上。因此對自然價值觀的正確闡發是中國環境倫理學理論建構首先要注意解決的問題。
但是抽象的自然價值觀在現有的環境倫理學理論體系中還很有市場。抽象自然觀在理論研究中的表現主要是:第一,強調自然的自我運動,排除任何目的對自然的干預。第二,把自然與歷史對立起來,滿足于撇開社會歷史條件,泛泛地談論自然,從而實際上使自然虛假化、虛無化。第三,把自然科學與人類的社會生活割裂開來,從而最終導致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的分離與對立。[4]而在當今環境倫理學的場域中,抽象自然觀的前兩種形式是隨處可見的,集中體現在對自然內在價值、自然權利主體的過分強調上,而把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奠定在抽象自然觀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會助推環境倫理學走上與現實生活疏離的道路上去。
要克服抽象自然觀的泛濫,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過程中要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而是一種實踐行動。這不僅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社會建設和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因為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作出了科學的解答。在人與自然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許多重要的論述,其精髓就在于強調人與自然的互動是歷史發展演進的不可獲缺的重要動力機制,自然作為“人的無機的身體”和“人的精神的無機界”,直接參與到歷史進程之中,不能離開歷史來虛構自然的進化,也不能離開自然來抽象地編造歷史。人不僅改造自然,即實現人化自然的目的,而且自然也對人有塑造作用,即自然化人。因而,在任何一個歷史階段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認為被抽象理解的完全與人無關的自然界等于無,這里的無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無意義。所以在歷史發展和文化演進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自然向人生成的這一永恒的主題。抽象的自然觀試圖剝離人與自然的歷史性和文化性關聯,實質上是對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基礎的解構。而從中國歷史發展和文化演進的過程中看,自然向人的生成性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彰顯,離開了人的純粹的“荒野”并不是中國歷史和文化中的亮點。
2.應當努力搭建我國環境倫理學生成、發展、內化的文化價值支撐系統
即要在對本土文化進行挖掘整理的基礎上來獲得環境倫理學建構的思想元素,即從自己的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地導引出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和規范系統,由此而使得環境倫理學所倡導的價值理念能夠獲得被社會民眾所熟悉、所容易內化的文化符號載體。
任何一個民族在自己的生存發展過程中都要與自然界打交道,都要形成具有特殊歷史文化內涵的自然觀念,這些自然觀積淀了這個民族的生存經驗,體現了獨特的生態智慧。這些觀念體系會規范制約著人們對待自然界和自然物的態度,如果我國的環境倫理學能夠充分吸取和包容這些思想元素,就會很容易為人們所熟悉和接受,消除隔膜感或疏離感。
中華民族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界和自然物有自己的認識或覺解,這些認識和覺解積淀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中,也通過人們的日常生活獲得了傳承和保留。那么中華民族在與自然界打交道的過程中形成了哪些獨特的認識或覺解呢?
我們認為,這一問題可以概括為:本體論意義上的生命意識,認識論意義上的整體觀覽,價值論意義上的人格化育,日常生活層面上的應時節用。所謂本體論上的生命意識,就是指自然界在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被看成是本根,換言之,自然界是化生萬生萬物的母體,此即為“天地之大德曰生”,因而在這一層面上人與自然之間的是一種生命本根性關聯;所謂認識論上的整體觀覽,指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倡導整體性思維,自然與人之間并沒有被看成是主客二分的對峙關系,人與自然萬物同質同源、共存共生;所謂價值論意義上的人格化育,則是指中國傳統文化常常從人格教化或養成的角度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愛護自然萬物被看成有德之舉,即上升到人格評價的高度;日常生活層面上的應時節用是指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們在利用自然時要遵循自然的節律,不能違背事物本身的生長規律而滿足人的需要。這一切實際上反映出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重生”特質,即自然界是被看成是有生命的存在,這種“重生”的屬性在人的生活中就表現為強烈的生命意識并貫通人生的不同層面:自然是生命的源泉應當被尊崇和敬畏,自然萬物對人的生命起到重要的支持和護佑作用應當與人共生共在,自然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材料應當得到持續地利用。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然對于人來說是具有內在性的,既是尊崇敬畏的對象,也是精神、情感共鳴的朋友,還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性要素,總之,自然界就是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
誠然,任何一個民族為了生存發展都要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也都可能產生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但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反映出的對待自然的立場和態度從來都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從來都不是敵視自然、排斥自然的。強調自然對生命的化育功能,重視人的存在與自然的整體關聯,強調親近自然,重視合理利用自然就是我們民族的生存經驗和生命意識,也是需要我們在今天繼續發揚光大的人生智慧,更需要我們通過環境倫理學的建設來吸取寶貴的思想資源。
3.應當積極吸納國外環境倫理學的優秀成果
本土化不是走封閉的學術研究思路,而是要以開放的心態和胸襟來汲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立足本土化又超越本土化,即通過對話和交流,使我們也能夠參與到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協商過程中。“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表達的就是這種意境。對于環境倫理學這門學科而言,它首先是在西方英美等國率先興起。作為先發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對自然界的野蠻掠奪使得它們首先遭遇到各種生態災害的困擾,日益迫近的生態危機為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現實推動力,但是其固有的文化傳統也為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西方環境倫理學的諸多流派所提出的許多觀點都有其特定的思想文化淵源。從總體上看,西方環境倫理學的自由主義思想背景、宗教主義傳統、中產階級烙印和殖民主義情結是我們要拒斥的。但是它們的環境倫理學所強調的與自然科學的結合、打破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發動民眾廣泛參與、重視環境立法和環境倫理規范的結合等做法則是我們應當汲取和借鑒的。
4.應當強化中國環境倫理學的實踐效能
倫理學的活力就體現在它的實踐效能上。中國環境倫理學要在環境保護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就必須要立足于我們的現實國情。目前中國最現實的國情就是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單邊主義肆虐的國際大環境下,加快發展是當務之急。在環境問題上,承擔全球共同的責任是必須的,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具體問題更是十分重要的。而實際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問題都要通過民族化或區域化的轉化才能獲得最終的落實。西方環境倫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一些基本認識,體現出了環境問題的普遍性以及人類應對這一問題的共識性,但我們必須承認,西方環境倫理思潮有其自身的形成背景,也有其介入現實的社會心理基礎和文化土壤,所以它對中國社會的適用性必然就構成了一個文化移植過程中的常態問題,特別是被譏諷為帶有“中產階級生活情調”或代表“白人中產階級生活情趣”的激進的環境倫理學對于思考或應對我國的生態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則更值得認真思考。激進的環境主義保護政策就是竭力減少人為因素對自然環境的干預,如通過減少和壓縮人的生存空間來幫助自然生態環境的自然恢復,或者通過轉嫁生態危機來緩解自己的生態壓力。而西方的一些環境倫理學流派也提出了一些體現這種激進的環境主義政策的觀點,如竭力強調和主張生態中心主義,強調荒野和自然的獨立意義,把人的社會生活和自然秩序絕對地對立起來等等。這些思想從理論上說是宣揚一種抽象的自然觀,從實踐上說帶有明顯的生態殖民主義的意味,因而在我國是很難落到實處的。從我國的現實國情出發,中國的環境倫理學應當更加重視通過發揮人的作用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即通過實踐的方式來實現人與自然的互動,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而決不能在停止發展或在可持續的不發展的基礎上來談環境保護。因此我國的環境倫理學就不應“走向荒野”,而必須走進生活,關注民生,而不能被生活所拋棄。
在此前提下,中國環境倫理在實踐層面上要努力擺脫“三重尷尬”,即政府決策的忽視、企業經營的排斥和社會民眾的隔膜。通過三個方面的改變來提高其實踐效能:
第一,要與國家的環境管理和治理戰略相結合,特別是通過與法律的互動成為國家環境管理和治理的價值依據或人文支持因素,即使得環境倫理學在國家決策的層面上被接納。
第二,要與企業的經營發展相結合,使得環境倫理學的價值理念轉化為企業的道德責任,從而規范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
第三,要與社會民眾的生活相融合,通過宣傳、教育等途徑,使得環境倫理學的理念、規范滲透入他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能夠接受、親近并自覺踐行。
注 釋:
① 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著有:余謀昌先生的《創造中國環境倫理學學派,建設中國環境倫理學》,《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期;曾建平先生的《環境正義:發展中國國家環境倫理問題探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楊通進先生的《儒家與當代西方環境倫理學:一個初步的比較》(《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1期),韓立新先生的《環境問題上的代內正義原則》(《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年第5期),雷毅先生的《荒野保護與第三世界:深層生態學批判》,(《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2期)等等。
[1]Ramachandra Guha:Radical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Wilderness Preservation:A Third World Critique.《People,Penguins,and Plastic Trees》-Basic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Pierce/Van Deveer 2nd Editio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P.358-364.
[2]羅國杰,唐凱麟,許志銳.應用倫理學叢書[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俞吾金.論抽象自然觀的三種表現形式[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1999,(4):3-8.
The Due Perspective in the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hina
LI Pei-chao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s the reflection on the thirty years'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hina and the theoretical awareness of its future tendancy.It refects an urge for Chinese environmental ethics to obtain the right to speak and to enhance its practical effectiveness.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Chinese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
Environmental Ethics;localization;the right to speak;practical effectiveness
B82
A
1000-2529(2011)04-0025-06
2011-01-20
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研究”(NCET-07-0277)
李培超(1966-),男,山東海陽人,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