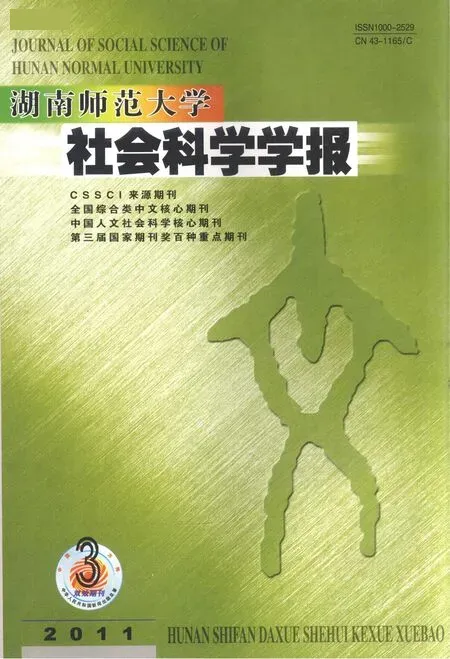人與自然協進的演化——中國文明起源的神話觀照
康 瓊
(1.湖南師范大學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1;2.湖南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人與自然協進的演化
——中國文明起源的神話觀照
康 瓊1,2
(1.湖南師范大學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1;2.湖南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家喻戶曉的上古神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中國文明的演化進程。通過對其進行解讀與分析,我們發現,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國家的形成,無論在“人與自然”關系的經濟基礎層面,還是在“人與人”關系的政治制度層面,都表現出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特點。因此,人類的文明史是一部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只有與自然協同演化和諧共生,數千年的文明之樹才能常青并不斷發展。
人與自然;神話;文明起源;國家起源
文明的形成,總是與其生存的環境息息相關,因此,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視域來看,文明的起源與國家的形成,既是“人與自然”關系推動的結果,也是“人與人”關系調整的結果。特別是中國國家的形成,無論在“人與自然”關系的經濟基礎層面,還是在“人與人”關系的政治制度層面,都表現出人與自然協進演化、交織相行的特點。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國家形成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人與人”的關系展開,而對于其自然生態前提則明顯關注不夠。
在中國文明的發軔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神話。這些神話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事實,但背后也存在一些“史影”。因為,在古代原始神話中,“神”和“人”是完全可以溝通的,凡“過去”的(死了的)人都是神,他們離開了這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繼續存在(活著),在這個意義上說,“神話”自然就是歷史。[1](P20)正如呂振羽所說:“傳說竟如此普遍地被傳述,說明它正是歷史真實的流傳和反映。”[2](P5)郭沫若也說:“這些神話傳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認為那時的一些血緣氏旅和部落集團,都分別出于各自的一個想象的祖先,而這個想象的祖先也往往是神話式人物。所以,傳說里的氏族和部落一般是從神話中引申出來的。事實上,氏族和部落比關于他們來源地神話要古老得多。盡管如此,透過這樣的神話,或者把這樣的神話僅僅作為氏族和部落的代號,仍然可以從傳說中理出當時的一些頭緒來。”[3](P108)也就是說,神話不一定確有其人其事,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歷史的發展情況。因此,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中華民族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神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中國文明的演化過程。因此,對其進行解讀與分析,可以在上古神話的蛛絲馬跡中,找尋中國文明發展與國家起源過程中人與自然、氏族組織與自然生態的原初關系與邏輯體系,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走向提供思考。
一、女媧補天: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最初嘗試
“女媧補天”講述的是,母系氏族時期的部落首領帶領氏族成員戰勝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傳說,被人們公認為中國最具魅力的上古神話之一。女媧時代,中國尚處于母系氏族時期,在這一時期,家庭和社會是合一的,家庭就是社會,社會就是家庭,各種組織都還沒有產生,它們只是作為萌芽存在于氏族內部。然而作為母系社會享有最高地位的部落首領的女媧,卻在行使著一些在當今看來是屬于社會“公共事務”的責任和義務,并以此推動人類社會組織與自然生態的共同發展。
據說,女媧創造人類不久,災難突然降臨。據漢《淮南子·覽冥訓》記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4](P54)描述了當時災難突發時的嚴重情況:天的職責是“兼覆”,因為支撐天的四根大柱子折斷了,塌開了一個大漏洞,不能全部覆蓋住大地,所以大火從天而降;地的責任是“周載”,因為遇上了強烈的地震,斷開了大裂縫,不能普遍負載著萬物,所以洪水從地下涌出;由于“天失其職”“地失其責”,而引發了水火之災。一時之間,猛獸吃人民、兇禽抓老弱,宇宙秩序大亂。關于災害發生的原因,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中解說是,水神共工與火神祝融為爭奪霸權而發生戰爭,共工失敗后惱羞成怒,以頭觸不周山,從而引發自然災害。其實,因權力之爭引發災害,這只是原始先民的想象罷了。當地震、洪災、山體塌方……等等從天而降的時候,處于蒙昧狀態的先民不能解釋這些自然災害發生的原因,就只能憑借生活的經驗進行猜度。而在原始先民心里可能想到更多的是以殺戮、破壞為主要內容的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女媧補天”神話雖然包裹了一層“天神戰爭”的外殼,但其原型也只能是因自然而引發的災害。如同2008年的汶川地震與2010年的玉樹地震,出現了諸如山體倒塌、地縫開裂、泥石橫流、河流改道、堰塞湖等大量生態災害現象,這些現象所造成的嚴重后果與女媧神話記載的恐怖情狀十分相似。由此觀之,我們可以說,女媧“補天”的主要內容就是治理地震等自然災害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次生災難。
對人類而言,自然生態是人類社會存在的自然基礎或載體,因此,自然災害不僅威脅著自然生態系統自身的完整與穩定,而且威脅著人類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安全。女媧時期,學者通常認定屬于母系社會,屬于新石器時代。這一時期,原始先民開始遠離舊石器時代的單純向自然索取的非生產性勞動——采集狩獵,而從事一種基于改造自然、適應自然的生產性活動——農業生產。而這種農業生產,與舊石器時代的采集狩獵不同,側重的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與和諧。首先,農業生產需要尋找一個適宜的自然生態環境,并且必須不斷地進行治理和改造,稍有懈怠或中斷便會前功盡棄。其次,農業生產還需要一套遠比狩獵復雜得多的生產技術——水利設施、天文氣象知識和養殖技術等才能進行。這就需要全體部落成員定居在一個相對穩定的農耕環境中,齊心協力去改善生存環境。因此,對以農業生產、定居生活為主要生存方式的女媧部落來講,一旦發生自然災害,不但直接破壞自然生態的整體平衡,而且還會嚴重危及到部落的農耕活動,甚至對部落的生存造成直接影響。因此,當人與自然的安全遭受到嚴重危機時,當時部落的女首領(家長)、“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女媧,必須帶領部落成員去戰勝自然災害。這是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之所需,是原始部落生存之所需,也是女媧鞏固其家長地位與政治權威之所需。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帶領與組織氏族成員,終于取得了治理自然災害的成功。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說,女媧治理自然災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維護部落農業生產定居生活的自然環境的需要,反之,這種對自然環境的成功維護又使部落最終定居下來,為其從事連續性的農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并推動著最初政治關系的萌芽。事實上,人類永遠都不可能在不觸及自然界、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前提下獲得生存和延續,因為人的本質是在通過有意識的對象性活動生成和顯現的,只要有人類存在,便有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但是人類的實踐活動并不會必然導向破壞自然這樣的惟一的結果上來,而完全可以成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中介或橋梁。[5]在女媧補天的神話中,女媧部落正是通過人類自覺地對地震自然災害的修復,維護了自然界的正常秩序,同時也推動了人類自身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一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類社會生活的進步與發展推動了自然環境的維護與發展,而自然環境的維護與發展又將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生活的進步與發展。
通過對地震自然災害的成功治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自然而然地被納入到女媧部落的重大議題和重要事務之中,并通過有組織的部落活動來維護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我們可以說,女媧治理地震等災害是中華民族通過有組織的、自覺的人類活動抗御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與恢復自然界的正常秩序的第一次,它是治理自然災害的開端。女媧以后的時代,每一位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或者是政治領袖,都不約而同地把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維護當作最為重要的政治事務,并通過運用社會組織與權力結構的各個環節和層面,來維護人類與自然的和諧。
二、后羿射日: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杰出事件
“后羿射日”,是原始先民追求穩定的生態秩序與社會秩序而治理干旱自然災害的一次杰出的政治事件,它與“嫦娥奔月”神話相結合,一個氣勢恢弘,一個精巧奇妙,恰似兩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奇異而迷人的中國神話天空。其中,射日神話的主人公后羿,雖然不是“公共事務”的最高管理者和部落首領,但卻因其戰勝自然災害成就了堯的“天子”偉業,而堯時代亦成為了中國古代政治清明與生態和諧的典范之一,數千年來為中國后人所頂禮膜拜與競相效仿。
堯時期,中國進入銅石并用的時代,銅器在當時的生活中占據一定的地位,生產力、生產技術得以長足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中原及周邊地區逐漸進入一個較原始氏族部落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實現著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過渡。同時,這一時期自然災害十分突出,先后發生干旱、洪水等大災害。據《淮南子·本經篇》記載:“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禊輸、鑿齒、九嬰、大風、封稀、修蛇皆為民害。”[4](P213)即是說,十個太陽同時出現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把禾苗曬干枯了,大地上斷絕了可吃的東西,狽輸、鑿齒、九嬰、大風、封稀、修蛇這些兇禽猛獸都紛紛從火焰似的森林和沸湯般的江湖中跑出來,傷害人民。如此嚴重的干旱災害,讓當時的政治首領、“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堯陷入了深深的憂愁和煩惱之中,他日夜向天帝祈禱,終于感動了天帝帝俊,他派了一名叫后弈的天神來到人間,幫助堯治理干旱等災害。于是,“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兇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輸,斷修蛇于洞庭,禽封稀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徹底平息了因干旱引發的各種自然災害,老百姓從此安居樂業,沉浸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喜悅之中。而當時“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堯因為派遣后弈射日有功,被人民尊為“天子”;后弈則成為受人民擁戴的神話英雄。
與治理自然災害恢復生態秩序如影相隨的是堯時期社會生活的重大變化。堯前后,各地的人群組織在內部的分配制度和地位分化上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已有私有制度,社會日益分化成多個等級,權勢顯貴階層產生,并且出現了擁有軍、政、財、神權于一身的最高首領。以前研究中國史前文明的學者通常把堯、舜、禹時代的社會組織稱為“部落聯盟”,而近年來隨著“早期國家”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通過研究把這一時期稱之為“部落國家”,或“部落聯合體”,或“酋邦”。本文認為使用“酋邦”這一概念更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況。堯舜禹時期,我國黃淮江漢廣大先進地區,已是一派酋邦林立的局面,文獻或稱之為“天下萬邦”。酋邦內部仍然維持了血緣親屬關系的社會架構,酋長依憑著與酋邦共同祖先最近的血緣關系享有無可爭議的權威,以下有貴族組成行政管理機構。而酋邦外部,同時又按照地區,根據他們的血緣聯系或姻親關系而結成酋邦聯盟或酋邦聯合體。[6](P242)酋邦聯盟的首領即所謂的共主。堯、舜、禹原本都是自己酋邦的首領,他們又都曾分別擔任這個酋邦聯盟的“共主”,但這個職位并不是世襲的,還要在各個酋邦之間流轉,因此,堯、舜、禹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以“公仆”的身份來協調處理共同體的重大事務,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禪讓制”。但是,此時的酋邦聯盟的權力還處于游移狀態,尚未形成一種具有強制性的凌駕于各個酋邦之上的固定的特權。
從后羿射日神話來看,堯委任羿治理干旱自然災害,主要是對酋邦內部事務的治理,而非以“共主”的身份協調酋邦聯盟之間的共同利益,而是在治理干旱自然災害后,才因“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取得“共主”的地位。在這里,人類社會對自然生態的自覺調整,再次成為了推動自身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使得人類社會邁入到酋邦聯盟的新階段。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推斷,正是由于堯酋邦率先取得治理干旱自然災害的成功,隨之在有血緣關系或姻親關系的其他酋邦推而廣之,所以才被酋邦聯盟推選為“共主”,也就是文獻所記載的“置堯以為天子”,而堯“共主”地位的確立,也最終使中國歷史進入酋邦聯盟時代(即傳統所說的“禪讓”時代),開始由原始社會向國家形式過渡。由是,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過程中,自然生態的修復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幾乎是同時與相互促進的,也就是說,通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最終實現了“人與人”關系的突破,在中國文明的發軔與發展的每一個腳步中,都鑲嵌著人與自然關系的深深烙印。
人類歷史的進步不在于感性的滿足,而在于理性的前行,這種理性的前行就是人類共同的生活原則。中國文明在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這一核心問題的形塑與規定之下,它的社會組織的發展與政治生活的起步都是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后羿射日神話,延續了女媧神話中維護人與自然和諧,從而保證農業生產和定居生活所需,最終推動人類文明繼承這一主題,并在其組織性、協調性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如果說,女媧補天,主要依靠政治首領親力親為而治理自然災害維護生態穩定的話;那么后羿射日,則主要依靠的是政治首領堯勤政愛民的政治價值情懷與知人善用的政治組織能力。在整個神話中,堯并沒有走在治災的前列,但他卻能夠選用善射的后羿完成干旱治理,最終成就“天子”之業,可見,當時“公共管理”的職能已經逐漸完善和有了相當的發展,這是人類政治發展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與進步。在此基礎上,國家、政治、法律、宗教、哲學、道德逐漸啟蒙與形成。此時,處于酋邦聯盟時期的中國正從無階級社會向階級社會邁進。
三、大禹治水: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最高典范
“大禹治水”,是原始社會后期最高領導層為治理自然災害的一次成功典范,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甚至一貫嚴肅的史書對此亦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大禹治水的功績后果,不單單是解除了洪水泛濫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的自然災難,更為重要的是它引發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把原始社會的酋邦聯盟制度推到了頂峰,從而為文明的發展及國家的出現創造了必備的條件。而大禹以后的中國歷代統治者,都以其治水的成功經驗作為治國典范與學習摹本,“善治國者必善治水”話語流傳至今,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堯舜時期,一度洪水泛濫、民不聊生,眾多酋邦在黃河中游集中、融合,引發矛盾和沖突,因此治理水災成為堯舜酋邦聯盟所面臨的最為緊迫的重大問題。夏的建立者夏后氏(或稱作有崇氏),原本是堯舜禹族酋邦聯盟中的一個邦,居住在占河濟之間,由于善于治水,它的首領鯀和禹先后被推舉出來領導酋邦聯盟治理洪水的工作。根據文獻的記載,堯派鯀治理洪水,鯀治水九年不成,堯禪位于舜,舜殛鯀于羽山,任用鯀的兒子禹繼續治水。于是,禹被任命為“平水土”的“司空”和總攝聯盟各項具體事務的“百揆”負責治理水患災害。“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4](P54),就是說,禹疏開渠排水、疏通河道的時候叫應龍走在前面,拿它的尾巴畫地,應龍尾巴指引的地方,禹所開鑿的河川道路就跟著它走,一直流向了東方的汪洋大海,成就了我們今天的大江大河。為把洪水引到大海中,禹還和老百姓一起勞動,戴著箬帽,拿著鍬子,帶頭挖土、挑土,以至于“排無朧,脛無毛”,小腿上的毛磨光了,腳指甲也磨掉了,“故行踱也”,得了足病,成了跋子。為了徹底治理水患的自然災害,禹還十分重視以興修水利為目的的溝、渠、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并發展了灌溉、農耕等技術。
水患,這樣重大的自然災害,直接關系到各酋邦基本生存與重大利益,因此,治理水災,是一項關系到各酋邦共同的公共事業。鯀、禹起初的角色都屬于“公仆”的性質,但是由于這項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全局性,需要組織各酋邦的廣泛參與,并對各酋邦的人力、物力進行調配、指揮和統一管理。在這個過程中,禹(包括他的父親鯀)難免利用聯盟賦予自己的職責與權力對各酋邦施加更多的影響,甚或強制和干預。治水過程中,大禹請來后櫻、皋陶、伯益等有名望的酋邦首領“合諸候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共商治水大計;政治上,團結酋邦作為自己的“股朧心替”,建立治水機構;組織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酋邦分布的地域調劑勞力;經濟上,“單平水土以品庶類”,按權力高下分配治水的勝利果實。這樣,使原本比較松散而缺乏約束力的酋邦聯盟的管理機構發生權力集中的傾向,并使之逐漸凌駕于眾酋邦之上。禹死后,其子奪得權力,通過武力控制局勢,變聯盟為世襲王朝,我國古代第一個王朝——夏代國家產生。也就是說,這次對自然生態秩序的維護,最終使中華文明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人類社會的面貌由此改寫。
長期以來,對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問題進行研究的指導理論,主要來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恩格斯在該書中指出,地緣關系代替血緣關系是國家區別于前國家社會的一個特點。但在中國國家起源發軔的階段,血緣關系沒有被地緣關系所取代。我們認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雖然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國家起源問題研究的代表之作,但實際上它只談到了西歐國家起源的途徑,即“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興起”的國家的起源。但事實上,國家的起源還存在著另一種途徑。恩格斯就曾在《反杜林論》中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古代的公社,在它繼續存在的地方,在數千年中曾經是從印度到俄國的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于利用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是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7](P524)這里,恩格斯指出,國家是在兩種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公社“繼續存在”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是印度、俄國那樣的“東方專制制度”的國家;而在“公社瓦解”的歷史條件下,則出現希臘、羅馬那樣的奴隸制共和國。為什么“東方專制制度”的國家原始公社沒有瓦解,也會出現國家的起源呢?恩格斯認為,在原始公社“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在中國,恩格斯所提及的這種“共同利益”當時主要表現為治理自然災害來保障農業生產的需要,也就是通過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維護人與人之間共同利益的內在所需。但是,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長,公社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密切,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及“相抵觸的利益”,這就需要“建立新的機構來保護共同利益和反對相抵觸的利益”。隨著世襲制的出現,這種執行“社會職能”的機關,對社會越來越“獨立化”,最終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的主人”,形成國家[7](P522)。西歐以外地區的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正是通過這種途徑產生的。
這種國家形成的途徑,與《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所說的“公共權力”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共同職能”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會有所側重,國家產生的原因也就有所不同:在某些地區,戰爭是生死攸關的問題;而在另一些地區,農業灌溉問題卻更為突出;可在別的一些地區,則可能是宗教原因;而在希臘和羅馬,社會分裂則為對立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緩和階級沖突便成了它們推動國家形成的根本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中國在治理洪水自然災害的過程中,階級分化并不十分嚴重,血緣關系也沒有被地緣關系所取代,但因治災及隨之而來的水利灌溉則需要建立一整套管理公共設施的機構,這一機構為未來國家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成為未來國家政權的雛形,從而使中國走到了國家的邊緣。
四、結 語
通過對以上三則具有典型意義的上古神話的分析與解讀,我們發現,“人與自然”關系的修復與和諧,最終推動“人與人”的關系的發展與突破,最終促進了中國國家的形成。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其實就是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過程,是“人與自然”關系在地理、時間和空間的三維合一的進程。在這種文明范式的影響之下,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治理自然災害與維護政治統治的關系。正如管子所說:“善為國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為大。”這里面蘊涵著深刻的辯證法。
著名的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曾提出,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原創國家文明中,處于西方文明區系的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毀滅,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區系的國家文明卻延續不斷。主要原因還在于兩種文明中國家起源的模式有根本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起源模式是連續性的,其先民在邁向國家社會時,是以自然與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過程,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而以蘇美爾文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起源模式是突破性的,很大程度上造成一種人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隔閡乃至對立。這種突破性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觀和價值觀上營造出人類高于自然的假象,并造成人和自然關系的緊張,進而引發生態危機。于是,古巴比倫文明、腓尼基文明、瑪雅文明、撒哈拉文明等,一個個隨著人類早期農業對土地的不合理的利用,以及各種各樣的生態學的原因最終消亡了,原來充滿綠色誘惑的土地變成了黃色的茫茫大漠。
由是觀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必須依靠生態環境的養育和支撐,只有人與自然協同演化,人類創造的文明之樹才能常青并不斷發展。但是,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的發展與自然的發展又不是完全同步的,當今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與生態危機再次威脅著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在神話與歷史的生態軌跡中尋找養分和智慧源泉,通過對自然環境的自覺調整與修復,使得生態環境朝著有利于人類文明進化的方向變化和發展。這樣,人類與自然將結成一種和諧的伙伴關系,也就是說,人類會成為大地的看護者和生態秩序的自覺維護者,在圓融互通的美善生活與文明的延續中協進演化,展現出各自的價值世界與意義空間。
[1]葉秀山.思·史·詩——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呂振羽.史前中國社會研究[M].北京:三聯出版社,1988.
[3]郭洙若.中國史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袁 珂.中國古代神話[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5]李培超.環境倫理學本士化的重要視點:傳統文化與環境倫理學的沖突[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24-25.
[6]沈長云,張渭蓮.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校:文 心)
Harmonious 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The Mysterious Observation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ulture
KANG Qiong1,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Ethic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2.Public Management College,Hunan Commercial Institute,Changsha,Hunan 410000,China)
The myth of“Nüwa Fixing up Sky”,“The Archer and the Suns”and“Flood Controlling by Dayu”,the well-known myth in China,to some extent,have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Through reading and analyzing these myth,we find that the origin and forming of Chinese evolution,no matter on the economic level of the relation of“Human Beings and Nature”,or on the political level of“Human Beings and Human Beings”,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rmonious 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So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is just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eings and nature.Only by the concerted evolu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and the nature can the thousand of years’civilization keep on flourishing.
human beings and nature;myth;the origin of the civilization;the origin of the country
K21
A
1000-2529(2011)03-0106-05
2011-01-20
第47批國家博士后基金項目“探求人與自然的原初秩序”(20100471222);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探求人與自然的原初秩序”(10YJA720015)
康 瓊(1971-),女,湖南長沙人,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湖南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