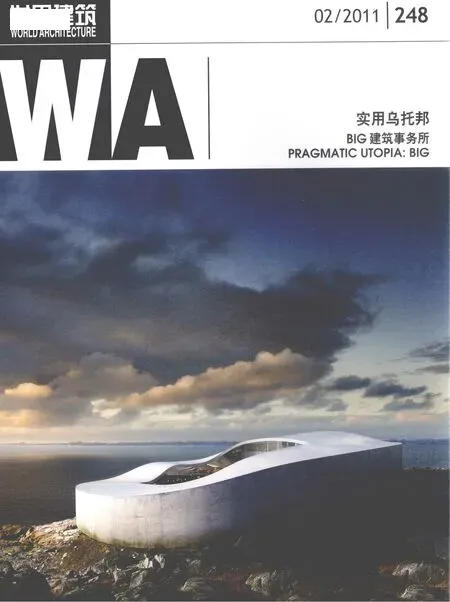“建筑是凝固的音樂(lè)”探源——提法及實(shí)踐
張宇,王其亨/ZHANG Yu, WANG Qiheng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lè)”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囊痪湓挘谜咄⒉徽嬲私馄鋪?lái)龍去脈,濫用誤用不時(shí)出現(xiàn)。若離開(kāi)了其闡發(fā)背景,這一比喻也就成了無(wú)本之木,無(wú)源之水。為此有必要從3方面厘清:
1.這句比喻由誰(shuí)提出?反映了怎樣的思想背景?
2.它背后有什么傳統(tǒng)思維源流?
3.歷史上的建筑實(shí)踐是怎樣照應(yīng)這一比喻的?
一、比喻的提出及衍化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lè)”這一說(shuō)法風(fēng)行于19世紀(jì)的歐洲,即便在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于是誰(shuí)是這句比喻的提出者就已不甚了了。這里依據(jù)國(guó)外近年的研究成果[1]及相關(guān)資料,歸納出“凝固”比喻最廣為傳布的幾個(gè)版本,并廓清它們各自的誕生背景。
1. 一般說(shuō)來(lái),建筑是凝固的音樂(lè)。
—德國(guó)哲學(xué)家謝林,《藝術(shù)哲學(xué)》[2](1859)
《藝術(shù)哲學(xué)》一書(shū)系依據(jù)謝林(Schelling,圖1)生前講稿整理而成,其中主要是謝林1802年冬-1803年在耶拿的講學(xué)內(nèi)容。書(shū)中不止一次出現(xiàn)“凝固的音樂(lè)”比喻,其背后有清晰思維脈絡(luò)可循。此外,英國(guó)人羅賓遜曾到耶拿聽(tīng)謝林講學(xué),其日記(1869)里寫(xiě)到“謝林講其‘方法論’時(shí),稱建筑為‘凝凍的音樂(lè)’”,[1]可作為謝林當(dāng)時(shí)提出此比喻的旁證。
2. 弗·施萊格爾曾將建筑稱為凝凍的音樂(lè);實(shí)際上,兩種藝術(shù)基于歸結(jié)于數(shù)之種種比例關(guān)系的和諧,因而易為理性從根本上予以把握。
—德國(guó)哲學(xué)家黑格爾,《美學(xué)》[3](1835-1838)
德國(guó)詩(shī)人弗·施萊格爾(F. Schlegel,圖2)曾與謝林在耶拿共事,其著作中曾稱“建筑是音樂(lè)般的造型藝術(shù)”,又喻哥特式教堂為“石化的音樂(lè)”;但“凝凍的音樂(lè)”似乎停留在口頭說(shuō)法,只見(jiàn)載于黑格爾及同時(shí)代多人的文字轉(zhuǎn)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