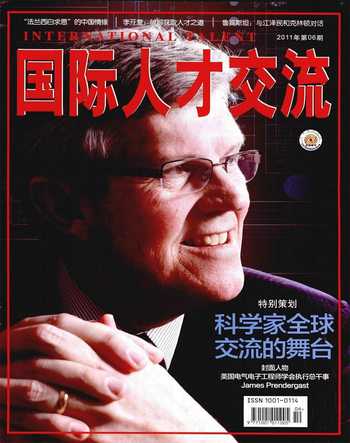姐姐的時間掛在墻上,弟弟的時間懸在海外
郭生祥
1911年的時候皇上被打倒了,1949年之后家長制被作為封建禮教取消了。今天,既有市場,又有習俗,還有權力與計劃的影子,農民如何面對這些環境,如何選擇自己的標準,的確是困惑著的。
今天拿什么來維護鄉村
我是中國農民的兒子。
可能很多人說,我們也都是。對于中國城市里的人,大都不過三代前就是農民。這說明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其實早不過三代前。
但是我說我是中國農民的兒子,更多是從學術視角而言的,也就是我的學術占位是以農民利益為視角的。要做到這點并不容易。一是始終保持感情上傾向這樣,當然也還要具有理性,二是還需要具備清醒的學術能力和自覺。我是不是這樣做到了。不敢說。
至少我是堅持這樣的,努力這樣的。
首先從情感上,除了了解農民的優點外,我更知道農民的缺點,農民分散、樸實,其實這是農民在自然環境、政治環境下的一種表現,并不完全就是農民的本質。今天的農民由于受到現代商業氣息感染相對較少,一定程度地保留著傳統習俗,以及1949~1979年時候、或者是1979~1989~1999年時候的部分習俗,因此,或多或少較之城市里更多一些誠信和質樸,更多一些勤勞與寬容,更多一些合作與友愛,我不知道這個較之城市化商業化落后不止10年的農村,隨著自身的商業化起來,會不會改變?
這種擔心好在孔子說過,“禮失求諸于野。”這說明不趕時髦的鄉野從來都是傳統保持的最好容器。
但近來我倒是觀察到城郊農村人格分裂的陣痛,這里晚上似乎保留了一點傳統的習俗,白天卻有著比城市里更嚴重的紛亂,也許他們認為自己比城市弱勢,他們夸張了城市的紛亂,因而自己模仿著的時候,就采取了過頭的策略,這也是一種博弈論。
但這不能說明農民的本能、本質。
我要說的是,習俗是根,良善是傳統,但是維護這公序良俗最后的保障是什么呢?今天又如何變化的呢?也就是農民之間是如何尋找自己的公平和正義的呢?過去是依靠家庭的父親來主持正義,家之外就希望清官主持正義,最高是皇恩浩蕩,主持最后的正義。
1911年的時候皇上被打倒了1949年之后家長制被作為封建禮教取消了。今天他們既有市場,又有習俗,還有權力與計劃的影子,他們如何面對這些環境,如何選擇自己的標準,的確是困惑著的。
所有這些混沌能否給今天的農民尋找到良善與可依靠的習慣、風俗、禮教、政治呢?如何能夠協助他們建立起基本的公平和正義呢?
姐姐的時間掛在墻上
我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離刑、村的。20多年后,我回到我的家鄉,路還是那條泥濘路,小道旁邊還是那些舊房子,時間在這里望去似乎是凝固的,但是田野依然是那么生機勃勃,如果3月下田甄鮮花和綠葉,同樣鮮活得讓你不知道時間。
其實在我腦海里,時間一邊是掛在墻上,一邊是生長在田野里的,所以我說我姐姐是鮮活在時間靜止中的姐姐。
相對于我的姐姐來說,盡管我們是同胞姐弟,童年生長在同一個鄉村,但是今天的我似乎趕在時間的前面,我不但在80年代中期就跨越了農門,而且在80年代末期趕上了出國。
我的時間似乎走在姐姐的時間前面。
但是我的情感卻還在姐姐與我的童年時代。人是感情的動物,血緣關系的情感今天至少還是沒有多少污染,還是具有高度的歷史積淀,給人類一絲溫暖和指引。
姐姐只讀過兩年書,出嫁前上小學4、5年級兩年。那時候我們那一代的農村女孩子在出嫁前,象征性地給念兩年書,然后就準備出嫁。我姐姐就是這樣。之前的女孩子是不是有這個福氣我不知道。大約是沒有的。我記得姐姐上學的時候,年紀顯然是大了點,當然村里還有其他類似的女孩,也是姐姐平時種田的伙伴,她們似乎比姐姐高、大些。
在我的記憶里,姐婦一直顯得并不大,而且單薄。
姐姐是我上面的一個,她只得帶我到學校去,這是農村的習慣,大帶小,再承包家里的洗衣煮飯喂豬。當時農村孩子們大都這樣,一邊上學,一邊干家務
我跟著姐姐,先是躲在課桌底下,后來也跟著學習起來。
偶爾我也跟姐姐們跳繩、踢踢皮球,偶爾也不去教室,姐姐們上課了我跟別的小孩在外面玩。
記得最真實的一個場景就是1976年9月9目之后緊接著的一天,記得那時農村已經比較冷了'地上似乎結了一層薄薄的霜,但是我舍不得把姐姐為我新做的鞋子穿上。那時小學教室里有為毛主席布置的靈堂,窗子四周用黑布蒙著,松柏樹做的花圈豎立在教室中央,毛主席的標準像安放在花圈中間。似乎點了什么燈?要不然黑咕隆咚怎么看到主席的遺像呢?
全村男女老少都成群結隊地排成長隊從教室一個門進去,另一個門出來,然后是穿過田間游行,我跟著姐姐,提著鞋子。在我準備進靈堂的時候,記得有大人過來要我穿上鞋子,我進去的時候穿上了,但在田野游行的時候,我又脫下來,提在手上。
還記得不久之后,為慶祝打倒“四人幫”,我寫的“鐵拳痛打‘四人幫…在全大隊開會的時候,上主席臺念。這是我記憶中最早的作文。
后來父母笑話我,說我上臺也不緊張,叉開兩條腿,雙手胳膊拐在桌子上,眼睛盯著念,但是卻不知道下面是破襠,據說有人笑,但是我當時是不知道的。
這就是我最早的上學記憶。
今天回想起來,我有時候覺得那么復雜的文明,居然在我那個落后偏僻的村子里可以傳承,我還可以從那里走出來,上大學,成為今天所謂的跨國人才。我不知道今天叫我回去,去村里代課,能否帶出一個大學生來?
從這個角度,從我內心深處,我敬仰我的那個小村,敬仰那里的父老鄉親,一個離文明那么遙遠的鄉村,居然還有可能培養一個鏈接世界的學生。
這么跨度的歷史,讓我在眾多的感激之中,當然最感激我的姐姐。
姐姐盡管上了兩年學,但是即使在這兩年,她還負責家里9口人一年一雙的鞋子,納鞋底、做鞋樣,一針一線。姐姐的小手那時經常被針剌破,每當流血的時候,我是最不敢看的,至今都怕看到血,可能這是小時候留下的記憶。
記得我做完作業后,姐姐還在煤油燈下納鞋底,我確實不知道姐姐什么時候睡下的,但是我知道姐姐辛苦,她第二天還要與我一塊兒上學。
記得不久我就比姐姐念的年級高了。
小時候盡管不懂事,但是我也是不敢驕傲的,因為我知道姐姐的辛勞。
每當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我都不敢寫下去,眼淚每次都打濕我的面頰,我不知道姐姐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人的一生無非是過眼云煙,但是這人世間的姐弟情卻是永恒的。
我常常這么想。
記得村子里,很早就說我很乖,很聰明,其實在我內心,并不覺得自己聰明,這都是姐姐納鞋底納出來的。
姐姐比我大不了幾歲,卻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生。
對比起來我是有愧的。
姐姐很快念完了兩年,就又去栽秧割谷、積肥做家務去了。
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冬天冰封雪凍的,姐姐要與上面兩個哥哥、父母上水利,開挖溝渠,在軟軟的沼澤
地里,小小的個子,像大人一樣挑擔子,踩在軟軟的泥土上,水與泥一直陷到膝蓋,走路都是難的,還要挑擔子。小時候我體驗過,幾乎全身都翻滾在泥里,我想我小小的姐姐,是如何從那里走過來的呢?而且一直在那里走著?
每當我回憶兒時的記憶,總揮不去上面兩個形象,一個是主席,一個是我姐姐,這么天差地遠的鏈接,可能在我心深處,我想無論怎么樣,要改變命運,其實就是要改變公平和正義。
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念想。
這是我研究追趕型經濟學之所以得出要矯正的辦法,首要的機制就是平權、確權、維權,其次才是外生的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排在后面的才是反哺機制和救濟機制。
姐姐出嫁的時候,我還在上學,我不知道姐姐的婚禮是如何辦的。
因為高考在身,容不得分心參加婚禮。
但在我的記憶里,出嫁后的姐姐塞了我不少次錢,每次都似乎是偷偷的,而且是不容分說的,我知道姐姐的錢得來不易。
但是我從來不敢問。
那時姐夫家在農村公路旁邊打鐵,是80年代最早的萬元戶,姐夫家鄉比我的家鄉離城市近些,那時我以為離城市近一些,就富一些。
但是不久姐姐因為生的不是男孩,就不斷地超生,還把一女孩送了人。
后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知道姐姐的心里肯定是難受的。
90年代初期,我從國外回國幾次,想在家鄉兼職做點事,那時其他兄弟姊妹還小,下面3個盡管都已經輟學種田了,我還是把他們從田間拉出來,一個個都上了大學,然而卻沒有考慮幫姐姐—下,因為姐姐早已嫁人,還有了自己的家,下面小弟小妹前途要緊,于是忍痛沒有顧及姐姐。
2000年之后,姐姐到武漢來,她自己在街上擦皮鞋,一次我看到她逃城管的人,提著皮鞋箱到處奔跑,姐姐看到我,也還跑,他可能知道弟弟其實也幫不上忙。
那一刻在我心里特別特別地痛。
我知道自己沒有本事,我知道所有像我一樣上了大學的朋友,其實在城里早忘記了自己的父母姐妹兄弟,因為今天許多的政策就是他們制定的。
有一次我去印度,我看到五星級酒店外,依然有乞丐,大家都相安無事,我想什么時候,那些由姐姐妹妹父母兄弟供養上了大學的人,再不制定驅趕自己姐姐的政策該是多好呀。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說夢話,但是我是真心地這么想。
對于這些,我實在是無能為力,所以躲在老遠老遠的國外,辛苦地學習、辛苦地養家糊口,為的是將來如果有出息,能夠建議我們的政府在城市里,即使為了市容,也不驅趕他們,比如可以考慮為他們留下一個小小的攤子?
為他們的勞作遮點風、避點雨。就像當初他們用同樣小的肩膀為我們遮風避雨一樣。
我繼續留在國外,為的是不斷地用功,看能否做一點學問,比如什么東方經濟學,研究如何改變類似我姐姐那樣的命運,看能否獲得一個什么大獎,讓自己的學說出點名,讓更多人被感召。
其實除了這個辦法,我的確是毫無辦法。弟弟的時間懸在海外
2010年的時候,姐姐的大女兒結婚,—對新人在婚禮上,在雙方親朋好友的見證下,非常熱鬧,幸福得完滿。
在一個大酒店里,宴席不無排場,姐姐分外驕傲,女兒女婿都在武漢過起了城市的生活。
講臺上,他們落落大方,講話得體,坐中姐姐姐夫喜不自禁。
‘
我在為姐姐高興的時候,卻掉下了最多的眼淚,似乎只有我知道姐姐的故事,知道她的喜怒哀樂,我知道姐姐走到今天的城市為自己的女兒結婚,那是多么遙遠的路,那是多么的不簡單。
但是我看著姐姐對過去似乎毫不牽掛,只感覺著眼前的幸福,于是我也為姐姐深深地感到了幸福。
或許痛苦和幸福,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之吧?
但愿姐姐永遠只感知幸福,而不感知不幸福。
這是小弟的心愿。
顯然這是多么的唯心,但是我只能這么唯心。
而我除了繼續努力,企圖把信用、價值、貨幣、精算、知識產權、銀發經濟學等研究到感動上蒼,讓天下人都知道這么個學問,然后齊心協力去改變它以外,別無他法。
我知道自己不能如宗教家們那樣給姐姐一顆感知幸福的心,也知道自己不是老板,不能通過外生的投資來改變他們的命運,更不是政治家可以通過解放政策,讓農民們擁有內生的談判能力,以及更加艱苦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只有希望自己學習、研究,再學習、研究,無論地老天荒,與孤燈為伴。
都說四十不惑,我已經走過了一個四十,接下來還會再走一個四十,甚或更多,也許沒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自己的將來,我對自己的將來沒有擁有任何勝算的概率,這一點與我姐姐一樣,祈禱似乎是唯一的。
外國政府官員來華取經
5月10日,由中國商務部舉辦,國家外國專家局承辦,國家外國專家局培訓中心具體負責實施的援外人力資源開發合作項目——“發展中國家智力引進官員研修班”在北京開班。此次研修班是國家外國專家局為發展中國家舉辦的第八屆智力引進官員研修班。共有來自巴基斯坦、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埃塞俄比亞、哥斯達黎加、萊索托、贊比亞、肯尼亞、烏干達、智利、加納、委內瑞拉、馬拉維和巴勒斯坦等15個國家的25位學員參加研修,他們均任職于所在國的外交部、貿易部、經濟部等部門。我國30多年來的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國家外國專家局希望通過開辦“發展中國家智力引進官員研修班”形式,與發展中國家智力引進部門共享引進國外智力經驗。(國家外國專家局培訓中心供稿)
外國專家看四川
中國外文局組團重訪災區
5月15曰,由中國外文局局長周明偉、副局長陸彩榮帶領的‘沖國外文局汶川地震3周年對外報道采訪團”抵達四川成都。采訪團一行24人抵達四川成都后馬不停蹄地與新華社四川分社、四川衛視及四川新聞網的代表進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座談,地方負責人分別就各自汶川地震3周年的新聞報道工作進行了總結,與外國專家分享了各自的采訪、報道經驗。據了解,中國外文局采訪團由來自美、法、西、日、俄等國的5位外國專家及《人民畫報》社、《今日中國》社、《人民中國》、《中國與非洲》雜志、《北京周報》社、《中國報道》社、《對外傳播》雜志及中國網等相關單位的領導、記者共計24人組成。活動發揮了中國外文局在多語種對外宣工作中的優勢,是外文局外宣工作中一次大膽的嘗試。(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