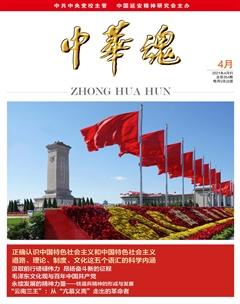祝福獻給偉大的黨
2021-05-04 08:47:37薛鑫良
中華魂 2021年4期
薛鑫良
寫首新詩訴衷情,
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孕育了我的身,
黨和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
從1921年到2021年,
從上海的石庫門到北京的新華門,
從嘉興的南湖水到首都的中南海,
從小紅船到大航母,
從地下黨到執政黨,
從五十多人到九千多萬——
百年黨史,百年滄桑,
百折不撓,百煉成鋼。
二
你是燈塔,
驅散著九天四洋的霧瘴;
你是舵手,
掌握著民族復興的方向。
在救亡圖存的硝煙中,
赴湯蹈火,愈戰愈強。
在“進京趕考”的征途上,
攻堅克難,又創輝煌。
三
共產黨人永不離崗退崗,
在黨、愛黨、憂黨、興黨。
常懷憂黨之心,憂黨為了興黨;
恪盡興黨之責,興黨先要憂黨。
繼往開來,敢于擔當,
分清敵友,亮劍斗狼,
守正創新,補短揚長,
固本培元,擁抱又一輪朝陽。
紅色基因世代傳承,
人民江山地久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