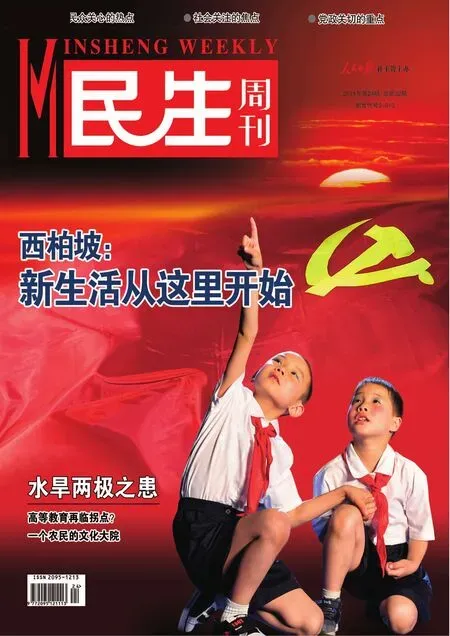大旱“烤”驗之后
□ 本刊記者 趙志偉
大旱“烤”驗之后
□ 本刊記者 趙志偉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來說,這段時間就是最好的注解。
6月3日前后,旱災“烤”驗中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隨著持續多天的降雨,在極大緩解旱情的同時,又因局部強暴雨而引發洪澇災害。
據中央氣象臺6月5日消息,目前,湖北東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大部等地降雨偏少的狀況得到不同程度緩和。不過,強降雨在緩解旱情的同時,也讓江西、湖南部分地區出現罕見的旱澇急轉現象,防汛形勢嚴峻。
“大旱之后,可能會有大澇。”記者在此次遭遇旱災比較嚴重的“千湖之省”湖北各地走訪時,當地不少黨政領導、專家學者以及普通百姓均表示過這種擔憂。
據湖北省氣象局武漢區域氣候中心6月5日通報,6月4日,江漢平原南部和鄂東南出現大到暴雨,其中咸寧、嘉魚、黃石、大冶、陽新、黃梅等6縣市出現大暴雨。降雨使鄂東南大部、江漢平原南部旱情得到明顯緩解。
盡管旱情有所緩解,但仍不能忽視,并且,干旱導致的旱災,給這個“千湖之省”乃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帶來的后遺癥影響依舊,“好了傷疤”不能“忘了疼”。
干旱導致的旱災,給這個“千湖之省”乃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帶來的后遺癥影響依舊,“好了傷疤”不能“忘了疼”。
干旱下的漁民生活
今年63歲的張欽明夫婦,住在洪湖里以捕魚為生,靠湖吃飯。盡管5月31日剛剛下過一場中小雨,但于洪湖無補。6月1日上午,老夫妻倆終于熬不住,駕駛著小船,奔岸邊來了。
岸邊上,張欽明兩只手不住地從船里向岸上搬著鋪蓋卷、漁網等雜七雜八的物件,時而抬頭望向先他上岸的老伴,嘴里嘀咕著什么。
老伴上岸時,手里提著一個漁網狀的大袋子,里面是她喂養的老母雞和十余只幼雛,隨手往地上一倒,轉身掏出鑰匙,慢吞吞地去打開灰撲撲的家,顯然很久沒有收拾了。
對于老頭子的吆喝,她并不著急,步伐的緩慢,緊連著的是心情的沉重。
“干旱對漁民的生活影響最大了。”在湖北省洪湖市內做土特產買賣的謝女士,說起今年的大旱對洪湖漁民而言可謂是大災,“投進去的錢全沒了。”
堅守湖里的漁民越來越少。漁民們上岸后被政府安置,每人每天領著10元補助,艱難度日。湖北省洪湖市螺口鎮的“漁業新村”,就是政府為居住在洪湖上的漁民提供的臨時安置點。
安置點里,三四家合用一個灶。政府工作人員送來一批土豆和皮蛋,漁民們再去街上買點咸菜。
據報道,包括湖北省在內的此次長江中下游地區大旱,除了造成部分漁民生計比較困難之外,還沒有發生嚴重的城鄉居民以及牲畜飲水困難。“局部地區飲水困難,主要發生在山區。”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防洪調度處調研員江炎生說。
農業損失有限可控
“湖北現在被旱情折磨慘了。旱情搞得中稻都推遲插秧了。”5月30日,家住湖北省荊州市,在當地電視臺擔任導播工作的小黃通過網上聊天對記者說,“去年大澇,武漢江堤水漫得好高。今年你再看,跟黃河一樣缺水。”
地處北方的黃河流域缺水少雨,在像小黃一樣的南方人心中,十年九旱,河流水位偏低甚至干涸斷流,都是家常便飯,并不奇怪。然而,這一次,是素有“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以及“水鄉澤國”之稱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缺水,去冬今春以來,居然持續200多天的干旱,“建國以來,從來也沒有遇到過。”記者采訪所到之處,都這樣不約而同地說。
6月4日,記者離開湖北時看到,江漢平原一帶的大量農田已經中稻插秧完成,部分農田改種旱作物。在湖北,“水還是有的,抗旱基礎條件有。”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防洪調度處調研員江炎生說,“損失在有限可控的狀態。”
事實上,湖北并不像黃河流域那樣真的缺水,“無水可取”只是相對而言,不是絕對沒有水源,雖然湖北歷史上也曾多次發生旱災。
“自秦至1949年,有史記載,共發生旱災214次(此統計數未計入年受災在5縣以下的干旱年),頻次約為10年一遇。”湖北省水利廳、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編著的《湖北抗旱指導手冊》稱,湖北歷史上就存在四季都可能出現旱災的情況。
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以來,1952年、1960年、1961年、1966年、1972年、1981年、1992年均為大旱年;1959年、1978年、1988年、2000年、2001年為特大干旱年。大旱和特大干旱平均約4年1次。湖北省易澇易旱的特點十分突出,常常是南澇北旱,先澇后旱,或先旱后澇,既有局部干旱,又有全省性的干旱。
“統計分析認為,一定規模的洪水會發生,同樣一定規模的旱災也會發生。”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副巡視員王井泉說。水產養殖沖擊明顯

6月1日上午,烈日下,家住湖北洪湖邊的68歲楊新明老漢,絲毫沒有含飴弄孫的興趣,一個人背對著洪湖,坐在堤岸上自家簡易房子的外邊,孤零零地打著盹。他的背后,波光粼粼的湖面早已退成淺淺的湖灘,大小船只人去船空,灘邊的各種雜草以及腐尸,吸引大量蠅蟲嗡嗡作響,隨處亂飛。
由于干旱,楊老漢的兒女都已經棄船登岸,只留下他一個人不想離開這片生活了將近一輩子的湖面,默默地堅守者。“養殖的魚蝦都沒了,湖里也捕不到魚。”楊老漢睜開眼,有氣無力的說,“20多萬元,都完了。”
在整個洪湖地區,由于大旱而遭受損失的不止楊老漢一家。
據洪湖市水產局初步統計,該市水產養殖面積116.6萬畝,受災面積41.3萬畝,約占全部養殖面積的三分之一。截至5月21日,直接損失接近6億元,約占去年全年水產產值的六分之一。
湖北省洪湖市水產局局長曾令旗稱,水產養殖業是洪湖市的主導、特色、優勢產業,該市有10萬人以上從事水產養殖和漁業經營,有2萬人左右是以湖為家。顯而易見,大旱給當地水產養殖業造成了極其明顯的沖擊。“隨著近段時間旱情加劇,直接損失肯定會增加,另外還有一些損失無法統計。”曾令旗痛心地對記者說。
6月5日,來自農業部漁業局科技處的消息稱,湖北受災水產養殖面積365.87萬畝,損失成魚15.1萬噸、魚種4.75萬噸,少繁育苗種101億尾,總計經濟損失24.8億元。
與此同時,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由于幾大淡水湖泊同時干旱,直接威脅著淡水養殖業的發展。數據顯示,由于近期淡水魚供應減少,5月份以來全國淡水魚價格開始上漲,近期漲速明顯加快。
6月1日,記者在湖北省洪湖市內一家土特產品商店了解到,干旱導致今年的魚類等水產品干貨價格比去年同期普遍上漲20%左右。
目前,洪湖市水產局一面組織調度水源,一面呼吁漁民們保護好魚苗和種魚,以便來水后能迅速恢復生產。“如果連這些都沒了,再要恢復起來就會更加困難了。”曾令旗說。
“洪湖的生態基本恢復,至少需要5至10年的時間。人工輔助,最快也要5年左右。”

洪湖干旱給水產業帶來沉重打擊,經營洪湖土特產品的謝女士開始為未來的生計擔憂。圖/閔杰
生態環境難恢復
這一次來洪湖,長江科學院副院長陳進再也沒能吃到洪湖地區的風味小菜“油炸荷花”。干旱,不僅給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水產養殖業造成損失,更讓這里的湖泊濕地生態環境遭遇嚴重打擊。
地處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洪湖,是湖北第一大湖、也是中國第七大淡水湖。洪湖濕地的植被覆蓋率曾占80%左右,被譽為“中南之腎”。
如今,在湖北洪湖,昔日的“洪湖水,浪打浪”讓記者只有想象,沒有實證。金壇湖附近,記者目之所及,看不到一望無際的湖水,更不用說露出水面的大片紅荷綠葉。
在干旱導致的不少裸露的洪湖湖底,一腳踩下去鞋幫幾乎不粘泥。潛水植物大量死亡,對水環境具有很大破壞作用的外來物種“水花生”開始附土而生,到處繁殖,眾多魚蝦變成魚干、蝦干,“魚死、魚臭,對水環境都有影響。”當地官員介紹說。
據了解,此次大旱,洪湖濕地植被覆蓋率明顯減少30%左右。大量的魚類、水草等湖底生物群被破壞了,即便是洪湖里很快有水,生態環境也不能較快恢復,“洪湖的生態基本恢復,至少需要5至10年的時間。人工輔助,最快也要5年左右。”洪湖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辦公室主任曾曉東分析認為。
據報道,長江流域生活著4.7億居民,中國40%的經濟發展來源于該流域。同時,該區域是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地區,包括江豚、麋鹿等多種珍稀野生動植物生活在該區域的濕地生態系統中。截至6月1日,它們的生存也在遭到旱災的嚴重威脅。
在利益的天平上,人與自然生態,孰輕孰重?眼前利益重要還是長遠利益更重要?普通百姓甚至不少行外專家學者,未必真正理解生態學家保護湖泊、濕地等自然生態環境以及生物多樣性的特殊重要性。“關鍵是保護物種的基因,那是最重要的。”陳進說。
“沒有生態系統的民生是不會可持續的。”世界自然基金會(瑞士)北京代表處的項目實施副總監王利民博士對本刊記者表示。
□ 編輯 尹麗麗 □ 美編 王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