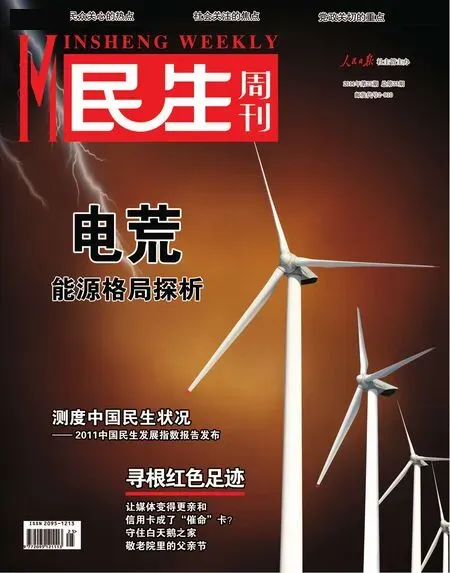古老昆曲在民間
□ 本刊記者 鄧凌源
古老昆曲在民間
□ 本刊記者 鄧凌源

北京陶然曲社的社員們在岳芃暉老師的指導下練習身段。圖/鄧凌源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曲調婉轉,笛音飛揚,古香古色的南京甘家大院里,昆曲愛好者們正在淺吟低唱。
這樣的場景并不罕見。在北京,在上海,在杭州,在廣州,在香港……昆曲愛好者們紛紛成立自己的曲社,他們隱身于公園的一隅,或聚會在深深巷落中,吟唱著古老的曲調,延續著千百年的民族文化藝術。
集體的努力
“2002年昆曲申請‘非遺’,2003年我們曲社就成立了。”作為北京陶然曲社的現任社長,張毓雯老師曾是北方昆曲劇院早期“北昆四旦”之一,退休后一直在陶然曲社教戲。當記者見到她時,這位66歲的老人正在排練廳里認真地指導一位女社員排演《昭君出塞》,盡管幾個月前下樓時不小心摔了一跤,腿腳還沒有好利索,但看到演員表演有欠缺,張老師還是忍不住站起身來親自示范。
“我自己就是從曲社啟蒙的,從11歲開始學戲,到現在已經55年了。”談起往事,張毓雯老師聲音宏亮,眉宇間顧盼生輝。
從業余曲社走向專業學習,從專業崗位退休后又回到業余曲社教學,張毓雯走了一個輪回,她頗有感觸地說:“我們陶然曲社雖然是業余學習昆曲,自娛自樂,但是經典的傳承太重要了,現在社里主要是我在做這個事情,從我退休時就開始了。我希望他們(社員)把我身上的東西傳承下去。”
張老師告訴記者,一般入社的曲社社員,都是沒有任何專業基礎的昆曲愛好者,有的連簡譜都看不懂。“但是他們從入社那天開始,就是我的學生,從識譜、唱曲到學身段,我都得一點一點地教給他們,只要他們肯學。”為了給社員們提供更好的教學條件,張老師甚至動員了自己唱京劇的老伴來到社里,給社友們講課,練習刀花、槍花。此外,張老師還請來了自己在中央戲曲學院的學生岳 暉,協助教學。
如今,陶然曲社已經擁有曲友一百多人,定期舉行社團活動,每年有四場匯報演出。2011年5月14日,陶然曲社折子戲專場在北方昆曲劇院大觀園戲樓開演,除了張毓雯老師的表演外,曲友們也粉墨登場,紛紛獻藝。入門不久的社員跑跑龍套,技藝高超的社友則演出自己的“拿手戲”。
“我本來就是曲社出身的,像這些事情就是要有人做,沒人做的話,這個東西不都完蛋了。”張老師談到,昆曲本來就起源于民間戲曲,如果失去民間的演員和觀眾,這門古老藝術的傳承也就如同束之高閣的古董了。
文化的傳承
作為張毓雯老師的母社,昆曲研習社是北京最早的昆曲愛好者研究和傳習昆曲藝術的業余文化團體,成立于1956年。當記者來到位于北京市文津街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臨瓊樓的臨時活動現場時,這里正在舉行“林燾、張琦翔先生九十誕辰”專題紀念會。據歐陽啟名社長介紹,二位已故老先生都為北京昆曲研習社的成員,在義務培養青年曲友、關注曲社發展方面做出過杰出貢獻。
午后的窗外夏日炎炎,暑氣逼人,但現場卻是人頭攢動,熱鬧非凡。一位剛大學畢業不久的男青年有些靦腆地對記者說,自己還不是曲社的社員,“是來旁聽的,因為喜歡昆曲藝術,所以很想加入社團。”
社員在閑聊中告訴記者,像這樣的活動幾乎每周都有,曲友們除了學習唱腔和表演技巧,還了解到昆曲博大精深的文化,同時也可以與前輩曲家的座談交流。
“我們昆曲研習社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研究,一是傳習,希望能將這門古老的藝術傳承下去,因為昆曲實在是太精美、太高雅了。”剛剛忙完紀念會的歐陽啟名社長顯得有些疲倦,但語氣仍然是平和而從容的。她告訴記者,早期的昆曲研習社,是由俞平伯教授等業余曲家發起的,成員大多是圈里的知識分子,日常活動也頗有些名士雅集的意味。近幾年來,研習社更多地向社會大眾和普通昆曲愛好者敞開了大門。“我們從拍曲到演出,都是義務的。只要喜歡昆曲,愿意學兩句的都可以來。”歐陽啟名說。研習社從此成為了一個百姓大講堂。
曲社每周有三次活動:一次是周日下午在北京東城區校尉小學教授唱曲,一次是周二晚上在海淀區紫竹橋教授表演身段,一次是周三下午在朝陽區安貞小區的一個文化站里教授唱腔。社員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和地點自由安排。
讓歐陽老師感到欣慰的是,昆曲研習社在北京東城區的織染局小學培養了一批小學員,這些孩子都是外來的打工子弟。社里的老師們教他們簡單的昆曲唱段,還組織他們參加演出。“古老的昆曲藝術有了傳承人,特別是年輕人和孩子們,這讓我們覺得非常興奮。”
“我們昆曲研習社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研究,一是傳習,希望能將這門古老的藝術傳承下去,因為昆曲實在是太精美、太高雅了。”
迎難而上
在南京升州路與中山南路交界的鬧市之中,有一條不起眼的巷子,巷中一處院落,白墻灰瓦,掛一串紅色燈籠,這里便是俗稱“九十九間半”的甘熙故居——甘家大院。
甘家是享譽江南的戲曲世家,被當地人戲稱為“南京第一票房”。1954年南京昆曲社成立,組建人正是甘家后人、有著“江南笛王”之稱的甘貢三先生。1980年,甘貢三次子甘濤出任社長。而如今,昆曲社社長的接力棒傳到了甘老先生的外孫女汪小丹的手上。
汪小丹擔任南京昆曲社社長以來,堅持不懈地為昆曲迷們定期開展活動。在交談中,汪小丹社長飽含深情地談起了曲社的發展歷史,輕聲感慨著自己身上的擔子太重了。曲社在發展過程中,面臨過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是在曲友們的共同支持下一步步走來,勞累中有收獲,辛苦中有快樂。“曲社是大家的,如果不是曲友們大家共同的努力,我想曲社也不會有今天。”
“現在南京昆曲社就我一個老師,我已經65歲了,真擔心沒有人接班。”盡管如此,南京昆曲社還是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邀請過上海昆劇團的蔡振任老師,江蘇省昆曲劇院的石小梅老師、胡錦芳老師,昆曲名家華文漪老師來社為曲友們拍曲、指導,為曲友們提供良好的學習氛圍。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各大業余曲社也收取一定的會費,基本是每人每月都是十塊錢,學生半價優惠。然而,如此低廉的會費,根本不夠平時的開銷,經費問題成為曲社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限制。“沒有文化部的補貼,我們基本上靠自己的努力,有時候有一些企業家會給我們一些贊助。”為了給曲友們請來優秀的拍曲老師,歐陽啟名社長和汪小丹社長只好動用自己的私人關系,邀請朋友圈中一些專業昆曲演員來為曲友們義務授課。
廣州五山曲社的負責人則告訴記者,他們計劃在2011年6月25—26日邀請專業老師來曲社為曲友們拍曲,但能否成功還要看情況,因為社里的經費少,活動費用得靠社員們自己掏錢。如果屆時報名人數不足或預算費用分攤后超標,那么拍曲活動就得取消。
“困難總是有的,但是我們迎難而上,曲社的學習、交流活動不能停下來。我的父輩們把這副擔子交給我,我一定要把曲社傳承下去。”汪小丹社長談起曲社,仿佛一位慈母談起自己含辛茹苦養育的孩子。
一位曲友在離開南京昆曲社時這樣寫道:
“冬天,喜歡坐在曲社里邊唱邊曬太陽;雨天,喜歡呆呆地望著門外屋檐下的雨滴,一滴一滴或水簾般的一串串落下。學習《游園》身段的時候,在甘家大院里隨便找一個庭院,只需避開那滑滑的青苔,便可以演一段“姹紫嫣紅開遍”,在這里特別有感覺……現在,曲社的不少朋友都已經離開南京,我時常會想起他們,想起和吳立文坐在曲社一角不停的吹牛的時光,還有拉著周豪吹笛子,而不久我也將離開南京,南京昆曲社和曲社里的朋友們將一直成為我的牽掛。”
□ 編輯 尹麗麗 □ 美編 龐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