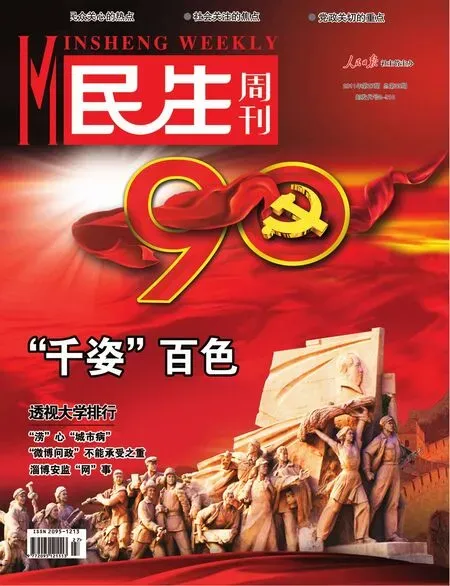“澇”心“城市病”
□ 本刊記者 尹麗麗
“澇”心“城市病”
□ 本刊記者 尹麗麗
2011年6月23日,對于很多北京人來說都是個不眠之夜。這一天,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暴雨幾乎淹沒了京城,也阻擋了人們回家的路。內澇,似乎和交通擁堵一樣,成了很多城市難以治愈的頑疾。當雨過天晴,“洪水”退去,這場暴雨,又將留給我們怎樣的思考?
到北京去“看海”
6月23日下午,北京遭遇十年以來最大降雨,局部地區雨量達到百年一遇的標準。截至當晚22時,北京全市平均降水41毫米,其中城區平均63毫米。據北京市氣象臺發布消息稱,多數站點雨量達到100毫米,達到暴雨級別,其中石景山區模式口出現了192.6毫米的最大降水量,這也是建站以來的最大值。
冷冰冰的數字似乎并不能直觀地說明問題。而更多經歷了暴雨的人們,則用自己的親身感受,印證著那一晚“水城”北京的痛。
下午4時許,暴雨裹挾著雷電,從城西北一路殺入市區,而此時,也正是首都交通晚高峰來臨之際。瓢潑而下的雨水很快占領了全城幾乎所有的主干道,積水越漲越高,暴雨卻未見停歇。北京仿佛成了一個大型水庫,水位急劇上漲。于是,地鐵告急、公交告急、機場告急……
由于地勢低洼,北京的西城和南城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西三環蓮花橋的主干道很快成了波光粼粼的河道,汽車在半米深的積水中化身一葉葉寸步難行的“扁舟”,有些甚至幾乎整個被淹沒,只剩下白色的車頂,成了名副其實的“潛水艇”……這里也成為當天北京各條主干線上積水最為嚴重的一段;而在南三環,陶然亭地鐵站驚現“瀑布”的場面更是成了各大門戶網站、微博、論壇、都市報爭相刊載的頭條圖片。
這一夜,故宮變成了“龍宮”,停車場變成了蓄水庫,地鐵一號線、亦莊線部分區段停運,很多人直到凌晨仍被困在回家的路上……這一夜,大暴雨讓北京人明白了這樣的道理: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和心愛的人來北京看海,在地鐵口看瀑布。”“北京地鐵站昨晚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積水潭。”“身在北京的人們都是‘北漂一族 ’。”
北京怎么了?
網友們的總結固然不乏調侃戲謔的成分,然而,經歷過這場災難性的暴雨之后,很多人不禁會問,作為首善之區的“帝都”北京,這究竟是怎么了?
落后的城市排水設施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
三年一遇,這是北京市防汛辦主任、總工程師王毅給出的北京市排水系統設計標準。如果用數字量化,那就是只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這樣的排水系統,在十年一遇乃至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面前顯然不堪一擊。
脆弱的不只是北京。據媒體報道,目前我國很多大城市的排水能力與北京類似,不過是每小時36毫米-50毫米左右。也就是說,但凡出現每小時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我國大部分城市的排水設施都難免捉襟見肘,城市內澇自然不可避免。
所謂城市內澇,主要是指由于強降水或連續性降水超過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內產生積水災害的現象。這一現象在過去數十年中并不鮮見,但近年來卻顯得尤為突出,且愈來愈嚴重。
2011年5月以來,隨著中國南方地區持續遭遇強降雨的侵襲,浙江、湖北、江西均出現了嚴重的內澇。于是,“去武漢看海”、“到杭州觀水漫金山”、“長沙東入海口建成”一時間成為新的網絡流行語,自嘲與娛樂的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城市逢大雨必大澇的質疑。
“建在地下的工程看不見,往往讓位于地上工程。”很多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的思路上不謀而合。中央廣播電臺的一位評論員評論道:“就像有的人穿衣服,可能外面的西裝很昂貴,但是內褲上面還有洞。我們的城市建設可能也是這樣。”
預警難見效
城市的合理規劃建設向來是個宏大的話題,改造地下排水設施,對于很多城市而言,也并非一朝一夕便能向巴黎、東京等國外發達城市跑步看齊。從我國大多數城市的現狀出發,一旦暴雨當前,及時有效的預警機制或許能夠最大程度減少內澇帶來的影響。
事實上,此次北京城的特大暴雨并非“突然襲擊”。
6月22日,北京市氣象臺就已經發布了暴雨橙色預警,提醒市民在23日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將會遭遇到今年以來最大的降雨,并提示大家做好防雨準備。6月23日16時,氣象臺再次發布暴雨藍色預警,稱北京市北部已出現局部地區暴雨,預計雷雨云團逐漸向城區移動,部分地區降雨量將達50毫米以上。
6月23日上午,北京市水務局網站發布消息稱,北京市防汛指揮中心副總指揮、副市長夏占義為此次暴雨親臨市防指辦公室,部署降雨應對工作。這說明此次應對暴雨并不是一場措手不及的“無準備之仗”。可是,肆虐的雨水為何仍在首都的大地上一瀉千里,幾乎淹沒了整座城市?
綜合規劃缺乏協調的現狀或許值得相關部門反思。
北京工業大學交通運輸規劃與管理博士生導師陳艷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盡管近年來北京市相關部門在對水澇的預警和部門聯動應急方面做得越來越好,但由于缺乏對積水點地埋管線復雜情況的全盤掌控,很多時候在做相關準備工作時是“按下葫蘆起了瓢”,難以統籌兼顧。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總工程師王毅介紹說,城市的綜合規劃缺乏協調,各方面建設存在時間差,進行統一的建設和改造,需要相當一段時間。
普通的北京市民或許對積水點、排水管線標準這些專業術語并不了解,但一個極其簡單的例子,便足以印證城市各部門間聯動應急機制的短板——
6月23日16:50左右,暴雨開始的半小時以后,一輛北京環衛的灑水車在雨中從容駛過望京橋北,挨個給花壇澆水。在這頗為滑稽的一幕背后,相關部門之間僵硬死板、缺乏聯動、面對極端情況無法靈活應急的弱點暴露無遺。

2011年6月23日下午,北京迎來大范圍強降雨。部分地區出現不同程度的積水,受此影響,城區部分路段出現擁堵現象,首都國際機場所有進出港航班均被取消。
變災害為資源
無論是提高城市排水設施標準,還是加強暴雨預警協調機制,似乎都是應對“災害”時采取的“對抗性”措施。從根本上說,都是被動的應對手段。其實,即使是因多年苦心經營下水道而聞名的日本東京,2010年7月也曾因一場臺風帶來的暴雨而全城被淹。在建設排水設施以外,大都市的治澇難題,也許還需要更多遠見和智慧。
與眾多南方城市不同,地處華北腹地的北京本是一座極度缺水的城市,如何能夠充分利用雨水,把災害變成資源,正是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思考的問題。
在俞孔堅看來,將“城市內澇”歸咎于排水管網,顯然是“抓錯了問題的關鍵”。“不能怪地下管網不夠粗,多粗的管網都無法消化這種暴雨。”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研究院防洪減災研究所副所長向立云也曾對媒體表示:“排水能力可以提高,但經濟成本并不合算。相反,如果能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就有蓄洪的意識,城市暴雨后的問題更容易被解決。”
“洪水不應是災害,而應是資源。”俞孔堅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出這個說法。他認為,如今的北京過分依賴地下管道等人工排洪系統,城市原有的河流反而喪失了調節洪水的天然能力。就在暴雨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內的兩條河流——清河和玉泉河卻仍然缺水。
而向立云則認為,如果這些大量雨水沒有隨著飽受詬病的排水管道奔向遙遠的江河湖海,它們還可以流進占北京市總面積50%的綠地。
在北京,為了突出城市景觀,幾乎所有的城市綠地都高出了地面。“如果綠地能比路面低20到30厘米,就可以吸收200到300毫米的降水”。向立云表示。如此一來,城市綠地也可以承擔起滯洪的作用,內澇問題也能得到極大程度的緩解。
在日本東京,公園、綠地和廣場均采用“沉降式”,比周圍地面低半米到1米左右。停車場和人行道等也廣泛采用透水性材料,雨水可迅速滲透到內層,最終進入城市的地下水系。歐美發達國家一般都有排雨水的“小排水系統”和排澇的“大排水系統”,一旦特大暴雨出現,地下停車場、運動場和蓄水池都可以作為臨時存水的地點,在加大排水能力的同時,也可用來儲存雨水,最大限度地利用雨水資源。
□ 編輯 劉文婷 □ 美編 閻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