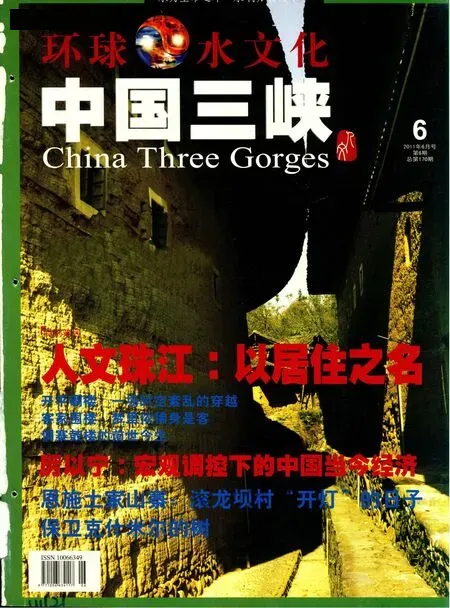無(wú)錫:多少樓臺(tái)煙雨中
文/范 敏 編輯/于翔漢

無(wú)錫太湖垂柳帆影現(xiàn)攝影/董金林/CFP

千百年來(lái),前有絲綢之都的吳中燈火,后有銀領(lǐng)搖籃的常州皓月,無(wú)錫則低眉順眼成一束寂廖的煙花,凝千年的風(fēng)霜,默默地等待,那千年一醉。
一座古城的歷史與典藏,一份生活的寫(xiě)意與真情,一種人文的懷念與傳承,在歷史沉淀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份味道,以自然的詩(shī)化山水,煙雨風(fēng)情,深深地,讓我找到記憶深處若隱若現(xiàn)的“ 江南好,風(fēng)景舊曾喑” 的柔美情懷。

陽(yáng)春三月,太湖山清水秀,垂柳依依,吸引了無(wú)數(shù)游人前來(lái)領(lǐng)略太湖之美。攝影/董金林/CFP

無(wú)錫南頻太湖,北依長(zhǎng)江,歷史上享有“布碼頭”之譽(yù),為中國(guó)“四大米市”之一。 攝影/北幻/cfp/CFP
劍花、暮雨、冷巷,煙雨的江南啊!
去無(wú)錫,我是一直渴望坐船的。且最好是從蘇州坐船,不需快,慢慢隨波蕩漾,劃過(guò)一程又一程的茉莉花香。就像很久以前的那個(gè)風(fēng)流才子一般,為了一抹嫣然,從蘇州追到了無(wú)錫。
進(jìn)入無(wú)錫,就被一場(chǎng)大雨捉住了,雨密密地下著,沒(méi)有雷電的狂暴,也沒(méi)有勁風(fēng)的急驟,只這樣密密地下著,不溫不火,像一層雨簾擋在我的面前。導(dǎo)游說(shuō),這就是梅雨。
無(wú)奈,只有在煙雨中感受太湖了。
煙雨太湖的深處,讓遠(yuǎn)山更加悠遠(yuǎn),柔媚的有點(diǎn)失真,那些打著雨傘的江南女子,猶如在水墨畫(huà)里、在唐詩(shī)宋詞里、在吳越歌聲里……
空氣中,氤氳著濕潤(rùn)的氣息,乳白的輕煙在云端變幻,清透的雨絲,鑲嵌在青山碧水之間。偶有伶仃的飛鳥(niǎo)掠過(guò)翠綠的枝頭,在迷茫的煙雨中,尋找屬于自己的方向。而我,沒(méi)有停留,一直向南。
雨中漫步,滋長(zhǎng)著妙不可言的閑情。流水過(guò)處,潺潺著無(wú)邊無(wú)際的憂(yōu)傷。山間的葉兒無(wú)聲地飄零,草圃的石榴兀自地紅著,湖中的清蓮寂寞地睡著。也許,只有這個(gè)時(shí)候,我才能擱歇腳步,讓心靈娉婷。
煙霧迷茫,浩淼的太湖看不到盡頭,青山無(wú)言地隱去。涼風(fēng)吹過(guò),湖中漫起了一圈一圈的螺紋,雨落在湖面上,濺起淺淺的水花。綠色的水藻漫在岸邊,靜穆的綠、沉淀的綠、流動(dòng)的綠,空氣中,彌漫著綠色的芬芳。
湖中央有座島,渡船過(guò)橋,便是太虛幻境。覓一艘木舟上島,撐船的老者披蓑戴笠,臉上的皺紋如同犁開(kāi)湖水的浪花。坐在船上,欲覺(jué)身輕,低頭望水,塵間沾染的浮躁歸于沉靜。
迷霧中有七桅古船,從旁邊駛過(guò),朝著遠(yuǎn)方,望著漸漸地只剩微蒙的背影,心有悵然。一路風(fēng)雨兼程,不知何時(shí),才能抵達(dá)停泊的港灣?
此岸越遠(yuǎn),彼岸越近。島上的樓閣與古塔愈漸清晰,煙云籠罩,恍如蓬萊仙境。下船上岸,不再回望來(lái)時(shí)的方向。岸旁,停靠幾只捕魚(yú)的小船,船上的漁民賣(mài)給游客一些捕撈的湖鮮。一蓑風(fēng)雨,見(jiàn)證著他們無(wú)怨無(wú)悔的人生。一時(shí)間,眼眸有濕潤(rùn)的潮汐在涌動(dòng)。
古典的橋梁橫在湖與岸之間,長(zhǎng)廊里,流轉(zhuǎn)著淡淡的回風(fēng)。眺望遠(yuǎn)方,只有一種顏色,叫蒼茫。穿過(guò)此橋,也許,可以尋得一生的去處!
在這樣的煙雨中,站在太湖黿頭渚上,遠(yuǎn)眺,煙霧朦朧下,湖水沉靜如玉,仿佛孕育著生命;近望,碧清湖面上,蒼翠古樹(shù)、亭閣樓臺(tái)倒影矗立,仿佛蓬萊仙島墜落湖中……是的,太湖的煙雨是潤(rùn)物無(wú)聲的,是足以包容一顆顆疲勞的心。
石階或陡或緩,時(shí)深時(shí)淺,感受著腳底板與這秀雅方達(dá)的水土間的親昵,無(wú)論是郭沫若的“太湖佳絕處”,抑或是名人手書(shū)“具區(qū)勝境”,描述的仿佛是另一個(gè)太湖,而我的太湖,原本,就是湖邊朦朧煙雨、習(xí)習(xí)清風(fēng),泊泊浪聲,繁花、淺草、風(fēng)荷、斜柳、秀石,以及葉叢草際間的蟲(chóng)鳴鳥(niǎo)唱,茂林修竹后的典韻書(shū)香。
在綠陰下穿行,一不小心,就被太湖的婉約俘虜,讓自己成為風(fēng)景中的一抹點(diǎn)綴。
置身此景,沐著如夢(mèng)似幻的煙雨,偶爾有簫聲入耳,人便如癡如醉,醉在煙霧朦朧的江南煙雨中。有什么辦法呢,在這江南煙雨中,再偉岸的男人都會(huì)變得優(yōu)柔多情,越王如此,白居易和蘇東坡如此,甚至,連金戈鐵馬征戰(zhàn)英雄左宗棠,亦如此。
想想,卻還是有些惆悵,我知道,這惆悵來(lái)自江南,來(lái)自這太湖的煙雨,來(lái)自這片專(zhuān)門(mén)滋生柔情與醉意的土地。面對(duì)一湖煙雨,渴念著渴念的人兒,此情此景,點(diǎn)點(diǎn)滴滴,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春的江南是綠的,是美的。當(dāng)然包括那生活在其間的人們。攝影/陸文君/CFP
在蠡湖畔,西施的石像佇立在碧水繁花間,那條小溪的名字,叫做“浣紗溪”……
絕代美人西施傾覆吳國(guó)江山后,與昔日的情人范蠡相攜淡入太湖。在這里,為后人留下了一個(gè)懸念——他們哪里去了?
西施莊,一個(gè)2400多年歷史傳說(shuō)的莊園,如今已經(jīng)浮出水面。
從黿頭渚出發(fā),伴隨轟鳴的快艇引擎聲,船尾噴射出陣陣水花,不一會(huì),便把黿頭渚美景拋在了身后,漸漸地,在身后越來(lái)越模糊,西施莊輪廓卻越來(lái)越分明,短短幾分鐘,似乎穿越了2000多年時(shí)空,踏上了相傳范蠡攜手西施隱居的西施莊。
2500多年前,吳王夫差曾為美人西施在太湖之濱建造離宮,專(zhuān)門(mén)修建了栽培荷花的“花池”,西施在那里留下了惆悵迷茫的芳蹤。當(dāng)一代人杰范蠡助越伐吳、功成身退之后,以身許國(guó)的西施,終于和心上人范蠡走在了一起,當(dāng)她凝視著出污泥而不染的滿(mǎn)池荷花,該有怎樣的人生感悟?我們自然不得而知。

吳越時(shí)期著名古跡:范蠡湖與西施妝臺(tái)。 攝影/馮軍/CFP
五里湖是當(dāng)年范蠡泛舟獨(dú)樂(lè)的地方,蠡園靜靜佇立在湖畔,綠水瀲滟,在光影的照耀下閃爍著碎金。范蠡泛舟的千古佳話(huà),重要組成部分是西施。如果沒(méi)有這個(gè)亂世紅顏,恐怕故事也少了些許纏綿。一個(gè)風(fēng)華絕代的美女,用她學(xué)歌則香喉清俊,習(xí)舞則奇姿翩翩的才情姿色,誘使敵國(guó)的君主縱情聲色,朝歡暮樂(lè),戀酒迷花,去賢用佞,為國(guó)報(bào)了仇雪了恥。卻因了“紅顏禍水”,與“亡國(guó)”相連,被奪去生和愛(ài)的權(quán)利。
古人口中“以色誤國(guó)”的女子不少,妲己、褒姒、西施、張麗華、妹喜等等。張麗華和褒姒已成為禍水的代表,妲己和妹喜更是被詛咒為妖孽,一次次被攻擊唾罵。而其中,懷揣目的的西施,倒是最惹人同情,自古多少文人墨客憐香惜玉,為西施傷懷哀嘆,連吳國(guó)的百姓也視她為憐憫的對(duì)象。不管歷史上的西施是被越國(guó)刺死,還是隨吳國(guó)湮滅,她與范蠡歸隱太湖的傳說(shuō)是流傳最廣的。
在蠡湖畔,西施的石像佇立在碧水繁花間,那條小溪的名字,叫做“浣紗溪”。林黛玉曾說(shuō)“莫笑東村效顰女,白首溪邊尚浣紗。”如果可以,還是,讓她做那個(gè)苧蘿水邊浣紗的村女吧,沒(méi)有陰謀,沒(méi)有戰(zhàn)爭(zhēng),沒(méi)有人利用她的容貌,沒(méi)有人利用她的感情,讓她單單純純,干干凈凈。
雖不見(jiàn)傳說(shuō)中的人,但可見(jiàn)傳說(shuō)中的物。在西施浣紗處,從復(fù)原的浣紗工具,依稀想像得出古代女子浣紗時(shí)的情景,淡淡地融入了鄉(xiāng)間的樸實(shí)與簡(jiǎn)單的快樂(lè)。
西施的歸宿,與水有關(guān)。水以其恣肆浩大、寬容和軟,朦朧滋生出西施之死的浪漫與凄婉。這樣的死,軟化了生命的質(zhì)感,沖淡了江山氣度,是把美艷和柔情撕裂揉碎,撒開(kāi)散落的方式,通身散發(fā)著一種悲劇的美,一種痛感的美,一種極致的美。
只是總想象,西施佇立“鴟夷”之上,依舊美麗絕世,風(fēng)吹起她翩然飛舞的長(zhǎng)發(fā),想來(lái),沒(méi)有了在異國(guó)他鄉(xiāng)凝望明月、傾聽(tīng)風(fēng)過(guò)時(shí)流落的淚珠和寂寞傷心,沒(méi)有了強(qiáng)顏歡笑取悅夫差的悲壯心緒,也許,會(huì)思緒飛揚(yáng),留戀“隱居山野,閑云野鶴,終老一生”的承諾。宛若,秋波的眼里,依然流動(dòng)著絲絲情意,浣紗溪上邂逅的激情,與分花拂柳的淺唱低吟,也許,也許,已成為最后的記憶……
江南風(fēng)景,花紅柳綠,草長(zhǎng)鶯飛;清風(fēng),流嵐,葦蕩,鷗鳥(niǎo),阡陌,野花;落花如雨,風(fēng)起云涌,水天相接的地方,幾只孤鶩斜斜地飛過(guò)。絕代紅顏,就這樣被自然風(fēng)物簇?fù)碇呦驓w途。
高挑的蘆葦,在思念的風(fēng)中,綠了又黃,黃了又綠,迎風(fēng)婆娑,搖曳成千年的守望,與默默的陪伴。

無(wú)錫大型民族舞劇《西施》隆重演出,西施與范蠡此時(shí)正登舟遠(yuǎn)去。攝影/宦瑋/CFP
一直以為靈山圣水是個(gè)傳說(shuō),不想在煙波浩淼的太湖之濱,讓我見(jiàn)識(shí)了這個(gè)傳說(shuō)中的勝境
煙霧似輕紗飄渺,山澗如瓊樓仙閣,縹緲空遠(yuǎn)的鐘聲敲醒夢(mèng)中人。靈山大佛,巍峨聳立于煙霧彌漫的山林之間,仙島之頂,云霧深處。我順著天階行走,才可抵達(dá)太虛幻境。山澗流瀉著飛泉瀑布,落花在回溪里輕靈流轉(zhuǎn)。拾一枚石子投入水中,看波光久久地蕩漾。
漫步在用一千三百多年歷史堆砌的石板路上,翻閱歷史的冊(cè)頁(yè),邁出的每一步,仿佛都牽絆著歲月滄桑。“千年古杏”、“六角井”講述著唐玄奘及其弟子開(kāi)創(chuàng)“祥符寺”的前塵往事;“菩提大道”、“誦經(jīng)廊”、“阿育王柱”向人們?cè)V說(shuō)著一個(gè)個(gè)大徹大悟、鳳凰涅磐的動(dòng)人故事。
聳立眼前的是釋迦牟尼佛祖,左手施“與愿印”,右手施“施大無(wú)畏印”,面相豐滿(mǎn)端莊,慈祥和藹,睿智敦厚。整個(gè)大佛形態(tài)圓滿(mǎn)安詳,無(wú)論身處何方,大佛的眼神都跟隨著,慈顏微笑著凝視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雙耳垂視,對(duì)眾生的關(guān)懷之情溢于眉宇之間。嘴角似帶微笑,欲言未語(yǔ),似有諸多囑托。正如已故的佛教協(xi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趙樸初先生所說(shuō):如法如律,莊嚴(yán)圓滿(mǎn)。
十時(shí)許,一聲洪亮的號(hào)角聲,在菩提大道盡頭的大千世界廣場(chǎng)奏響,廣場(chǎng)上屹立著國(guó)內(nèi)最大的音樂(lè)動(dòng)態(tài)青銅群雕塑?chē)娙琵埞嘣 iL(zhǎng)號(hào)齊鳴,噴泉也隨著音樂(lè)跳躍起來(lái),時(shí)而沖向二十多米高蓮花高臺(tái),時(shí)而在低處歡跳,煙霧迷蒙,一種神秘而又神圣的氣氛,籠罩著整個(gè)廣場(chǎng)。
此時(shí),嘈雜驟停,梵音裊繞,高聳的蓮花依次打開(kāi),一尊通體鎏金的太子佛,從蓮花中慢慢升起,先是面北背南,再一點(diǎn)點(diǎn)地轉(zhuǎn)向南方。一時(shí)間,偌大的廣場(chǎng),萬(wàn)人俱寂,只有梵音在心頭回蕩。
梵音一點(diǎn)點(diǎn)激越起來(lái),猶如京劇中的快板,讓人隱約覺(jué)得有什么事情要發(fā)生。猛然間,九條水柱從底座上的龍嘴里噴出,直射蓮花座中的佛身上,呈現(xiàn)九龍灌浴的奇觀。沐浴后的佛像高高在上,安詳里透著威嚴(yán)。飛濺的水花,生發(fā)成無(wú)數(shù)條彩虹,猶如,每個(gè)人心中旖旎的夢(mèng)。
一種強(qiáng)烈的心靈震撼悠然心會(huì),妙處難與君說(shuō)。
梵宮內(nèi),匯集了藝術(shù)家和工藝大師的各類(lèi)藝術(shù)作品。精湛細(xì)膩的東陽(yáng)木雕、光彩奪目的琉璃巨制、精美的景德鎮(zhèn)青花粉彩虹、精致典雅的歐塑浮雕,美不勝收。一副以琉璃等珍貴材料打造的《華藏世界》,營(yíng)造了宏大浩淼、光明燦爛的宇宙境界,是梵宮的鎮(zhèn)宮之寶。還有那敦煌藝人合力繪就的穹頂敦煌壁畫(huà)《天象圖》,將一幅鮮見(jiàn)的天文星象奇觀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走出梵宮,憑欄而望,煙雨之中,天地蒼茫,群山靜默。曾經(jīng)蝕骨的傷痛與忘形的快樂(lè)都已忘記,只是不知,這是迷失還是新生?
短暫的邂逅,也許是瞬間,也許,是一生。
水是無(wú)錫的夢(mèng),是無(wú)錫的魂,而讓人魂繞夢(mèng)縈的,則是無(wú)錫的弄堂
或許,我曾輾轉(zhuǎn)設(shè)計(jì)的無(wú)錫弄堂,就應(yīng)該是這樣罷:
是錯(cuò)錯(cuò)落落的運(yùn)河蜿蜒繞過(guò)一排排古老的房屋,是窄窄灰灰的一段段青石馬路,是屋前低低矮矮的絲瓜棚,是朵朵黃花下斑駁的門(mén)板后走出的風(fēng)霜老人,是深深雨巷里撐著油紙傘丁香一樣的姑娘……

時(shí)光就在這街巷中慢慢流去…… 攝影/高磊/CFP
于是,我一如遐想的在這個(gè)霧靄氤氳的清晨,冒冒失失的闖進(jìn)了無(wú)錫弄堂,渴望依偎著她,融入她的祥和與寧?kù)o。
狹窄、幽長(zhǎng)的弄堂,如一只深鎖在江南煙雨中的洞簫,春去秋來(lái),訴說(shuō)著寂寞芬芳、憂(yōu)愁彷徨、及舊夢(mèng)與往事。于是,一條條原本默默無(wú)聞、或曲或直的灰白小弄,便有了一份撲朔迷離的情感。與此同時(shí),無(wú)錫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悠長(zhǎng)而又浪漫的表情。
“宅弄深處,曲徑通幽,不知深幾許,行至盡頭,豁然開(kāi)朗,別有新洞天。”其實(shí)是一種境界。這境界,對(duì)生活在弄堂內(nèi)的人來(lái)說(shuō),就是他們最普通的生存空間,但對(duì)整個(gè)江南文化來(lái)講,卻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組成部份。
一座城市就如一個(gè)生命的肌體,弄堂就是無(wú)錫的命脈。從高空俯瞰,這些間隔交錯(cuò)在現(xiàn)代建筑與老宅之間,或舊居、老宅與小橋、堤岸、水閣之間的弄堂,它們就像是一條條縱橫交織的記憶之線(xiàn),把無(wú)錫的昨天、今天都編織在它的經(jīng)緯之間。
這其中,既有最普通的市井生活、故事、傳說(shuō),也有以往名人的舊聞趣事,更多的是屬于江南的歷史文化,屬于江南人家那份難以割舍的精神依托及夢(mèng)境家園。
一條條弄堂如一部部古書(shū),浸在潛移默化的變遷里,帶著溫情的渴望,波動(dòng)在京杭運(yùn)河碧波的漣漪里。最有名的要數(shù)那西門(mén)橋堍的日暉巷。“旭日滿(mǎn)晴川,翩翩賈客船。千金呈百貨,硅步塞齊肩。布褐解市語(yǔ),童烏識(shí)偽錢(qián)。參差魚(yú)網(wǎng)集,華屋競(jìng)烹鮮。”廖廖數(shù)語(yǔ)間,繁華熱鬧的景象,躍于眼前。
現(xiàn)今,日暉巷商家店鋪依然云集,荷葉粉蒸排骨的香氣依然四溢,八珍糕的名氣依然響亮,磨豆腐、配鑰匙、日用銅器制作、冷作工匠、木器雕花……應(yīng)有盡有,巷口的一片茶館店,雖已作了居民住宅,但房屋未改,格局未變,樓上的一排格子窗,依然保持原貌。茶館里依然人來(lái)人往,川流不息,只是,往來(lái)的,大多不再是四鄉(xiāng)八村的鄉(xiāng)鄰,而是來(lái)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以或欣賞,或?qū)?mèng),或好奇的心境,探訪(fǎng)這些古老的弄堂。
沿著三里橋前行,很快到北塘大街,這里是昔日無(wú)錫最為繁華的商埠,巷弄密集,商賈云集。可惜,歷史上曾遭遇兩次劫難,一次是太平軍和清政府軍隊(duì)的焚毀,一次是日寇侵略時(shí)引發(fā)的大火。歷經(jīng)滄桑,卻無(wú)曾保留,不免讓人有點(diǎn)唏噓。
幸好,這里的接官?gòu)d弄,尚保留許多舊式的建筑,雖然不是年代久遠(yuǎn),但簡(jiǎn)單質(zhì)樸。我的午飯,就是在這里一居民家小食店解決的。一碗清甜滋潤(rùn)的涼粥,一碟涼菜,有排骨,還有辣椒,蓮藕,青豆,在這春暖還寒的午后,真是莫大的享受。
站在弄堂口看弄堂,它就像一位冬烘的歲月老人,每天習(xí)慣地邁著它那恒久不變的步伐,默默地守侯著那方并不寬敞的天地。在這些窄窄的街巷里,時(shí)光的痕跡,彷佛觸手可及,無(wú)論是在嶺南的古村,還是在巴蜀的老街,亦或如今的錫城弄堂,這種懷舊的感覺(jué),都特別深刻。
去民主街需要穿過(guò)數(shù)條弄堂,寬不過(guò)兩三米,還時(shí)常被涼曬的衣服所遮擋。時(shí)值中午,主婦們正炒著菜肴,香味直入鼻孔,小孩兒在巷頭巷尾奔跑著,老人們搖著扇子擺弄家常。尋常人家的生活情景歷歷在目,那么的栩栩如生,倍感親切。

弄堂,人文俚俗的演繹。 攝影/江心/CFP
也許,正是縱深、淡泊的弄堂文化,使生活在弄堂里的人們,養(yǎng)成了一種溫雅而安詳?shù)纳盍?xí)慣,也讓他們擁有了一份割不斷、理還亂的弄堂情結(jié)。
坐在雕花木柵前抽著水煙的老人,閑話(huà)家常的老太太,以新鮮而又習(xí)以為常的目光,打量著我,和其它三三兩兩的游人,時(shí)不時(shí),流露出善意和友好的微笑,在他們布滿(mǎn)皺紋的記憶里,一定還會(huì)有無(wú)錫的舊事吧,那些舊事,是否也如他們一樣,坐在自家門(mén)前,任陽(yáng)光暖暖地晾曬呢?
已是黃昏,在巷口遠(yuǎn)眺,弄堂的路、棚廊及模糊的黛瓦粉墻,在斜陽(yáng)的暈染下,如淡彩的宣紙畫(huà);無(wú)錫彎彎曲曲的弄堂,平平仄仄的石板,清清澈澈的運(yùn)河,高高低低的石橋,如泛黃的照片,在記憶里層層清晰,仿佛歲月的印痕,在自然的畫(huà)面中流動(dòng),樹(shù)影、船影、橋影,晃動(dòng)著,漸漸隱去。
這樣遠(yuǎn)遠(yuǎn)近近的望著,目光沾染了水的痕跡,便醉成濕漉漉的癡情。
拍照的時(shí)候,旁邊一老伯細(xì)心地提醒我的資料掉在地上了,他接著打開(kāi)了大門(mén),我下意識(shí)地想跟進(jìn)去,他卻笑笑擺了擺手,只一會(huì)兒功夫,弄堂便恢復(fù)了平靜。
在清名橋上拍完最后一張照片,我便悄悄地離開(kāi)了。華燈初上,遠(yuǎn)處的市區(qū),無(wú)數(shù)高樓大廈映射出奪目的光彩,繁華,立刻,覆蓋了整個(gè)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