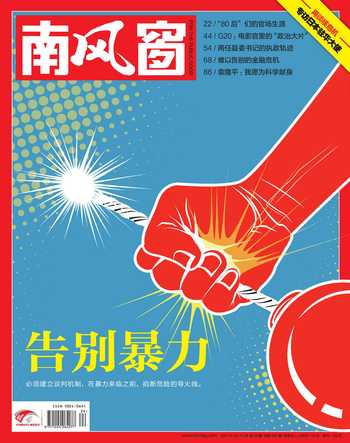再修《民訴法》,能否破解“三難”
葉竹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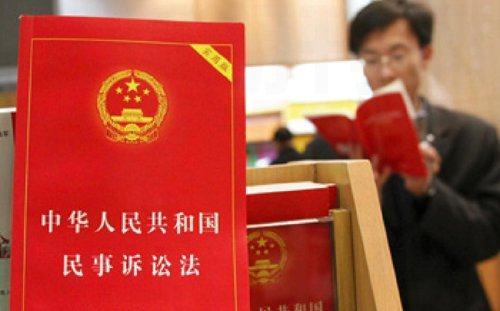
佛山“小悅悅事件”發生后,5年前的“彭宇案”又一次擺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公眾紛紛指責該案的主審法官,認為他的錯誤判決“使社會道德倒退了50年”,加劇了現今社會的冷漠程度。
在著名民訴法專家江偉教授看來,“彭宇案”并非錯在道德,而是因為“證據規則過于簡單”,致使“彭宇案”在事實認定方面存在諸多爭議,這屬于訴訟程序內部的問題。
我國調整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法律是《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性法律,其基本價值在于通過合理的程序設計,使當事人能夠獲得高效且公正的司法結果。司法程序上的問題,最終可能演變為“彭宇案”一樣引起極大爭議的判決。
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制定的法律之一,《民事訴訟法》“試行”了10年后,才在1991年正式通過實施。這足見立法者的審慎態度。
然而,我國在民事司法實踐中仍然大量存在“三難一煩”的問題,也就是“立案難、取證難、執行難”和“調解煩”。程序上的又難又煩,自然會影響實體正義的實現,為司法結果的不公正埋下伏筆。
2007年,《民訴法》經歷了首次修訂。時隔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醞釀修訂該法。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公布了修訂草案,向各界征集修訂意見。大家關注的焦點自然在于,此次《民訴法》返修能否破解諸多司法難題?
期待破解的“立案難”
“才11月,法院已經都不立案了。和立案庭的同學交流,大家都很無奈,法院要考核結案率,要理解支持和包涵。我不知道中國的法院為什么要考核結案率這個指標……法院為一個工作考核指標,就公然去違法,這合適嗎?”時值《民訴法》返修之際,有律師在微博上這樣抱怨說。
1991年,《民訴法》正式頒布時,將“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列為首要任務。立案是啟動訴訟程序的第一步,很多人卻因為難以立案而被擋在了法院門外,遑論其他訴訟權利的保障。
“結案率”是法院出于內部考核制度不愿立案的一個原因。此外,北京理工大學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教授對本刊記者說,“‘立案難問題曾經較為嚴重,主要表現為立案手續復雜,起訴條件過高,但近年來,‘立案難主要體現為法院拒絕受理某些敏感案件,也往往拒不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有的法院對土地承包、勞動爭議、企業轉制等‘敏感案子,退避三舍。有的是聽了‘將令的,有人甚至拿著省人大信訪辦開具的介紹信去起訴,但就是立不了案。”在上海執業的律師沈彬這樣總結他所理解的“立案難”問題。
難怪有人調侃說,立案庭的主要工作其實是“不準立案”,更合適的稱呼應該是“不立案庭”。
針對這個問題,此次修正案草案規定,“人民法院對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7日內作出裁定書。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原條文僅規定應當在7日內做出裁定,修正案草案將裁定的方式限定為書面出具裁定書,排除了口頭裁定的可能性,方便當事人上訴。
但是,“即使這么修訂,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徐昕認為,“首先應該將立案的實質審查改為形式審查,進而改革司法體制,提升司法審判權的獨立性,才可能保障法院獨立受理一切可訴的糾紛。”
不少學者和律師都支持采用立案登記制。但在法院看來,采用登記制就意味“敞開大門”,使不堪重負的法院雪上加霜。
過去數年,最高院曾多次下發旨在解決“立案難”的文件,但收效甚微。就此次民訴法修訂草案來看,也還是著力不足。法學教授周永坤說,如果不解決“立案難”的問題,“從公民進入法院的第一天就碰到了違法,而且是法院違法,公民有何想法?公民還會相信司法?”無疑,對此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更深遠的司法體制改革。
“調解前置”爭議
此次修訂案草案中增加規定:“當事人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糾紛,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有解讀認為,這個條款相當于“調解前置”。實際上,在此之前,法院已經大量使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
2004年,最高院發布《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要求嚴格執行“能調則調、該判則判,判調結合”的審判原則。2008年,進一步提出“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在這個司法政策下,不僅在審理階段可以進行調解,甚至在立案前也進行“訴前調解”,判決后進行“執行調解”。案件“調解率”已經成了法院的一個重要考核指標。
學界對大量采用調解來解決糾紛的做法表示了擔憂。江偉教授說:“現在有人一直對民訴法的這一條予以反對。意思就是說調解可以不分是非,不查明事實,這還叫什么解決爭端。”
調解最注重的是實際效果,即便調解結果不符合法律規則和案件事實,只要當事人能夠接受,都算調解成功,因此大量使用調解有利于快速靈活地解決糾紛。但有學者指出,這種做法治標不治本,因為如果當事人對調解不滿,仍然可以提起訴訟,實質上是對原本就有限的司法資源的浪費。
在實踐中,學者所擔憂的這種情況似乎并未出現。據一位民事庭夏姓法官介紹,調解后當事人又起訴的情況并不多見,“首先是因為當事人不懂法,比較好蒙;第二是因為法院主持的調解,再通過法院訴訟翻盤的機會不大。”
在青島執業的呂士威律師對本刊記者說,在保護當事人利益的前提下,會力勸當事人接受調解,很多糾紛都是因為溝通不暢造成的。她所代理的經調解成功的案子中,沒有反悔的例子。她說:“對于徹底解決一個糾紛來說,調解確實能節約不少司法資源。”
盡管如此,夏法官透露,年輕法官并不太歡迎這種做法,“學了那么多法律,還要像居委會大媽一樣做調解,更何況還挺費時間的。”另一位在法院執行局工作的法官則說,執行生效判決時也要進行調解,有時候會使判決結果“打個七八折,甚至打五折”,他說,“這么做感覺法院很沒有威嚴。”
也許短期來看,調解的效果確實不錯,但是如果過度強調調解,“將來還有什么法治可言,時間長了人們就沒有法制觀念了,我們要注意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決不能忽視訴訟在解決糾紛中的核心作用。”江偉教授說。
以公開倒逼公正
判決書公開是此次修正案草案中的一大亮點。審判公開是我國民訴法的基本原則,判決書公開是審判公開的一部分。意大利著名法學家貝卡利亞曾提出:“審判應當公開,犯罪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輿論能夠約束權力和欲望。”
在普通法國家,判決先例是重要的法律依據,因此法院判決后,一般會第一時間以最便捷的方式公布判決書。這些公開的判決書成為律師執業、法學院教育和新聞報道的重要材料,對培養公民法律意識,提高法治水平有莫大功用。
公開判決書更大的意義在于通過公開倒逼公正。現實中,公開判決書的最大阻力來自法院內部,夏法官說:“并不是每個法官都愿意公開。(不公開的話)搞定兩個人就可以了。公開的話,考慮的問題就更多了。”他表示,對他本人來說,公開判決書“沒有什么可以顧慮的”,但對“水平比較差的,收了錢的,判得不公平的,他們會擔心留下口實。”
雖然最高院曾兩次下發要求推動司法公開化的文件,但各地法院反應不一。某地中院在回應市民申請查看判決書時曾經這樣答復:“本著保護當事人隱私權的角度考慮,我院暫無將判決書向全社會公開的計劃。”青島呂士威律師告訴本刊記者,即使是律師,“要查閱某案的生效判決文書,如果不是該案的代理律師,在實際操作中也很困難。”對普通公民來說,就更有難度了。2009年,上海法院在網上公開了13余萬份判決書,雖然已經邁出了關鍵一步,但這個數字只占當年審結案件的1/3。
法院可能會以這種選擇性公開的辦法來應對判決書公開造成的壓力。如果民訴法修訂沒有規定更具體的措施,要求全面公開不涉密和涉及隱私的判決書,那么公開倒逼公正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法院不會愿意公開見不得光的判決書。”夏法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