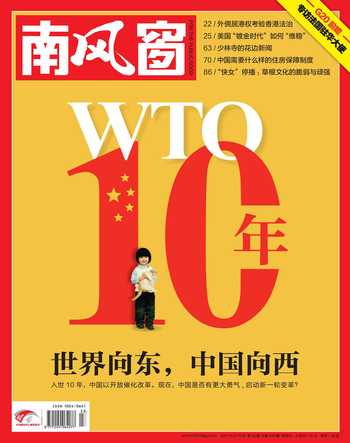打撈中國人的“道德契約”
石勇
佛山“女童遭兩車碾壓,18路人見死不救”事件不僅刺痛整個中國,也讓國外媒體目瞪口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常委會議上稱此悲劇令人“心靈受到巨大沖擊”。
在近年來諸多和“道德”有關的公共事件中,能在民間和官方都產生如此沖擊的,并不多見。可以說,中國那么多年的道德滑坡對人心的刺激,經過“累積”,在這一事件中達到了頂點。其恥辱,足以叩問國人的良心。
而反思,當然也一并出現。
但在公共領域,由于此事件營造了一個“劇場心理”,彌漫著諸多偏激、老套,甚至離譜的言論。
比如,很多人對“18冷漠路人”的指責充斥著話語暴力。比如,把一切責任都算到制度頭上。又比如,在抒情中,“反思”成為一種言之無物的虛偽姿態。
這是滑稽的。“劇場心理”一消失,想象自己并不像“18冷漠路人”那樣缺德的人們,是否真的有道德,還真的難說。
中國社會是出了不少問題。制度的環境,包括權力監督、法律審判等方面發生的個案,形成了惡劣的“示范”。就道德資源來說,這個社會也所剩無幾,而制度,還沒能生產出維護政治、社會、經濟秩序所需的道德資源。
不過,這些都已經是重復了無數次的常識。完全鉆進這種思路,把自己的責任豁免,倒恰恰是“路人”的思維。不客氣地說,假如一個“彭宇案”就可以擊潰人性本能的話,那只能說明,大多數人本來就已經打算放棄道德,而終于,找到了能夠說服自己的合理借口。
道德行為和一個人內在的同情心、良知等聯系在一起,相對而言,制度更多地只是一個激勵或扼殺道德的心理動機的外部條件。當一個人的生命痛苦無法引發另一個人的出手相救時,那并不只是或總是制度的錯,說明我們中的很多人,可能基本人性都已經守不住了。而離開人性,期待制度能夠像變法術一樣變出道德,只是一場春秋大夢。
反思是可貴的。但是,那么多年來,在道德本身,以及它和權利的復雜關系中,整個社會在認知上的混亂,事實上也加劇了道德淪喪。如果沒有觸及這一點,我們將又失去一次機會。
一種混亂,就是關于道德“律己”和“律他”的混淆濫用。
道德至少有兩個方面:防止相互傷害、危難時啟動救助;個人用來加強自身修養,或防止自己墮落。
顯然,指向個人修養方面的道德是律己的,和別人無關,不能指責或要求別人按照自己認為的標準有什么樣的道德修養,這無須多說。但道德當然并不僅僅是律己的,要維護道德秩序,就必須有社會輿論機制。如果一個人道德敗壞,都不允許別人去指責,那就在邏輯上取消了具有一定強制性的道德規范,把道德變成了個人修養之類的東西。
但是,在打算指責別人之前,有一個約束,就是一個人必須先在道德上審視、剖析自己,同時,看一下別人的道德錯誤,他能夠承擔多少責任,這責任,自己有無一分。如此,方能阻止道德他律的濫用。
非常清楚,“18冷漠路人”,已不僅僅是18個單獨的個人,而是這個社會所有人的符號,沒人跑得掉。正因為如此,預設自己沒有問題而譴責他們是蒼白的,指向的,應該更多是每個人的自我解剖。汪洋呼吁用“良知的尖刀”來解剖我們身上的丑陋,認知是相當清晰的。
還有一種混亂,就是用“權利”吞沒道德,結果,權利沒見到,道德倒是被虛無化了。這一點,從“范跑跑”事件以來,就非常明顯。
如果還要在今天澄清一下的話,必須說的是,假如在危及個人生命的時刻,范跑跑的“跑跑”有道德正當性,那也只是因為他生命的道德分量,壓倒了他作為一個教師的職業倫理,這可以理解和原諒,但卻絕不意味著放棄職業倫理本身是正當的,可以毫無愧意,甚至還是什么“自由”、“權利”。當“自由”、“權利”以這種近乎道德無賴的姿態出現時,道德只能死掉。
任何一種權利,正如制度一樣,都要提供一個道德正當性的證明。比如制度經民主程序產生,比如權利不越出道德的邊界,絕不試圖挑釁人性。這決定了“見死不救”之類冷血行為永遠無法成為權利。
人類組成社會一起生活,一般而言,相互之間有兩種道德契約。一種是自然法意義上的道德契約,也就是政治哲學家們所說的“自然義務”,針對的是“人”:積極方面,看到一個人處于危難之中,你有道德義務去幫一把、救一把;消極方面,你不能去害人。還有一種,是一個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道德契約:當弱者遭受災難時,強者有幫助的道德義務。而強者之所以有這樣的道德義務,是因為他受益于所有其他人和他的社會合作,他更多地利用了共同體的資源。
但這兩種原本可以在人心中存在的道德契約,在這個社會邏輯上自敗的“權利”話語中,悉被消解。
而在道德上沒有形成契約觀念,也就難以讓人與人之間具有或恢復道德關系,挽救已經淪喪的道德。
現在,我們必須回到人性本身,以內省之心,打撈沉沒的“道德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