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的邏輯:這一年的公權力
石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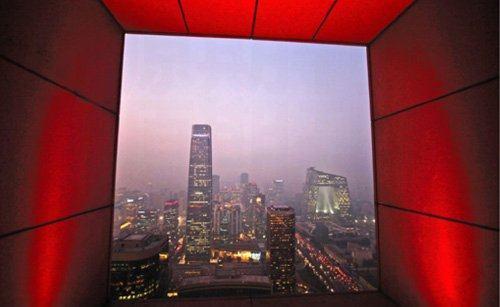
近年來,中國崩潰論和崛起論一直并駕齊驅,在中國迅速崛起的同時,總有一部分人在擔心,哪一天腳下的大地突然就崩塌。
2011年,這種心態的傳染性似乎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不安全感,對未來沒有預期,成為一種“存在”方式,驅動人們做出理性或不理性的選擇。
非常幸運,2011年馬上就過了。它不是中國社會劇烈痙攣的時間節點。它只是2010年,甚至更遠年代的延續。和它們一樣,它在繼續積累、惡化問題,具有問題發作時的一些癥狀,同時也在見證政府對民意期待的回應,做出解決問題的努力,或解決問題的姿態。
這一年,對政府而言,“政治認同”的壓力繼續加大。無論是司法不公、官員濫權、財政支出不透明,還是階層固化、物價上漲、房價畸高,都引發民意的進一步沸騰,質疑政府解決問題的誠意。而執政者則直面挑戰,通過政策實施、機構改革,甚至“合法性”來源的調整,做出應對,給出信心。
2012年不是傳說中的“世界末日”。即使有“末日”,那也是一種隱喻。無論如何,2012年馬上就來了。對于中國社會來說,肯定會延續2011年的腳步,但同樣有著它的變數。不確定性仍然是一個無法驅散的幽靈。
但很多東西是有跡可循的。2011年尤其如此,看到我們的過去,也可以看到遠方。
焦慮
2011年,對于中央政府來說, 一方面在為過去收拾似乎已不可控的殘局—它們總會間或發作,使政府疲于應對—同時,它也在為中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業謀劃未來。
“危機”彌漫中,中國一直在跟時間賽跑。民眾也在等待。2011年,是本屆政府在任期最后兩年中解決多年來“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最關鍵的時間段了。召喚民眾對未來的預期,成為2011年的“主旋律”。
這決定了2011年3月3日到13日在北京召開的“兩會”與往年有所不同。
不同之處在于,今年一系列影響巨大的政策,政府的諸多行為,都可以從“兩會”找到最初的聲音。對于其實誰都知道的問題要害,“兩會”也沒有遮遮掩掩。溫家寶總理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直接表示,“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于改革制度和體制”。事實上對于其它事情,也莫不如此。“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愿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這是政治承諾。
2011年的中國從“兩會”出發,迅速展開兩條路徑。一條是努力體現政治文明,一條是解決“民生”。它們共同的目的地是召喚“人心”,為執政,為政府權力尋找道德上的感召力。
這個過程,當然充滿曲折。
自從被拋入“現代性”的歷史階段后,人類社會就有一個特征:已經上路了,就無法回頭。
因為即使“現在”被證明有錯,在人們的心理上,對的道路、美好的東西也是在前方。“保守主義”遠非一種可以返回往昔的運動,而最多是一種鄉愁。
在這個大背景下,現代的政治,已經不可能假裝不存在一種其關鍵詞是“民主”、“正義”、“自由”的學問叫“政治哲學”。后者發出一個個“道德命令”,告訴前者,在制度上,在政府和人民的關系上,怎么做才是對的,怎么做是錯的。無論前者是否理睬后者,它一定感受到了后者給它的道德壓力。
如果說在人類歷史上,從“統治”產生的最初歲月里,“合理性”的問題就如影隨形,那么,沒有什么歷史時期,比之于現代—特別是比之于現在,在一個對于“民主”還處于“完善”進程中的國家更為明顯了。
推動
從2012年開始,2011年的諸多遺產一定會得到繼承。
在這件事情上尤其會如此:在高漲的民意與政府的互動中,“三公”經費,在大部分的中央政府部門那里終于不再是所謂的“國家機密”。
這一點很讓人遺憾:納稅人花錢讓一幫人為自己提供公共產品,后者拿去買車、出國、搞招待,在這一塊上用了多少錢納稅人居然不知道,也無法知道,只是憑一些研究性報告的披露得知是天文數字。
民主政治并不支持這樣干。對于民眾來說,引發的并不僅僅是不滿,而是憤怒。
高層順應民意,和民間聯手解決問題的景觀由此出現。從2011年的“兩會”開始,一直到下半年,人們聽到了兩種和諧一致的聲音。
一種在高層,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三公”經費零增長,并且要在中央部門的財政預算中公開。另一種在民間,以北京律師李勁松為代表,表明政府部門不公開“三公”經費違法,如果不公開,他將以公民身份起訴。
低估龐大臃腫、具有自己的利益本能的部門機構對于國家法律的消解能力是錯誤的。即使在近幾年來,財政預算的“曬賬本”早就在廣州等地出現,但公開“三公”經費卻無異于把一些部門機構的“小九九”曝于陽光下。政府部門當然想呆著不動。這個時候,需要有勇氣、理性的公民推一把。
到2011年8月底,“三公”經費公開塵埃落定:95個中央部門公開,而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和僑辦則以“國家秘密”的理由拒絕。
中央的示范之下,是北京、上海等市的“三公”公開,雖然真正的懸念要等到2012年,而離“透明政府”,我們還有很長的路。
但也許在多年以后,人們會懷想2011年的這件大事。在努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并且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的時代,在符合民眾期待邁出了一大步后,人們期待再繼續前行。
權衡
一種符合政治倫理的觀念可能當不了飯吃,像在印度這樣的民主社會,窮人并不少。
但缺失政治倫理,政府沒有盡到提供公共產品的義務,或權力過度干預扭曲市場,導致權力—資本聯手對社會的宰割,很多人很可能真的吃不上飯,至少,會被“相對剝奪”。
無數中國人當“房奴”,更多的人想當“房奴”而不得,就是這種“結構”的結果。
進入2011年后,很多人對于畸高的房價事實上已經絕望。加上物價上漲,在2008年“救市”政策的正面效應被權力—資本群體笑納后,他們在收獲其負面效應的苦果。激憤,卻又漠然。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民生不是合法性的來源,卻是它的保障和表現。在近年來的房價調控一次次淪為笑柄,而保障性住房也時出丑聞時,是到“下決心”的時候了。
2011年3月5日,今年有關“房子”的兩件事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同時被定調:保障性住房再開工建設1000萬套;繼續調控房產市場。雙管齊下,人們能夠有一間房子住的希望被激活。
從表面上看,今年的“房事”是一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開發商、炒房者、民眾的多方博弈,實際上不過是地方政府利益、政府短期利益與整體的“根本利益”的權衡。保障房建了多少,房價會如何調控,最終說了算的只是權力:如何在感覺有“穩定”預期時,仍繼續賺錢。
所以,盡管到2011年年末,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在中央政府多次施壓下已有所進展,限購似乎也已讓房價開始下跌,但考驗的標準可能只有一個:能讓權力形成“穩定”的預期判斷嗎?
從這個意義上,它們都沒有真正結束—尤其是房價調控,它的結束也將意味著民眾希望的冷卻。2012年,理應阻止這種情況的產生。
變化
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說法,“遵從一個統治的體系,比服從的事實更為重要”。就是說,對于政府而言,關鍵是要“以德服人”。
當民意對于政府權力該如何運作才能不損害公民權利具有強烈的呼聲時,在政策、措施方面回應是不夠的。它們是應急性的,而且是在一個變動的世界里,就生活領域進行的淺層次應急。
邏輯上,回應當具有這樣的內容:重新界定“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厘清“統治”和“自治”各自的領域。
有理由認為中央政府看到了這個問題。30多年的改革開放,近年來民間社會的成長,政府包辦一切已經不行。調整權力結構,可視為對民意期待的一種回應,目前政治上面臨諸多挑戰,正是既定制度下權力運作的直接結果。
所以,從幾年前就提出的“社會管理創新”命題,在2011年作為實踐四處開花。變味的不少,比如貴陽引入商人出錢“維穩”。但當然不乏靠譜,在改變權力結構的前提下展現了探索精神的。
6月,海南率先在全國成立省委群眾工作部,與省信訪局合署辦公。信訪“擴權”使其具有了解決問題的一些能力。8月,廣東成立省級社工委,省委副書記兼任主任,“社會建設”獲得更大空間。9月,安徽銅陵全面撤銷街道辦,政府權力和公共服務直達社區。10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治安”的強力色彩淡出,而“社會管理”的職能凸顯。
相對于在既定制度下像一架龐大機器一樣運行的整個權力體系來說,這些局部性的權力結構改變以及理念的調整,當然遠遠不夠—而且,在回應現實挑戰時,“控制”的預設巋然不動。
不過,這是政府在2011年送出的禮物。
超越
2011年11月底,廣電總局還給電視觀眾送出了一份暫時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益的大禮:從2012年1月1日起,電視劇中禁止插播廣告。而同時,明顯喧賓奪主而并沒有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符碼的娛樂節目,也必須明白它應該是什么地位。
風云變幻。但并非不能理解。
背景體現在10月15日到18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對“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強調中。這次會議在2011年召開,“風向”的特征尤其明顯。
也許可以這樣說:當中國思想界的“新左派”、“自由派”、“儒家”,還在為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是什么關系,以及該不該崇奉儒家而爭論不休時,務實的執政黨已經做出把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吸收、運用、創造的努力了。
與2011年力圖為中國社會、為公權力解套的諸多政府行為相比,它屬于一個更高、更遠的謀劃。
把“文化”作為一個國家政治、經濟上的一種戰略,執政者實際上看到了“現代性”深處的邏輯:越來越原子化的個體,其心理結構受到“文化”、“民族”這些抽象共同體的感召。一旦搭建起政治和文化在實踐上、心理上的聯系,文化認同就能轉化為政治認同—當然,這是理論上的。
但如果把黨和政府以“文化”來應對挑戰放入歷史視野,其意義并不一般。30年來,經濟發展帶來了政治認同,卻也固化了一個不利于政治認同,存在合理性危機的政治社會經濟結構。而“文化”對這樣的結構,正是一種超越。
可以看到,在2012年,它會邁開大步行走。2011年里隱藏的這些邏輯,將在2012年繼續演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