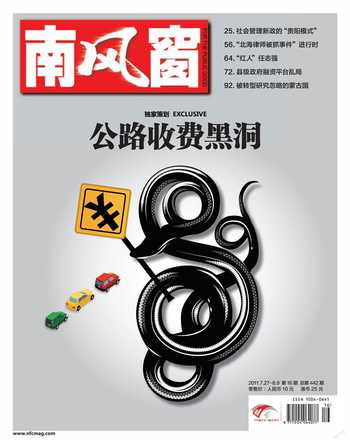認識一個新的社會政治倫理
張天潘
“氣”傳統上是一個哲學概念,或者說一直是一個很玄乎的概念,比如老子《道德經》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在我們的詞匯中,與“氣”有關的詞語有很多,“戾氣”、“義氣”、“憋氣”、“勇氣”、“生氣”等等,具體意義不一而足。
在《“氣”與抗爭政治》這本書中作者把氣具體化以及社會學化了,認為氣在中國鄉土傳統中既不是一種純生理的沖動,也不是一種純利益的反應。它是一種融合了本能與理性、道義與利益的激情,是中國人在人情社會中擺脫生活困境、追求社會尊嚴和實現道德人格的社會行動的根本促動力。它具體的含義應星將其解釋為:“現實性社會沖突與非現實性社會沖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種狀態,是人對最初所遭受的權利和利益侵害,而后這種侵害又上升為人格侵害時進行反擊的驅動力,是人抗拒蔑視和羞辱、贏得承認和尊嚴的一種人格價值展現方式。”
作者采用“氣”這個概念,含著克服當前國內學者研究中的兩種趨向(一是不加反思地移用國外的概念和方法,二是不帶任何理論地去做天眼調查,然后炮制各種概念)的努力。因為“究其實,人本身就是理性與情感兼備、時而為利益所驅動時而為道義所激的復雜動物,更何況,群體行動更增加了事情的復雜性”。這樣就可以“克服學界在抗爭政治研究中理性與情感、權利與道義之間的對立,克服在中國農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與鄉土派的對立,從而推進抗爭政治理論和鄉村社會的研究”。
該書通過幾個案例的深入比較分析,研究了中國鄉村農民群體抗爭行動(主要體現為上訪)的根源機制,分析了各級政府在維穩技術和策略上的轉變,并探討了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后果。
因為“氣”而引發的上訪與集體行動,在不同的人看來,可能有著不同的鏡像。在北大教授孫東東看來,“那些老上訪專業戶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其實這句荒謬話的背后,倒是也能反映出應星所說的“氣”,正是因為咽不下那一口“氣”,才屢屢上訪,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消氣即解決了問題)。但是,我們不能把分析停止在這個上面,而是應該更進一步,即問“這口氣”是誰給予他們的?他們又是如何讓氣悶在心頭,不惜代價地艱難上訪呢?
應星認為,中國農民也好、作為中國弱勢群體也好,它和西方人講的“為權利而斗爭”其實有不同的地方,它比較接近另外一個概念:“為承認而斗爭”,換成中國人的俗話講,“人活一口氣”,這個“氣”也好,這個“承認”也好,和利益、權利是不同的。在強大的傳統文化影響之下,中國人一直會把面子看得比生命更有價值,“委屈”、“冤枉”之類的氣,比直接的利益受損,或許更令人憤怒。
群體事件的升級,實際上是和集體行動的組織者或者牽頭者受到殘酷的打壓直接有關。基層政府本來是想用打壓的方式控制上訪、控制群體事件,但是效果恰恰相反,你越打壓,激起的反彈越大。因此,作者認為許多群體抗爭實際上不是為一般的經濟利益所驅,在某種意義上民眾是在為“氣”而斗爭,換句話說,他是在為獲得人格尊嚴和底線承認而斗爭。在作者看來,所謂“承認的政治學”,就是說政府在面對弱勢群體的集體抗爭時,不僅僅是從經濟上來解決問題,而是要保證他們最基本的人格尊嚴。這無疑與總理溫家寶提出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有著共同的價值認識,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社會政治倫理的漸漸浮現。顯然,我們不能在維穩的偏執型政治行為中,將那些“氣”都當作視而不見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