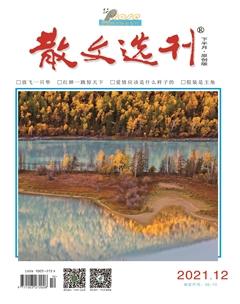我成功了
劉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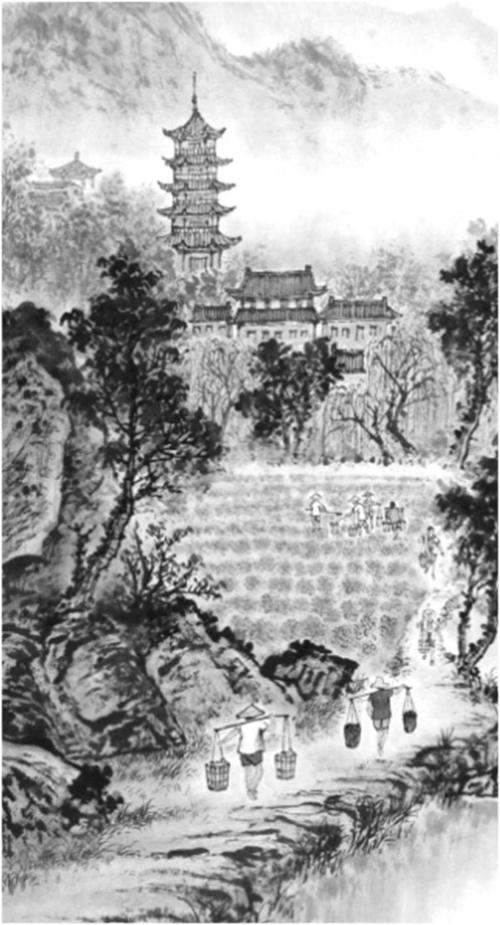
一次作家年會上,一位教育專家問我:“劉明,你的女兒那么優秀,你的教育秘訣是什么?”我笑著如實回答:“沒秘訣,只是叮囑她身體第一,精神第二,學習第三。”他笑了,隨即伸出大拇指:“高,這就是最絕的秘訣!”
說起我女兒,她的確不算優秀,學習成績一直是中等偏上一點點,每次考試成績出來,無論好壞,我和愛人除了鼓勵還是鼓勵,總是讓她自己總結經驗,找出問題根源,讓她形成好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態度。我總告訴她:你在爸媽的心里是最優秀的。
女兒上小學,每天回來,我從不過問她的學習和作業,因我自己是教師,要備課上課,業余時間還要讀書寫作,的確沒有工夫顧及。閑暇時和女兒談話,不知她懂不懂,我老是囑托她一句話:“玩耍是孩子們的天性,學習是孩子們的天職,你要學最好的別人,做最好的自己!”只是說說而已,關于她的學習成績及名次卻從不過問。出乎意料的是,小學畢業,女兒高分考入重點初中。
女兒升入初中,我仍在堅持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仍堅持在業余時間讀書寫作,對女兒的教導仍是那幾句話:學最好的別人,做最好的自己;身體第一,精神第二,學習第三,不爭第一。意外的是,數學老師找我愛人談話,說我女兒數學成績不太理想,專門讓她擔任數學班長后,數學成績仍在班里中等水平。咋辦?為了滿足數學老師的心愿,我與愛人絞盡腦汁想了個辦法,馬上找女兒談話:“我們想補習一下初中數學,想讓你每周二、四、六、日晚上給我們上課,在學校學什么就講什么,行嗎?”“行呀!”女兒一聽爽快地答應了。我隨即到商店買了一塊白板,還買了白板筆和板擦。
要給爸媽講課,女兒很認真,她總是認真備課。其實,我們的用意是一方面促使她學好當天的課,另一方面促使她溫習和穩固學過的知識。每當她給我們上課時,我和愛人都端端正正并排坐在女兒面前聽課,有時她講得不透徹,我們還故意像學生一樣舉手提問。這樣堅持了兩個多月,數學老師又讓我愛人進校,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愛人,說是我女兒的數學成績上去了,多虧她讓我女兒當了數學班長,哈哈,她卻不知我們在家里所做的努力,我愛人也沒有告訴她。
初中三年學滿,中考結束,女兒成績總分664 分,超分數線20 分考入市重點高中。我一直覺得高中三年如油煎,學生要耐得苦熬,尤其是到了高三,油熱到了至高點,必須頑強掙扎才能熬過去;高考如過鬼門關,闖過才有一片天。高中開學,我對女兒講:“高中是很苦的,尤其是你們的重點高中,人才濟濟,都是各校的精英薈萃,咱不和別人比,只要做最好的自己,盡心盡力即可,不必強爭第一。”說句良心話,我女兒天賦不高,她在小學和初中所取得的優秀成績,都是自己苦拼出來的。
高中第一次年級統考成績公布后,女兒心灰得要死,全年級3000 名學生,她考了1800 名,這是個天大的打擊,她實在承受不住了,她說:“我爸爸是市內教學名師,還是作家,我的名次讓我無顏面對老師,無顏面對爸爸教過的學生,我要退學,堅決退學!”又一個周日的下午,該送她返校了,她哭了,哭得很可憐,說啥也不去學校了,這可愁壞了我與愛人。
女兒要退學,她不是厭學怕學,而是羞愧自己沒考出好成績,這咋辦呢?我愛人愁得不得了,我只好耐下心來與女兒交談:“乖女兒,爸媽對你的要求,成人第一,成才第二,從來沒要求你考第一,也從來沒要求你將來考什么名校。在高中的緊張學習中,健康的身體第一,愉悅的精神第二,考試成績排第三。只要你努力了,我和你媽從不在乎名次。這只是進入高中的第一次考試,不算什么,爸媽相信你,以后考試你會一次次進步的,你要退學,是最不明智的選擇……”我和女兒談了一個多小時,她非常不情愿地同意返校了,我送她進校,結果遲到了……
三年的油煎生活過去了,高考成績公布后,我女兒超出本省一本成績20 分,我和愛人皆大歡喜。報志愿時,她多年受我的寫作影響,想學傳媒。由于我和愛人退休后,都移居云南西雙版納,于是,報了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輕松錄取。
近年來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有三分之一的人埋頭學習就蠻不錯了,我女兒卻是三分之一中的佼佼者,第一年就以優異成績獲得學校獎學金。
大一放暑假本該休息,她卻報考了中國傳媒大學的“輔修雙學位”,錄取后大一、大二暑假都要到北京上課,學習比學校功課還緊張。我和愛人一直想讓女兒注意休息,女兒的回答是:“我爸爸那么大年齡了,還在像小學生一樣,拼著讀書寫作,我現在年紀輕輕,正是拼搏求學的好時光,何樂而不為呢!”就這樣,女兒在大二又獲得省級獎學金,大三獲得國家級獎學金……
大學4 年,我對女兒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注意身體,注意休息,不爭第一,可她在大學4 年的學習中,每次考試成績都是年級第一名,2018 年至2019 年,榮獲中國教育部獎學金。大四,云師大對她保送免試讀研,她卻拒絕了,要報考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研究生,我和妻子既心疼又無奈。
考研復習期間,女兒收到通知,榮獲省級優秀大學畢業生稱號。報考中國傳媒大學讀研,只有一項選擇,不能有第二志愿,很苦很不容易。女兒每天清早6 點多起床進入復習,夜里11 點還在學習。我和妻子每天都在勸她多睡一會兒,她根本就不聽。
考試結束,她一邊在云南西雙版納電視臺實習,一邊等待成績公布。成績公布后,因疫情影響,三個月后等來通知,她考上了,但還要在網上視頻復試,這又是一個難關,她白天實習,晚上認真復習,終于復試通過,她被中國傳媒大學錄取了。女兒高興得跳了起來,我和妻子高興得抱著跳起了舞。
啊,現在我終于明白了,教育子女,身教勝似言教,逼著不如引著,安慰和鼓勵超越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