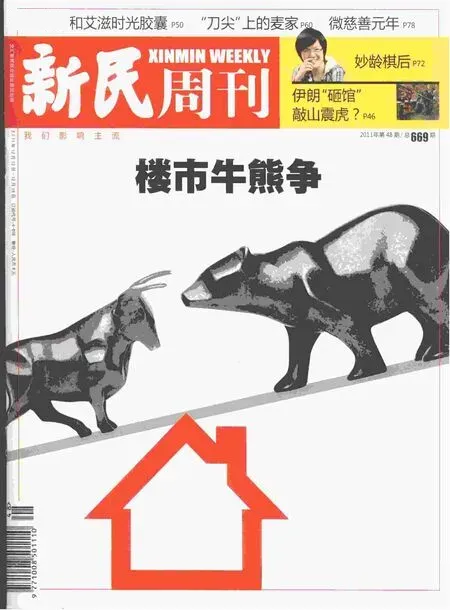梁志民:我不喜歡重復
王悅陽



第一次見到梁志民,是在臺北藝術大學的表演藝術研究室。作為該學科的帶頭人,梁志民不僅有著長期一線教學實踐,更有著一個頗為自豪的劇團——大名鼎鼎的果陀劇場。自1988年他白手起家算起,果陀劇場堅持朝著“精致舞臺劇”及“中文音樂劇”的創作路程邁進,率先將百老匯專業劇團經營模式帶進臺灣戲劇界,隨即掀起一股風潮。
如今,這股風潮逐漸由臺灣轉向大陸,隨著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大陸戲劇人這些年的探索與實踐,在梁志民看來既親切又陌生,相同的是夢想,不同的是道路。然而殊途同歸,懷著華人戲劇共同的繁榮夢想,梁志民越來越多地來到大陸,不僅在近年內巡回上演了《跑路天使》、《單身公寓2011》等作品,最近還將聯手知名表演藝術家金士杰在上海上演《最后14堂星期二的課》,更為老朋友蔡琴年底的演唱會擔任總導演。
“在果陀近25年的歷程中,原創音樂劇的比重約為全部創作的三分之一,不高也不低,我希望可以一直這樣維持下去。”事實上,臺灣戲劇界最早知道果陀劇場,正是因為原創音樂劇的大熱。1995年臺灣第一部完整規模的自制大型中文音樂劇《大鼻子情圣西哈諾》演出,突破臺灣劇場技術與演出人才的極限,驚艷觀眾、媒體及劇評家。1997年臺灣首演現場Live Band搖滾歌舞劇《吻我吧娜娜》,更是完全顛覆臺灣觀眾對戲劇的形式概念,造成熱烈回響,兩年內應觀眾要求連續加演三次,創單項戲劇演出場次最多之紀錄。1998年拉丁歌舞劇《天使-不夜城》更一舉創下單場觀眾數最多紀錄。至今持續創作結合東西方音樂的《東方搖滾仲夏夜》、第一部原創音樂劇本的《看見太陽》及經典老歌歌舞劇《情盡夜上海》等多出膾炙人口的中文音樂劇,使得果陀劇場成為臺灣音樂劇的絕佳代名詞,梁志民亦成為音樂劇在臺灣蓬勃發展的幕后第一推手。
在音樂劇開始于大陸蓬勃發展的今天,梁志民的經驗越來越為大陸同行所看重,三年來他常常往返于臺北與上海之間,參與音樂劇高峰論壇,與國內從業者切磋交流,更在上海開設了自己的公司,專門負責果陀劇團作品在大陸的演出。“臺灣與大陸戲劇界的風格各有千秋,從現在來看,大陸音樂劇的發展走的是橫向移植的道路,而臺灣音樂劇從一開始就堅持走原創道路。我想,這是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與梁志民面對面,言談間最大的感受,莫過于其多年來所積累的豐富制作經驗與營銷手段。
堅持原創
說起果陀劇團的創辦,其實源于梁志民的畢業創作《動物園的故事》。作為賴聲川的得意門生,梁志民此作受到極佳的好評,這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憑借著滿腔的熱情以及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在當時戲劇生態并不成熟的嚴峻形勢下,梁志民一手創辦了果陀劇團。
從最初的小劇社到后來逐漸登上大劇場,成為一家頗具名氣的中型劇團,果陀并非一炮而紅的幸運兒,道路走得曲折而艱辛。1993年,由于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梁志民踏上了赴紐約研習導演創作的道路。也就是在音樂劇風靡的百老匯,梁志民第一次看到了《貓》,親身感受到身段及肢體語言的運用是可以如何地達到極致,從此他愛上了音樂劇。回到臺灣不久,憑著觀摩音樂劇的經驗與所學到的管理手段,梁志民跳開了“引進”這一看似不可或缺的一步,直接來了一次大膽的“移植”。果陀劇團隨著時間而成長,逐漸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當時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張雨生。”梁志民介紹,張雨生不但是自己的工作伙伴,也是很好的朋友。當年果陀不少贏得良好票房和口碑的音樂劇,都出自這位才子的手筆。“張雨生的過世對我打擊非常大,他的音樂素養非常高,是個很適合做音樂劇的人,原來我們還有許多做音樂劇的計劃,現在都只能擺在心里。”而另一位合作伙伴蔡琴則同樣是梁志民的好友。“果陀第一次來大陸演出的音樂劇就是蔡琴主演的《天使不夜城》,一般歌手排演舞臺劇兩三個月就差不多了,而蔡琴整整投入了九個月的時間。”正是由于主創們的傾心投入,使得音樂劇在臺灣邁開的第一步走得頗為成功。“這和我的個人思想有關,我不喜歡重復。創作時間本來就有限,只會模仿就不會創造。更何況市場和觀眾是需要培養的,他們一旦習慣了舶來品之后,就真的很難接受原創的了。這是我當初開始做音樂劇至今一貫的堅持與要求。”
說起當今兩岸三地蓬勃興盛的音樂劇創作演出現狀,梁志民在肯定之余仍然堅持“人才培養是最重要的”。在他看來,再好的藝術院校,也很難培養出許多全方位的音樂劇專業人才。既要能唱,還要會跳,更要善演。“只有靠時間。急不出來的,演員需要磨練,導演需要實踐,大量的訓練與演出機會之外,更要有良好的物質條件作為后盾,保證留住人才。假以時日,有經驗的專業音樂劇演員會帶動這一藝術形式在中國的全面發展,起到酵母的作用。”除了人才,音樂創作更是至關重要的一點。“音樂劇的靈魂就是樂曲,現代化的舞臺技術其實倒并非是最重要的。以果陀的經驗來說,既有流行樂出身的作曲,也不乏古典音樂的創作人才。多種風格,多元嘗試,要從劇本內容和演員特長出發,不拘一格地為我所用。”從大音樂環境中找尋人才,或許比單一的音樂劇作曲來得更有效。
“臺灣的音樂劇發展還是很幸運的,20多年的積累,腳步已經站穩了。每次果陀上演新的音樂劇,票房總能有所保證。其實一開始,對于音樂劇、歌劇和歌舞劇,大家的概念是十分混淆的。但通過不斷創演劇目,配合引進一些國外的優秀作品,觀眾的視野打開了,自然而然就了解了,接受群體也相對穩定了。”對于大陸音樂劇的興起,梁志民以臺灣為例,強調了時間與實踐的重要性。“其實我是一個不太回頭看過去的人。我喜歡向前看,喜歡和一群有夢想的人一起合作的感覺;當你有夢想的時候,就可以往前進,或快或慢,總是可以往前走的!”對梁志民而言,將一個原始的概念變成一出完整的舞臺劇呈現在觀眾面前,這是他非常享受的一個過程。“一出戲幕拉起來開始有了生命,而幕落下來就再也找不到另一出與之一模一樣的作品了。劇場藝術是一個時間藝術,也是一個空間藝術,我對于這種把瞬間變成永恒的藝術非常著迷!”
重視經營
從近年來巡回大陸好幾輪久演不衰的《寶島一村》到三度來上海依舊爆滿的《瘋狂電視臺》,從“屏風表演班”的《三人行不行》到李國修即將來到上海演繹的《京戲啟示錄》,還有果陀帶來的《最后14堂星期二的課》。2011年幾乎成了臺灣話劇在滬演出蔚然成風的一年。正是大陸演出市場的巨大潛力,才讓這一風潮成為現實。而與大陸文藝團體商業化進程尚在起步階段不同,臺灣地區的文藝團體已自負盈虧運作了20多個年頭,熟知市場運作規律的他們對于市場的嗅覺更靈敏,懂得如何在市場風向標出現變化前拔得先機。故事或許簡單,但手法一定不一般,這正是為什么賴聲川、李國修、梁志民等臺灣地區知名話劇導演一直在追求創新、改變的原因。因為他們明白觀眾一旦看膩了某種形式的話劇,市場必然將那些沒有改變的人拋棄。
“我想,用一句話來形容果陀的經營方針,‘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果陀不僅在音樂劇創作上有著大量值得大陸同行借鑒學習的經驗,在其宣傳經營方面,則更是走在文化體制改革進程中的大陸戲劇人極大的參考。
“在經營果陀劇團的初期,我也看了許多經營管理的書,因為經營一個劇團的風險很高,而當自己把經營的經驗學會了,更專業的人出現了,就把事情交出來,我只要負責聽取結果,確認是不是當初我要的構想具體呈現即可。”梁志民認為劇團發展走向企業化經營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在文化日趨多元化的今天,劇場究竟還有多大的存在價值,一直是戲劇人關注思考的問題。梁志民認為,劇場這一形態之所以可以存在兩千多年至今,基本上有幾個特質。“只有了解這些特質,才會讓你思考如何作為一個劇場的行銷人員把劇場的一些產品行銷出去。”劇場第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質就是不可預測性。“果陀需要仰賴觀眾的支持,我們必須努力維持彼此之間的良好互動;不同于一般的企業團體,我們永遠在販售一個觀眾不知道的東西!幕沒拉起來,沒有人知道會出現的將是什么!所以行銷人員要去想象觀眾要的是什么,從其中找出與觀眾互動的接點。同時,你不能因為其不可預期就亂做、夸張、吹牛。表演藝術最要不得的就是這一點。如果一個劇團被觀眾否定之后,接下來的行銷會變得很難做,所以這是舞臺劇經營的一大禁忌。”
另外,當行銷人員在策劃一出舞臺劇的主軸時,必須要想到這出戲某種程度上的統一性。“概而言之,就是這出戲到底是喜劇還是悲劇?你要捕獲的是喜歡看喜劇的觀眾還是喜歡看悲劇的觀眾?還是喜歡看悲喜劇的觀眾?還是喜歡看歌舞劇的觀眾?你不能一個網撒下去什么魚都要撈,那最后的結果就是你撈了一堆雜七雜八的、亂七八糟的海藻而已。我們的這個網是要經過設計的。”
除了在戲劇本體上的探索,果陀在各種的行政、宣傳、電腦資源上的努力一樣做得認真。“我們每次所做的戲到最后都會有一個結案的file,記錄得非常詳盡,總共開了多少次記者會,每次記者會有多少票房的累積,上過幾個媒體,對票房有多少收益……這些東西都被完整地記錄下來。之后在做新戲行銷的時候,第一想到的就是參考過去的資料跟資源,第二就是根據這出戲的特質做不同程度的分析。”
當然,一出戲的成敗,社會影響、經濟狀況同樣至關重要。表演藝術既有娛樂性也有教育性,但所謂的“食衣住行育樂”,戲劇永遠是排在第五第六位。“也正因此,當社會開始復蘇成長的時候,藝術永遠是排最后的,當經濟開始往下滑的時候,表演藝術最先受傷。所以作為一個行銷人員你要會觀察、判斷和分析。我們劇場的行銷人員每天都要看股市,看股市是為了要了解整個社會經濟的動向,他要知道有哪些企業是將來我們可以去合作的對象。”與云門舞集、表演工作坊等知名表演藝術團體一樣,果陀劇場除了訂閱表演藝術專業雜志之外,還會大量閱讀兩岸三地財經、新聞類雜志、報紙,“因為表演藝術最原始的點就是在這個社會里面。所以當我們在定票價的時候,第一要參考的就是目前現階段整個經濟的浮動。第二,要根據這個產品的本身價值,參考市場普遍價格。也就是說,便宜要有便宜的便利,貴要有貴的質感,做到物有所值。”
在臺灣現階段的表演藝術市場中,常常會聽到一些爭論,即所謂商業劇場跟非商業劇場的討論。梁志民認為,“我可以這么說,在臺灣根本沒有商業劇場。商業劇場的意思就是本小利多,你演一出戲可能成本1000萬臺幣(約人民幣250萬左右),但是你放在那里演三年,你可以賺3億,這就是商業劇場。百老匯、倫敦就屬于這種劇場。但臺灣根本沒有這種環境,所以在臺灣所有的劇場都應該被稱作精致手工業,它沒有辦法復制,只能花兩三個月的時間,七搞八搞,大家絞盡腦汁做出一個漂漂亮亮的東西放在那里,然后演個十天八天就結束了,所以它根本就不夠資格叫作商業劇場。但是要做出這樣一個精致的東西,它背后一定有付出的成本在,所以我們需要賣票,這就是商業劇場與非商業劇場的迷思,那么既然賣票,既然有了商業行為,你就要顧及到消費者的反應,不要為了所謂的實驗、先鋒或創新,破壞了戲劇觀眾群體的熱情。”事實上,何止臺灣如此,對于大陸話劇題材雷同、質量平平、過度追求小制作娛樂化的傾向,梁志民的觀點,同樣值得我們思考與反省。或許,如何擁有更健康、良好的發展,才是兩岸戲劇人共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