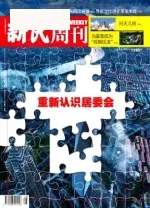茅臺拍賣:博傻開始了?
任蕙蘭

“茅臺”成了熱詞。貴州省長在記者會上談“茅”色變,各地拍賣會上老茅臺頻破百萬。前者只是微博上的作料,后者卻牽動了廣大群眾的財富神經——未來姑娘們的擇偶標準,會不會將“有房有車”再加一條:“有陳年茅臺”?
眼看茅臺身價飛升,不知聶衛平是何心情。2001年國足沖進世界杯時,有記者通過電話采訪了鐵桿球迷聶衛平。老聶表示,他會把一瓶出廠70多年的茅臺酒拿出來送給國家隊,以了卻他多年的心愿。如今一瓶1958年的茅臺拍出了100多萬元,紅軍長征時期的老茅臺該是什么價?茅臺身價飆升之前,老聶就表示很后悔為中國男足開了那瓶酒:“瞧瞧中國男足踢的什么球?為他們開那瓶酒太不值得了!”
“五幾年的老茅臺,別說跑幾兩酒,就算一只空瓶子,不上拍賣臺,圈子里內部交易的價兒,絕對超過一件清中期的中件瓷器。” 資深茅臺收藏家趙晨如是說。趙晨是《茅臺酒收藏》一書的主編,他說,就在幾年前,老茅臺只能在做禮品回收買賣的酒販子手里倒騰,連正規典當行的門都進不了。
茅臺火了,但未必所有人都買賬。“30年前的茅臺能找,300年前的茅臺呢?只怕早就被喝下肚了。”一位金融界人士語帶不屑。雖然標著個古董的價兒,但茅臺歸根到底就是件消費品。
老茅臺走上拍賣臺,成為一件有“金融屬性”的投資品,這是不是新的博傻游戲?現在人們很難斷言。但可以肯定的是,許多普通人家的玻璃櫥空了。
從玻璃櫥走上拍賣臺
你喝,或者不喝,茅臺都在漲價。
上海人老鄭默默注視著自己的三瓶茅臺,心情有點糾結,好像在看三張存折。
去年6月,一瓶1959年產的“五星”茅臺在北京拍出103.4萬元,老鄭把家里的茅臺從客廳移到朝北房間,避光避暑。緊接著秋拍中,1958年的茅臺酒在北京保利以112萬元成交,中國嘉德拍出91.8萬元,老鄭連忙給每一瓶茅臺加了個套子。不久前,1958年的茅臺在杭州拍出145.6萬元的天價,老鄭開始琢磨電視里專家教的用蠟密封酒瓶蓋。
老鄭不愛喝高度數白酒,頂多在老婆燒了好菜時啜兩口黃酒,但和大多數上海人家一樣,玻璃櫥里必須有幾瓶茅臺“扎臺型”,這是打結婚起的傳統。
三瓶酒都有些來歷,一瓶是建軍80周年紀念版茅臺;一瓶是20多年前精品商廈開張第一天,老友購來送給自己的,當時袋子里還有一張發票——7.5元一瓶。另一瓶是1974年的“飛天”,“文革”初“飛天”商標因“封建色彩”獲罪,外銷茅臺酒一律改成“葵花”標志,70年代初“飛天”才重見天日。老鄭托人打聽過,1974年的“飛天”如今值三四萬。
老鄭一直想把茅臺藏到家有喜事時品嘗——比如寶貝女兒的婚事。但以茅臺的漲速,到時喝的可能不是一瓶酒,而是十桌酒席的代價了。“再漲一漲就拿一瓶去拍賣。”老鄭思索著,但建軍節那瓶是紀念版,精品商店那瓶象征老友情義,1974年的“飛天”有歷史意義,哪一瓶都不舍得割愛。
“總不見得要靠賣酒過日子。”老鄭試著壓住自己蠢蠢欲動的活絡心思,但顯然不太管用,“如果漲到50萬元一瓶,可以給女兒的婚房付個首付了。”
“兩場拍賣會征集的200多瓶茅臺,100%來自老百姓家里。”上海國拍副總裁范干平告訴《新民周刊》。更確切地說,全來自老百姓家的玻璃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市民結婚時興在婚房里放“26條腿”,其中有4條腿屬于玻璃櫥。
“上層是三面透明玻璃,下層是木箱。上層主要放茶具、工藝品、酒類等,倘若能夠在里面放上兩瓶茅臺酒,就是最體面的事了。”
范干平觀察發現,茅臺送拍者都是差不多年紀,五六十歲的樣子,70年代時他們也就是二三十歲的小青年,正是結婚的當口,家里的茅臺也是結婚時置辦下的。“上海人節儉,又不喝高度白酒,于是大量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出廠的茅臺酒就這么沉淀在上海人家里。”
“當時茅臺不好買,但是上海人講究面子,有海外關系,家境好的,就用僑匯在商店買,家里有人在部隊工作的就帶幾瓶回來,還有在貴州插隊的知青也會帶茅臺。”范干平還記得自己頭一次喝茅臺,就是在貴州插隊時,不過嚴格算不能叫喝茅臺,一瓶酒十五六個人分,兌上四五斤土酒,喝完了根本咂不出國酒的滋味。
范干平記得,上海首場拍賣中最老的一瓶茅臺,就是一個年過八旬的貴州老知青送來的。上世紀60年代初,他支援內地建設,在貴州省清鎮發電廠工作,直到70年代中期退休回到上海。1966年,小伙子回上海探親前,在貴陽市用3.50元人民幣買了一瓶茅臺,還買了一瓶竹葉青,全都孝敬給了岳父,岳父喝了竹葉青,把茅臺留了下來。幾十年過去,岳父已去世,小伙子也成了老人,他在收拾岳父遺物時找到了這瓶酒。
初見這瓶50年代末的“車輪”酒時,范干平按捺欣喜,利用曾在貴州工作、對當地情況熟悉的條件,旁敲側擊問起老人當年工作的地方、買酒時貴陽市街道的情況,以印證酒的來源的可靠性,老人一一清晰作答。“除了具體出廠時間已經模糊外,其他茅臺酒特征保存得不錯。”
同在貴州插隊的上海作家葉辛也送了兩瓶1985年的茅臺酒參拍。80年代,葉辛任貴州文聯《三花》雜志主編,有一次受邀到遵義市給領導干部講文學知識,講座結束時,主辦方要向其支付50元授課費。當時葉辛一個月工資才80多塊,50塊錢無疑是一筆巨款,葉辛是個厚道人,想想對方車接車送,管吃管住,沒好意思要。等他回到省城貴陽市,發現車上有兩瓶茅臺酒,大概是充作授課費的,那個年代茅臺7.5元一瓶,兩瓶酒價值15元。葉辛把這兩瓶茅臺酒一直保管至今,一瓶酒的市場估價已經漲到4萬多元。
老百姓急著把家里的玻璃櫥翻空,莫非看準茅臺漲到頭了?
“上海市民很實際。白酒不適合收藏,因為普通人不懂怎么去貯藏茅臺,放在玻璃櫥里陽光燈光直射,密封不好,酒都揮發了。另外外包裝如果沒保護好,酒的價值也會打折扣,所以與其毀了不能喝,不如趁市場好賣了。”范干平談到。
誰來接盤?
從玻璃櫥到拍賣臺,下了拍賣臺,老茅臺的歸宿在哪里?老百姓在心里勾畫著“茅臺收藏者”的神秘肖像。
“來拍賣會的三分之二是茅臺收藏家,經常是三三兩兩相伴而來。”范干平認為,收藏家有專業的酒窖、地下室來貯存茅臺,懂得用蠟密封酒瓶,甚至是真空貯藏,茅臺在這些人手里更具升值空間。
“對,上次趙晨也去了。”
趙晨出現在哪個拍賣場,在圈子里可以算一件新聞,不僅因為他已經擁有了幾乎沒有斷代的茅臺藏酒,更因為他在2011年1月2日在南京舉辦的一場拍賣中,以146.5萬的價格拍下一整箱12瓶1985年的“醬瓶茅臺”。
業內人士介紹,醬瓶茅臺是上世紀80年代的特殊產物,為當年國宴的特供酒,相當于古代的“御酒”。這種茅臺“瓶外施醬色釉,瓶底露胎,制作規整”,藏界稱為“醬茅”。
趙晨還記得,這箱酒起拍價只有25萬元,經過數十輪的激烈競價,最終以130萬元成交,加上傭金達到145.6萬元。“我本來預計50多萬拿下,可東西一上了拍賣臺就控制不了了。”
說到底,這已經不是幾年前了。
從90年代開始收藏各種茅臺,趙晨看著這個市場逐漸興起,打交道的對象,也從民間藏友,酒販子,到現在的拍賣行,典當行。茅臺客的搜酒地圖上,最重要的是貴州和北京。
“老工業基地集中在東北三省,茅臺酒廠以前在東北有很大的配額,東北的茅臺都集中到北京。北京本身政治氣氛濃厚,領導愛喝茅臺,部隊也都是以茅臺宴客。現在北京專職和業余的酒販子至少有5000人。”
“以前叫酒販子,現在叫專業搜酒人士。”看來茅臺漲了,從業人員的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
2000年以后,專業藏友涌進了茅臺市場,據趙晨介紹,隨著網絡發展成熟,2005年有藏友在山東泰安創立了華東煙酒網,茅臺酒友可以在網上交流交易,現在專業的藏酒論壇已經發展到五六個。
這一切都是茅臺熱拍的前傳。
茅臺第一次走上拍賣臺是在2004年10月,茅臺酒廠在某個活動上拍賣了一瓶“葵花”酒,以10萬元成交。“以前是比如普洱專場順便拍幾瓶茅臺,量很小,專門開茅臺專場是最近幾年的事。”
“懂酒的人去民間搜,不懂的上拍賣會拍。”趙晨的收藏中來自拍賣臺的數量很少,偶爾會在藏友圈子里交換酒,“價格比拍賣會低一些。”但更多的還是自己下去淘酒。
2006年,趙晨去貴州淘酒,聽說有位省政府的退休老干部家中有瓶老茅臺。趙晨登門拜訪,可老人就是不愿將酒拿出來。無計可施,趙晨只得懇求著說看一眼就成。架不住趙晨死纏活磨,老人最終拿出了這瓶酒。趙晨一看,眼睛都亮了,竟是一瓶1956年的繁體“五星”。他將這酒的名稱、特點、背后的典故一一說來。老人聽后立馬拍板:這酒給你算是最好的歸宿。
“一瓶七八十年代的酒當時只要1000多,現在漲到三四萬,這瓶酒老人家開口要兩萬,我說這酒肯定會漲,你以后肯定會后悔,我多給你一萬,三萬成交。現在已經漲到150萬。”
5年上漲50倍,回報率就連房地產行業也望塵莫及,熱錢嗅到血腥味,迅速擠入這個市場。“茅臺市場剛剛興起,價格還很便宜,吸引了很多投資者,用專業術語來說,就是逢低吸納。”一位業內人士分析。
“全國茅臺藏酒超過一萬瓶的藏友,好幾個是做房地產的。”趙晨透露,“不過他們未必完全是為了投資,對這些人來說,一頓宴請開一瓶幾萬塊錢的‘三大革命或‘地方國營,既有這個需求,也完全消費得起,這批人有些是終端買家。”
茅臺的“金融屬性”
老茅臺還能熱多久?沒人能說清楚,但至少可以掐指算一算,還剩多少老茅臺能炒上一炒。
“上海這座城市,藏著兩三千瓶老茅臺是正常的,茅臺專場拍賣還可以做幾次,等民間藏酒全部進入市場,市場有一定量以后就會有流通,茅臺拍賣可以穩定在一年做兩次左右。”
此前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上世紀70-80年代散落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茅臺酒數量大約分別在3萬瓶(70年代)、4萬瓶(80年代),算上保存不善毀掉的酒,以及在各地拍賣中消耗的,民間藏酒已快探底。
各方數據強調了老茅臺的稀缺性,使得投資合理化。但是當一個市場充滿噴薄欲出的投資欲望時,數據支持并不重要。1958年和1959年的茅臺拍出天價,盡管這兩年正是“大放衛星”的時候。事實上,茅臺走上拍賣臺的一刻,已經從一件消費品變成投資品。
“投資品具有某些金融屬性,比如是否容易變現,以前茅臺酒變現渠道很少,只能找禮品回收,但現在許多典當行會收陳年茅臺。”一位業內人士分析。
老茅臺一旦扯上“金融屬性”,離不開“大鱷炒作,散戶吃套”這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定律。或許已經有人產生了一個陰謀論的想法:老百姓忙著翻遍家里的玻璃櫥,搭上這一輪上漲的便車,守著幾窖老茅臺的資本大鱷笑而不語。
玩過“紅心大戰”的人都知道,當把牌面上的紅桃都收入囊中,就掌握了牌局的主動。轉換成經濟學定律,誰壟斷了市場上所有老茅臺,誰就獲得了定價權。
如果把這個設想推進一步,拍賣會上熙熙攘攘,也許在某個無人知曉的地方,靜靜地躺著一批陳年茅臺,等待著市場價格登頂。“經銷商處留著陳酒的可能性不大,但茅臺廠如果放出一批存貨,市場價格會產生怎么樣的波動?”這樣的邏輯推理自有道理。
“據我所知,茅臺酒廠也沒有裝瓶的陳年茅臺了,就連樣本也沒有保存。”趙晨坦言,“只有酒缸里還有陳年茅臺,用來勾兌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