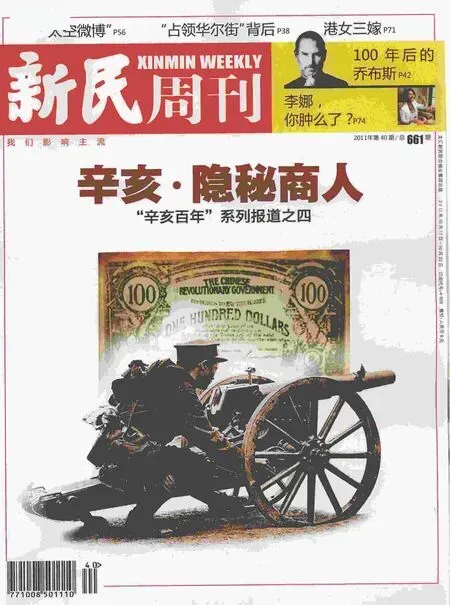辛亥元老鄭烈與曹禺的翁婿之交
曹樹鈞



鄭烈,辛亥革命元老,我國杰出戲劇家曹禺第一位夫人鄭秀的父親。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曹禺在很長一段時間,對他與鄭烈的交往,諱莫如深。從1948年至1988年,曹禺與鄭烈的音訊中斷了將近半個世紀。上世紀80年代,筆者在從事文學傳記《攝魂——戲劇大師曹禺》創作和第一部關于曹禺的電視傳記片《杰出的戲劇家曹禺》的拍攝過程中,多次訪問鄭秀,并采訪了解這段歷史的鄭秀的表妹沈澧莉、表弟沈祖戡,才重新打開了鄭秀多年諱言的記憶,今年欣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特將塵封已久的這段史實公之于眾,以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驅韃虜黃花崗九死一生
鄭烈的女兒鄭秀原系清華大學法律系學生。年輕的女大學生鄭秀,身材苗條、面容清秀,一副大家閨女的儀表,是清華園的“校花”,追求她的男生不勝枚舉。比她高兩屆的曹禺,是清華外國文學系的學生。他久仰鄭秀的芳名。一次初見,便與她有一種親近感,狂熱地追求她。
起先,鄭秀看不上曹禺,覺得他個子太矮,又是一個文科生(鄭秀希望自己找一個理工科大學生,不要兩個人都學文)。
一次,曹禺與鄭秀在風景如畫的清華園散步。走著走著,忽然左臂夾著的一疊書散落在地上。曹禺忙蹲下去撿書。慌亂中,一副眼鏡又掉在地上。鄭秀見他的窘狀,禁不住咯咯笑了起來,忙幫他將眼鏡撿起來。這時,她忽然發現曹禺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閃現出異樣的光彩,蘊含著深邃的智慧之光,似乎有一種攝人魂魄的美。鄭秀凝神注視著曹禺,曹禺也深情地看著她。
從此,兩個人的關系發生了十分微妙的變化。原先兩人散步,是曹禺一人談的多,鄭秀很少插話。自從“撿書”事件之后,似乎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她的芳心。鄭秀開始主動談她的家庭,她的經歷,尤其喜歡談寵愛她的爸爸鄭烈。于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辛亥元老的形象,在曹禺的腦海中越來越清晰起來……
在散步過程中,鄭秀滔滔不絕向曹禺談起她父親鄭烈的往事。
“我的父親鄭烈,字曉云,福州人。他和辛亥先烈方聲洞是至交,還是親戚。他們都是日本留學生,第一批同盟會會員,在孫中山先生主持下,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宣統三年(1911年)父親與方聲洞一起,在同盟會最高軍事指揮員黃興策劃下參加廣州起義。
“起義缺乏武器,方聲洞、鄭曉云等商議,事先買了一口大的楠木棺材,將武器放在空棺內。進廣州城門時,清官喝令開棺檢查。方聲洞急中生智,謊稱開棺鑰匙忘帶在身邊,同時又給清官塞了一些好處費,這才將棺木運進城里。不料起義時,寡不敵眾,方聲洞、林覺民等許多人在戰斗中犧牲,方聲洞身中數槍。也有的人受傷被俘慘遭殺害。廣州起義共死難烈士86人,事后收拾烈士遺骸72具,合葬在廣州城郊黃花崗,這就是民國史上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聽父親說,在這次起義中,他幸免于難。他和辛亥元老胡漢民一起從死尸堆里爬了出來。胡漢民抱了一把胡琴化裝成京劇琴師,父親化裝成郵差,才逃出封鎖線,撿回了一條性命。
“方聲洞視死如歸,舍生取義。廣州起義前一夜就寫好兩封遺書,一封給父母,一封給妻子王穎。在給妻子王穎的遺書中,方聲洞寫道:‘刻吾為大義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無憾矣。并叮囑妻子他死后要‘教旭兒長大一定要愛國。
“旭兒指的是方賢旭,他生于1910年,和你同年。二姨罹難時,他剛滿周歲……”
聽著鄭秀滿含深情的描述,曹禺對尚未謀面的未來岳丈及滿門忠烈的方氏一家充滿了崇敬之情。
撰史劇《精忠柏》翁婿暢論
1934年~1936年,曹禺的兩部大型話劇《雷雨》、《日出》先后發表,轟動全國。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后改為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簡稱“劇專”, 多次邀請曹禺來校任教。1936年秋,曹禺終于來到南京任教。在鄭秀的引見下,拜會了仰慕己久的鄭老先生。老先生見他彬彬有禮,又能侃侃而談,益發喜歡。不料年過半百、喜歡舞文弄墨的鄭老先生竟對話劇創作也發生了興趣,試著寫了一部多幕話劇《精忠柏》。他讓秘書用毛筆認認真真抄了一遍,親書“請家寶斧正”幾個字,送給曹禺過目。曹禺一看啼笑皆非,劇本寫得不倫不類,既不像京戲,又不像文明戲,但曹禺仍恭恭敬敬地提了一些修改意見。鄭老先生看了連連點頭:“講得極是,講得極是。”
為了進一步修改劇本,同時也為了進一步加深對曹禺的了解,鄭烈多次邀請曹禺到他寓所,南京山西路一幢帶車庫的洋房里詳談。
鄭烈的《精忠柏》寫得很長,取材于宋朝岳飛抗金的歷史題材,從岳母刺字、受宗澤重用、朱仙鎮大捷,一直到十二道金牌召回、風波亭遇害等情節,都寫得十分詳細。劇中出場的人物不少,除岳飛、岳云等主要的正面人物之外,秦檜、王氏等賣國奸佞也都全部出場。鄭烈當時任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負責檢察署、監獄等部門,他又是辛亥元老,因此曹禺在他面前十分謙恭,敬稱為“伯父”。但談到劇本意見,他也較坦誠。他說:“伯父,您的這部劇作好在寫得嚴謹,主要歷史事件、主要歷史人物處處有出處。情節發展原原本本,脈落十分清楚。不過,劇本本身可能長了一些,搬上舞臺的話,至少要七八個小時,才能全部演完。您如果允許的話,我可以冒昧幫您再作一些刪削。”同時,曹禺又謙虛地問:“劇本為什么取名‘精忠柏?”
“這是因為杭州西湖的岳廟中,樹枝都向南傾斜。后人認為這是岳飛堅決抗金的精誠感召所致,故贊譽為精忠柏。岳廟久經滄桑,此事是否屬實,已難稽考。但我幾次去過杭州,岳廟內仍有精忠柏亭。亭中陳列若干柏樹樹段,據說精忠柏已枯萎而死,留此以供后人憑吊。我覺得這是國人對岳飛精神的敬仰之情,故取名‘精忠柏,你意如何?”鄭烈問曹禺。曹禺極口稱贊,兩人共同贊譽岳飛還我河山、精忠報國的精神。
“很有深義,它象征了岳武穆的精神,一種堅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悲劇精神。”未來的翁婿越談越投機。這段時間,曹禺經常陪鄭烈吃飯、喝酒、聊天,親密無間。
1987年,鄭秀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對筆者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父親后來喜歡曹禺甚至超過了喜歡我。”當時,他們在南京由鄭烈主持訂了婚。
1937年10月,在戰亂中,在雙方父母的電報祝福下,曹禺與鄭秀在長沙喜結連理。
《三人行》再頌岳飛
當年在南京的日日夜夜,曹禺與岳丈暢談話劇《精忠柏》,岳飛留給他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1943年1月,在重慶,《戲劇月刊》創刊號上“特刊稿件預告欄”中,公布了曹禺創作的有關岳飛的歷史劇《三人行》即將問世的消息,曹禺為此還寫了一篇《創作經驗談》。這年2月,曹禺又應邀在上清寺儲匯大樓重慶儲匯局同人進修服務社作了一次題為《悲劇的精神》的學術講演。在講演中他認為莎士比亞筆下的普魯托斯,中國的屈原、諸葛亮、岳飛、文天祥是有著可歌可泣悲劇精神的人物,處于抗戰時期的中華民族要存在,“中國要立足于世界,我們要救亡,要反抗”,就要弘揚這些真正的悲劇人物雄偉的氣魄,他們的勇往直前、堅持不懈的悲劇精神。
從30年代到40年代,曹禺希望民族富強、國家要立足于世界的崇高理想始終是與岳飛和鄭烈的心是相通的,與辛亥先烈的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
《三人行》的創作,在藝術上曹禺嘗試詩體劇的探索。早在南開中學學習期間,曹禺就將自己省下來的零用錢買了英國著名女演員愛倫·特雷主演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一劇的錄音唱片。他反復聆聽這些唱片,對莎士比亞詩劇出神入化的藝術魅力佩服得五體投地。在《三人行》中,他想嘗試一下這種詩體劇的創作,用詩一般的語言頌揚岳飛這樣一位具有崇高悲劇精神的民族英雄。
1943年6月,在重慶火爐一般的季節里,曹禺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北碚復旦大學附近的一個小村子里,開始了《三人行》的創作。
關于這部已經預告的歌頌岳飛的劇本,曹禺這樣描述道:“《三人行》是岳飛、宋高宗和秦檜的故事。在重慶只寫了一幕,太難了。全部是詩,沒有別的對話,吃力得不得了。大熱的天,搞得累死了。
“第一幕是從金回來,我想寫出點新意,但是,也沒有歷史可考,材料上遇到問題,不得不罷手了。我記得很清楚,就寫在一個記賬用的條紙上,寫了無數次,只寫了一幕。‘文革期間,我把它撕毀了。”
遺憾的是這部歷史劇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完成。但它所要歌頌的悲劇精神我們從曹禺的講演中,已經可以觸摸得到了。
別生父淚灑機場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國民黨軍隊土崩瓦解,全國已處于革命勝利的前夜。上海龍華機場,一架即將起飛的專機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鄭秀一個人站在飛機旁,焦急地向機場入口處張望。
“穎如,你還在望什么?”父親鄭烈焦急地問。
“你不是說通知家寶與我們一起去臺灣嗎?怎么到現在還沒有來?”
“誰知道呢,也許他碰上什么事……”鄭烈含含糊糊地搪塞著,其實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處,根本就沒派人去接曹禺。為了讓女兒同自己一起離開大陸,鄭父曾四次動員女兒。
此時,鄭秀與曹禺的感情已漸趨冷漠。從江安遷居重慶后,曹禺住南岸復旦大學教書,每周回來兩三次,與孩子們恢復了感情,但與方瑞(后為曹禺的第二任夫人)仍藕斷絲連。回到重慶之后,鄭秀如魚得水,交游廣泛,與男性朋友接觸頻繁,既有清華過去的老同學,也有新交的朋友。這引起曹禺的誤會,以為鄭秀經過江安一場風波之后已不愿意同他恢復關系,兩人之間的關系又漸漸疏遠起來。
1947年,曹禺從美國講學回國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一度在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今上海戲劇學院前身)任教,又經黃佐臨介紹,擔任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編導,創作并導演了電影《艷陽天》。此時,鄭秀則帶著萬黛、萬昭兩個女兒住在南京,偶爾到上海小住,也總是很快返回南京,因為她在南京就業。時局緊張以后,當局通知鄭烈攜全家撤往臺灣。這使鄭秀感到十分為難。一頭是父親,一頭是丈夫,哪一頭都依依不舍。她愛曹禺,父親說已通知曹禺同行,她這才同意動身。
現如今見不到曹禺,鄭秀心中一陣酸痛,但又決然地說:“爸,女兒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說著她含淚拉著兩個女兒,轉身就往出口處走。
“穎如,穎如!你給我回來!回來!”
鄭父聲嘶力竭地叫著,鄭秀和兩個孩子噙著淚,一步一回頭地走出機場,她就這樣和父親一訣成永別了。
不思量情自難忘
1950年春,中央戲劇學院成立,歐陽予倩任院長,曹禺與張庚任副院長。面對新的時代,曹禺覺得應該結束與鄭秀的令人痛苦的婚姻關系了。自從抗戰后期,他與鄭秀產生裂痕之后,由于性格不合等復雜的原因,兩人關系時好時壞,但總的趨勢是日漸惡化,長期過著分居的生活。現如今除了情感因素,已遠赴臺灣的鄭烈也成了橫在兩人頭上的一片陰影。
曹禺向鄭秀提出了離婚的要求。經過一番周折,鄭秀弟弟鄭還從中做了工作,戲劇家歐陽予倩、張駿祥去說服鄭秀,那時新婚姻法規定,男人不能一夫多妻。他們誠懇地對鄭秀說:“為了家寶的名譽,希望你能接受現實。”鄭秀嘆了口氣對好友說:“過去我愛家寶,嫁給了他,現在我仍然愛他,我成全他,我同意離婚,希望他幸福。”1951年春,為了讓這對共同生活了十幾年的夫妻好合好散,減輕感情上的痛苦,鄭秀所在的單位人民銀行經濟研究處和曹禺所在的單位中央戲劇學院共同商議,決定在中央戲劇學院會議室舉行一個協議離婚儀式。曹禺、鄭秀協議離婚手續的見證人,男方是歐陽予倩夫婦,女方陪同鄭秀去的是周有光夫人張允和。協議內容明確規定,曹禺給兩個孩子撫養費,每人每月三十元,到十八歲成人為止。
協議離婚裁判書剛一念完,鄭秀忍不住放聲大哭。想到兩人當年月下定情,岳父鄭烈南京主持訂婚和八年離亂中共同經歷的艱難歲月,曹禺也情不自禁地失聲痛哭起來、百感交集。
改革開放后,一位德國著名記者烏葦多次采訪曹禺,以《戲劇家曹禺》為題,發表了采訪長文。在這次采訪中,在沉默了30多年之后,曹禺第一次向外國朋友談起了他與岳丈鄭烈的交往,流露出真摯的緬懷之情。
“不思量,自難忘。”歷史是不可能割斷的,血濃于水,民族的感情、愛國的感情、骨肉的感情更是無法切斷的。(本文作者系中國曹禺研究學會副會長、上海戲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