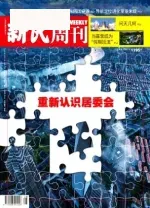被隱蔽的強制閱讀
劉洪波
山東省教育廳禁止全文推薦《三字經》、《弟子規》、《神童詩》等傳統讀物,引起了質疑。
禁令無人喝彩,但質疑者的文化立場并不相同,有對傳統蒙學讀物在中小學推廣持反對意見者,也有對此樂觀其成者。但無論如何,反對禁令的聲音是壓倒性的。
不贊同在中小學推廣傳統蒙學讀物者,更反對行政權力以為掌握了是非標準的自以為是;贊同傳統蒙學讀物進課堂者,反對的是禁令使蒙學讀物不能全面地被學習。兩者看似相當,主旨并不相同。前者是對權力的警惕,后者是對傳統的維護。
現代國民教育,概言之要“成人”。但何為成人,何為不成人,成為怎樣的人,操持者是國家,而決定者在民眾。教育的成人目標,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所設定的公民標準。但國家設定的公民標準,是由國家或具體來說由國家權力的掌握者制定,還是由民眾對國家的定義和對人的發展的認識而定,可能形成很大的區別。近些年來,教育問題一直糾結,根本在此。
談論教育的人們,既憤怒于收費之重,也無奈于課業之重,還反感于教育內容的虛偽空洞或價值顛倒。這三種困境,不能說完全沒有聯系,但仍屬不同問題。收費重,是國民支付的教育成本問題;課業重,是教育實施的方法問題;而教育內容的虛假空洞或價值顛倒,涉及的才是國家應當通過教育使學生成長為怎樣的人的問題。
《三字經》之類,既被列入中小學推薦讀物,表明在教育主管部門,也就是國家教育權力的實施者看來,強制性閱讀此類讀物是必要的。同時,禁止全文推薦,又表明教育權力的實施者看來,強制性地進行部分閱讀是必要的。一個禁令,引出的是兩個強制性,一個強制是閱讀的強制,另一個強制是不得全面閱讀的強制。兩個強制結合起來才構成了權力的全部,分辨兩個強制才能更加明確地看到權力的強力介入。
強制不得全面閱讀,正在受到各種文化立場的人的共同抨擊。而強制閱讀的問題,則悄然被放過了。顯然,在強制閱讀這個問題上,不同文化立場的人會產生分歧,形成贊成強制閱讀與反對強制閱讀兩種態度。在反對強制不許全面閱讀的共同聲音之下,那個帶有分歧的部分被隱蔽起來,未得討論。
其實,中小學是否要強制閱讀《三字經》之類讀物,是更為根本的問題,然后才是閱讀是否應該全面。當所有人都去反對禁止全面閱讀的命令時,放過是否應當強制閱讀,實際上就做了一個“是該全面讀還是部分讀”的選擇題,而先在的選擇“強制讀”則幾乎暗度陳倉地成了默認狀態。
我并不認為《三字經》之類讀物就一定不可以被設定為課堂內容,被強制閱讀,但認為這應當是一個交予公眾討論的問題。教育主管機關固然有權設定課堂內容,但國家的教育方向、“成人”標準,根本上應當在民眾手中,而不是權力機關自便決定。讀經、不讀經,讀《三字經》、不讀《三字經》,經過公眾討論并決定,都不是問題,而不經討論而悄然強制于課堂,則是問題。自便下令禁止全面閱讀的強制令,固然要反對;但尤其要反對的是悄無聲息地強制閱讀。
傳統文化納入課堂,大概很少有人反對。然而傳統文化以何種方式進入課堂,教育對“成人”有何總體設定,現代公民養成訓練是否受到重視,《三字經》之類在教育中置于何種地位,一系列問題,都應得到討論。傳統蒙學的強制推薦,意在使學生擴大視野,了解傳統,還是建立基本價值,形成認知“根器”?
傳統當然有其價值。中國傳統缺乏有公益的價值、責任的價值、同情的價值、群體的價值,同時也缺乏自由的價值、權利的價值、理性的價值、個體的價值。不能說中國傳統沒有發育出科學和民主,就一無所是。在科學精神與社會民主之外,還有人生的開展問題,還有文化和心理上安身的問題,還有個人精神空間選擇的問題,還有觀察世界的多種可能性是否存在的問題……多樣性、豐富性總是有價值的,根系多元總是好的,單一總是有缺憾的。然而,另一個問題是,選擇總是比強制好,未經公眾討論的強制則更是權力的蠻橫。權力的正誤表上,無論寫著什么字樣,最深處的源頭必是迫使人們順遂自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