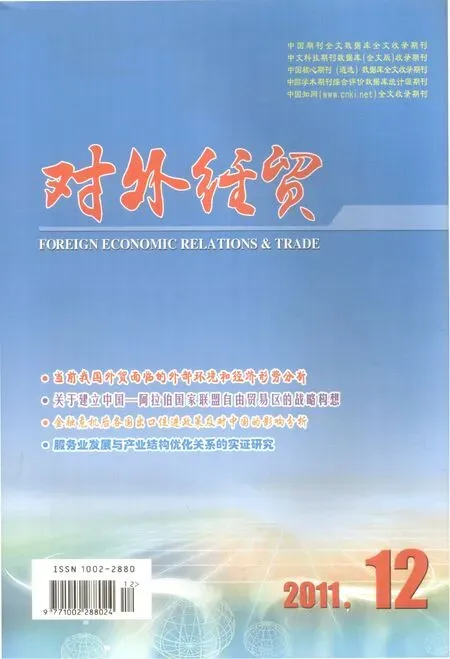基于Zipf法則的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分析
張 玎
(浙江工商大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在社會(huì)科學(xué)中,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的Zipf法則是最引人注目的實(shí)證結(jié)論之一。Auerbach(1913)發(fā)現(xiàn):在某一區(qū)域內(nèi),一個(gè)城市的人口規(guī)模與該城市在城市體系中所處等級(jí)的乘積近似地等于一個(gè)常數(shù)。Zipf(1949)進(jìn)一步指出,城市人口規(guī)模不但服從帕累托分布,而且帕累托指數(shù)趨近于1,該實(shí)證結(jié)論被稱作Zipf法則。之后,帕累托指數(shù)成為衡量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主要指標(biāo)。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由于各種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因素的影響,帕累托指數(shù)在1左右擺動(dòng),從而形成一個(gè)分布區(qū)間。
一、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的Zipf模型
位序-規(guī)模法則認(rèn)為在城市規(guī)模和城市等級(jí)之間存在一般的等式關(guān)系:

通過(guò)對(duì)等式兩邊取對(duì)數(shù)后我們可以得到關(guān)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一元線性回歸方程:

其中R為城市的位序,S為城市的規(guī)模,α是Zipf指數(shù),又叫帕累托值,即是方程需要估計(jì)的系數(shù)。α表示該城市體系中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均衡程度。若α=1,說(shuō)明城市規(guī)模分布接近Zipf規(guī)則所認(rèn)為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各個(gè)規(guī)模等級(jí)城市數(shù)量比例合理,不同等級(jí)城市發(fā)揮各自的職能,所有城市共同發(fā)展。
若α>1,說(shuō)明城市體系中城市規(guī)模分布比較平均,高位城市的規(guī)模相對(duì)不是很突出,中小城市比較發(fā)育,城市體系中的城市之間差距較小。α值越大,城市體中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越平均,當(dāng)α無(wú)窮大時(shí),該城市體系中所有城市具有相同的人口規(guī)模。但是如果α值比較大,城市體系中的所有城市的差距就會(huì)比較小會(huì)造成城市體系部分功能的缺失。若α<1,城市規(guī)模分布較為集中,大城市很突出,而中小城市不夠發(fā)育。α值越小,城市體系中人口分布越不均衡,人口分布集中于部分城市中。當(dāng)α=0時(shí)城市體系中只有一個(gè)城市。同樣的,如果α值過(guò)小,城市體系中的所有城市的差距就會(huì)比較大,也會(huì)造成城市體系部分功能的缺失。
二、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值測(cè)算及對(duì)比分析
(一)數(shù)據(jù)的選取
本文選用了非農(nóng)業(yè)人口作為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指標(biāo),原因在于:第一,非農(nóng)業(yè)人口在數(shù)量上與建成區(qū)常住人口比較接近;第二,對(duì)于城市體系而言,各個(gè)城市的非農(nóng)業(yè)人口與建成區(qū)常住人口在總體上呈線性關(guān)系;第三,非農(nóng)業(y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持統(tǒng)計(jì)口徑的連貫性和可比性。
本文采取1988—2009年這22年的非農(nóng)業(yè)人口作為城市規(guī)模的測(cè)量數(shù)據(jù),通過(guò)分析可以清楚顯示浙江省自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城市規(guī)模的變化過(guò)程。
其中,R即城市的位序是被解釋變量,S即城市規(guī)模為解釋變量,通過(guò)回歸得到的系數(shù)α即為所求的浙江省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值。
(二)實(shí)證結(jié)果
借助回歸方程lnRi=lnA-alnSi,運(yùn)用Eviews5.0軟件,采用OLS方法對(duì)浙江省1988—2009年的城市人口進(jìn)行回歸分析,研究這22年中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的一個(gè)大概的趨勢(shì),本文根據(jù)22年的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α,制作圖1。

圖1 浙江省1988—2009年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比較
運(yùn)用雙對(duì)數(shù)模型進(jìn)行的一元回歸得到的系數(shù)p值為0,均可通過(guò)置信度為1%的假設(shè)檢驗(yàn),T值較為顯著,調(diào)整后的決定系數(shù)較大,說(shuō)明該模型很好的解釋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和城市等級(jí)之間存在的線性關(guān)系。從圖1可以發(fā)現(xiàn)以下特征:
1.浙江省城市人口規(guī)模呈現(xiàn)明顯位序—規(guī)模分布
從圖1可看出浙江省22年來(lái)α值都在1附近,說(shuō)明浙江省的城市規(guī)模和位序之間呈現(xiàn)比較顯著的線性關(guān)系。并且選取1988、2000、2009年的浙江省城市體系中22、35、33個(gè)城市作圖擬合,發(fā)現(xiàn)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大小不一,在雙對(duì)數(shù)坐標(biāo)圖上,近似的排列成一對(duì)相當(dāng)連續(xù)的直線,在所排列的空間上基本沒(méi)有出現(xiàn)明顯的規(guī)模空白的間隔區(qū),說(shuō)明這一區(qū)間內(nèi)的各個(gè)規(guī)模上均有城市分布,城市體系發(fā)展相對(duì)完善,進(jìn)一步驗(yàn)證了浙江省的城市規(guī)模呈現(xiàn)位序—規(guī)模分布。
2.浙江省城市人口規(guī)模相對(duì)分散,中小城市眾多
從圖中看出α值在這22年來(lái)一直大于1,這表明說(shuō)明城市體系中城市規(guī)模分布比較平均,高位城市的規(guī)模相對(duì)不是很突出,中小城市發(fā)育較好,城市體系中的城市之間差距較小。杭州作為浙江省的首位城市,雖然呈現(xiàn)比較理想的首位分布,但浙江省高位城市還是相對(duì)較少,超過(guò)50萬(wàn)人口的城市十年來(lái)一直是杭州、寧波和溫州這三個(gè)城市,金字塔的高層過(guò)于單薄,中小城市大量存在,浙江省之間的城市之間差距較小,城市人口比較分散,分布在等級(jí)城市中,特別是較多分散在中等城市中。
3.高位城市還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
圖1中α值衡量的是整體城市間的集中度,α值大于1,表明城市規(guī)模分布比規(guī)模排序法預(yù)測(cè)的更加分散。這說(shuō)明其他適度規(guī)模的大城市數(shù)量不足,高位城市還有很大發(fā)展空間,高位城市的發(fā)展并不是單單指現(xiàn)有的大城市的規(guī)模擴(kuò)張,更主要的是需要形成新的大城市,即需要一些具備條件的小城市發(fā)展為中等城市,浙江省一些中等城市需升級(jí)為大城市。
4.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位序—規(guī)模等級(jí)結(jié)構(gòu)較穩(wěn)定
浙江省22年來(lái)α值一直在1.05~1.20之間徘徊,說(shuō)明自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浙江省的位序-規(guī)模等級(jí)結(jié)構(gòu)比較穩(wěn)定,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慣性,一段時(shí)間內(nèi)位序-規(guī)模分布型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不會(huì)有較大的改變。隨著經(jīng)濟(jì)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個(gè)別大城市的積聚能力和輻射功能將不斷增強(qiáng),從杭州首位度近幾年的緩慢上升就可看出來(lái),大城市的帶動(dòng)作用將增強(qiáng),城市規(guī)模結(jié)構(gòu)的均衡狀態(tài)可能被集中發(fā)展的城市所打破,但在短時(shí)間內(nèi)不會(huì)有很大的改變。
5.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大體呈現(xiàn)“倒U”型變化
1988—2000年浙江省的α值大體呈現(xiàn)上升的趨勢(shì),該指數(shù)是用來(lái)衡量總體城市規(guī)模分布集中度的,因而它的增加就意味著1988—2000年浙江省整體城市規(guī)模分布集中度的下降,即浙江省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在20世紀(jì)90年代變得更加分散。這主要是因?yàn)?988年之后浙江省大量新型城市的涌現(xiàn),從浙江省城市數(shù)量圖中發(fā)現(xiàn)1988—2000年浙江省城市數(shù)量從22個(gè)增加到35個(gè),一批經(jīng)濟(jì)強(qiáng)縣晉升為城市,這導(dǎo)致了浙江省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更加分散,從而使城市集中度的下降。原有城市間的相互變化并不大,它對(duì)浙江省城市集中度的影響不大。2000年以后α值呈下降趨勢(shì),表明城市集中度的加強(qiáng),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開(kāi)始不均勻,大城市的積聚能力增強(qiáng),更多的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這一過(guò)程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程度有密切關(guān)系。
三、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值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指標(biāo)的選取
1.工業(yè)化率
自英國(guó)工業(yè)革命之后,工業(yè)發(fā)展所導(dǎo)致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演進(jìn),成為城市發(fā)展及其空間規(guī)模分布變化的重要推動(dòng)力量。在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城市化進(jìn)程中,工業(yè)發(fā)展一直被當(dāng)作推動(dòng)“鄉(xiāng)—城”人口流動(dòng)的決定力量。Fujita和Krugman(1995)發(fā)現(xiàn)當(dāng)農(nóng)業(yè)發(fā)展水平一定時(shí),工業(yè)空間集聚力量的大小決定了城市規(guī)模的大小。由于各個(gè)行業(yè),甚至行業(yè)內(nèi)的各個(gè)企業(yè)由多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部分組成,每個(gè)部分表現(xiàn)出不同的空間集聚力量,從而可能分布于不同規(guī)模的城市。同一區(qū)域內(nèi)不同城市的相互作用,影響著區(qū)域城市體系的特征和變化趨勢(shì)。
2.非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比
工農(nó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是影響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農(nóng)業(yè)發(fā)展是城市發(fā)展的保證。Ranis和Fei(1961)指出,農(nóng)業(yè)剩余對(duì)工業(yè)部門的擴(kuò)張和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城市化)具有重要意義,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推動(dòng)了城市化進(jìn)程;另一方面,農(nóng)業(yè)發(fā)展為城市工業(yè)發(fā)展提供市場(chǎng)需求,并影響城市發(fā)展的集中和擴(kuò)散。在產(chǎn)業(yè)集中和擴(kuò)散的過(guò)程中,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與需求擴(kuò)大的相互作用,推動(dòng)工業(yè)從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到非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在空間上進(jìn)行魚(yú)貫轉(zhuǎn)移(Puga和Venables,1996)。
3.路網(wǎng)密度
Krugman(1991)將冰山運(yùn)輸成本引入空間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分,論證了運(yùn)輸成本對(duì)于工業(yè)在空間上集聚和擴(kuò)散的重要作用。之后,新經(jīng)濟(jì)地理學(xué)的分析方法在城市規(guī)模和城市體系問(wèn)題的研究中得到普遍應(yīng)用,交通運(yùn)輸對(duì)于城市發(fā)展和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影響逐漸被人們所認(rèn)識(shí)。更好的交通運(yùn)輸條件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城市規(guī)模的擴(kuò)大,因?yàn)椴煌鞘虚g的交通越便利,越有可能降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必要性。本文把區(qū)域交通運(yùn)輸能力作為我國(guó)省際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解釋變量,進(jìn)行實(shí)證檢驗(yàn)。
4.人口密度
隨著人口密度越高,土地資源越是稀缺,而由于大城市人均占地少,可能越會(huì)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以利于節(jié)約土地資源。但也有可能出現(xiàn)一些相反的因素,即在人口稀疏的情況下,運(yùn)輸距離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因此人口就更有向大城市集中,以便形成同城效應(yīng)。到底哪種因素占上風(fēng),還需要實(shí)證檢驗(yàn)。
5.城市化率
基于城市間協(xié)同作用的考慮,一個(gè)國(guó)家達(dá)不到一定的城市化水平,大城市可能難于獨(dú)立發(fā)展。隨著一個(gè)國(guó)家的城市化發(fā)展,大量的人口開(kāi)始向城市集聚,在城市化初始階段,人口可能向城鄉(xiāng)結(jié)合區(qū)的小城市遷移,隨著城市化的深入,人口可能大量向大城市集聚。
此外,一個(gè)省份在不同時(shí)期實(shí)行的政策也會(huì)對(duì)城市規(guī)模的分布產(chǎn)生很重要的影響,但由于沒(méi)有可用數(shù)據(jù),無(wú)法檢驗(yàn)。
(二)模型的構(gòu)建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計(jì)量分析的結(jié)論,構(gòu)建分析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值的影響因素的計(jì)量經(jīng)濟(jì)學(xué)模型如下:

其中,α為被解釋變量表示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a值越大,城市體系中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越平均,當(dāng)α無(wú)窮大時(shí),該城市體系中所有城市具有相同的人口規(guī)模,即α值越大表示中小城市發(fā)育完善,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α值越小,城市體系中人口分布越不均衡,人口分布集中于部分城市中,即α值越大表示大城市發(fā)育完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i表示工業(yè)化率,即工業(yè)產(chǎn)值占總社會(huì)產(chǎn)值的比例,反映工業(yè)化水平;g指非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值比,反映經(jīng)濟(jì)的結(jié)構(gòu)性特征;d是人口密度,即每平方公里國(guó)土面積的人口數(shù);r是路網(wǎng)密度,即每平方公里國(guó)土面積的鐵路、公路和水路公里數(shù);u代表城市化率,反映城市發(fā)展水平。α1、α2、α3、α4和 α5為回歸系數(shù),μ 為隨機(jī)誤差項(xiàng)。
(三)實(shí)證分析
根據(jù)浙江統(tǒng)計(jì)年鑒(1989—2010年)的數(shù)據(jù),計(jì)算整理得到解釋變量的數(shù)據(jù),對(duì)計(jì)量模型進(jìn)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結(jié)果見(jiàn)表1。

表1 方程(3)回歸結(jié)果
其中R-squared為0.958,F(xiàn)值78.85,工業(yè)化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和人口密度在1%水平上顯著,城市化率和路網(wǎng)密度在10%水平上顯著。從中可以看出此模型較理想地解釋了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與工業(yè)化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人口密度、城市化率和路網(wǎng)密度的線性關(guān)系。
從表1可以看出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α值與工業(yè)化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隨著城市化水平提高,浙江省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明顯變大,表明中小城市開(kāi)始發(fā)育,工業(yè)化進(jìn)程明顯推動(dòng)了中小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擴(kuò)大。這說(shuō)明在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中小城市對(duì)于吸收鄉(xiāng)鎮(zhèn)轉(zhuǎn)移人口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與工農(nóng)業(yè)比率存在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農(nóng)業(yè)發(fā)展是推動(dòng)城市人口規(guī)模分布均勻化的重要因素。
人口密度與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也存在比較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更多的人口是向中小城市的集中。雖然按照常識(shí),在人口稠密、因而土地資源緊缺的情況下,人口更有向大城市集中的需要,但在浙江省中中小城市發(fā)育比較完善,對(duì)于人口的吸引力比較大。
城市化率對(duì)城市規(guī)模分布值也表現(xiàn)一定的負(fù)的影響,顯示了隨著城市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口開(kāi)始向大城市集聚,證明了隨著經(jīng)濟(jì)和城市的發(fā)展,大城市在經(jīng)濟(jì)中的作用會(huì)上升,大城市人口在總?cè)丝诘谋壤矔?huì)顯著上升。
路網(wǎng)密度具有一定的正的影響,隨著路網(wǎng)密度的提高,浙江省城市的分布值越大,城市規(guī)模分布越均勻,說(shuō)明良好的交通運(yùn)輸條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duì)城市集中度產(chǎn)生替代作用。如果交通便利的話,各個(gè)城市可以很好地協(xié)調(diào)溝通,那么大城市的吸引力就會(huì)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相反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會(huì)上升。
四、結(jié)論
浙江省的城市規(guī)模和城市位序之間呈現(xiàn)比較顯著的線性關(guān)系,城市體系發(fā)展相對(duì)完善。城市人口分布值a值22年來(lái)一直大于1,說(shuō)明城市規(guī)模分布比較分散,中小城市發(fā)育完善,高位城市的規(guī)模相對(duì)不是很突出。現(xiàn)在需要一些具備條件的中小城市發(fā)展為大城市。隨著工業(yè)化率和人口密度的提高,浙江省的分布值明顯變大,即城市體中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越平均,說(shuō)明浙江省的中小城市發(fā)展完善,中小的城市的吸引力比較大。在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中小城市在吸引非農(nóng)業(yè)人口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浙江省的中小城市對(duì)整體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城市化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城市化率和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比的提高,浙江省的分布值變小,即城市體系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開(kāi)始集聚。說(shuō)明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的進(jìn)一步深化和工業(yè)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大城市的集聚效益開(kāi)始體現(xiàn),大城市的吸引力變大,更多的人口開(kāi)始向大城市集聚。
[1]許學(xué)強(qiáng),周一星,寧越敏.城市地理學(xu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高鴻鷹,武康平.我國(guó)城市規(guī)模Pareto指數(shù)測(cè)算及影響因素分析[J].數(shù)量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研究,2007(4):43-52.
[3]金波,熊國(guó)和.浙江城市化的合理規(guī)模與效率分析[J].杭州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2(1):35-41.
[4]裘建娜,趙秀云,錢曉群.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 Zipf定律的實(shí)證分析[J].經(jīng)濟(jì)師,2006(12):67-69.
[5]陳其霆,苗建軍.江蘇省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演化分析[J].生態(tài)經(jīng)濟(jì),2010(2):51-53.
[6]王小魯,夏小林.優(yōu)化城市規(guī)模,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J].經(jīng)濟(jì)研究,1999(9):22 -29.
[7]Arnott R J.Optimal City Size in a Spatial Econom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79,6:65 -89.
[8]Gabaix,x.,1999,Zipf’s law for Cities:An Explaan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1.114,No.3,739- 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