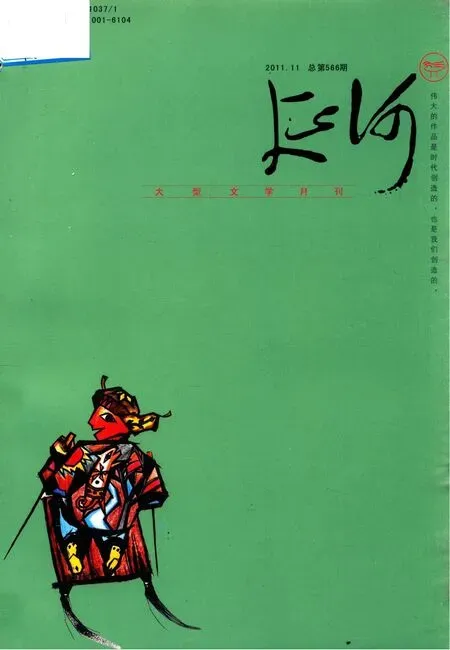《古爐》:歷史與人性的寓言
徐 琴
作為一位始終活躍在當代小說創作一線的著名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創作以其富于個性特質的現實關切和敘事創造成為不同時期的文壇焦點。《古爐》是反映“文革”的,那么賈平凹對“文革”的書寫和已有的關于“文革”的作品有何不同呢?賈平凹在接受《大眾日報》記者采訪時說,他不滿意他曾讀到的那些關于“文革”的作品,認為都寫得過于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賈平凹寫作《古爐》是試圖再現歷史的真實面貌,寄予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憂思。這種書寫,是對“文革”歷史的全新體認,切入“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牽制的整個過程”(《古爐》后記),也袒露著賈平凹的承擔意識和人文追求。
一
“文革”曾是一代中國人的噩夢。對賈平凹而言,無論他自己還是他的家庭,在“文革”時期均遭受了很大的創傷。在做客新浪網時,他對自己創作《古爐》的緣由這樣解釋道:“文化大革命也是繞不過去的事情,起碼在我少年時期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沒辦法忘記的,年紀大了這個記憶就特別清晰,想寫一下。如果我這個年齡再不寫,比我小的人就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當然以后的人還可以繼續寫,但是沒有一種實感的東西在里面。既然自己活在這段歷史中間,自己也有責任把這段歷史用自己的眼光把它寫下來,這就是用了幾年時間寫這本書的原因。”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促使他要把這段歷史用小說的形式記載下來。
賈平凹的生活和體驗在陜南山地,如古爐村一般的“古堡”和“故里”,是作家深刻體認并畢生闡釋的文學“情本體”(李澤厚)。賈平凹被公認為是當代中國最具傳統意識的作家之一,這種傳統意識在他身上鮮明地表現為一種現實擔當意識,一種立足于鄉土文化根基的獨特創作習性。以習性的概念來觀照,賈平凹小說的意象載體“古爐村”的鄉土習性實質上也就是文革歷史時期中國鄉土社會現實行動的“在場”。我們可透過這一普通鄉村的物化歷史來全面地把握歷史的本質性征如何滲透、衍化于特殊情境中。
當曾經的真實逐漸被歷史的腳步掩蓋,當所有的過去都成為記憶并逐漸被湮滅時,賈平凹穿過歷史的隧道,回到了“文革”年代,將視點落在“文革”的初期,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期。賈平凹關注到了一個在“文革”文學書寫中別人尚未關注或者很少關注的點,就是“文革”初期的武斗,都是所謂的革命,但兩派卻互相攻訐與殘斗。村人霸槽得風氣之先,成立了榔頭隊,接著天布領導成立了紅大刀隊,村人按照親疏遠近以及各自利益站隊。原本有著亙古傳統的古爐村,原本有著儒家文化積淀的村子,在這時陷入狂亂之中,釀成了一幕幕血案,村民越來越貧窮,人心越來越窄怨逼仄。在作者筆下,沒有聲嘶力竭的控訴,只有一幕幕的日常生活映現,以及在巨大的時代波動下,人在歷史發展中被裹挾而走的荒唐與禍亂。霸槽和天布在武斗中作為對立兩派的首領進行著爭斗,然而最后兩人都被處死,像阿Q一樣稀里糊涂地被“革命”給革了命。在這場“革命”狂潮中,代價不僅是人命和苦難,更是人倫精神的喪失。
“古爐”村倫理喪失的根本,是一種心性之善的損毀,古爐村賴以支撐全村的人性本真、“情本體”在身體欲望的張揚和鼓噪下被遮蔽,隱性存在于鄉土社會(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性惡”以近乎夸張、變態的顯露,噴薄為一種解構、顛覆社會習性的強大力量,沖擊著理性的堤壩。

李檣攝影作品·北方風景系列 青海 2006年
他的寫作,沒有批判,沒有怨恨,沒有張牙舞爪的痛苦,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雞零狗碎,寫吃喝拉撒睡,寫抓癢,寫女人用指甲花染指甲,寫男女茍合,寫家庭矛盾,鄰里關系,日光之下,并無新事。然而正是因為這些日常生活細節的呈現,使得我們真正地感受到了“文革”。作者寫這些,既是有意為之的新寫實手法,更是一種對于鄉土社會——肉身化社會方式的本質特征的理解。在作者看來,中國社會的倫理秩序變更之道最本然地體現在以肉身欲望、一己生存來發散出的家庭、社會存在狀態上。每一個肉身化的個體的性情的復蘇、變異或生長,才是最為鮮活的意象、最應關注的存在。這既是一種當代現實主義創作的理念取向,更是一種歷經文化反思之后的主體精神自覺。也是為新時期以來所反復印證了的人性化寫作的價值尺度。故而,作家寫作既不是立足展示現實創傷,亦不是形而上地批判反思,而更多的是一種歷史的再現與對掩映在歷史之下的人心的反省,是一種觸及人的本質存在(從生物性到精神性,從肉體饑餓到精神完形,從本能欲望到理性自覺的人化——社會性生成過程)。“文革”就是這樣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在肉身化的鄉土社會秩序中潛移默化地變革著生活,身體化的歷史的生成,既是一種本能欲望、力比多的喚醒,更是一種社會禁令(文革的文化規訓和意識形態鉗制)對于以“古爐村”為原型的基層社會共同體的氣質教化、氣質導向,鄉土的多舛命運又何嘗不是中國社會行動歷程的縮影和前兆?。
石獅子在“文革”時被砸,千年老樹也被炸掉,善人作為鄉間智者死去,疥瘡的蔓延等,這都具有隱喻之意。此外,賈平凹不僅僅思索“文革”,而且對這之前的歷史都進行了一定的反思。如在“文革”初起時,支書和霸槽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小伙子,看著你這沖勁,我倒想起一個人了。霸槽說:誰?支書說:我!年輕時鬧土改,就是你現在的樣子!”在榔頭隊和紅大刀隊爭奪勢力時,霸槽請獸醫給隊里的豬打針,紅大刀隊有人卻不愿意打,這時天布說:“給病豬打針就給病豬打針吧,豬的病好了,不一定人人都會說他霸槽好。咱支書土改那年批斗守燈他大,守燈他媽來求情,支書不是把她睡了還繼續批斗守燈他大嗎?睡是睡,批是批,那是兩碼事!”高行健曾言:文學并不旨在顛覆,而貴在發現和揭示鮮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為知道而其實不甚了了的這人世的真相。賈平凹是有歷史意識的,他舉重若輕地寫出了他對歷史的思考,還似不經意地牽出了“土改”,有多少曾經的真實還被掩藏在政治的外衣之下?
列寧說: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當“文革”被有意或無意淡化忘記的時候,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心中的烙傷卻可能永遠不會平息,因為這慘痛的歷史改變了中國太多的東西,改變了太多人的命運。一些傳統的倫理觀念被顛覆,人性丑的一面被極度地放大,那個瘋狂年代的諸多瘋狂舉動畢竟在我們這塊神奇的大地上發生過。“文革”為什么會在中國發生,僅僅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嗎?錢理群曾經在《我的精神自傳》中剖析了自己當時的心理,認為“文革”不僅僅是政治層面上的事,還與每個身處其中的個人有關。
在賈平凹的作品中,同樣有一種自我批判的精神存在。賈平凹在后記中這樣寫道:“面對著他們,不能不愛著他們,愛著他們又不能不恨他們,有什么辦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憐的族類啊,愛恨交集。”在文革初期,霸槽首先在村子里掀起了破四舊的浪潮,然而沒有一個人站起來反對,這是因為:“如果霸槽是偷偷摸摸干,那就是他個人行為,在破壞,但霸槽明火執仗地砸燒東西,按照以往的經驗,這是另一個運動又來了,凡是運動一來,你就要眼兒亮著,順著走,否則就得倒霉了,這如同大風來了所有的草木都得匍匐,冬天了你能不穿棉衣嗎?”在《古爐》的歷史深處,深藏人性的絕望。然而在絕望的根底里,我們又分明地能夠感受到作家那種痛楚中的期待和訴求。他期待著人性還沒有完全湮滅,《古爐》中的繭婆、善人、狗尿苔等人身上還有人性之美,即使是在慘絕人寰的時期還有可珍貴的。“小說只寫苦難,只寫惡、黑暗和絕望,已經不夠了。在這之上,作家應該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參照。卡夫卡也寫惡,魯迅也寫黑暗,曹雪芹也寫幻滅,但他們都有一個更高的精神維度作參照的:卡夫卡的內心還存在著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沒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魯迅對生命有一種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懷著對生命的大愛;曹雪芹的幻滅背后,是相信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情感的知己,存在著一種心心相印的生活。相比之下,現在的作家普遍失去了信念,他們的精神視野里多是現世的得失,內心不再相信希望的存在,也不再崇尚靈魂的善。作家的心若是已經麻木,他寫出來的小說,如何能感動人?又如何能叫人熱愛?”(謝有順:《被忽視的精神——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一種讀法》)
二
賈平凹在《古爐》的書寫中,重在對日常生活中人性的刻畫。通過一些雞零狗碎的事情再現了“文革”時期的面貌,將世態人心呈現在讀者面前。作品寫了一個村莊、百十戶人家的生活,細節綿密,有聲有色。他們的生活就在勞作、吃飯、睡覺、戀愛、偷情、雞零狗碎之中,隨著社會政治運動的到來,他們被裹挾其中,人性中的惡和善也由此激發,古爐村在變化。在“文革”的背景下,他揭示人性之惡,正因為人性中的愚昧、狹隘、偏執、自私、保守、盲從,使得“文革”的發生有了社會基礎。
《古爐》的中心人物狗尿苔,是蠶婆撿來的棄兒,他形體猥瑣,身材矮小,是個侏儒,但像那個年代的許多中國人一樣,被寄予了美好的期望,他被婆叫做平安,然而環境逼仄,從小就因家庭成份不好而倍感壓抑。狗尿苔的處境是卑微的,但他卻心靈通透,如同王安憶《小鮑莊》中的撈渣一樣,充滿仁義;如同阿來《空山》中的格拉一樣,受盡委屈而又通靈一切;又如同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一樣,敏感壓抑,向往著美好。因為出身不好,他要格外去討巧別人,因為有著一顆善心,他能細膩體察別人的難處,雖然年齡尚幼,卻能分清是非人心,他秉天地靈氣,能與樹木鳥獸說話,能聞得到死亡的氣息,每當古爐村有大事發生,他總能事先嗅到。在“文革”這樣一個逼仄的環境中,苦澀無處不在,怕聽到罵聲,他將耳朵堵上,怕被人看見,他擋住了自己的眼睛,他要承受委屈和卑微,在文革中“如今,最快活的仍是狗尿苔和牛鈴,雖然牛鈴是榔頭隊的,他不能再到紅大刀隊的老公房去,而狗尿苔就拉著他哪兒人多去哪兒,哪兒熱鬧去哪兒。狗尿苔完全忘記了婆的叮嚀,他覺得這日子就像是節日,天天都是節日。他是不嫌人作踐的,到哪兒受人作踐就作踐吧,反正是蒼蠅,蒼蠅還嫌什么地方不衛生嗎,被作踐了別人一高興就忘了他的身份,他也就故意讓他們作踐。”在文革中,小小的他敏感的心時時會受到傷害,但也并沒有陷入到苦難的最深處,繭婆、杏開、支書,包括霸槽、牛鈴等都給他帶來溫暖和內心的慰藉。在作品中,他盡管是“四類分子”的孫子,但繭婆和村人卻給了他許多溫情,他并不是孤獨無助的。
在苦難中有溫暖,在癲狂中有清醒,這就是這個世界呀,賈平凹感知這個世界,記載下了點點的人心。也使得一個個被扭曲的人物、被衍化的時代悲劇具有了人性的悲憫之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賈平凹還寫了在災難歲月映照之下所顯現的人性的溫暖。不能不提的是作品中的繭婆,這是一個鄉村女性,然而在她身上,有著一種生活的柔韌與智慧。因為丈夫去了臺灣,她成了四類分子,但在她的心里,從未覺得自己低賤。她有著鄉村生活的智慧,心靈手巧,會剪紙,雖然自己生活困頓,卻處處替他人著想。因為她的存在,許多人的心靈有了依托,狗尿苔的天空也不至于陰暗,因為她的存在,雞零狗碎的生活有了亮點。即使是處在最底層,她的靈魂卻始終是高潔的,譬如在支書得意時,跟她要一個秀花裹肚,她嘴里雖然應承著,但沒有實際行動。在支書被批斗時,她卻主動給支書送去裹肚,雪中送炭,絕不錦上添花。在自身難保之際,她還保護灶火、善人,幫助杏開等,她是《古爐》中最活靈活現、最讓人感到心靈熨帖的一個人物。
此外,作品中善人的存在,還讓我們感受到了鄉村倫理的美好。相比其它人物而言,善人這一形象較為抽象,他是一種鄉村隱喻,類似《白鹿原》中的朱先生。通過他,賈平凹闡明了在鄉村生活中,自有一種道德秩序的存在。賈平凹關于這方面的描寫,與他先前的《廢都》、《秦腔》等作品在實質上連起了一條線。在“文革”時期,鄉村倫理受到了沖擊,使得村社規范產生了動搖,最終,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所有的一切都土崩瓦解,使得城市成為“廢都”,鄉村成為“廢鄉”。我們可以看到,賈平凹有著自己對歷史的思考,在他的思想深處是有一種深沉的悲涼存在的。由此,作者在有意識地引導我們思考:鄉土社會的文化改造、文化復興,其生命力和關節點何在?鄉土人文的歷史,其內在的合理性、合法性規律究竟是什么,這種內在的鄉土生存之道,和中國社會的關聯性、和傳統文明(文化)現代改造究竟有著怎樣的異質同構的關系?梁簌溟先生和費孝通先生都曾指出,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是農村問題。作為中國當代鄉土小說寫作的代表人物之一,賈平凹始終直面農村鄉土問題,深度思考其內在關系和前途命運,也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在《古爐》中,面對歷史再現和社會描摹的大命題,賈平凹強調細節的真實、生活的質感和體驗的鮮活,力求在風俗的建構中顯示習性(人性活動)的本然。為了能夠真實地呈現歷史的原貌,他沿著《秦腔》所構建的敘事方式繼續開拓,以生活流的方式展現了古爐村的方方面面,對生活細節的刻畫更為真實可信,展現出日常生活固有的片斷化、零散化的特征。
他筆下的古爐村,有聲有色,有氣味,有溫度,開目即見,觸手可摸。他用還原生活原生態的寫法,在雞零狗碎的言說之中,形成了一種細節鮮明,整體混沌的藝術風格。因為對日常生活的細致刻畫,已經逝去的“文革”逼真地浮現在我們眼前,“革命”彌漫在漫無邊際的鄉村日常生活之中,顯得更為真實和怵目驚心。純熟的技巧使得賈平凹的先鋒氣質和擔當意識得以彰顯,正是因為這種探索精神,讓我們感受到他對藝術的執著,對文學的承擔。他的敘述是一種不受世俗影響的探索,迫使我們去發現日常生活或歷史中被壓抑的真實,看到過去的驚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