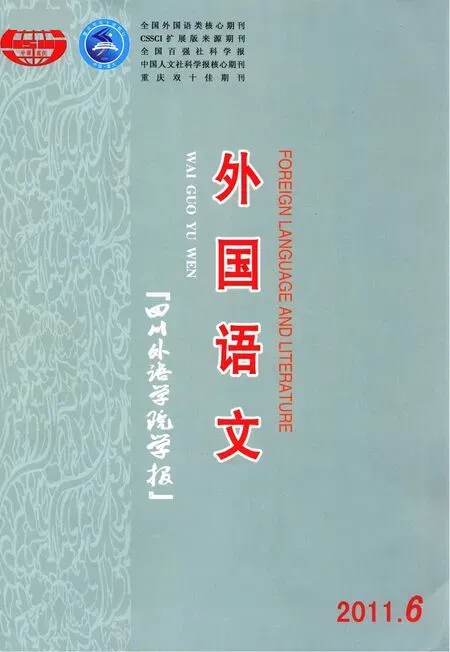都市異化之一斑——中德文藝作品中出租車司機異化之比較
張莉芬 孔德明
(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一、引言
在不同階段和不同文化環境下的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有著天壤之別。德國的現代化進程道路是一條普魯士式的道路,即通過貴族立憲政權的干預來緩慢地實現經濟現代化、工業化。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則是“政治驅動型的后發現代化模式”[1],從鴉片戰爭被迫打開國門,到改革開放加速現代化進程至今,經歷了經濟市場化、政治制度化、社會多元化和對外國際化的重大突破。改革開放后的短短30年,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實現了質的飛躍。盡管中德兩國現代化進程道路和速度迥異,兩種文化背景下,由于現代化、城市化進程導致的勞動異化、人的整體異化乃至城市異化卻體現出驚人的相似性。
工作這一主題與現代化、城市化密不可分。前工業化時期自給自足的勞作與工業化時代帶來的薪酬工作有著根本的區別。德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有關于職業在社會中主導地位的討論,階級、種族甚至貧富差距都已不是主要問題,“有工作”和“沒工作”才是主要的矛盾源頭。如此看來,工作對于評判生活質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沒有工作的生活是不幸福的,亦是不被社會認可的,也就是說沒有工作的生活是異化的。然后,有工作的生活也未必方方面面都能得到認同。
作為一個社會的價值因素,工作在文藝作品中占有突出地位。特別是在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和后現代工業社會以后,對工作和工作帶來問題的反思成為現當代文藝作品社會批判功能的重要體現。本文基于中德文藝作品中出租車司機異化個案對比分析,闡述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因城市化進程所導致的個體工作與生活雙重異化之相似性,以及工作異化與生活異化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德國女作家Karen Duve的長篇小說《出租車》以及中國導演寧瀛的電影——北京三部曲中的《夏日暖洋洋》為研究提供了絕好的素材。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均為出租車司機:《出租車》中是一位名叫亞桑娜的年輕姑娘;《夏日》中是小伙子德子。故事都發生在大城市,一個在20世紀80年代的漢堡,一個在90年代末的北京。
20世紀90年代末的北京,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后迅猛發展,出租車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朝氣蓬勃,但由于競爭的日益激烈,這個職業也已不再像80年代那樣風光和多金,開桑塔納的德子就處在這么一個轉型的時期。雖然他拼命掙錢養家,卻還是弄得妻子跟鄰居私奔;80年代的漢堡已是相當的繁華,出租車司機早已不是受青睞的好工作,而只是沒有完成職業培訓的人或者大學生兼職的一份“雞肋”工作。亞桑娜就是為了生計被迫選擇了這份職業,然而她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份工作她一干就是十年。這十年里她一事無成、感情生活一塌糊涂,最后還是因車禍被吊銷駕照而被迫結束出租車司機的職業生涯。
二、全球化語境下的都市異化
全球化背景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伴隨而來的除了積極的政治經濟效益外,還有各種的社會問題與隱患,其中都市的異化日益顯著。如果以都市居民為研究對象,那么都市異化主要表現為個體工作異化、生活異化以及主體性的喪失。
工作異化可追述到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第一次提出勞動異化的概念。在哲學的語境里,異化是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而這個對立面又變成外在的異己的力量,并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2]這里的對立面不單單指的是勞動產品,勞動活動本身與勞動者也是對立的,因為勞動不是自發的需要,而是被迫地強制勞動,只是維持生存的必須手段。人只有在發揮主體性、自由自覺地活動時,才真正體現出作為人的特性。在現代社會,所有的薪酬工作都具有異化勞動的性質,異化勞動并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物,而是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的衍生物。
齊美爾在《大城市與精神生活》[3]一文中指出,大城市中快速的生活節奏、詳細的社會分工、貨幣經濟的高度發達使得大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而持續緊張則導致他們對于事物差異性的冷漠,乃至對于人際交往的拘謹和排斥。實際上,結合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齊美爾在這里闡述的正是大城市人工作和生活的雙重異化現象:詳細的社會分工、貨幣經濟的高度發達體現在個人身上便是工作的異化;快速的生活節奏、對于事物差異性的冷漠、人際交往的拘謹和排斥便是生活的異化。
韓恩(ChristopherHann)在施威默(Erik Schwimmer)的符號學模型基礎上發展出了工作與生活異化及認同的模型[4]。

韓恩認為,第一類型的人代表的是普通工廠工人,他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且購買能力低;第二類型的人多為自由職業者,自由度高,收入也高;第三類型的人主要特征在于工作中雖異化,但借助于高薪收入亦能達到工作外的認同;第四種類型就是所謂的工作狂,人生的意義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得以實現,工作外的生活則充滿了異化。某些執著的科學家或落魄的詩人便是這類人的代表。
但是,工作內、外在哪些方面會產生異化?哪些方面能取得認同?通過進一步深究可以發現,韓恩的模型顯得過于簡單化,因為他僅僅涉及了收入以及工作自由度、繁重度的問題。本文將分別從工作和生活兩方面中具體的、有著決定性意義的下屬范疇來對兩部作品中的異化表現進行分析:工作中工作對象、工具、同事、收入、是最重要的范疇;而生活的意義則取決于愛情、家庭、朋友、業余生活等。
三、個案分析
出租車司機實際上是一個古老的國際性職業,西方世界的馬車,中國的黃包車就是它的雛形。每天接觸不同的乘客,穿梭在熟悉的大街小巷,聽到看到各種不同的故事。然而,事實上,這份職業并不是常人所想像的那樣豐富多彩,面對太多短暫和無意義的“相逢與別離”,使得出租車司機的自我空間遭受劇烈的沖擊,片刻屬于自己的安寧顯得彌足可貴。本文將結合產業結構、外部社會環境以及主體性危機三大框架,兼顧上文中提出的研究范疇來比較中德語文學境中出租車司機的形象,闡述二者在表現工作、生活雙重異化時的相似性以及工作生活雙重異化的復雜關系。
1.產業結構服務業化導致工作異化
從產業結構自身來看:出租車司機屬于服務業,他們的工作對象是人。服務業的日益發達則催生出了大量無法完全區分生活與工作的從業人員,尤其是出租車司機,多勞多得的游戲規則使得工作大量地侵占生活時間;24小時服務的原則使得夜班司機幾乎完全脫離正常的生活。由此,他們的工作、生活態度和人生觀與前現代時期的工作主體就存在著很大區別。
在《出租車》中,亞桑娜和她的同事一樣,憎恨所有的乘客,即便他們是衣食父母。在他們看來,所有的乘客都是豬,不論是衣冠楚楚的商業人士,普通的小市民或是從事低賤職業的妓女或是坐霸王車的無賴和變態,他們均不區分對待,而是一視同仁地厭惡和鄙夷。每天面對著各種各樣的客人,虛偽的紳士、高傲的白領、骯臟的醉鬼,他們或毫無顧忌地在車里吸煙、扔垃圾,或充滿鄙夷地評價你的職業,甚至會一拳打在你的臉上,誰能不憎恨呢?即便是有彬彬有禮的老貴婦、出手闊綽的俱樂部小姐,也不可能挽回這毀滅性的印象。當然,這里是因為文藝作品采用了夸張的表現手法,是從已經對工作和工作對象產生厭惡心理的角度來絕對化地丑化乘客,從反面證明這樣的工作失去了最初的服務行業宗旨,工作中的人際關系極度惡化。
電影中,德子實際上對于乘客并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感情,除了他搭載過的女性,其中包括他的前妻、女友小雪、圖書管理員趙媛。然后乘客并不都是上帝:德子被迫給黑社會老大開車,辛苦一天不僅分文未得,還被其手下打得鼻青臉腫,因德子怕車被砸,只能忍氣吞聲,事后一個人在車里忍淚咒罵。偏偏這個時候還遇到了一對父子,爸爸帶著年幼的兒子打車去東郊,到了之后才說沒錢。德子便拿他們撒氣,懲罰他們脫光了所有的衣服。但是最終,德子還是把衣服扔還給了他們。這種私人承包式的工作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演變成了以金錢為紐帶的服務——被服務關系,潛伏著危機。電影同時也利用這一點制造了喜劇效果。但觀眾捧腹之余,感覺到的卻是苦楚和辛酸。
亞桑娜剛剛開始入行的時候,曾經試圖幫助一個女孩兒離開她殘暴的混蛋男友,甚至愿意出錢買火車票送她回家,但這個女孩兒最終還是沒有接受亞桑娜的幫助,而是回到了她男朋友身邊。時間久了以后,亞桑娜也變得麻木,亦或是認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使得她對于搭霸王車的醉漢沒有一絲憐憫,還趁跟他回家取錢之際偷走了他唯一值錢的象牙小雕像。
亞桑娜的最后一位客人是一只黑猩猩,也是她最喜愛的動物。然而它卻葬送了她出租車司機的職業生涯:亞桑娜想從它不仁的主人手中將它解放出來,于是趁它主人下車去后備箱拿行李的之際“綁架”了它。然而,這只黑猩猩沒有領情,而是頑固地跟她搶奪著方向盤,最終造成車禍,使得她被吊銷了執照,并且黑猩猩也并沒有回到它的主人身邊,而是就此失蹤。由此看來,亞桑娜對乘客的憎恨厭惡沒有給她帶來什么損失,而唯一實施的一次相助卻讓她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丟掉了自己的飯碗。然而,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把她從中解放了出來,單憑她自己的毅力和能力,恐怕她無法擺脫這個令她憎恨但又不得不繼續的職業。
雖然出租車司機是服務性工作,但工作的最終目的不是服務大眾,而是和其他任何薪酬職業一樣,都是以掙錢為目的的。這個目的決定了對顧客很難有一種溫情脈脈的人文關懷;而且由于個體工作者的經濟地位薄弱,導致了他們即使有心也無力,人之為人的那點情懷逐漸喪失。這是異化的典型癥候。
如同上文所述,德子努力工作,賺錢養家:德子與妻子協議離婚回到家里,老母親看到兒子很是高興,因為兒子難得回家。但又不免埋怨兒子回家太少。德子面對老母親的責備,只是回道:“我要賺錢。”為了多拉活,德子在街上吃盒飯,晚上就在洗浴中心過夜,用他自己的話說“每天早上四點起來出車,不掙滿五百塊絕不下班”。
亞桑娜開的是夜班車,起初同樣有著工作的“熱情”,所以也賺得不少,一夜少則一百馬克,多則兩三百。這使得她能夠早哥哥一步就搬出父親給他們在花園里搭的“棚居”,有了自己的家。然而除此之外,亞桑娜只是把她掙來的五十、一百的大票子扎成捆,放在床底下的鞋盒里,“以便她躺在床上伸手就能摸到它們”。
這樣看來,出租車司機不失是一份多金的職業。然而如果把妻子私奔、朋友疏離、家庭不和、脫離日常生活這些成本算進去,這份工作完全就是賠本的買賣。那么,工作內部的同事之間的關系是否也像生活中同朋友、家人的關系一樣糟糕呢?
《出租車》用了較多的筆墨來展現亞桑娜和她的同事陸迪鴿、烏多等人在候客時或者清晨咖啡廳吃早餐時的對話,特別是和陸迪鴿關于兩性關系的爭論。在亞桑娜看來,陸迪鴿是一個反女性主義者,而陸迪鴿眼中,亞桑娜則是個女權主義者。且不論當中體現出的性別問題,亞桑娜跟她的同事們除了工作時間有接觸外,業余時間毫無接觸。換句話說,從同事中沒有發展出朋友。但是亞桑娜發展出了愛情,不管是不是真愛,迪特里希成了她的男朋友,只是這愛情還要悲劇。
德子和他的同事之間也沒有私交,他們只是一起吃盒飯、泡澡的“酒肉朋友”罷了。話題無非是錢、女人還有車。當德子幫黑社會老大開車被打時,同他一起的那位同事竟然自己開車先跑了,全然不顧德子是因為幫他說話才惹怒了那幫混混。所謂同事也就只是“做同樣的事”,其他再沒有什么了。
工作中另一重要的因素是生產工具。對于出租車司機來說,就是他們的愛車。德子和亞桑娜對于車的態度有所不同:德子為了護車可以忍受被人拳打腳踢,而亞桑娜對車卻沒有絲毫的愛惜和維護,她將嚼過的口香糖全貼在大奔的儀表盤上,極少給它打掃衛生,并且最后她的車在車禍中完全報廢。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因為德子的桑塔納是自己買的,而亞桑娜開的大奔是出租公司的,所以才會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然而,亞桑娜對自己不愛護、不修飾打扮,連洗澡洗頭她都懶得去做,即便是亞桑娜自己買的車,也可想而知她也不會愛惜到哪里去。
二者對車態度迥異,追根溯源,不論是將出租車視為身家性命般重要還是如破銅爛鐵般輕視,都反映了出租車司機這份工作對于生活的異化:對于德子而言,他的桑塔納就是他的一切,取代了他的妻子、家庭、朋友、業余生活,他覺得自己在靠車掙錢生活,所以必須對其百般愛護,卻不知自己實際上已成為出租車的奴隸,活著就是為了開車;對于亞桑娜而言,因工作時間限制她已日益脫離正常的人際關系,在她眼中,出租車和其他的事物沒有區別,她對于它們一視同仁地冷漠。從整個社會來看,出租車司機的工作不過是整個現代化困境的一個縮影:人在分工細化的情況下只能是整個經濟體系里的一個螺絲釘,價值關懷讓位于工作需要和經濟追求。
2.商業化、物化導致人際關系異化
從外部社會環境來看:兩國高度的商業化和城市化都加重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日益被人與物之間的關系所浸染,另一方面趨向拘謹和排斥。在工作和生活的對立中,生活模式趨向于遭受工作模式的鉗制。
愛情,這個生活中最甜蜜的因素德子無福消受,亞桑娜則弄得一塌糊涂。德子是有婚姻的,然而沒有能維持住。妻子小芳因為德子常年累月不歸家,于是跟鄰居小五走到了一起。但德子并不認為自己有錯,他認為妻子“身上穿的、戴的、掛的,哪樣都是他買的”,辛苦賺錢養家,沒有半點對不起妻子。之后的女朋友小雪,是一名餐廳服務員,長得漂亮,但是脾氣刁鉆,愛吃醋,容不得德子一點錯誤或者怠慢。德子開車辛苦,開始還一直哄著小雪,漸漸地也失去耐性,最終導致分手。
在和小雪疏遠之后,德子在路上搭上了送修吸塵器的圖書管理員趙媛。雖然德子文化程度不高,但還是靠幽默風趣、出手闊綽博得了不甘清貧、向往富足奢華生活的趙媛的好感,兩人還在趙媛家中發生了一夜情。但趙媛最終沒有看上德子,而是介紹了學校食堂從河南來的打工妹郭順給德子認識。而郭順唯一的要求是結婚時拍一組婚紗照。德子帶著她去了長城,但并沒有打算娶她。
也許是小雪的死極大地觸動了德子的內心,也許是夜總會醉生夢死、精神空虛的無名姑娘讓德子突然厭倦了到目前為止的不羈生活,頓悟到生活的本質在于腳踏實地地過日子,亦或他就此看開了一切,不再同生活、工作進行無謂地搏斗,德子決定娶郭順,并且滿足了她的要求,帶她去拍了婚紗照。雖然德子有了新的婚姻,讓他的生活顯得不那么地異化,但我們不能說,德子得到了真正的、美好的愛情。相反地,我們從德子的愛情中明顯可以解讀出物化社會浸染的痕跡:德子認為有足夠的錢就能讓老婆生活幸福、愛情美滿;出手闊綽就能贏得姑娘的芳心。太過于復雜的心靈交流完全不在德子的能力之內,他希望將一切都簡化為物質的量化關系,從而造成了生活異化的悲劇。
相對于德子,亞桑娜本身就是個“愛無能”的人,是排斥人際交往、拘謹冷漠的典型代表。“我從來沒有過固定的男朋友,我也不想有。哪怕只是想一下,我都會覺得不舒服。”亞桑娜同迪特里希在一起完全是稀里糊涂地被動接受,在她內心里根本不想要男朋友。與迪特里希交往的同時,她還與中學同學馬克以及馬耶夫斯基同時保持關系。馬克要求她與迪特里希分手,然后嫁給他。亞桑娜盡管內心喜歡馬克,但還是堅決拒絕。因為在她看來,“結婚是愚蠢人做的事。婚姻就是男人滿足統領女人欲望的工具”。馬耶夫斯基是個花花公子,同時有很多個女朋友。亞桑娜或許是為了擺脫迪特里希,或許是根本無所謂和誰在一起,就草率地答應了他。當然,這段感情幾乎沒有真正開始就很快地破碎了。最后因車禍被吊銷執照,亞桑娜還是孑然一身,遭遇工作、愛情雙重缺失。
家庭是生活中最溫馨的因素,是給予人們歸屬感的地方。然而對于兩位主人公德子和亞桑娜來說,家是一種負擔、一種苦痛。德子為了家而努力工作,但卻因為努力工作而疏離了妻子,反而失去了家。所以,德子在同妻子離婚以后,除了惱怒,應該還有解脫的自我安慰,沒有了負擔,更加可以不分晝夜地工作、交女朋友、享受自由。然而,德子最后還是結婚了,僅僅靠工作、自由不羈填不滿他的心,家庭即便是負擔,但它是不可缺少的,跟工作一樣,有了家不能保證幸福,但沒有肯定不幸福。
亞桑娜沒有自己的家庭,她只有父母的家。當她還沒能經濟獨立之前,父親已經將她趕出家門,讓她住在花園的“棚居”里。在她當上了出租車司機、能夠付得起房租以后,便立刻搬了出來,之后由于工作繁忙,只跟母親偶爾保持接觸。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說,亞桑娜沒有家。
如果工作艱辛,愛情無果、家庭不能提供歸屬,那么剩下的唯一希望是業余生活和朋友。首先,兩位主人公沒有業余生活:德子除了開車還是開車,亞桑娜去過兩次哥哥開的派對,就因為沒有共同語言和耽誤工作時間再也沒有去過;書中唯一提及的是和馬耶夫斯基的朋友們去劃獨木舟,也是以失敗告終。如果一定要說亞桑娜有業余活動的話,那么就是讀書。她除了讀關于靈長類動物的書,還讀迪特里希推薦她的書:法國著名作家亨利·德·蒙泰朗的《憐憫女性》,以及斯特林堡、尼采、愛騰貝格的著作。然而,迪特里希和陸迪鴿都是大學生,亞桑娜卻只受過義務教育。沒有知識基礎作為支撐,這些大師們關于兩性、人生哲理的思想給亞桑娜的誤導多于幫助。亞桑娜同陸第鴿激烈地爭論兩性問題,將婚姻視為女性的地獄與這些書有相當的關系。然而,出租車司機這份職業同這些大師級思想之間的不對稱、不協調,將亞桑娜擠在中間,忍受雙方施加的痛苦。至于朋友,電影和書中均鮮有涉及,除了德子妻子小芳對德子破口大罵時提到:“你以為你交那些人有什么用?想起你的時候呼你啊,吃個飯用個車,想不起來的時候你是個什么東西啊你!”
已經遭受了愛情、家庭的不幸,朋友這一維度的缺失,讓兩部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愈加顯得異化和悲劇性。
3.城市居民主體性危機
從現代化中的主體性危機來看:工作對生活的壓制與滲透導致了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也逐漸喪失了主體應有的生活信念和生活理想。不管是德國的個體自由,還是中國的倫理社會都面臨著巨大的危機。
電影《夏日暖洋洋》是以表現德子出租車里各種各樣乘客的形態結尾的。有要求開收音機的、關音樂的、開空調的、關窗的、帶著孩子的女人們、操著蹩腳英語練習外語稿的白領、失戀的女孩等。外面的世界在飛速地發展,而這一切都好像與德子無關,他只是默默地開著車、叼著煙凝視前方。如果說之前的德子被工作異化,那么這里的德子已經在現代化中完全喪失了主體應有的生活信念和理想。
相對于德子,亞桑娜是個徹頭徹尾的沒有主體性的個體。小說的點睛之句“我總是期待事物自動產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亞桑娜在德國提供自由發展空間的前提下,仍放棄自主性、喪失生活理想的異化狀態。由此可見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工作生活雙重異化的危害力之大。
四、結語
兩部作品都反映出租車司機這份職業,其所選取的表現視角也驚人地一致:工作上與乘客“斗爭”、與同事“競爭”;生活上愛情不幸、家庭不和、朋友不仁。出租車司機仿佛是一份極盡悲慘的職業。根據韓恩的模型,這兩部作品中反映出的出租車司機這份職業屬于第一種類型:工作內、外均異化。然后造成異化的原因并不在于物質上的匱乏,他們經濟上并不極端貧窮,被異化的是他們的精神。
這其中反映的實際上是現代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都市異化,就個體而言即為工作、生活雙重異化以及主體性的喪失。工作是為了活著,它提供了生活所必須的物質基礎,由此它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工作僅僅養活了生活,它不保證生活的美好。在很多的時候,它甚至在破壞人們的生活,例如德子的婚姻、亞桑娜的青春和愛情。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工作之于生活取得了絕對的優勢和統治地位,沒有工作的生活是困頓的、不安的;有工作的生活是勞累的、異化的。生活被工作置于了一種尷尬的兩難境地,生活成了工作的奴隸,任其宰割,仿佛不是工作為了活著,而是活著是為了迎接工作的垂青。
不同文化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面臨的困境是類似的,文藝作品是一種最為敏銳的社會危機傳感器。兩部作品塑造的非常類似的出租車司機形象證明了:工作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而工業化、城市化又是全球化的左膀右臂。如果生活是文化的真實載體,那么全球化對于文化的影響力是操控性的,也是損傷性的。唯有加強人文精神建設、重塑人類主體性尊嚴,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才能阻止都市異化的進一步加劇。
[1]胡偉.探尋現代化的中國模式[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1).
[2]胡懷亮、杜凌霞.馬克思異化勞動思想研究——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解讀[J].大連干部學刊,2008(3).
[3]格奧格爾·齊美爾.大城市和精神生活[C]//橋與門:齊美爾隨筆集.上海:三聯出版社,1991.
[4]Hann,Christopher:Echte Bauern,Stachanowiten und die Lilien auf dem Felde.Arbeit und Zeit aus sozialanthropologischer Perspektive[C]//Kocka,Jürgen & Offe,Claus(Hg.).Geschichte und Zukunft der Arbeit.2000,Campus Ver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