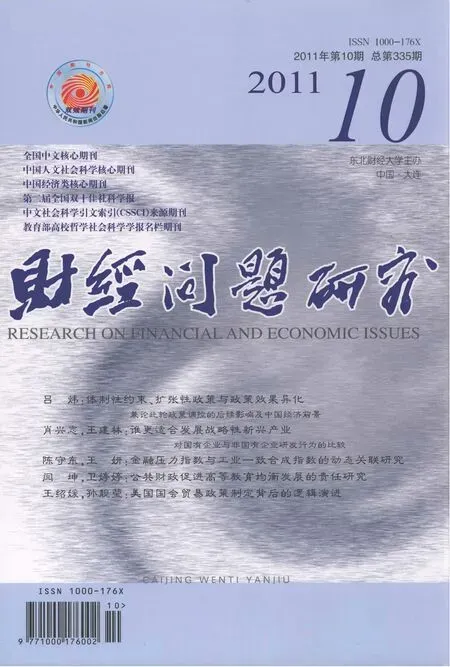跨國技術聯盟中文化差異與知識轉移績效研究
葉 嬌,原毅軍
(大連理工大學 經濟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一、引 言
目前,跨國技術聯盟成為企業吸收知識的重要形式。跨國公司由于掌握著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其國際化經營對東道國的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經濟國際化產生深遠影響。許多中國企業希望通過與跨國公司組建技術聯盟達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知識的目的。但是以“市場換技術”的聯盟策略并沒有達到目的[1],跨國公司并沒有把先進技術轉移給中方合作者。
跨國技術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過程可類比為信息溝通的過程,是知識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下從來源方向接收方的知識傳輸過程。知識轉移的基本要素包括:發送者、轉移渠道、知識、接收者和情境[2]。跨國技術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影響知識轉移效果的因素很多。Liu綜述了1980—2004年有關知識轉移的135篇文章后,總結出阻礙知識轉移的因素有:國家特征 (文化差異、文化距離)、環境特征 (環境距離、環境不確定性)、技術特征 (技術積累程度、技術復雜化程度、技術年齡)、知識特征(隱性化、因果模糊性)、組織特征 (知識保護程度、經驗)、知識轉移方 (缺少動力、知識源的不信賴感)、知識接收方 (缺少動力、吸收能力差)、其他權變變量 (單調的組織背景、缺少信任)等[3]。陳菲瓊在討論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知識聯盟的知識轉移層次時提出,對于大多數在國際間的合資項目上遇到的問題都可追溯到民族間的或組織間的文化因素上,合作者之間的距離和文化差異是學識交流的主要障礙[4]。
在前面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有必要研究跨國技術聯盟內知識轉移績效與文化差異的關系。多數有關民族文化差異影響跨國公司知識轉移的研究,都提出了概念模型和假設的研究,但缺乏實證研究[5-6-7]。在文化差異實證研究方面,李自杰和張雪峰在中外合資企業調研數據的基礎上進行了實證,研究表明國家文化差異對企業績效有正相關關系,組織文化差異與企業績效負相關[8]。徐笑君對德資跨國公司和美資跨國公司進行調研,獲得微觀數據;然后利用Hofstede國家文化模型進行分析,實證研究文化差異對德資或美資跨國公司總部知識轉移的影響[9-10]。徐笑君研究表明,知識轉移能力 (發送方的轉移能力和接收方的轉移能力)、轉移意愿和轉移渠道是影響轉移效果的主要因素[11]。
本文將從知識接收方的角度,分析跨國技術聯盟中知識接收方的學習動力、吸收能力,以及跨國技術聯盟中的知識轉移渠道豐富性對聯盟內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根據理論分析提出假設,并用數學方法進行推理證明。
二、跨國技術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分析
1.知識接收方的學習動力
接收者的學習動機決定著其搜尋和獲取外部知識的努力程度。Minbaeva等認為,學習意圖與參與知識轉移的動機聯系在一起。在知識轉移過程中,那些具有較強學習意圖的組織或個體,知識轉移的效果會更好[12]。Simonin認為,戰略聯盟合作伙伴之間若沒有知識轉移的動機,它們就會把自己的知識保護起來,這種防御行為會阻礙知識轉移[13]。Liu也提到,知識轉移方缺少轉移意愿阻礙了知識轉移[3]。
在跨國技術聯盟中,雙方的知識轉移動機一般不對稱,知識高勢企業會設法保留或隱藏關鍵技術,知識低勢企業會通過多種途徑來獲取或學習聯盟知識。此時,由于跨文化因素,技術知識低勢企業在接觸、獲取、領悟新知識方面會面臨更多困難,因此也會產生更大的學習動力以得到聯盟知識。
根據已有研究,于是我們得出命題1:跨國聯盟中企業文化差異越大,聯盟企業學習動力就越強。
2.技術接收方的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是指知識接收者用已有的知識發現新知識的價值,消化它,并利用它來創造新知識的能力。Liu的研究表明,知識接收方吸收能力不足和缺乏吸收意愿是阻礙知識轉移的主要因素之一[3]。Minbaeva等學者經過研究,得出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越強,跨國公司知識內部轉移水平越高。知識的吸收能力與接收者原有的知識儲備、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知識距離有關[12]。
Lane在對跨國公司母子公司之間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后指出,子公司的知識吸收能力受到以下四項因素的制約:母子公司間的信任程度;母子公司間的文化相似程度;子公司先期積累的從母公司學習的經驗;母公司所轉移的技術與子公司產業的相關性。同時還指出,母子公司間良好的相互信任和文化適應性是知識順利轉移的必要條件;滿足相互信任和文化適應必要條件,知識提供者才會主動積極地幫助知識接收者克服學習障礙,幫助其學習到其所要傳授的知識。子公司若已具備先前來自母公司的知識轉移經驗,則有助于提高子公司的學習意愿與學習信心[14]。相關研究表明,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的吸收能力都受到知識轉移雙方關系的影響。根據Lane的觀點,跨國聯盟中如果雙方文化差異越大,知識的吸收能力是越弱的,對知識轉移績效有消極影響。
于是我們得出命題2:跨國技術聯盟企業文化差異越大,聯盟企業知識吸收能力就越弱,聯盟知識轉移績效越差。
3.知識轉移雙方文化差距
聯盟組織知識轉移績效受限于知識接收者對被轉移知識缺乏相關的知識與技能經驗。Grant的研究展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知識整合的目的在于將不同個體所具有的獨特知識緊密結合,以創造新的知識或是獲得利潤。擁有完全不相關知識經驗的兩個個體,知識整合無法達到最佳的狀態;但是如果是兩個完全相同個體進行知識整合,那將得不到任何好處[15]。因此在進行知識轉移時,雙方的知識基礎不宜差距過大,否則將會影響學習的成效。合作伙伴間的知識缺口差距懸殊,學習幾乎不可能發生。
當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收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知識落差時,知識提供者將無法在知識轉移過程中了解知識接收者的需求與學習障礙,更無法了解其學習的心路歷程,造成知識提供者雖然有很豐富的知識內容和強烈的知識分享意愿,卻仍然導致知識轉移績效不佳得結局[16]。Hansen的研究表明,產生組織學習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知識提供者與接收者雙方的知識距離或知識落差不能太大。這是因為雙方的知識距離過大會導致學習步驟明顯增多,以致知識轉移的難度加大。因此,知識提供者與接收者在知識背景和知識距離等方面的適度匹配對知識轉移績效的提升起著關鍵的作用[17]。
知識轉移雙方的情境差異是知識轉移過程中的最大困難。在跨國技術聯盟中,聯盟雙方的文化差異和技術認知距離有著密切的關系,文化差異越大,雙方的技術認知距離越大。存在一定文化差異的聯盟雙方,會因為雙方對技術認知的差異性而產生新穎感,促進雙方的互動交流,促進知識轉移績效;但是當文化差異過大,雙方對技術的認知達不到交叉的可能,這將會對聯盟知識轉移效果產生不利的影響。根據已有研究,本文提出假設1:文化差異與跨國聯盟知識轉移績效之間關系呈倒U字型的函數。
4.知識轉移機制
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已有一些相關研究。不同的知識特性和知識構成,決定了知識轉移需要采用不同的轉移機制。日本學者Nonaka和Takeuchi在比較日本與西方公司的研究中發現:西方公司與日本公司在跨國交流中,西方公司強調顯性知識,強調諸如手冊與數據庫等顯性化的知識;而日本公司則強調隱性知識,認為知識是不可言喻的,需要親身體驗,需要在實際操作與觀察中學習[18]。也就是說,當知識具有較高的內隱性時,無法以文件資料、數據圖表等形式轉移所有內容,比較有效的轉移方式可能是人際交流、會議研討、雙方面對面交談、在職培訓和師徒制等。即轉移不同特性的知識,需要采取不同的轉移方式。
Gupta和Govindarajan等在對跨國公司知識流動進行研究之后得出結論,子公司的知識流入與其知識傳輸渠道的數量呈正相關關系[19]。對于知識傳輸渠道,日本學者Szulanski指出,知識傳輸渠道是指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進行知識轉移的媒介與途徑,是構成知識轉移的基本要素[2]。關濤在其博士論文中對知識傳輸渠道進行了分類。根據被傳播知識的特征,知識的傳輸渠道可劃分為正式整合機制和社會化機制兩類。其中正式整合機制是指在正規的體系、政策和標準之上建立的協調模式,這種機制通常有利于顯性知識的共享和轉移,而對隱性知識的轉移顯得作用不大。另外一種是社會化機制,這種機制所進行的聯系是一種個人之間的、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許多研究表明,企業內部絕大多數的信息交換和決策制定,是通過非正式渠道或非正式關系進行的;也有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將個人間的非正式聯系作為信息溝通的首選方式[20]。
從前述相關研究來看,團隊內部知識轉移機制的選擇,需要考慮到被轉移知識特性、知識轉移雙方以及一些情境變量。同時許多學者的研究特別強調,知識特性與轉移機制的配合對于知識轉移績效的提升具有積極意義。因此,在雙方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景下,知識 (尤其是隱性知識)轉移更需要知識轉移機制的靈活多樣,如增加轉移媒介、豐富轉移渠道和改善轉移方式等。于是我們提出了假設2:文化差異越大,知識轉移機制越需要改進、豐富和完善,給知識轉移績效的提高帶來更大的挑戰。
三、文化差異影響知識轉移的數學證明
1.基本模型
根據命題1和命題2,我們利用數學公式來描述上述分析。用P表示聯盟企業的學習動力,即用向上的斜線表示:

用C表示跨國聯盟中知識獲取企業的吸收能力,即用向下的斜線表示:

其中,CD是跨國技術聯盟伙伴之間的文化距離 (文化差異)。
借鑒吳先華等[21]的研究,本文將式 (1)和式 (2)相乘,所得結果即為聯盟的知識轉移績效的簡化模型。

式 (3)用來作為分析的基本模型。
2.驗證假設1
從式 (3)可以分析得,在納入“學習動力”和“吸收能力”的基本模型中,知識轉移績效達到最大時的文化差異距離 (CD*):

最優的知識轉移績效 (TP*):

從式 (4)可以看出,若要使最優文化差異距離為正值,必須有 b1>a1b2/a2或a2>a1b2/b1;從式 (5)得TP*始終大于0。因此,假設1中認為文化差異距離與聯盟知識轉移績效之間關系可以看作一個倒U型函數,已經得到驗證。
考慮到b1(對a2的分析同理,但不在文中體現)對最優文化差異距離 (CD*)和最優知識轉移績效 (TP*)的影響,即

這說明隨著b1的增加,即企業吸收知識的初始能力增強,最優文化差異距離也隨之增強,符合現實推導。
且當 CD為正值 (即 b1>a1b2/a2)時,式(7)成立。

可見隨著b1的增加,最優知識轉移績效也隨之增加。
綜上,在跨國組建的技術聯盟企業中,國家文化或組織文化的差異在一定范圍內 (0<CD<CD*,a2b1>a1b2)是促進知識轉移的;或者說正是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聯盟才會組建起來。
許多研究跨國組織間知識轉移的文獻都認為,文化差異是影響知識轉移的障礙因素。本文從新的視角探索文化差異對于知識轉移的影響,發現文化差異是可以作為資源或動力來推進聯盟組建和聯盟組織內知識轉移的。
3.驗證假設2
我們就跨國技術聯盟中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轉移的作用來討論。知識轉移機制功能越強大,如轉移渠道豐富、轉移媒介眾多、轉移方式完善和轉移形式多樣等,聯盟組織的學習動力和吸收能力就會因為外在環境的優化而增強。基本的模型式 (3)中沒有轉移機制的變量,這里我們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情形1:聯盟內知識轉移機制 (M)的完善,增加了聯盟企業學習動力變量的斜率a2,設有如下表達式:

將該公式帶入式 (3)得到:

將式 (9)對M求導,得到下式:

說明知識轉移機制對聯盟知識轉移績效的邊際影響與文化差異距離有關。
制對知識轉移邊際的正向影響逐步減弱。
情形2:聯盟內知識轉移機制 (M)的完善,增加了聯盟企業學習動力變量的截距a1,設有如下表達式:


將該公式帶入式 (3),并對M求導,得到下式:(1)當CD>,聯盟的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轉移績效有負向的影響;
同樣,我們可以分析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接收方接受能力的影響。隨著文化差距的擴大,轉移機制 (M)趨于完善,可以提高知識吸收能力,其對吸收能力函數斜率b2或者截距b1的影響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通過兩種情形的分析,驗證了假設2,證明在適當范圍內跨國技術聯盟企業的文化距離越大,聯盟組織的知識轉移機制發揮的作用越大;也還可以說,文化差異在一定情況下推進了知識轉移機制功能的高效發揮。從這一角度看,也說明文化差異可以促進技術聯盟知識轉移。
四、結論和研究展望
有別于大多關于文化差異的研究,把文化差異看作是跨國聯盟組織知識轉移的障礙因素,本文考慮到動態中由于跨文化的背景長期存在,聯盟組織會經過調整知識轉移機制來促進知識轉移。因此,本文認為文化差異在跨國技術聯盟知識轉移可以當作是一種資源或動力,刺激知識轉移機制的完善,增加知識接收方的學習動力,以及提高知識接收方的吸收能力,最終達到聯盟知識有效轉移的結果。
對于文化差異的研究,多數學者采用企業調研數據來進行實證研究,工作量相對較大。本文把文化差異抽象、提煉,把文化差異對跨國技術聯盟的知識轉移績效的復雜影響用簡明數學公式來表達,是一種新的思路。
當然,本文不可避免存在不足,局限在于研究的實證性。如文化差異和知識轉移績效,難以找到可對應的衡量指標,或者是適合的量表,類似的實證研究較難進行。如何在缺乏數據的條件下建立文化差異對跨國組織知識轉移績效影響的模型,并進行仿真模擬,是筆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1]彭紀生,孫文祥.跨國公司對華技術轉移的理論思考——基于本土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分析框架[J].中國軟科學,2005,(4):112-119.
[2]Szulanski,G.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s):27-43.
[3]Liu,T.L.Knowledge Transfer:Past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J].The Business Review,2007,7(2):204-221.
[4]陳菲瓊.我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知識聯盟的知識轉移層次研究[J]. 科研管理,2001,(2):66-73.
[5]Bhagat,R., Kedia,B., Hareston,P. Cultural Variations in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204-221.
[6]Holden, N.Knowledge Management:Raising the Spectre ofthe Cross - Culture Dimension [J].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2001,8(3):155-163.
[7]Kedia,B.,Bhagat,R.Cultural Constraints on Transfer ofTechnology Across Nation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Manage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3(4):559-571.
[8]李自杰,張雪峰.國家文化差異、組織文化差異與企業績效——基于中外合資企業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0,(9):93-98.
[9]徐笑君.文化差異對總部指示轉移的調節效應研究:基于德資跨國公司的調查[J].研究與發展管理,2009,(12):1-8.
[10]徐笑君.文化差異對美資跨國公司總部知識轉移影響研究[J]. 科研管理,2010,(7):49-58.
[11]徐笑君.跨國公司總部向在華子公司轉移知識的影響因素模型構建[J].管理學報,2010,(6):896-902.
[12]Minbaeva,D, Pedersen,T.,Bjǒrkman,I.MNC Knowledge Transfer,Subsidiary Absorptive Capacity,and HR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3,34(6):586-600.
[13]Simonin,B.L.Ambigui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trategic Alliance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7):595-623.
[14]Lane,P.J.,Salk,J.E.,Lyles,M.A.Absorptive Capacity,Learning,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12):1139-1161.
[15]Grant,R.M.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4):109-122.
[16]Swap,W.,Leonard,D.,Shield,M.,Abrams,L.Using Mentoring and Storytelling to Transfer Knowledge in the Workpla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2001,18(1):95-114.
[17]Hansen,M.T.Knowledge Networks:Explaining Effective Knowledge Sharing in Multiunit Compani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3):232-248.
[18]Nonaka,I.,Takeuchi,H.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9]Gupta,A.K.,Govindarajan,V.Knowledge Flow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4):473-496.
[20]關濤.跨國公司內部知識轉移過程與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21]吳先華,郭際,胡漢輝.技術聯盟企業的認知距離、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8,(3):53-58.